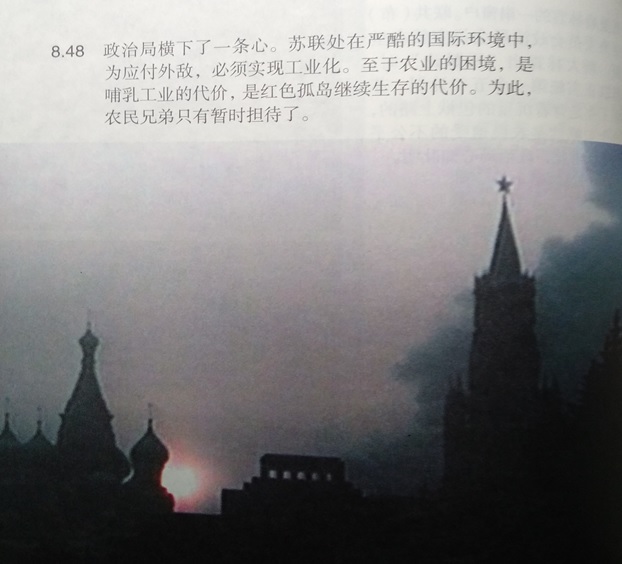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55)
红色帝国覆亡之谜(7)
对于阿.雷巴科夫在《从阿尔巴特街到西伯利亚》一书有关苏联1932一1933年大饥荒的数字以及肖洛霍夫向斯大林反映的情况,斯大林要么无动于衷要么竭力掩盖。1933年,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一次会议上,乌克兰CP中央书记帖列霍夫汇报哈尔科夫州农村闹饥荒,并请求拨给一些粮食。斯大林打断他的话,说: “我们听说,您,帖列霍夫同志是一位很好的演讲者,原来您还是很好的故事员——您编造了关于饥荒的故事,以为可以吓唬住我们,但这是行不通的!您最好放弃州委书记和乌克兰CP中央委员会书记的职务,参加作家协会去,到那里编故事,供傻子们阅读吧……”
布尔什维克不是口口声声说“要密切联系群众”吗,苏联当时闹没闹饥荒,斯大林同志只要下去“密切联系群众”,掌握真实情况并不难,怎么能武断地说汇报情况者是“编故事”呢。
有关这次大饥荒的记载当时无论是在苏共党史还是在苏联历史中均无片言只语,看来布尔什维克在遮盖负面信息方面可谓得心应手,无人能及。而且还会运用生花妙笔把疮疤写成鲜花。斯大林时代这段历史不用说了,即使在斯大林去世20年后,《苏联CP历史》(下)还在竭力美化这段不堪回首的历程。请看下面文字是这样粉饰当时的现实的:
党有计划地领导了农村的社会主义发展。……
党组织在个体农民中间展开了解释工作,同时还吸收集体农庄的积极分子参加这项工作。集体农庄运动又开始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在党的十六次代表大会(1930年)以后的一年中,有七百多万农户加入了集体农庄。……
富农在全盘集体化的地区被消灭了。反抗集体化的富农被迁出原来定居的地方。从1930年初到1932年秋天,迁出的富农达240757户,约占农户总数的1%。苏维埃政府为过去的富农在新居住地的劳动就业做了一切必要的安排,为他们创造了正常的生活条件。绝大部分富农移民都在森林工业、建筑工业和采矿工业,以及在西伯利亚西部和哈萨克斯坦的国营农场里工作。党和苏维埃政权对这些人进行了改造,帮助他们成为有充分权利的公民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积极劳动者。
所谓“为他们创造了正常的生活条件”,就是把人赶到冰天雪地中去做苦工,美其名曰“帮助他们成为有充分权利的公民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积极劳动者”。罗伊.麦德维杰夫在《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一书披露了一些细节,对照上述文字,人们就会知道富农是怎样“被消灭了”的。
有些地区在消灭富农时期宣布处于特别戒严状态。被迁出的富农连规定的最低的工具和资金数量都不留。连家里有人参加红军的富农户也被迁出,这和指示精神是相违背的。这种过火行为不是个别的,是普遍的。
难道还能够解释说那些(符合指示精神的)把富农或其帮手一起全家逮捕,甚至其幼小子女的行为是正确的吗?(注:关于被剥夺富农的全家迁出的严酷指示显然首先和这样的事实有关: 即1930年苏维埃政权没有掌握为支援迅速产生的成千上万集体农庄所需要的物质资源,所以才决定把富农的所有财产移交给新成立的集体农庄。至1930年5月,半数集体农庄的公共基金中有34%来自富农财产。这样,急促的加速集体农庄运动的结果必然导致对待富农的极端残酷性。)在那些寒冷没有任何取暖设备的车厢中,成千上万的老人、妇女和儿童被运往东方——乌拉尔、哈萨克和西伯利亚的边缘地区。老党员M.兰道1930年在西伯利亚看到这种情况: 严寒的冬天,有大批富农同他们的家人一起用马车运到离本州三百公里的外地。孩子们因饥饿和寒冷而喊叫。一个农民实在忍受不了空吮母亲奶子的婴儿的哭叫,从妻子手里夺过小孩,把他的头往树上乱撞。
在许多情况下首先逮捕和关押在集中营或监狱,甚至枪决的是富农本人。富农的家庭成员没有被触动,只是把财产登记一下,这时家庭成员好像作为看守已没收的财产的人。几个月后才迁出全家。
许多原富农和他们的家人在那些人烟稀少的乌拉尔、西伯利亚、哈萨克和苏联东北部地区没有几年就死去了。这些地区那时建立了成百上千的“富农专门居住区”。这些居住区的所有居民都是流放者,所以没有迁移自由。
富农是农村中的生产能手,消灭富农意味着农村中劳动效率最高的那部分人被排除在生产集体之外,这就是苏联农村生产力长期低下的重要原因,概莫能外。而《苏共党史》却另有说法:
集体农庄的活动中出现了许多缺点,使它的优越性不能很好地发挥。集体农庄的群众和领导干部还没有管理大生产的经验。许多集体农庄的劳动组织得很不好。计算工作做得也不好。广泛实行着按人口分配收入的办法。这就降低了对工作的兴趣,削弱了劳动纪律,许多集体农庄庄员常常不出勤。收割期往往拖得很长,损耗很大。牲畜、机器和其它财产没有专人负责照管。无人负责的现象使集体农庄的财产遭到很大的损失。钻进集体农庄的过去的富农和其他敌对分子不断地盗窃财产,破坏机器,弄死马匹和其他牲畜,劳动时故意不注意质量,千方百计地阻挠忠诚的集体农庄庄员妥善安排集体农庄的生活。
这里首先要澄清的一个问题是: 集体农庄有没有优越性?还是引用罗伊.麦德维杰夫著作中的数据来说明吧:
农业的集体化本应该导致农业、畜牧业总产量迅速提高,同时产品的商品率也应有所提高。例如,在制订第一个五年计划时规定农业总产值从1927一1928年的166亿卢布提高到1932一1933年的258亿卢布,即增加50%以上。但是在集体化过程中所发生的错误很快使这些打算被打乱了。原来估计农业总产值的提高被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不断下降所代替。如果把1928年各类成分的农业总产值作为100,那么1929年为98,1930年为94,1931年为92,1932年为86,而1933年下降到81.5。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下降最多的是畜产品生产,1933年只有1913年水平的65%。五年中牛的数量从6010万头下降到3350万头。马、羊、猪的数量下降三分之二以上。……总而言之,1933年农业总产值不仅没有增加到258亿卢布,反而下降到131亿卢布。而二战前年代农业总产值只有两次稍为超过了1928一1929年水平,这就是1937年和1940年。
其实,如果我们把三十年代后半期不同二十年代后半期比较,而同1913年比较的话,基本农产品并没有任何增加。例如,1933一1940年粮食平均年产量为45.63亿普特,而1913年为47.7亿普特。肉的产量下降更严重,特别是如果我们不把小城镇和城市郊区职工所生产的肉食品计算在内的话。
据苏联官方披露,苏联的粮食总产量直到斯大林去世时的1953年都没有超过1913年的产量。
第二个需要澄清的问题是: 是谁“千方百计地阻挠忠诚的集体农庄庄员妥善安排集体农庄的生活”?集体农庄庄员为什么对工作没兴趣?为什么常常不出勤?这里还是用罗伊.麦德维杰夫著作中的数据文字来说明: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农业生产的下降当然会影响不断增长的农产品收购计划的完成。
与此同时国内的工业继续发展,城市人口每年增加二百多万人。结果,虽然建立和发展了集体农庄,但是迅速发展的工业的需要和农业总产量之间的比例失调仍然很严重而且大大增加了。
毫不奇怪,热衷于搞命令主义和滥用权力的斯大林在当时的形势下只找到了这样的出路: 重新走上用暴力剥夺农村剩余的(甚至不仅是剩余的)农产品。如下数字很说明问题: 如果把1926一1929年平均农产品产量当作100,那么以后十年(1930一1939年)平均指数为95。可是三十年代国家征收的农产品比二十年代后半期增加了许多。例如,粮食就增加了一倍。如果说,1932年集体农庄交售给国家的粮食是四分之一多,那么1933一1934年是三分之一强,1935年几乎达到40%。这还是1928一1930年间为义务交售制而定的、直到1935年没有变的指示价格,这种价格比粮食和其他一些农作物的成本低好几倍。这种收购和零售价格之间的差额实在太大。1933一1934年粮食区的小麦收购价格是一公斤3.2至9.4戈比(按当时价格情况);同时一公斤面粉的零售价格,按购粮卡是35至60戈比;商业价格(即不用购粮卡的高价)是4至5卢布;国家统一的零售价是3.4卢布,比收购价多39倍。一公斤土豆的收购价是3至4戈比;零售价格按购货卡是20至30戈比;商业价格是1.2至2卢布;国家统一的价格是35至52戈比。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斯大林从农业集体化最初几年起就实行了一套严重违反集体农庄庄员在发展社会生产方面的物质利益的政策,一套按随意规定的收购价格强制购买农民粮食的政策。不仅如此,还强制购买许多集体农庄所必需的饲料粮和口粮。
这种从集体农庄强行运出全部粮食和其它农产品的做法使三十年代初期许多集体农庄的劳动纪律涣散,粮食被大量偷走。我国一系列地区特别是库班、顿河、乌克兰发生了独特的“粮食怠工”,这就是不仅个体农民,就连集体农庄也把耕地面积缩小了,拒绝向国家交售粮食,把粮食埋藏起来。斯大林并没有对自己所犯的错误和过火行为加以纠正,而是首先采取强化原来的暴力措施,对盗窃集体农庄粮食的行为实行极为残暴的政策。许多农民由于盗窃了自己种植出来的农产品而被判处长期徒刑,甚至极刑。对没有完成粮食收购计划的地区停止供应商品,国家和合作商店关闭了。地方干部大批被免职,开除党籍,送交法庭审判。个别情况下甚至还用了如此残酷的办法: 把整个村庄或乡镇的全部人口迁到边缘的北方地区。……
在《苏共党史》中,强行低价收购农民粮食的政策依据只用一句话作了交代: “1933年初取消了收购粮食的合同(预购合同)制度;规定集体农庄有按固定价格向国家交售的义务。交售粮食的定额按播种计划所规定的每一公顷计算。”而对饥饿的农民盗窃农作物的严厉惩罚的法理依据则是斯大林亲自起草的《关于保护国营企业、集体农庄和合作社的财产以及巩固公有制(社会主义所有所)》的法律草案。斯大林公然指出: “公有制(国有制、集体农庄所有制和合作社所有制)是苏维埃制度的基础,神圣不可侵犯。侵犯公有制的人是人民的敌人,同他们斗争是苏维埃政权的首要职责,可以枪毙他们并没收其全部财产。” 1972年出版的《苏共党史》尽管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作出否定的立场,但仍然萧规曹随,对这一法案持肯定态度: “苏维埃政权于1932年8月7日颁布的关于保护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法律,促进了集体农庄制度的基础的巩固。根据这一法律,集体农庄的财产同国家财产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这一法律宣布,集体农庄所有制同国家所有制一样,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无论是在保卫公有制(实为官有制)方面,还是在维护社会主义制度方面,勃列日涅夫和斯大林都是一脉相承,心心相印的。当年斯大林亲自编纂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对农业集体化极尽美化之能事不足为奇,而勃列日涅夫对斯大林先抑后扬,站在布尔什维克的立场上,对集体化也是大加褒扬。《苏共党史》在评价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的成就时首先指出: “苏联由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而且进一步评功摆好写道: “农村里建立了集体农庄制度,建立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农业。苏联已经由小农的国家变成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农业的国家。在全盘集体化基础上消灭了富农阶级。” 接着居然大言不惭地宣称: “集体农庄制度消灭了富农的盘剥和劳动农民群众的贫困化。贫农和下层中层在集体农庄里成了生活有保障的人。”
布尔什维克党人骄傲地宣布: 1933年初,一个令人欢欣鼓舞的消息传遍了全国: 第一个五年计划在四年零三个月内提前完成了。苏联由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但是,几百万农民在一年多中被活活饿死,这种万年难消的耻辱布尔什维克却置若罔闻,仿佛是发生在外星球的事情。
罗伊.麦德维杰夫在《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中就苏联1932一1933年农村发生的饥荒情况仗义执言,秉笔直书,写出如下文字:
还应指出,我们三十年代的文学中并没有关于1933年饥荒的“任何故事”,有关这一时期的饥荒一直到1956年我们的报刊都禁止提到它,三十年代许多人由于提到“南方饥荒”几个字就作为“反革命宣传”被逮捕。这一禁区直到现在才有作家在作品中敢于提及。
巴.坦德利亚可夫写道: “彼得拉科夫斯卡亚村的牲口因没有饲料都死亡了,人们吃的是荨麻草和湖荻做的面包,独活草做的粥。在区中心沃霍罗弗城的临近火车站的街心小公园里,从乌克兰迁出的富农在那里死亡。在那里看见死人已成惯例,医院的马车夫阿布拉木赶车到这里来收尸体。有些人没有死,他们在小巷里拖着因水肿而变得像大象腿那么粗的没有血色的发蓝的腿,用狗一般的乞求的眼光探索过路的人。但沃霍罗弗人没有给他们什么,他们自己为了得到购物卡上的面包从晚上就开始排队。这就是1933年……”
著名作家瓦.格罗斯曼在他去世后国外出版的小说中描写了乌克兰南部饥荒的悲惨局面:
“秋天起大家开始吃土豆,没有面包,土豆很快吃完了。圣诞节前开始屠宰牲口,没有什么肉,全是骨头。当然鸡也全杀了。肉很快就吃完了,牛奶一滴也没有了,全村一个鸡蛋也见不着。没有粮食,颗粒没有剩,全拉走了。春播没有办法进行,连种子都给拉走了。……怎么办?孩子们从早就哭个不停,要吃东西。母亲给他们吃什么?雪?但是冬天真正的饥荒还没有到来。当然大家没有精神了,因为吃土豆皮肚子鼓起来了,但是还没有全身浮肿。后来从雪地底下挖出橡树籽,把它烤干,磨坊主人转动他的磨盘,把橡树籽磨成粉,做成烤饼吃。橡树林很少,两个村子的人都涌到这里来了,很快这也没有了。可是国家连一粒粮食都没有发给饥民,他们吃的可都是农民种的粮食。难道斯大林不知道这些?所有的道路都设有哨卡,不让饥民从农村出来,城市进不去,车站周围都是守卫队,连小车站周围都有警卫人员……
“雪融的时候全村真的都挨饿了。小孩不睡觉,连夜里都要吃的。人们面如土色,眼睛也昏花了,和喝醉了一样……人们已不多走路,总是躺着。他们有幻觉,好像车轮响了,斯大林从区中心送面包救孩子来了。妇女比男人更能坚持,活得更顽强。可是她们的负担更重——孩子们向母亲们要吃的。有些妇女亲吻着孩子,劝他们说: ‘呵,忍着吧,不要喊了,我从哪里弄吃的?’ 另一些妇女和疯子一样骂孩子: ‘别叫了,弄死你!’ 她们随手拿到什么就用什么打孩子,只要他们不再要吃的就行……猫、狗全没有了,全杀了吃了。雪融化了,人们饿得全身浮肿,腿和枕头一样,肚子里浮水,不断小便,都来不及到院子里去。孩子们的头和铅球似的,脖子细得如同仙鹤,能看见手和脚上的每块骨头在皮肤下面活动,整个骨架子好像被黄色纱布包起来一样。小孩的脸衰老不堪,和70岁的老头一样,不是人的脸,只有眼睛。上帝啊!斯大林同志,你见过那样的眼睛吗?……
全村人一个接一个地死亡,起初是小孩和老人,后来是中青年人。一开始还埋起来,后来也不埋了。死人就在街上,在院子里,最后的人在房子里扔着。全村安静了——全死光了。”
作家阿.科斯杰林写道: “我在去斯塔夫罗波尔的路上遇到一个背包袱的农民。我们互相打了招呼,抽起烟。我问他: 同志,你到哪里去?
“到监狱去。
“我因惊奇连话都说不出来,只是看着他。他大约40岁,十分淡漠地说: 我是个中农,由于不愿意加入集体农庄和反对上面来的全权代表,镇干部按(刑法)第58条10节(反动宣传)判了他10年监禁。镇里的民警不愿意也没有时间送他到斯塔夫罗波尔,所以让他一个人去。
从表面上看他对自己的命运是无所谓的,但实际上他有自己的聪明打算: 在监狱里他不至于饿死。那时村里人成百成百地在饿死。
当几百万人被饿死的时候,斯大林仍坚持把粮食出口到欧洲国家去。1928年出口的粮食不到10万吨,1929年为130万吨,1930年为4830万吨,1931年为5180万吨,1932年为1810万吨。甚至在饥荒最严重的1933年还出口100万吨。这时欧洲正处在经济危机,所以苏联的粮食只能廉价出售。可是1932一1933年出口粮食的一半就足以把我国南方各省从饥荒中挽救出来。
西欧各国人民在安详地吃苏联粮食,这是从我们挨饿的和饿死了的农民口中夺过去的。有关当时发生饥荒的一切消息,无论是苏联宣传机构,还是官方人士都予以辟谣。
至少五百万饿殍换来了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和国家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在这些冤魂的基础上,布尔什维克洋洋得意地宣称: “苏联的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已经证明,没有地主、资本家和富农,他们也能够成功地应付一切,能够成功地建立新的、美好的、没有经济危机和失业现象、能够保证劳动人民的福利不断增进的社会主义制度。”
那么我要问: 没有布尔什维克掌权,苏联会发生三次大饥荒并饿死上千万人吗?
(未完待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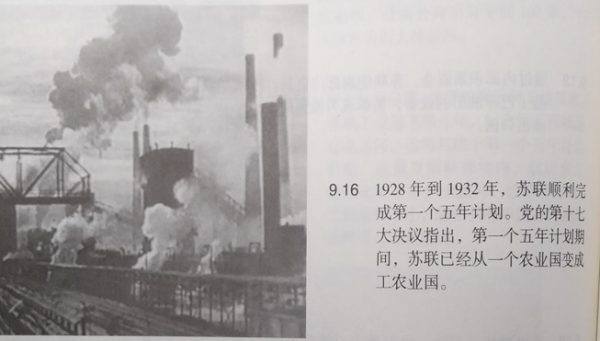
荀路 2022年3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