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沉闷的七月天,多淫雨,少和风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拉开了序幕。
这是一场整肃知识分子运动,也是一场整肃民主党派、尤其民主同盟(其中多数是知识分子)的运动。
,章伯钧(左),罗隆基(右).jpg)
图:沈钧儒(中),章伯钧(左),罗隆基(右)
这时报纸电台转了方向,每天报导反右派斗争的消息。反右派斗争轰轰烈烈,如火如荼地展开。
在大鸣大放初期,民主党派和知识界原本并没有多少人对大鸣大放感兴趣,但在诸多方面的鼓动下,就加入了大鸣大放的队伍,而且提出了不少过于尖锐激烈的意见,点名批评共产党的某些错误。
为首的是两个大右派章伯钧和罗隆基,被毛泽东称作“章罗同盟”(后称作“章罗联盟”)。对于章伯钧,批判的是他的“政治设计院”的发言。罗隆基的代表言论是“平反委员会”。两个人都被划成全国头号大右派。
那是阴沉的七月天,多淫雨,少阳光。
在北京师大,往日喧闹的校园,一下变得冷清了,人无声,鸟无语,好像绿园的小鸟,也感到大难临头,不再叽叽喳喳地叫。
一些在“鸣放”初期叽叽喳喳叫的同学,此时望着阴沉的天空,胆战心惊,如履薄冰,感到大难临头:那些被认为是“中间分子”的,也在选择何去何从的方向:而那些“左爷”们,磨刀霍霍,天天关起门来开着“临战”前的秘密会议。
我几乎每天都和洪镇涛、张俊在一起,议论这一次突如其来的反右斗争,我们十分不理解,准确地说是十分抵触。为什么相处和谐的同学和老师,一夜之间却成了阶级敌人。
同学之间互相说话少了,有些熟悉的人见面也不敢说话了。一次早饭,我在大饭厅见到即将毕业离校的四年级同学魏锡林,他眼睛一直盯着我,却不说话,只是把右臂抬起来向我晃动,看我不解,他才凑到我耳根下悄声说:“我右了!”
魏锡林也是《蓓蕾》月刊编委,我们曾经在一起策划、研究《蓓蕾》月刊的编辑、出版工作。他从读初中时开始写作,1952年他写了一个“三反”“五反”的剧本,在《天津日报》上发表。当时天津人民艺术剧院排演了他的剧本,当剧本在南市人民剧场演出时,他跑去看,因为他没钱买票,把门的人不让他进,他说他是这个剧本的作者,把门的人不相信,找来了剧务,确认后才让他进去看剧,那时他还戴着红领巾。
从初中到大学,魏锡林一直在《天津日报》的文艺副刊发表作品,到大学四年级出版了自己的小说集。
那时他临近毕业分配,因为他除了写些小说,他“右派言论”和“罪行”不多,就没有像其他右派那样送去劳改,被分配到天津市一所普通中学。
因为他和我高中同学焦琤同在天津市谦德庄中学,我才知道他在这个中学总务处工作,管卖饭票,但经常把饭票卖错,而招致领导的批评。
后来,他又曾把他落难后发表的一些作品寄给我。但是,因为我忙于杂务,竟没有给他写一封回信。听说,他早已经离开人世,应该是带着这个世界给他的不公平和遗憾离去的。
随着时间推移,反右斗争逐渐进入高潮,党员们经常在一起开会,但那开会的内容却是一点风都透不出来。原来几乎每天和我们在一起议论反右大事的一些同学,也不太跟我们讲话了,有时好像还有意无意地躲避着我们。
“擒贼先擒王”,中文系最先被划成右派的自然是率先“出洞”的穆木天,小会的批判,大会的斗争,轮番轰炸。昨天还诚恳地说“穆木天教授对我的批评是对我的爱护,欢迎继续鸣放帮助党整风”的何副校长,也一改常态,指挥着千军万马,进行这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在过去揭发何锡麟的大字报区,一夜之间贴满了声讨穆木天的大字报。什么“猫头鹰”(穆先生高度近视),什么“转向诗人”,什么“夫唱妇随”(“妇”指穆先生夫人彭慧教授)。……那些大字报充塞着谩骂与污辱。
一次最大的由党校党委组织的全校师生员工参加的斗争会,是批判中文系系主任黄药眠教授的大会。那是一个炎热的七月天,大会在大饭厅(兼礼堂)举行,中国新闻电影制片厂的探照灯火烧火燎的热光,把台上正作自我检查的黄药眠先生照得满头流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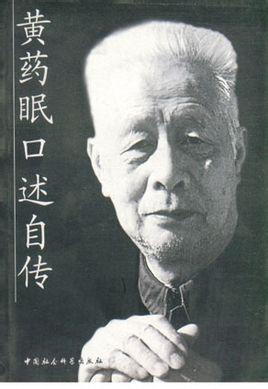
图:黄药眠先生
对黄药眠先生的批判,主要是批判由他起草的《关于高等院校领导问题的建议》。那时黄先生担任民盟中央宣传部长,这个“建议”是他为民盟中央起草的一个文件,还没来得及通过,反右斗争就开始了。因为毛主席在此前曾说过:“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是否分两个组织,一个校务委员会管行政,一个教授会议管教学。这些问题要研究。由邓小平同志负责找党外人士和民盟、九三学社等开座谈会,对有职有权和学校党委制的问题征求意见。”黄先生就是根据这样精神起草了《关于高等院校领导问题的建议》,没想到这就成了他的一大罪状,批判他的人说他的“教授治校”是要从根本上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向共产党夺权,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继续统治学校。
另外的一大罪状是黄先生在一次民主党派参加的整风座谈会上,批评某些党员“在其位不能谋其政”,某些党员提拔任用干部不是任人唯贤,而是任人唯亲。
黄先生还说过:“听说我的档案有一尺多厚,装了些什么也不让我知道,我要在人代会(黄先生那时是全国人大代表)上去控诉”。
这些话就都成了黄先生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状。批判会一直进行了两个多小时。
那是我入学后第一次看到系主任黄药眠。他头发已经全白,脸上布满皱纹。我在入师大前曾读过他写的《论约瑟夫的外套》,知道他是国内起来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第一人,并且知道他是在1926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这样一个人,怎么一夜之间就成了阶级敌人呢?
黄先生批判胡风的事,自然在会上无人再提。
于是校园里贴满批判黄药眠的大字报,有一张大字报的题目至今我还记得:“还要眠(黄先生名字的谐音)是你清醒的时候了!”这种近于人格侮辱的大字报,出自谁人之手已经不得而知。
1991年5月,作家秦牧在天津《今晚报》上发表《奸臣的“定场诗”》一文,写到:“在所谓‘反右’运动期间,康生亲自跑到北师大,要把一级教授黄药眠划为‘右派’。何以他如此赤膊上阵呢?有一次我曾问过黄药眠这是什么道理,黄的回答是:多年以前,在莫斯科的时候,他奉派当过康生的翻译,深知他的为人勾当。康生当时对王明是极尽巴结恭维之能事的。为了封住黄药眠口,免得露馅,他就亲自出马,使出浑身解数……”
原来如此,他们是借“反右”来公报私仇,诛杀异己!
中文系还有一个特殊“右派”是启功。启先生是个既未鸣、又未放,对共产党整风运动没说过一句话的“右派”。

图:启功先生
原来启功先对痴爱绘画,因为“画院”的叶公绰先生被划为“右派”牵连到他。后来启功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我属于叶先生的死党,所以要打倒叶先生必须一并打倒我,而通过打倒叶先生周围的人也才能罗织罪名最终打倒他。于是我成了必然的牺牲品……”《启功自述--我是怎样成为“右派”的?》
此后,我们在大跃进中深翻土地、大炼钢铁时,启先生的工作是管理劳动工具。那时劳动工具有锹、镐、筐等,都放在文史楼地下室里,他负责这些劳动工具的出借、收回。我们借这些工具时要写借条,还回时再把借条收回。
我们班有位L同学,过去他很崇拜像启功先生这样的学术权威,也曾找些借口和理由去向这些学术权威请教,真有点程门立雪的劲头。但现在却不同了,他常瞪着牛眼喊:“启功,去拿工具,快点。”
启先生是系里唯一的没摘掉“右派帽子”就给我们上课的一位副教授(他本来已经被评为教授,成“右派”后降级使用,仍为副教授)。
本来幽默风趣横生的他,却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上课时低着头,不看同学,也不板书,只拿着讲稿,一字一句地念着讲稿上的话,唯恐念错一个字!
启功先生被划作右派是在“反右”后期,在反右之初,他还上台发言批判“苦药社”,批判稿登载在《师大教学》上(见附录2)。
反右派斗争,采取的是群众斗群众的办法。群众斗群众是历史的悲哀,但同时也是历史的常态。所谓的反右派斗争就是群众斗群众最突出、最典型的表现。,这不能不说明很多群众其实都被某些错误思潮给欺骗、利用了。历史的悲哀在于总是有一些群众要被欺骗、利用。
就说此后被称作国学大师的、当初的副教授启功先生吧,他不也是被欺骗被利用的吗?当他上台振振有词地批判《苦药特辑》、装出一副“革命相”不久,他在劫难逃,也被划成右派!这不能不说是一幕滑稽剧。
八十年代,我热衷中国古代女性诗词,完成了《古代闺媛诗词选》一稿,夏承焘先生为书写了序言,启功先生为我题写了书名,成都出版社对书稿完成终审终校之后,正在付梓之际,成都出版社因为涉嫌卖书号被出版署判了死刑砍杀了。书稿和启先生题写的书名一直存放在我的书箧中。
中文系是这次“反右”运动中的重灾区。
全系18名教授,其中8人被划成右派,占近二分之一。除以上说的3位之外,还有钟敬文。彭慧、李长之、陈秋帆、俞敏5人。
据说俞敏被划成右派,是因为他好开玩笑,讲话随便,有时还讽刺挖苦领导。在那个多言多失的年代,乖巧的人的信条是“逢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
中文系共有学生250人,有近50人被划成“右派”,占五分之一。
学生中的小右派一般放在班级进行揭发、批判、斗争。在全校进行批判的都是大右派。
俄语系的谢昕是唯一的一个在全校进行批判的学生右派。她的前夫据说是国民党特务,谢昕与前夫离婚后考入师大俄语系,肃反中受前夫牵连,被逼供审问批斗,平反后恢复名誉。这次整风开始,她找到全国人大代表黄绍竑(也被划作右派,后自杀)申诉委屈,黄绍竑表示要过问此事。反右开始,学校就把她作为学生中攻击肃反运动的典型,划为极右分子。
批判大会在大饭厅举行,会场气氛极为严肃,有人带头呼口号:“打倒反革命右派分子谢昕!”谢昕被揪上台后,她扬着头,直直地站着,不亢不卑。主持会的人高喊:“右派分子谢昕低头!”谢昕仍原地直立,这时过去两个人,拧住她的胳膊,把她头硬摁下去,但一松手,她的头又抬起来了。
批判会结束的当晚,她就被公安部门逮捕了。此后,她在监狱中关押多久,什么时候出狱,出狱后去了哪里,至今是死是活,不为人所知。
另一次是批判生物系武兆发教授的大会。
武兆发是生物系主任,一级教授,曾留学美国,是国内外著名的生物学切片专家。他的切片远销欧美各国。解放初期,他回国被聘为师大生物系教授,因有海外关系,肃反中被批被斗。在整风运动初期,他就肃反运动中自己的遭遇提出意见和看法。
于是武兆发就以攻击肃反运动的典型代表人物被划为右派。
批判武兆发的大会是在定阜大街的师大北校进行的,我们中文系同学没去参加。据后来说,在会上一些人大揭武兆发私生活的一些问题,还找了一个村妇模样的所谓助教,上台揭发武兆发怎么强奸了她,于是会上有人喊出“打倒大流氓、大坏蛋、大特务武兆发”的口号。士可杀不可辱,会后武兆发用他的生物解剖刀割腕自杀了。
这样一位声望极高、威信极大、在国内外有显著影响的生物界名流就这样死于非命。
武兆发是北师大“反右”中第一个被迫害致死的教授,他死后还继续被批判,说他是没有任何学问的大流氓、大坏蛋、大特务,抗拒改造,顽抗到底,自绝人民,死有余辜……这与封建时代的“鞭尸”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全校范围受到批判的还有俄语系主任胡明、政治系教授何廷杰、教育系教授朱启贤等。
那天,我参加了在合班教室举行的批判朱启贤的大会,会上抓住朱启贤的一句话,批来批去。朱启贤说过的一句话是“马、恩、列、斯、毛,老子天下第六”。这句话可能是出自朱启贤之口,如果这句话是朱启贤的真意表述,只能说他狂妄,怎么能与右派连在一起呢?如果是一句吹牛皮的玩笑话,那开玩笑也是罪吗?
在师大,我们度过那阴沉多雨的七月天!
以上所写,只是师大反右运动的一个侧面,而且是仅仅就我所知的一个侧面。据有关专家考证:在毛泽东“引蛇出洞”的“阳谋”之下,全国县级以上城市,被打成的右派的是55万,加上县以下的农村右派及内控右派,不戴帽右派,总数有300多万人,另有100多万中右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也在反右运动中制造出来,总共不少于500万人,这是一个多么宠大的数字啊!
这里我要说明的是:1957年的反右运动的教训是沉痛的,它对中国当代的历史影响是巨大的,尤其这次运动发生在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地方,它给中国知识分子心灵上造成的的创伤是难于平复的,这次运动的打击面之广、涉及人数之多是建国以来历次运动之最。目前对于1957年的反右运动的原始档案还没有解密,对于反右运动的研究犹多阙如。究竟这次运动有多少人受到伤害,多少人死于非命,多少人被关入大牢,多少人受到株连……这些还有待于1957年反右运动的原始档案解密之后,才能让人有一个清楚了解。
近闻, 1957年反右派运动档案已经解密。
1957年反右运动划的右派分子,不是50万,而是317万人,还有143万被划为“中右”……
反右运动档案近期解密,暴露了毛泽东1957年疯狂迫害知识分子的滔天罪行。原来当年划的“右派分子”不是50万,而是3178,470人,是50的6倍以上。另外还有1437,562被划为“中右”……
全国共划右派317万多人,有500多万人受迫害。实际上是制造了400多万人的冤假错案。
列宁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板!”一个失去记忆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民族。让我们千秋万代永远记住在人类历史上这不光彩的一页吧!
【附录】(一)1957年反右派运动档案解密,解密内容如下:
毛泽东:阶级斗争要持续一百年 :
1956年11月10日至15日,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14日晚,毛泽东提出临时发言,他在会上说:“东欧一些国家不断在政治上混乱,基本问题是领导层没有阶级斗争观念,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新老反革命没有搞掉,这方面我们要引以为戒。……我敢说,我们党内也有阶级斗争。”刘少奇在会上补充发言,说:“毛泽东同志的讲话是他个人的意见,中央政治局没讨论过,会议要备案。”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会议进行了三天。毛泽东提出:“革命时期大规模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斗争要几经反复,还要持续五十年、一百年。你们信不信?我看,坐在主席团上,也有不信的。”
毛泽东藉“鸣放”引蛇出洞 :
1957年4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1957年4月11日晚,毛泽东和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谈话。毛泽东说:“我赞成放,放得尽些,才能让各阶级都出来表现。不放,怎样来辩论?放半年,不够,放一年。左派要有准备。”
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
5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什么要整风?》的社论。毛泽东作了指示:“不要搞那么多条条框框来束缚,要改。怕放,无非怕引火烧身。”
5月2日至5月12日,全国各地召开28,250多次各类会议,向党中央、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提出了372,345条意见、建议。
“一放,各阶级就原形毕露” :
毛泽东在《情况汇总》上作了批示:“一放,各阶级就会表现出来,原形也毕露。共产党执政还不到八年,就有30多万条意见、错误、罪状,那共产党是不是该下台?那我姓毛的不是要重返井冈山!”
5月13日至14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局势,意见分歧,但同意“要正确引导,要再观察一个时期”。
毛泽东写《事情正在起变化》:
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此文送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阅,建议发至党内17级以上干部参阅。17名政治局委员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林彪、林伯渠、董必武、罗荣桓、陈毅、李富春、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李先念;政治局候补委员为:乌兰夫、张闻天、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薄一波。陈云、李富春、刘伯承、张闻天4人阅后,没有在毛泽东文章上批注意见或“已阅”。
毛泽东文章,在党内分二个阶段下达:第一个阶段,发至十级以上干部;第二个阶段,再发至十七级以上干部。
毛泽东的《事情正在起变化》内指出:“我党有大批的知识分子新党员(青年团员就更多),其中有一部分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他们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联成一起,亲如弟兄。……社会上的中间派是大量的,他们大约占全体党外知识分子的百分之七十左右,而左派大约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右派大约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况而不同。”“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
中央发指示“反击右派分子进攻” :
1957年6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该指示称:“这是建国以来一场大战,战斗是无烟、无光的,在党的心脏展开。他们大该指示称:“这是建国以来一场大战,战斗是无烟、无光的,在党的心脏展开。他们大多已在不同领导岗位,有一定追随力量。”
1957年7月17日至21日,毛泽东决定在青岛召开一次省市委书记会议,会议讨论了关于反右斗争的部署。会议期间的八月三日,毛泽东写了《一九五七夏季形势》一文,作为党内文件印发。毛泽东在青岛会议上说:“匈牙利事件会不会在中国重演?我看有可能,可能五年、十年,也可能不用五年。纳吉式人物有可能在会场内。”这时,会场内有三十五张纸条递上主席台。大会主席周恩来当场宣读了这些纸条。其中有支持毛的意见,并要求毛泽东能公开谁是纳吉式人物;也有反对毛泽东这种无的放矢的观点。
党外人士对毛搞反右的异见 :
1957年5月30日,人大副委员长宋庆龄致信毛泽东主席,对全国范围在党内、民主党派内、知识学术界展开反右斗争,表示十分忧虑、十分诧异、十分惊奇,要求对没有行动“反党”的右派、右倾人士,作不同意见的争论处埋。
1957年6月10日,人大副委员长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陈叔通,分别写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信中都对展开反右斗争表示很不能理解。李济深在信中写道:在政治上出尔反尔、营造斗争气氛、制造对立阶层,会造成深远创伤。
300万人被划“右派分子” :
1958年5月3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反右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定性为右派集团22,071个,右倾集团17,433个,反党集团4,127个;定为右派分子3,178,470人,列为中右1,437,562人;其中,党员右派分子278,932人,高等院校教职员工右派分子36,428人,高等院校学生右派分子20,745人。在运动中,非正常死亡4117人。
【附录】(二)启功先生在反右批判会上的发言
批判《苦药特辑》
——启功副教授在批判“苦药社”大会上的发言
主席,诸位同志,诸位同学:
《苦药特辑》--《新今古奇观》、《奇冤记》等,是一种极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作品,它的反动本质,已经从各个方面受到许多同志的分析、揭发、反驳和批判,我就不多重复。此外它还有一副蒙人的外衣,即是好像它的“文笔还相当不错”,“够古典文学味儿”。因此甚至有的右派分子便以为这即是可以留当助教的条件和资本。还因有人说了句:“看不懂”,它们自以为又助长了身价,深奥莫测,便算高明。我们不妨先从艺术形式、写作技巧这方面来看看这些文章到底怎么样?后面再谈它内容的反动。
三言二拍的形式,在明末清初封建的正统文学当统治地位时,这种市民文学自有它的进步性,但到五四以后,为新的生活内容服务的新的文学形式产生,那些旧形式只成为历史遗产。当然我们是重视遗产的,我们对待遗产是批判的接受它的精华,去掉它们的糟粕,是恰当的借鉴,不是仅仅从形式上模拟就够了的。仅仅模拟形式,是一种落后办法。假如模拟好了,也不过是“假古董”,模拟不好,便是“东施效颦”,越发增加丑恶。我们初次接触这些作品,它的形式首先给我们一种没落感。章回体何尝不可用,现代也有不少反映新社会的章回小说,但《苦药特辑》这种用法,尤其用以宣传反动内容,除了使人愤慨之外,还觉得无聊、拙劣、庸俗、可厌……
有人看不懂就算好文章吗?新文学运动就是向着这种开倒车文学来革命。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文艺创作不能脱离生活,不能脱离群众,不能安心不叫人看懂。所以庸俗的文学作品,正式革命的对象,有什么价值!何况他们的使人看不懂,并非合乎古汉语语法的古奥,而等多的是不通,才使人看不懂。随便一翻,一些生硬、幼稚、拙劣、不合语法、不合程式的现象可见。
下面随手举一些从字到词到句不通的例子来看:
第十回“徇私就妙龄”,“就”字怎讲,牵就呢,往就呢,就是呢?二辑序“夸张薰染”,我只知道有“渲”染,没听说过“薰”染(这里不是当习染用的),又“正之于事实”,全句不是讲纠正、举证,原来是证明之“证”,第二十一回“闻者哑言”,既哑又怎么能“言”?原来是哑“然”的错误。还有像一辑序“源源而来,层层迭出”,我们只知道“曾见迭出”这个成语,他们为了硬凑对子,不惜乱加删改。
又如第六回“似生活在地雷之域,栗栗而自颤。”地雷如何成域,栗栗已经是“颤”。又如第十九回“后查明此事,乃知是同学某君,梦中闹鬼从四楼竟奔野外事。”“闹鬼”有两个涵义,一是舞弊,一是迷信的以为鬼来胡闹。“梦中闹鬼”是梦中见鬼呢,还是梦中淘气呢?第十七回“有一迷途家犬”,接着说“常随康先生后头”,“后头”和“家犬”真是“文”“白”不称。本回末诗曰“犬命呜呼成礼物,敬献座主得孝贤。世间衙门官无狗,无主奇冤向谁申。”仅仅四句,上言不搭下语。不是科举师生,哪里来的什么“座主”又怎么叫“得孝贤”呢?第三句更不知所云,四句联起,又谁会“串讲”呢?
还有语义模糊像第十二回“一群众逼作地主”是这一群众被逼呢,还是他逼了上文所说的“党书记”呢?第十五回“为祸为殃”是指“作威作福”呢,还是指“受祸遭殃”呢?太多了,多举徒占篇幅。虽然,末了还要举一个。第二十六回“兴有幸”,猜不出是什么话,我至今还在“不懂”之列。
至于回目、诗词的平仄不调,对偶错误,体裁乖谬,更是不一而足。只看《奇冤记》的开场西江月词,即可见根本不合词律,其他随处可以遇到使人读着别扭难过的不通词句。
如果不是这样内容,即仅仅以形式、技巧论,叫我判分数,我也没法给他及格,再加上如此的反动内容,便要给负分数,向他们讨债。
帮助党整风,原是极其庄严郑重的事情,即普通的提意见,实事求是也是最基本的要求。比如那只狗,如说是本文作者所打的, 一定不承认,以为诬赖他,不实在。但是他们怎么便可以扑风捉影,随便捏造种种事情呢?更有 许多人物心里的思想活动,像第六回“心中嘀咕道,第十七回”因自思曰“,作者又是从何处得知呢?他们在二辑序里说:“首先以事实之精神为依据而撷摘事物之一面,选撮事物之数端,稍事夸张,略加衬托。”且看“一面、数端,夸张、衬托,”这种片面造谣的本意,已经自己明白供出。再看一辑发刊词说:“特别是要打还无风无雨的地方去”,这实际应该说是要到有风无雨的地方去,好临风放火。
文学艺术有其特殊性质和用途,也不是凡属文学作品处处都可以用夸大,都可以用虚构。《西游》《封神》可以用虚构,讲史小说便不容完全虚构。《三国演义》如借东风等事可以渲染,而大关节目便不容完全颠倒。比如不能写孙权统一天下,曹操被处死刑。何况一般文件,有的绝对不容夸大,如会计账目,工作报告、XXXX(?),考试卷子,……这是人所共知的,难道严肃的提意见的事,就能采取这种特殊的虚构手法吗?
《苦药特辑》是以文学的特殊形式为掩护,对党进行诬蔑和进攻,如果有人责问他们的事实根据,他们便可以推移是文学虚构,如果没人责问,便可以混淆视听,颠倒黑白,手段是极毒辣狡猾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文艺的政治性第一,艺术性第二,但二者又是不可分割。如果说脱离政治,立场反动,则艺术性越高毒素也就愈大。《苦药特辑》的艺术性本不高,但他以古典文学外衣出现,炫惑读者,使稍微好奇的人,不免要拿起看看,他们散毒的企图,便因而得逞。唐人说:“德成而上,艺成而下。”仅仅艺成,尚算下品,何况《苦药特辑》的“艺”还并不够“成”,再加上内容的“恶德”,真成下品之下了。
我很痛心,他们这班的古典文学课我曾教过一部分,我通过教学对他们的思想教育进行的不够,我自己应该引疚检讨的,但我也没有叫他们学来作这项用途,无聊地模拟古典形式,借以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我现在正告右派分子们:你们应该及早改邪归正,接受党的挽救,老实交代,深刻检讨,争取回到人民队伍中来,这是唯一的出路,否则XX,后悔莫及了。
(未完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