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做“世界人”:“大爱”与“真善美”和谐奏鸣;不同凡响的生命轨迹完美交集

世界如此之大,我和刘华源、王昭英伉俪完全可能如陌路之人,擦肩而过,一辈子也互不认识。事实上,二十年来,以前已经有数次失之交臂。最早一次是1994年12月。首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在新加坡召开,王昭英看到报纸上的消息自费前来与会,我作为新西兰代表名字已印上大会手册,并定了论文题目,但人却因分身无术未能露面。翌年也是12月,王昭英出席了在新加坡举行的“世华”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我虽然即将离开工作了两年的新加坡,也特地抽时间到会场走动,但在几百号人中无从认识昭英、华源兄他们。我从昭英的《青山不老绿水长流》一文,得知他们夫妇俩也共觞2004年9月在北京八達嶺长城脚下举办的“全球百国华文作家手拉手团结和平友谊大会”,记得中秋节那晚,来自全世界几百位作家诗人朋友,在长城上一起举杯邀明月,对酒欢歌,可惜我却不知道华源兄和昭英就坐在身旁……
我们最后终于萍水相逢,彼此认识,回想起来也有点戏剧性。那是2011年11月,在广州召开的“共享文学时空”世界华文文学研讨会期间,一次乘坐电梯,突然站在对面的人看了我挂在胸前的参会证,欣喜地喊了一声,“你是何与怀?!”发声之人就是刘华源,他旁边就是王昭英。原来他们看过网上传来传去的我写的拙文,如关于刘宾雁、储安平、王若水、张志新、遇罗克、林昭……那些篇什,很有感触,就把我的名字记住了。我们一见如故,相见恨晚,共同的理念、梦想,让我们冥冥之中神交已久矣。
走笔至此,我不禁好奇地想:我此刻坐在英语国度澳大利亚悉尼我家里的书桌旁,而在广袤地球另一个小点上,在汶莱那个称为马来奕的小镇里,在他们布置得富于中华文化气息的家里,也是在此时此刻,华源兄和昭英正在做着什么呢?
……浮想联翩。我又一幕一幕回想去年在文莱的点点滴滴。

文莱地处婆罗洲岛北部,与东马砂劳越及沙巴为邻,国土面积只有五千七百六十五平方公里。根据2014年年鉴,全国人口约四十二万三千,马来族是最大民族,占总人口百分之六十六,华族占百分之十一,约四万七千人。在文莱出生的华人,不能自动成为文莱公民,必须经过语文(巫文)考试及格,方给予公民权。因此文莱有相当大部分的华人,由于通不过语文考试而成为无国籍人士。华文文学赖以生存的华文报刊至今还没有创办;华文文学作品只好到邻国的华文报刊发表。全国只有八所华文学校,其中仅有三所华文中学。这些学校的创建和办学经费,都来自华人社团,文莱政府不予补贴。酷爱中华文化的有识之士,在极为艰难的环境中,怀着“路漫漫兮其修远,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执着精神,为赓续中华文化传统做着孜孜不倦的努力。
华源兄夫妇带我们去参观过一间华文学校——创立于1931年的马来奕中华中学。1968年华源兄从英国学成返回文莱后,一面协助哥哥刘鸿祥经营家庭生意,一面执律师业,其间从1975年到1983年,文莱华文教育面临办理教学经费和改制的危机,华源兄临危受命,出任奕中董事会董事长;其兄也深明大义,积极支持奕中,并慷慨捐赠一座命名为“刘鸿祥楼”的教学大楼。当年还发生过抗争事件。政府要国有化即是接管全国八间华校,华源兄夫妇和其他友人组织起来进行抗争。最后妥协——数理化课程改用英文教科书,但全部华校得以保存至今。
面对着亡兄及自己心血的成果,触景生情,华源兄脸上露出压抑不住的自豪,但也掠过一丝淡淡的无奈;我们除了敬佩之外,也多少杂生一些困惑之情。

但这是已和他们生命密切相连难以分割的国度家园!他们毕竟是这里的华人,毕竟从小在这里接受了华文教育。回想上世纪六十年代,他们远到英伦留学,异国生涯对他们是既艰苦又充满挑战。面对与东方迥异的西方世界,他们不但有普遍意义上的乡愁,还有深沉的文化乡愁。他们想家,思念故土,亦对自己的文化传统充满眷恋之情。昭英回忆道,当学成归来踏上故土那一刻,她突然对艾青的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块土地爱得深沉”,产生深深的共鸣。
我再一次阅读昭英所写的《第二故乡》。这篇散文是她参加由世界福州十邑同乡总会主办的“冰心文学奖”的参赛作品,在来自世界十九个国家的一千一百二十一篇参赛作品中,获选为三十二篇入围作品之一收入《千花集》一书。可见此乃佼佼之作,很为她所珍惜,足可反映他们夫妻对居地的乡情。
昭英写道,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从英国返来,她的家已不在古晋,而必须在另一块陌生的土地、夫家的故乡文莱重建家园。真是逝水流光。自1968年她随华源兄定居文莱以来,转眼之间至她撰写《第二故乡》之时,已经三十个寒暑——如果计算到现在,则已经四十六个寒暑了。
她忆及自己初到汶莱时对今生此世要长久居住的马来奕小镇的感觉:
婚后随夫定居文莱一个叫马来奕的小镇。
小镇一边濒临南中国海,一边则傍马来奕河。
滨海而居,虽得水趣,却不得山情。
小镇地势平坦,连个山坡都没有,可说是个没有什么山川气势的地方。
有云:地灵人杰之地,是古代文化和文人留下较深足迹之处。不知是地不灵以至人不杰,还是人不杰以至地不灵,这里既无令人发思古之幽情的文物,亦无文人墨客的遗迹。
走过不少小镇,可谓风韵各异。有的似风华绝代的佳人,令人惊艳;有的如秀外慧中的闺秀,使人赞叹;马来奕却似小家碧玉,清纯温婉,平易近人。既无慕名而来的游客,打破它的平静,亦无牟利而来的淘金客,破坏它的清纯。到小镇来做客,十居八九是亲朋好友,因此常有“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喜悦。
结尾是这段韵味绵远悠长又大有深意的情感抒发:
小镇生活有如一潭平静的湖水,偶尔泛起一阵涟漪,很快又复归平静。小镇的人生有如这里的公路一样平直,既无上坡下岭,亦不蜿蜒曲折。
没有戏剧性的大起大落,当然也没有繁华梦醒的怆然落寞。
喧腾热闹不等于丰富充实,淡泊宁静不是单调空虚的代名词。只要胸怀世界,心系人生,小镇虽小,天地亦可以是辽阔的。
已达知命之年,最响往的还是平和冲淡的田园诗境界。小镇让我有机会实现这种追求。
为此,我心怀感恩。
好一句“只要胸怀世界,心系人生,小镇虽小,天地亦可以是辽阔的”!真是深得哲理之高妙。

我想到前文谈及的华源兄《因为我已经爱上了你》一诗。如有论者已经指出,诗中的“我”,从明面上象征了诗人自己,而从暗面上则隐喻了已决定落地生根的汶莱华人群体形象;诗中的“你”,从明面上象征了诗人的情人,而在暗面上则隐喻了生长于斯的汶莱华人群体已真正开始认同汶莱为自己的家国。“我”和“你”这两位寄寓着无限情思的抒情主客体形象,是由生活真实和艺术想象结合创造出来的人格化形象,从而使该诗显示出了比现实景象更高一级的境界。特别是“我”一再深情表白“因为,我已经爱上了你”的句子,使抒情主人公的缱绻眷恋之情一步步被无声推进,掀起了读者心湖底一层又一层的波澜。作者如此直言不讳地写出自己的心情,不单自我形象写照,是个人情感宣泄,更多的是民族感情的抒发,是众多居留于汶莱的炎黄子孙群体心境的写照。
我又想到昭英《另一种乡愁》,读来就整个人被“乡愁”所感染:
家乡!家乡!有家才有乡。当年的异乡也因我们曾在那里安过一个家而成为我们的另一个故乡。
有乡就有乡愁。而乡愁说穿了,不过是对一段日子的缱恋之情。
故乡在某种情况下,是一段日子的代名词。唐朝诗人崔颢在离开他家乡不远的“黄鹤楼”发出“日暮乡关何处是”的喟叹,显然不是因为乡关无觅处。
人对生活过的地方,都有故乡情意结。都会在离开之后不断的思念,不断地产生回去看看的念头。然而,若真的有一天得以如愿,重临旧地,却会对不依旧的江山与人事,产生怅然若失的情怀。可见怀念故土,许多时候是在怀念一段生涯。
……
啊!乡愁,正是渐行渐远渐深……

谈起乡愁,我不得不提到在文莱认识的华源兄和昭英的挚友丘启枫先生。这位先生是个奇人,奇就奇在他身世的奇特。祖藉广东大埔的他,在汶莱出生成长,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学成返汶莱执教十年,在台北驻汶莱机构服务八年。先后担任新加坡《联合早报》驻香港、北京、台北特派员;香港《联合报》资深编辑兼港闻组组长;《亚洲周刊》副总编辑,现为汶莱时报(The Brunei Times)集团副总编辑。他曾经有过七种旅行证件,有过十种国民身份。最初,1954年1月,汶英当局发给他一张单薄的旅行证,他的国民身分是“中国客家人”。两年后,他取得居留证,国民身分变成汶莱永久居民。1961年1月,申请到英国护照后,他的第三个国民身分变成“汶莱英国保护籍民。1990年,他有了第七个国民身份:新加坡永久居民。1992年,他申请放弃中华民国国籍,获得内政部长签发的“国籍许可证书”,又取得另外一个鲜为人知的国民身份:“许可丧失国籍人”。这时候,他按照国际法已经没有国籍了。同年,他获得第九个国民身分:新加坡公民。2002年,他取得附有三颗星的香港身份证,又多了一个国民身份:香港永久居民。
乍听起来,好像是间谍电影,仿佛一个人手持多种护照,在国与国之间变换,取得一个个生存的空间。其实,丘启枫先生并没有花钱或使用什么奇巧手段取得国民身份,是国际政治和职业选择决定他的国民身份,然后决定他可以持有的旅行证件。以他的经验,不同的国民身份和旅行证件,在不同的移民、关卡、保安人员面前,偶有不同的挫折和意外,总得有点耐心,有点认命,从来不敢奢望“来去自如”。因此,他总是在排队或者等待制服官员的时候,读读唐诗,遥想古人间关万里,证件就在诗与诗之间等待。所以,他行囊里总带着一本翻得破烂的唐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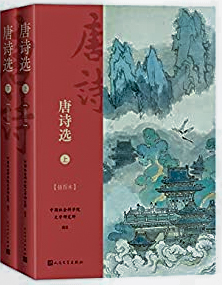
丘启枫先生说,很多时候,唐诗是他这个“精神难民”心中的“护照”,是他神游长安的“身份”。当一切挫折过去之后,总会有美好的归属,好像唐诗拥抱了他。想起唐诗“笑问客从何处来?”他欣然接受自己是永远的过客。带着那本唐诗,历经他十个身份的转折,书页已破损,可是,他喜欢这本伴随他东奔西走数十年的旧书。
他不无自豪地总结说,唐诗才是他的身份,他的故乡……
丘启枫先生的身世和他的感悟给了我莫大的启示。
的确,人一旦失去了精神家园,找不到心灵的故乡,就像漂浮在茫茫大海中的一叶扁舟,随时面临覆灭的危险。但是,作为一个华夏子孙,不管身在何处,何时何刻,怎样的境况,当想到自己与中国、中华文化的关系,可以借用一位波兰作家的话,坦然自若地告诉自己:“我就是中华文化。我的中国意识就在自己身上。”当年,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前所长刘再复先生离国,在最初的六年里,写下《西寻故乡》这部集子,叩问故乡的意义和生命存在的意义。他在叩问中告别了“乡愁”的模式和族群的土地观念,为寻求生命最后的实在。在六年日日夜夜的游思中,他把故乡分解了:地理之乡,文化之乡,灵魂之乡,情感之乡……这样,他终于寻求到心灵的安稳。而现在昭英,对“乡愁”和“漂泊”,也有自己豁达、超然的理解,因为她也以自己的经历让体会有了升华:“昔日的异乡汶莱,如今已是我魂牵梦萦的故乡。偶尔踏足英伦,我也有回家的感觉。置身异乡而无深刻的漂泊感,我想可能是因为我能用心坚守自己的文化家园。”其实,一千两百余年前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先生就说过:“身心安处为吾土,岂限长安与洛阳。”九百多年前的苏东坡先生也告诉我们:“此心安处是吾乡。”真不愧是豁达的大诗人,其真知灼见几乎预见到千年之后的人类地球村。世界何其之大,世界也何其之小。只要心安,只要坚守自己的文化家园,哪个地方都可以安家啊!

就让我们做个“世界人”吧。我在多年以前的一篇文章中曾经引用过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在太平洋途中,感怀身世,写下的这样一段话:“余乡人也,九岁后始游他乡,十七岁后始游他省,了无大志。懵懵然不知有天下事。曾几何时,为十九世纪世界大风潮之势力所颠簸、所冲击、所驱遣,使我不得不为国人焉,不得不为世界人焉。”(梁启超,《〈汗漫录〉序言》)今天是二十一世纪,我们──特别是作为华裔作家/诗人的我们──是否更应该做一个“世界人”并以此使我们当下的生活更具有可信度呢?我们似乎不必在“原乡”“异乡”的观念中纠缠,不必为“在家”“不在家”或“有家”“没有家”的感觉所困扰而不能自拔,不必因为“土地家园”不是“终极家园”而极度怀疑而灰心丧气。这些纠缠、困扰、怀疑,为文学创作提供无限的思考和想象空间,但作家作为一个“世俗”的人,应该有平常心也应该拥有积极的人生观和广阔的历史哲学视野。我们毕竟都在同一个世界怀抱同一个梦想。
现在,我知道为什么去年在文莱那几夜我连续进入如此文开头所回忆的梦境了;我知道如何去解释那些梦境了。

如今算来已经是很久以前了,在1993年7月25日,王昭英在《诗华日报》“思维集”专栏发表一首诗,题为《南中国海——我底梦乡》,抒发她的梦想:
我爱海/更爱那浩翰无边的南中国海/在海底深处/曾经隐藏着我无数的梦/曾几何时/汹涌澎湃的南中国海/背负着我走向理想与希望/陪伴着我迎接幸福与欢畅/在海的彼岸——狮城/开始了人生最美丽的时光/海岛那灿烂的岁月/留下无数的歌声与欢笑/驰聘在学术疆场上/爱情的花朵在“云南园”开放/生活呵!是百花盛开的园地/青春啊!是一首唱不完的赞歌/潮涨潮退/花开花落/时代的浪涛/吞没了理想的王国/满地的落红/掩埋了春的足迹/青春是荷叶上的露珠/生命是张白纸/抱负掩没在账部文件堆中/理想埋葬在柴米油盐堆里/南中国海——我底梦乡/那年那月/你才能再次激起我旧日的情怀/为生命的光华/奏起一支雄伟的颂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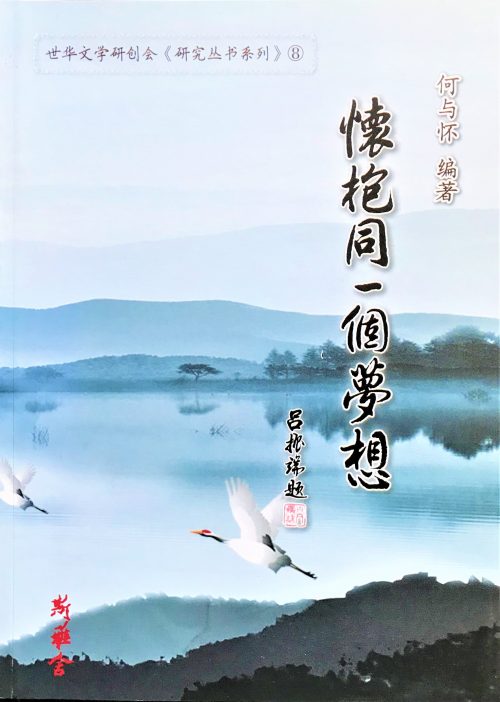
虽然生命也曾出现低谷,如今,昭英的梦想实现了,她“旧日的情怀”早已再次激起;她为生命的光华正奏着一支雄伟的颂歌。
这二十年是怎么过来的呢?看看华源兄写于2013年4月29日的这首题为《悟》的诗吧。这是他的感悟,也可看作他的誓言:
在一个空旷的空间 无边无际/在一个静寂的世界 滴水可闻/一个孤独的灵魂/最贴近那终极的力量/仰望夜空 北斗星闪闪发光/迷路的人 找到前进的方向/高山 大海/森林 野兽/挫折不了你/追求/真 善 美 的意志

就是在心中那颗闪闪发光的“北斗星”指引下,他们贴近“那终极的力量”;在对真善美不屈不饶的追求中,这对夫妻比翼齐飞,携手前行。同极其真切的人生之“悟”紧密相连,他们把一己之爱升华为对家乡、国家、民族以至整个人类的大爱。他们以“爱”作为出发点作为推动力,来促成“真善美”在人生各个领域中的实现。在其作品中,人们可以听到他们的“大爱”与“真善美”的和谐奏鸣。

我也喜悦地听到他们的“大爱”与“真善美”的和谐奏鸣,看到他们不同凡响的生命轨迹的完美交集。在这交集中,散发出深深的南大情结、六四情结、中华文化情结。他们怀抱着同一个梦想,开出文学之花,思想之花,永不凋谢!
(2014年11月13日完稿于悉尼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