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107)
赤色帝国覆亡之谜(60)
发生在苏联各地的民族主义浪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使当局穷于应付。散见于西方媒体中的此类消息让世界各国关心这个问题的人心情既沉重又振奋。除了前文披露的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的民族主义运动,下面是六、七十年代西方媒体有关苏联其他少数民族运动的一些消息:
美国纽约时报新闻社1969年3月报道:
雅希莫维奇家里的朋友昨天(25日)说,雅希莫维奇由于所谓散布反苏谏言被逮捕了。
雅希莫维奇约40岁。据说他25日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郊外被捕,自去年被解职后,他就和妻子以及三个小孩住在那里。
他曾经一度被认为是集体农庄主席的模范。1964年10月30日的《共青团真理报》刊登了他的日记摘要,并且说,他的庄员认为他“工作努力、正直和公平”。
他和妻子都是拉脱维亚国立大学哲学系毕业生,据信,妻子仍然是位教师。
去年6月,西方媒体刊登了雅希莫维奇给政治局委员苏斯洛夫的一封信。
他在信中说: “在50%以上的人口都还不到30岁的国家里,迫害持不同意见的青年人是极端危险的”。
去年7月,他和另一个有名的持不同意见的人,苏军前少将格里戈连科到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表示他们支持杜布切克政权的政策。
去年11月他散发了一封公开信,说由于他给苏斯洛夫写了封信而被解除集体农庄(主席)的工作。
他说,他一家人从这个农庄所在的尤马尔搬到里加附近的西维尔加拉,但是他没有得到寻找工作、享受医疗及其他福利的必要的证件。
(雅氏随后被送到里加一家精神病院,于1971年5月3日被释放。)
美国《华盛顿邮报》1970年9月28日报道:
当学生们正在(立陶宛维尔纽斯)大广场转来转去的时候,警察下令他们散开,他们拒绝了。因此警察采取了行动,接着发生了连续几个小时的冲突。没有人受重伤。好几名在这场冲突中被捕的学生后来都被释放了。
美国《波罗的海研究公报》1971年第六期报道:
在1965一1970年间,针对基辅、里加和塔什干的民族反抗中的领袖人物采取了许多镇压行动。他们当中被判刑的有84岁的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领袖门德斯博士。
英国《泰晤士报》1971年12月31日报道:
苏联摩尔多瓦劳改营中的一批政治犯呼吁国际红十字会,帮助使他们在监禁中受到的那种严酷的状况得到改善。
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参加了各种民族主义运动,敢于反对党的民族政策。
法新社莫斯科1972年3月27日消息:
一些外国记者今天在这里收到了致苏联党首脑勃列日涅夫备忘录的副本,这个备忘录斥责了它所说的对立陶宛天主教徒的迫害。这份文件附有17054人的签名的123件请愿书。
写明致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的序言说,请愿书迄今得到的唯一结果是镇压加强了。
有一个附件说,签名的只是那些希望请愿的人的很少一部分,因为国家安全人员使用各种手段,包括“威胁、逮捕和手铐”来制止征集签名。
备忘录指责说,信教仍没有自由,(天主教)教会继续遭受迫害。它指出: 当局对两位主教判处了流放;逮捕了两名神父,他们去年曾向为圣餐作准备的孩子们传教。备忘录抱怨说,在立陶宛,训练天主教神父的学校已被置于当局的控制之下,他们只准许最多有十名学生。请愿者说,信徒的子女受到“疯狂的无神论”的折磨,被迫违背自己的良心讲话。他们还指责说,当局拒绝恢复教堂,并且举例说有一个教堂已被变成了舞厅。
签名者还说,国家在立陶宛实行的无神论是个民族灾难。
英国《每日电讯报》1972年7月7日报道:
在立陶宛共和国过去两个月发生了激烈的反俄抗议之后,俄国的特别治安部队和警察增援部队大批开入那个国家。
从爱沙尼亚首都塔林传到西方的一封信透露,在其他波罗的海共和国里反俄情绪也很强烈。塔林理工学院的学生最近举行了一次反俄示威,为此,许多学生受到的威胁不仅仅是被开除学籍和被动员加入武装部队。这封信还抗议压制爱沙尼亚语言,让大批俄罗斯人进入这个国家,利用爱沙尼亚的自然资源为俄国谋利。信中说: “五百万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不要俄国占领。”
日本《读卖新闻》1972年5月13日报道:
次于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盛行的地方是三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它们)对苏联制度的反感是最强烈的。去年立陶宛天主教徒一千多人抗议对宗教自由的干涉,据说在给勃列日涅夫的抗议书上签了名。今年年初有17名拉脱维亚的老共产党员在联名给西欧共产党领导人的公开信中控诉把俄罗斯化政策强加于拉脱维亚和对民族文化进行压制。
路透社莫斯科1972年7月9日消息:
据来自立陶宛共和国的最近消息说,在6月份,反苏情绪的又一次爆发使当局感到震惊。上月在首都维尔纽斯一次国际手球比赛中爆发了这种情绪。学生观众在演奏苏联国歌时拒绝起立,他们挥舞立陶宛国旗,散发反苏传单。据说有150人被捕。
西德《播种》1975年第六期报道:
摩尔达维亚则在悄悄地、暗暗地和深沉地进行着为民族文化的斗争。下面就是这一斗争的行动之一。
一个学校举行音乐晚会,唱的是“摩尔达维亚歌曲”,实际上是罗马尼亚民间歌舞节目。当穿着显然是俄罗斯服装的女报幕员说: “现在请听几首不同风格不同时代的著名俄罗斯歌曲……”
她的话还没有说完,就响起了推动椅子的响声。有一半观众示威性地离开了会场……
在现代摩尔达维亚的条件下,这种行动以及其他一些类似的公众抗议形式,都是民族解放斗争的行动。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1977年2月14日报道:
在几乎每一个少数民族地区,民族的压力和苏联压制民族情绪的努力都在明显增长。例如在格鲁吉亚,发生了一系列火灾和小炸弹爆炸事件,这些事情的背后都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反对情绪。格鲁吉亚人(由于他们的个人主义和独立的天性、他们的文学中的强烈的神话影响以及他们传统的不可控制性,常常被称为苏联的爱尔兰)在批评苏联在民族问题上的做法时要比其他少数民族来得公开。
而从爱沙尼亚经过中亚直到苏联远东部分,民族主义的高涨是显而易见的。
在塔林的一次歌咏大会上,官方的节目结束后,一大批群众开始高唱爱沙尼亚的爱国歌曲,当局就用吵吵嚷嚷的扩音器来把歌声淹没下去。
在乌兹别克,一些穆斯林节日活动使人们那么感兴趣,以致当地CP首脑不得不下令开展一场以“苏联的共同传统”代替这些节日活动的运动。
1970年4月19日美国《星期日电讯报》报道:
俄国苏维埃制度的反对者已经拟订出实行政治和经济改革的第一个全面纲领。这个一万字的纲领称为“民主运动纲领”。
它在莫斯科及其他苏联城市散发巳有好几个月了。印本现已传到西方的俄罗斯和波罗的海的流亡者手中。
这个说理谨慎、很有感染力的文件拟制者的姓名尚不知道,文件上只写“俄罗斯、乌克兰、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民主主义者”。
1970年第九期的西德《播种》杂志报道说:
1970年4月7日,白俄罗斯明斯克的中学生马克萨科夫因携带要求民主自由的传单被人打死,一些同学因此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出版和言论自由。他们斥责警察的干预,高呼“这里不是捷克斯洛伐克!”
1972年2月22日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报道:
摩尔达维亚宾杰市一位42岁的教师苏斯连斯基给苏共中央写过公开信,抗议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结果他被捕了。搜查他家的警察发现了一些录下了英国广播公司播音的国产磁带和一些表达他的自由思想的日记。在摩尔达维亚最高法院的一次审讯中,起诉人要求给他判三年徒刑。而这家法院对苏斯连斯基判处了七年徒刑。
1972年6月26日美国《新闻周刊》报道:
据来自波罗的海地区的消息说,现在立陶宛境内的动乱正在沸腾。
在苏联政府开展了一个干扰立陶宛罗马天主教的运动、加紧反教会的宣传和逮捕那些没有许可证而布道的神父后,这种麻烦显然开始了。在立陶宛310万公民中,大约有80%是是天主教徒。今年早些时候,有1.7万人在一个要求联合国确保立陶宛宗教自由的请愿书上签了名。据说,这份请愿书是在立陶宛犹太人的帮助下偷拿出来的,并交给了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但是那里的抗议活动没有停下来,5月14日,一个19岁的名叫卡兰塔的学生在考纳斯市闹区自焚。之后几天,数以千计的学生蜂拥走上该市街头,高呼“自由!自由!”
学生们遇到了手舞警棍的警察,警察无法把他们控制住。汽车和大楼被烧毁,最后,苏联当局被迫派出特种警察和伞兵部队。据说到骚乱被控制住的时候,有两名警察被打死,八百名学生被捕,其中六百名学生后来被释放。
但是,立陶宛爱国主义的激动情绪是不容易压制的。6月初,又一名青年登上瓦列纳城的一座大楼的顶层,自焚后跳楼。虽然考纳斯当局已把卡兰塔的尸体从原来的坟墓运走了,但是有消息说,许多人仍每天来到他的殉难地安放鲜花。一位专家说: “立陶宛激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使苏联人手足无措。但是他们将设法使这一事件置于控制之下,他们不允许立陶宛变成另一个捷克斯洛伐克。”
这期《新闻周刊》还报道说,5月29日,立陶宛瓦列纳青年工人斯托尼斯为抗议当局禁止他在一次展览会上升立陶宛国旗而自焚。
1972年7月4日美国《洛杉矶时报》报道:
考纳斯的示威是生动的证据,表明莫斯科没有能赢得在苏联统治下成长和受教育的年轻立陶宛人的效忠。5月14日自焚的卡兰塔只有19岁,他在自焚前发表了讲话,谴责苏联压制民族和宗教权利。那些参加示威游行的人绝大多数属于30岁以下这一代。指出下述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卡兰塔是共青团员,并且生长在其兄弟们都是共青团和父亲是CP员这样一个家庭里。同时,据旅行者报道,尽管卡兰塔是共青团员(团籍要求坚信无神论),但他是忠实的宗教信仰者。一些已公布的被捕者的身份表明,工人的人数几乎与学生一样多,在年轻人中,甚至在CP人的家庭里,还有在工人队伍中的这种坚持民族主义的效忠的做法暴露了莫斯科的思想灌输的无能。
这种民族问题同民权问题的结合是苏联一个新的事态发展。它表明俄罗斯自由势力同非俄罗斯民族势力联合的可能性。这种联合在俄国革命史上是重要的,并且最终可能大大影响政府的民族政策和苏联社会自由化的前景。
因此,不应把最近立陶宛的革命的、表示抗议的自焚和示威看成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应看成是对苏联国内事态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
1972年7月5日美联社从莫斯科报道:
立陶宛工人胡卡维立斯(生于1912年)6月3日在考纳斯广场自焚身死,抗议苏联对立陶宛的占领。六天后,一位名叫考斯卡斯的工人(生于1910年)企图自焚未遂被捕。6月11日至18日在维尔纽斯举行的国际手球赛期间,约有150名大中学生被捕,因为他们嘲笑苏联运动员,向外国人喝彩,在奏苏联国歌时拒绝立正站立;他们还散发反苏传单,并且在大街上挂起立陶宛国旗。这表明在立陶宛,对苏联的政治和宗教压迫的反抗日益高涨。
1972年7月9日英国路透社从莫斯科报道:
苏联的立陶宛共和国有几百人被捕,在该共和国的天主教徒中仍然感到愤慨,加之三个立陶宛人自焚身亡,这表明克里姆林宫碰到了新的、可能是爆炸性的问题。
自今年三月一万七千多名立陶宛天主教徒向苏联当局请愿,反对对教徒采取歧视态度以来,通过可靠的渠道传到这里的骚乱消息变得越来越富有戏剧性了。
至少有两个因素似乎特别使莫斯科的领导机构感到不安。
这两个因素是,年轻的立陶宛人的卷入,以及把宗教和民族主义的不满情绪联系起来的连锁反应产生的可能性。
按照官方的看法,立陶宛人没有理由抱怨对他们的宗教或他们的民族愿望的镇压。据苏联报纸和电台说,第一个自杀者(卡兰塔)精神错乱,在他死后,有一些“流氓和年轻的懒汉”卷入为时两天的骚乱。
可靠人士对骚乱作了不同的描绘。骚乱是在19岁的卡兰塔在考纳斯自焚之后爆发的。他们说,年轻的示威者高呼“给立陶宛自由”的口号,有几百人被捕,非立陶宛的伞兵部队被用来镇压骚乱。
据来自这个共和国的最近消息说,六月,反苏情绪的又一次爆发使当局感到震惊。当时,在首都维尔纽斯的一次国际手球比赛中爆发了这种情绪。……这些年轻人像卡兰塔和第二个自杀者一样,是属于不记得独立的立陶宛的一代人。
第二个牺牲者的名字叫斯托尼斯,据报道,他在今年5月29日,即在警察阻止他和他的三个朋友在立陶宛东南部的瓦列纳举行的一次展览会上升起立陶宛国旗的第二天自焚的。
(合众国际社6月13日报道,这名青年在一座四层楼的楼顶上,把汽油浇在自己身上用火点燃,然后跳下楼。四天以后他死了。)
1974年5月23日,英国《苏联问题分析家》杂志报道说,立陶宛施亚乌里亚伊的大学生在公共场所张贴传单,写有“打倒苏联统治!俄罗斯人滚出立陶宛!自由属于立陶宛!”
1977年11月15日奥地利《新闻报》报道:
苏联边缘地区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基础比这个欧洲帝国内部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基础广泛得多,但是,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反对国家政权的行动却软得多,暧昧得多。有三百多万居民的立陶宛加盟共和国却是例外,立陶宛人民坚决反对慢慢脱离中央俄国的做法。
不久前才被允许离境的列宁格勒持不同政见者鲍里斯•韦尔在维也纳谈到对波罗的海三国形势的评价时,叙述了他在西伯利亚一所监狱里一名克格勃军官向他谈话的情况。那位军官说: “我们可以征服爱沙尼亚人和拉脱维亚人——但对立陶宛人则必须杀掉一半。” 有件事发生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以独特的方式庆祝十月革命节之前,当地代表队和(俄罗斯)斯摩棱斯克代表队举行一场足球赛时,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但是,几千名观众高呼“俄罗斯人滚出去!”的口号声无论哪里都没有谁能听到,甚至连苏联的其他地方也听不到,因为一位电视技术人员在这时干脆中断了实况转播。
多次给勃列日涅夫的请愿书——有几千人签名——仍未得到答复,尽管根据苏联的法律,当局有在一个月内对这些请愿作出答复的义务。
这种做法的后果是使立陶宛的知识界转入地下。五年来,《立陶宛天主教大事记》已经出了二十多期。它比俄国所有的地下刊物的发行量都大,因为每一期都被同情者翻印。人们从大事记里可以了解到这个加盟共和国实际发生的事情。
在第六期,人们可以看到一些立陶宛人被传讯的情况,因为他们曾拜访过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的立陶宛同胞。在这期大事记上也谈到应当同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人民建立联系的问题。克格勃当然也对以下几个问题感兴趣,即为什么在联欢会上只唱立陶宛歌曲,人们为什么搜集立陶宛(苏共)党员的材料,已经解散的大学生俱乐部“罗穆瓦”的成员又在干什么。同住在白俄罗斯共和国的立陶宛人之间所有的接触以及《大事记》发表的来自波兰的消息(这些消息使人们得出关于该刊出版者的联系已经超出了国界的结论)当然也都是有嫌疑的。
八月底,秘密警察逮捕了教育学家佩特库斯,他曾蹲过14年监狱,但是刑满后他又继续给中学生们辅导宗教和历史课。(当局)因此不准这些中学生参加中学毕业考试,同时还准备指控佩特库斯是《大事记》的精神主编,并且还企图成立“波罗的海沿岸各民族解放委员会”。
唐科斯在《分崩离析的帝国——苏联国内的民族反抗》第六章《处于危机的一体化》最后是这样总结苏联民族问题的症结的:
苏联领土上四面八方零零星星爆发的这些危机证明了什么?一个民族共同体不愿永远受歧视,并希望大约30万人返回故乡;在一个丝毫还没有让出自己的权利和自由的地方主义的民族中,出现了预防性的恐怖主义;苏联第二大民族在其他共和国里充当中央政权的助手,但同时又反对俄罗斯对它的事务的任何干预,它发生的变化是比较模棱两可的。以上所有这一切是否有共同之处?
这些危机证明,苏联不是一个消除了一切差别的完全统一的大家庭,各民族对自己领土和文化的感情并不只是对往事的回忆。这些危机还证明,所谓的“苏联人民”仍然是各民族的集合体。这些大小不同、情况各异的民族之间的共同之处,就是它们都与中央政权发生了明显的危机。它们希望实现自己的愿望,都共同针对着中央政权,竭力要说服或威胁它。最后,这些危机都共同出现在苏联政治制度内,并且是按照苏联的标准与意义发生的。这些危机是否影响苏联的整个制度?看来没有。根据所看到的材料,大部分非俄罗斯社会显然都得到了维护。人口众多、生机勃勃的穆斯林社会似乎就属于这种情况。它是补偿已出现的危机、并对苏联制度起稳定作用的因素呢?还是这种稳定掩盖着另一种潜伏的、危及整个团结的更可怕的危机呢?
在这本书写作出版的1978年,作者虽然认为在苏联面临的所有问题中,“最急需解决而又最难解决的显然是民族问题”,“苏维埃国家似乎也无法走出民族问题的死胡同”,但他还难以想像十年后苏联的民族独立运动便风起云涌,仅仅三年,苏维埃红色帝国的大厦便轰然坍塌了。
这真是形势比人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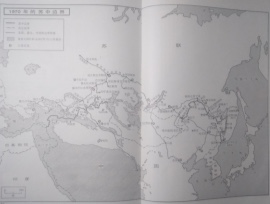
(未完待续)
荀路 2022年12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