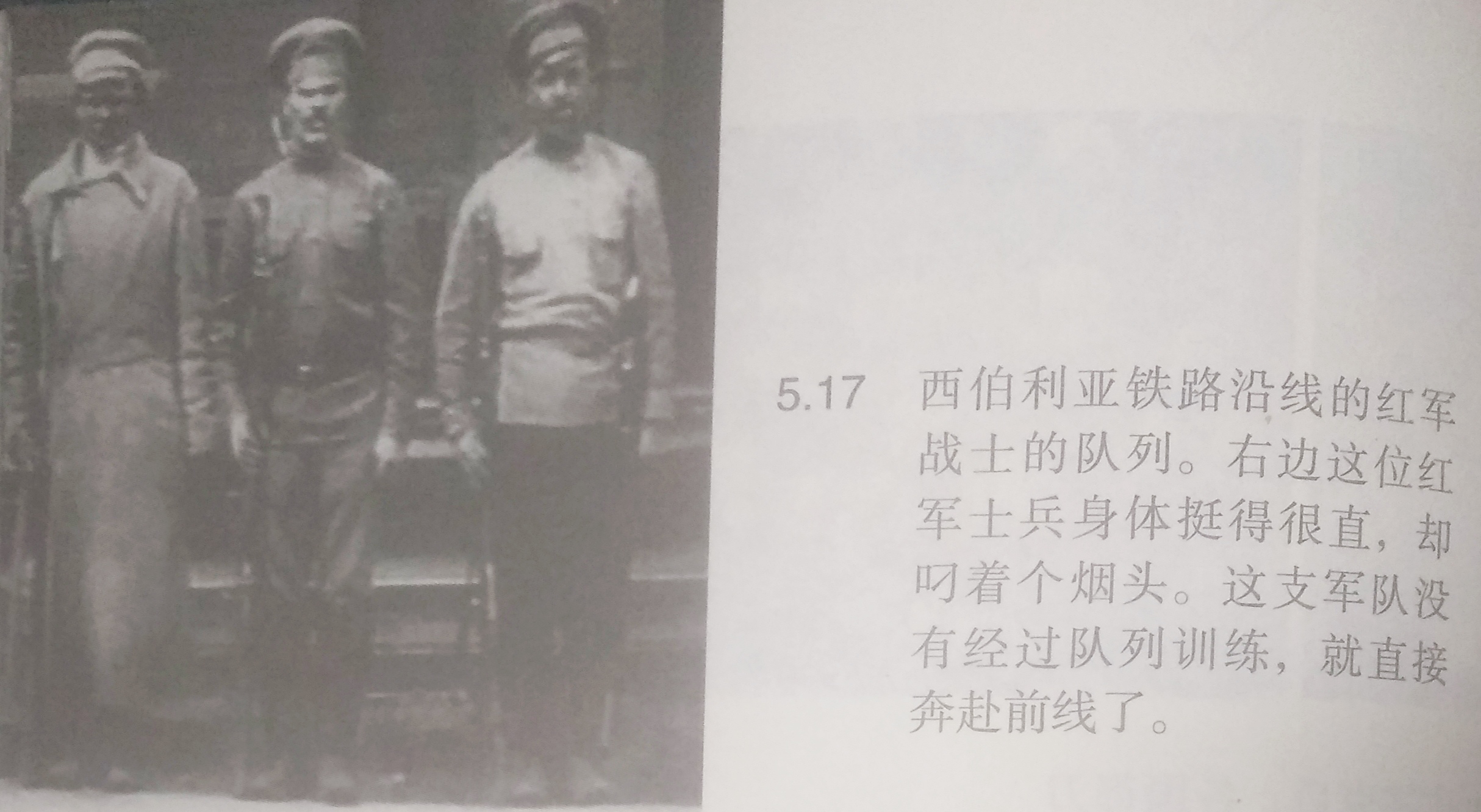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117)
赤色帝国覆亡之谜(70)
下面论述苏共中央委员会实际作用的演化过程。
从中央委员会的实际运用来看,它既是权力实体,又是权力空体。它在某些时期是权力实体,而在另一些时期则成了权力空体。
在十月革命前后,中央委员会是俄共的实体。举行武装政变推翻临时政府的决定就是在10月23日中央全会上作出的。中央全会至少每两个月召开一次,解决党的重要问题。但从1919年俄共(布)八大以后,中央委员会开始成为权力空体。八大决定,在中央委员会内部设立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政治局“对不容拖延的问题作出决定”,而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则讨论“一切非急需解决的最重要的政治和组织问题”。在内战时期,由于许多中央委员都在前线作战,中央委员会很难召开一次全体会议。当时的许多重要问题都是中央政治局解决的。
1921年转入新经济政策时期,俄共高层不断有人批评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中央委员梁赞诺夫在俄共(布)十一大上批评道: “我们的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是一个特殊的机关。据说英国的议会无所不能,它只是不能把男人变成女人。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可要强得多,它已经把不止一个十分革命的男子汉变成了胆小怕事的娘儿们,这样的娘儿们现在多得简直叫人难以置信……只要党和党员对以党的名义贯彻的一切措施不进行集体讨论,只要对党和党员来说这些措施是突如其来的,那么我们这里就会出现列宁同志所说的那种惊慌失措的情绪。”
晚年的列宁对中央委员会十分重视,他准备把中央委员会改造成党的名副其实的最高权威机构。在此之前,俄共中央规模很小,只有十几位中央委员组成。为了“防止党的分裂”,加强全党的稳定性,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建议“对我们的政治制度作一系列的变动”,即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几十人甚至一百人。列宁认为: “为了提高中央委员会的威信,为了改善我们的机关,为了防止中央委员会一小部分人的冲突对党的整个前途产生过分大的影响,这样做是必要的”。
在《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一文中,列宁进一步对中央委员会提出改革建议。他说: “我党中央全会已有发展成为党的一种最高代表会议的趋势。它现在平均每两个月开会一次,至于日常工作,大家知道,则由我们的政治局、我们的组织局、我们的书记处等等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处理。我认为,我们应当走完这条已经走上的道路,把中央全会完全变成党的最高代表会议,每两个月开会一次,有中央监察委员会参加。”
列宁建议从工人和农民中选出75一100名新的中央监察委员。当选者也像中央委员一样,应该经过党的资格审查,因为它们也应享有中央委员的一切权力。
列宁提出把工农检查院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结合起来。列宁认为,“经过这种改革,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能更好地了解情况,在政治局会议以前能更好地进行准备。我认为,除了上述政治上的好处外,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在我们中央委员会里纯粹个人因素和偶然情况的影响会减少,从而分裂的危险也会减少。”
列宁还指出: “我们中央委员会已经形成一个严格集中的和威信很高的集体,但是这个集体的工作条件还和它的威信不相称。我提出的改革必将有助于改变这种状况。有一定的人数必须出席政治局每次会议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们,应该形成一个紧密的集体,这个集体应该′不顾情面′,应该注意不让任何人的威信,不管是总书记,还是某个其他中央委员的威信,来妨碍他们提出质询,检查文件,以至做到绝对了解情况并使各项事务严格按照规定办事。”
列宁的思路是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建造成名符其实的党的最高权力机构,把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置于最高权力机构的领导和监督下,增加最高权力实体的普通劳动者成分。
然而,列宁的继承者们并没有按照列宁的改革建议行事。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人数虽然扩大了,但这些人并不是普通的劳动者,而是经过斯大林主持的组织局和书记处选拔的基层干部。这种扩大无助于改变俄共的官僚主义倾向,无助于党的稳定。
在19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初,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处于分裂的情况下,中央委员会成为党内斗争的重要场所。斯大林通过中央书记处和中央组织局控制中央委员会,使得党内反对派屡遭失败。随着斯大林个人权力的增长,中央委员会的作用降到了极限。党的代表大会从十四大开始就不再一年召开一次了。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大之间竟然相隔了13年。(中共六大到七大间隔了17年)中央全会更是很少召开。在1938年和1939年只召开过一次中央全会,整个卫国战争期间没有召开过一次中央全会。1946年至1952年也只召开过一次中央全会。
不仅如此,在大清洗时期,联共(布)中央委员会遭到斯大林毁灭性的破坏。1934年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其中83人被逮捕枪毙(大部分是在1937年至1938年)。十七大代表中拥有表决权和咨询权的1966人中有1108人被定为反革命遭到逮捕判刑。
联共(布)十七大党章规定,对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采取党内最高处分时,必须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邀请中央委员会全体候补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委员出席。如果这种全体会议有三分之二赞成必须把中央委员或中央监察委员转为候补委员或开除出党,那么,这种处分就应立即执行。但斯大林在逮捕和枪决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时根本没有经过中央全会讨论。在斯大林时期,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连形式上的权力也不存在了。
赫鲁晓夫执政后,恢复了中央委员会的权力实体作用。由于赫鲁晓夫在中央主席团中并不占优势,所以他把许多重要问题都提交给中央全会解决。
例如,农业改革、垦荒运动和工业大改组等许多重大改革措施和决策都是由中央全会讨论并通过的。在这个时期,苏共中央全会定朝召开,大多数中央委员都支持赫鲁晓夫。这就使得赫氏能够以中央委员会为依托同莫洛托夫等人占优势的中央主席团相抗衡。1957年6月,当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等人联合起来在中央主席团发动一场“宫廷政变”,企图以七比四罢免赫氏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时,中央委员会显示了自己的权力实体的权威。在紧接着召开的六月中央全会上,莫洛托夫等人由中央主席团上的多数变成了少数,全会重新确认赫氏为中央第一书记。莫洛托夫等人成了“反党集团”,被赶出了中央委员会。但赫氏大权在握后,中央委员会的权力又被削弱,许多重大决策都是赫氏一个人作出的,只是在中央全会上象征性地通过一下。
在赫氏执政后期,苏共中央全会的作用也下降了。赫氏经常召开扩大的中央全会,将一些党外人士和非中央委员召来开中央全会。这表面上是发扬民主,实际上是降低了中央全会的作用,使中央全会无法作出负责任的决策。实际上这是赫氏在党内地位下降时所采取的恢复权威的一种做法。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中央委员会成为形式上的权力实体。中央全会虽然按时召开,但不解决重大问题。中央全会在空转。像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富汗这样的重大决策都是由政治局的少数人作出的,随后才向中央全会通报一下。勃列日涅夫表面上对中央全会很重视,实际上并非如此。他曾经表示: “全会决议应成为各级党委会、全体共产党员切实工作的战斗纲领,应作为旨在进一步提高劳动人民的政治积极性和劳动积极性的组织和教育工作的基础。”但是,中央委员会并没有起到这样的作用。戈尔巴乔巴乔夫后来说: “多年来,党和人民关心的许多问题没有被提到全会的议事日程上来。同志们都记得,曾不止一次地举行过时间很短和形式化的中央全会。许多中央委员在其整个任期内没有可能参加讨论甚至提出建议。中央全会的这种气氛也影响到地方党委和党组织的工作作风。”
戈尔巴乔夫执政后,中央委员会在开始的一段时间里成为权力实体。如1985年4月中央全会,1987年1月中央全会,1987年6月中央全会,1987年10月中央全会,1988年2月中央全会,1988年9月中央全会,1989年3月中央全会和4月中央全会,等等。在这些全会上,有关苏联的改革问题得到了充分的辩论。那时,戈尔巴乔夫认为,“在我们全会上,应该讨论党的生活以及国内外形势的真正的重要问题。这种讨论是自由的、坦率的,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并且是在思想上团结,对各种观点广泛地加以比较的情况下进行的。”戈氏认为,“中央委员会在党内和社会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间这段时期,正是由中央委员会解决对内和对外政策的最重要问题的。中央委员会如何工作,讨论哪些问题,作出哪些决定,中央委员会活动的气氛民主到什么程度,这对于全党和我们整个社会来说都具有重大意义。” 戈氏在谈到中央委员会的作用、权力和责任时指出: “在全会上,必须保证每一个中央委员有权提出问题和参与对这些问题的集体的创造性的讨论。在党内,尤其在中央全会上,不可能有不受批评的人,也不可能没有批评他人权利的人。”
为了使中央委员会真正起到权力实体的作用,苏共在中央委员会设置了有关负责重要决策的委员会,这些委员会成为两次全会闭会期间和全会本身工作的新形式。这样就把党的权力重心由政治局和书记处真正转到中央委员会中来。
但时间不长,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兴奋点开始转移到最高苏维埃体制上,尔后又转移到苏联总统制上;苏共中央因此成了戈氏推行改革的“累赘”,于是戈氏干脆将它抛到一边去了。
戈尔巴乔夫后来为什么不但将苏共中央委员会抛弃了,而且就连苏共这样一个大的执政党也不放在眼里。他的思想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剧烈的变化呢?曾经担任戈尔巴乔夫总统顾问和新闻发言人们安德烈•格拉乔夫在其回忆录《戈尔巴乔夫之谜》中,以《“惟有党不会背叛我”》一章中这样阐述戈尔巴乔夫思想变化的脉络和社会背景:
在官方的改革编年史中,1988年是转折的一年。戈尔巴乔夫本人对此有多种说法。有时他将其说成是第二阶段的开始,“群众集会阶段的结束”,“其时人们都明白体制应予改革,而不是改善。”有时又说得更加坦率:“其实改革是从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开始的。”第一阶段也好,第二阶段也好,毕竟都没有意义,重要的是这一年标志着一个新的界限;与其说是在国内形势的发展方面,倒不如说是在戈尔巴乔夫本人的内心演变上(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至少在初期,“党所开始”的改革是顺从地跟着新的苏共中央总书记走的,有如线跟着孔,他让去哪儿就去哪儿)。
按照他的表白,他与自己的追随者在对于“并不令人宽慰的1987年”进行总结时,他显然已经做好了扔掉列宁指示和语录这副“拐杖”的准备。然而他尚未下定决心彻底离开“马克思主义码头”,开始独立的航行,尽管无法纳入语录的生活愈来愈执着地促使他这样做。据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注: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助理、总统助理)回忆说,有一天戈尔巴乔夫如释重负一般地对他说: “你知道吗,阿纳托利,我又把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哲学笔记》读了一遍。他在那篇文章里并没有拒绝私人所有制啊!”总书记还不敢把这个“发现”告诉政治局委员。
党的“非国家化”,使党的机关摆脱对于国家机关活动的监督,这应当成为新阶段的格言。党在甩掉国家管理和经济管理的职能之后,成了毫无生气的官僚主义机构,按照戈尔巴乔夫的意图,它应当还原自己以政治运动的“活的灵魂”。这位昔日的边疆区委书记、经验丰富的党的干部不会不明白,将苏维埃政权期间像暹罗双生子一样长在一起的党和国家分开无异于冒险,无论其中的党还是国家都经受不起这样的手术。因为除了党委以外,国内实际上再无其他的管理机构。
他应当清楚,试图将这个“党-国家”改头换面,使之像手套一样里子朝外,开始的时候将其变成“国家-党”(戈尔巴乔夫在那个阶段明智地没有提起多党制),在不知为何称之为苏维埃政权长达数十年的一党专政之后,力求将实际权力交给虚无缥缈的苏维埃政权,这就无异于一头扎进问题的汪洋大海,而那些问题当时尚无答案。此外,他有无现实的可能性,去“说服”党的官僚即便不是全部交出自己不受监督的权力、那也同国家机关和经济权力机关分享权力,而且同意通过选举,哪怕事后使权力具有合法的基础呢?因为使机关离开发号施令的阵地,使凝固的官僚结构返回溶化开的状态,就无异于实际上既与斯大林的“圣剑骑士团”章程、也与列宁的“新型政党说”一刀两断,就无异于离开布尔什维克投奔孟什维克,几乎回到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感到自己与其欧洲兄弟有着亲缘关系的时代。
可见,利加乔夫(注: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保守派)说得对,他是很晚才猛然想起,一声惊叹。他发现戈尔巴乔夫“进行了针对马列主义的政变,以社会民主主义取而代之”。失去了国家权力标志,按照戈尔巴乔夫的图纸改造过的党,更像是陶里亚蒂(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和贝林格(法国共产党总书记)的党,而不大像勃列日涅夫、契尔年科或者安德罗波夫的党。区别仅仅在于: 意大利领导人使本国共产党挣脱共产国际十诫的羁绊要比戈尔巴乔夫简单得多,戈尔巴乔夫与他们不同,他有个与国家死死长在一起的僵化的官僚机构。
可是谁知道呢,也许他并未给自己提出这个明知无法达到的目标,他又是在“耍滑头”,打算利用党的机关——国内惟一有效的执行机构的组织资源和行政资源,将其变成苏维埃的、也就是世俗的国家。他自己曾经断言,他想削弱机关,不让这个“怪物”将“职业革命家”的党变成反对改革的反革命势力的堡垒。
在这方面,戈尔巴乔夫又打算遵循列宁的遗训。列宁当初曾经认为可以对资产阶级实行“赎买”,以免发生内战。戈尔巴乔夫打算干列宁没有干成的事,他提出让党的书记兼任地方苏维埃主席的建议,以此来对党的官僚进行“赎买”。这个表面上看来无可非议的建议,其狡诈之处就在于,为了将其付诸实施,只需党的书记干一件小事: 通过选举这一关。于是,1988年他便开始将国家–党这头疑心很重的执拗的骆驼塞进政治民主化的针孔。
(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雅科夫列夫回忆说,早在1985年年底,他就给戈尔巴乔夫写过一篇报告,建议将苏共分成两个党: 一个自由派,一个保守派,均属同一个共产主义联盟。戈尔巴乔夫在看过报告之后说: “早了点儿。” 戈尔巴乔夫当时认为: “在一定的阶段,只有极权主义的党能够对付极权主义的制度。不过,这只有在党的机关阶层仍然支持自己总书记的时候方可办到。”
尽管如此,却仍然没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戈尔巴乔夫当时就企图“利用”党的帮助来摆脱党,并且预先计划好了通过实行总统制完成从党的专政到他个人专政的过渡。另一个政治派别的代表提出的责备也不少,他们说戈尔巴乔夫的长期动摇不定简直无法饶恕,在下定一刀两断的决心之前磨磨蹭蹭,结果是必然又一次坐失良机。
然而,当时是1988年,距离同他所领导的党“离婚”还很遥远,也许总书记完全是真心地认为他有责任向党的大军解释,时代不同了,如今是另一个时代,如果党适应不了这个时代,它就会面临政治上的灾祸。召开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的意图,正是为了进行这次“重大”的党内对话。
作为经验丰富的调音师,戈尔巴乔夫试图做到未来音乐会上所有的乐器都发出和谐的声音。在同自己不久前的同僚——州委第一书记的多次会晤中,他一再地说:“应当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构想的基础上搞出新的法律体系。因为坦率地说,党就是通过非民主的途径将政权据为己有的。后来又通过宪法宣布自己为执政党……我国最大的不守法纪就发生在党委,在州委,那里是第一批违反法律的人……我们党所拥有的这种权力,任何地方都没有,即使在专制制度下也没有。那里的领导人受到私有制的限制。而我们这里限制器只有一个: 我的良心和党性。”
州委书记们闷闷不乐地听着自己上司讲他们本来就知道的道理,在所讲的内容中,他们注意到两条主要的新闻: 一是他们每个人都得通过竞选执行机构首脑的选举;二是他们已经习以为常的官场生涯以两个五年的任期为限。“谁要是特别突出,如果票数够四分之三,可以连任第三个任期。主要是别考虑我如何保住位子,应当考虑国家。”
当然,如果希望那个开始变成既定改革的障碍(这点戈尔巴乔夫已经感觉到了)的党不再考虑自己、只关心国家的事情,那就未免太天真了。然而,戈尔巴乔夫认为,在同实际上自己有理智的一生均属于其中一分子的党彻底分手之前,哪怕是为了摆脱负罪感,他也应该给党一个机会。他本人就与自己党内的同志属于同一血型、具有同样的生活经验,他应该想像得到他们将怎样利用这个机会。
大家记住戈尔巴乔夫总书记的这段话: “在一定的阶段,只有极权主义的党能够对付极权主义的制度。不过,”他补充道: “这只有在党的机关阶层仍然支持自己总书记的时候方可办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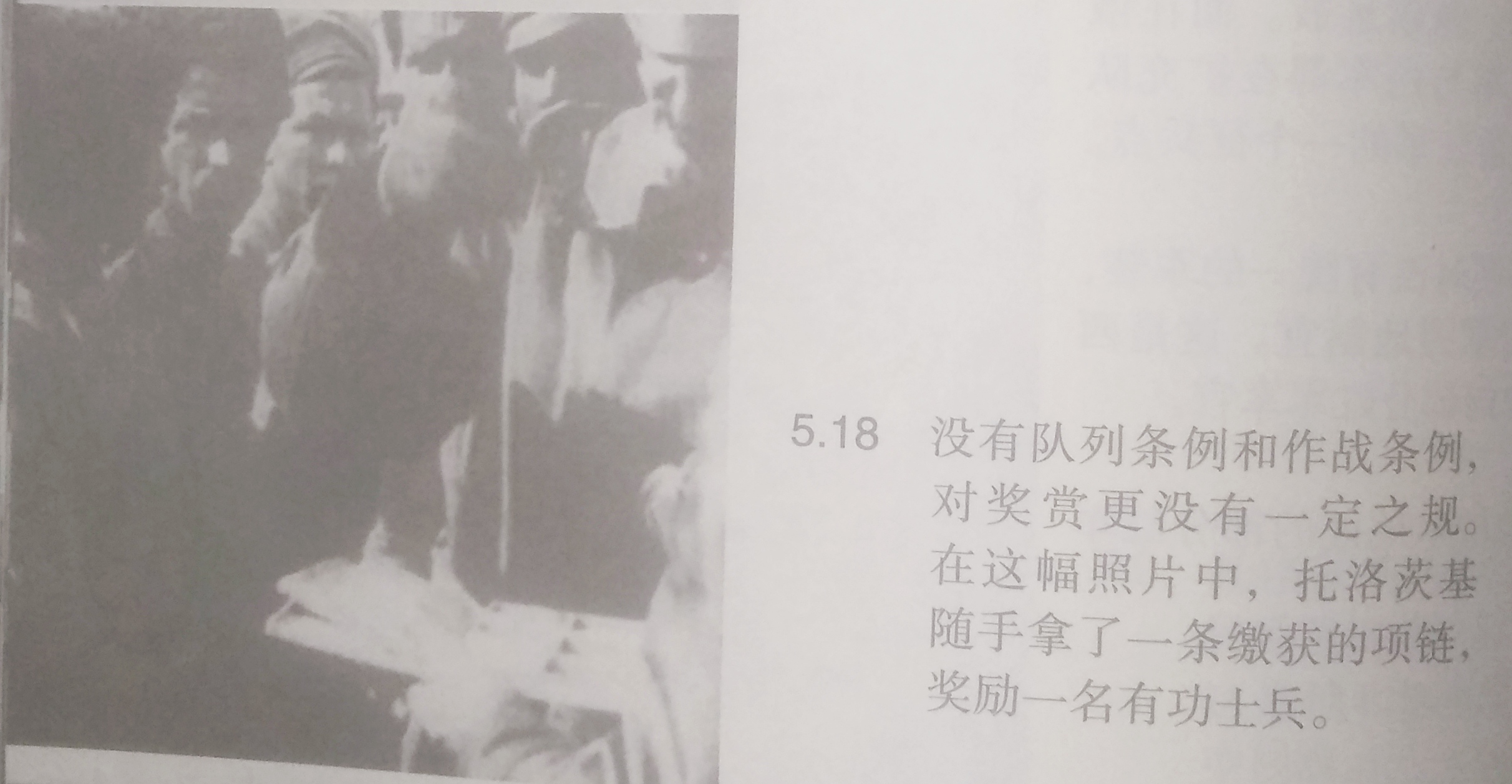
(未完待续)
荀路 2023年4月29日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