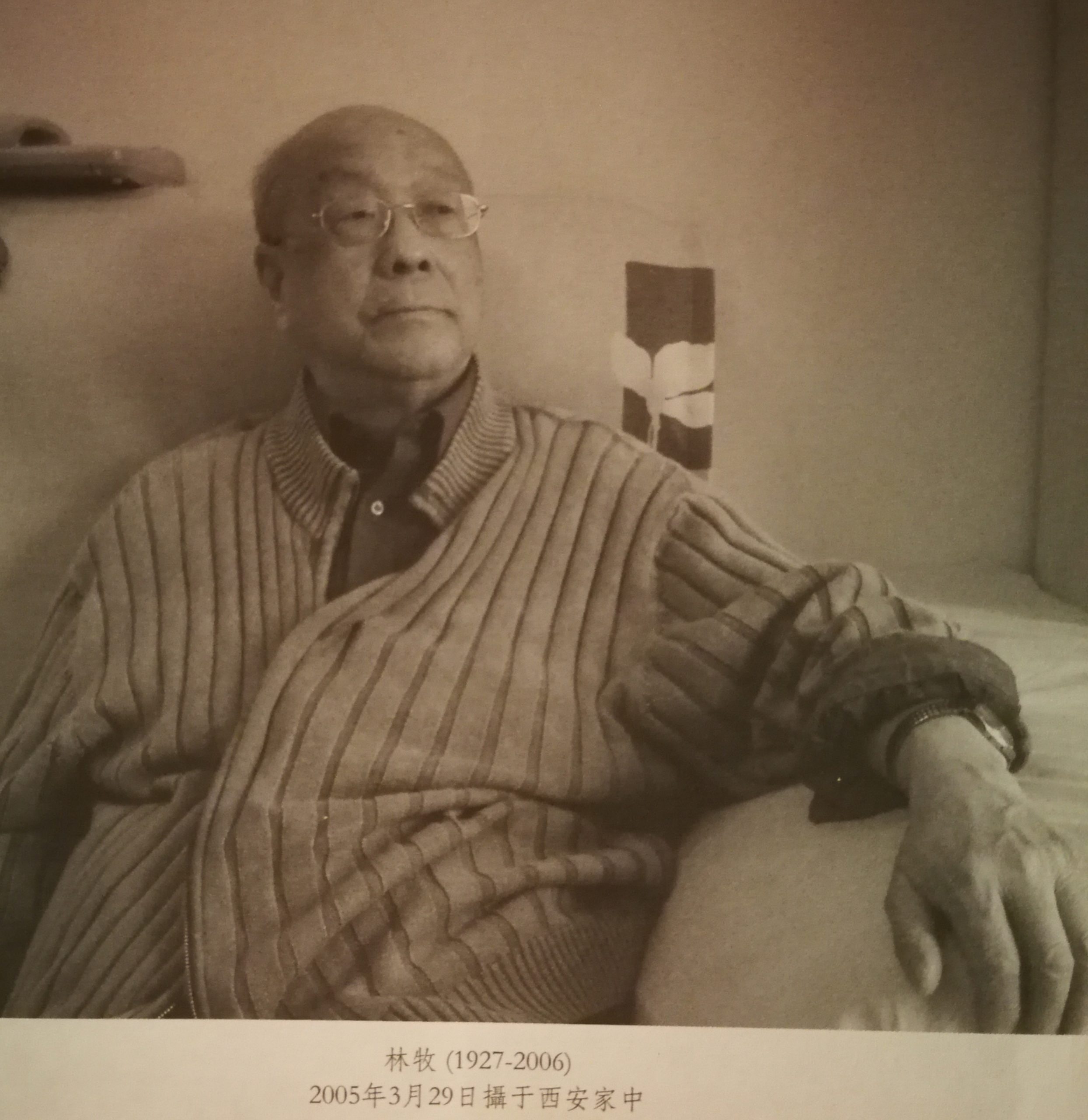二、动荡的学生时代
17岁的同盟会员
一气考上了四所大学
中校军统特务报信使我逃出西安后来也因此给我留下了祸根
逃亡中睡在上海的柏油马路上向巴金求救
我再说自己,我是17岁参加中国民主同盟的,上高二的时候,我不是共产党,当时叫第三条道路,它的纲领只有一个,英美式的民主战争。开始在学校里搞学生运动,我并不活跃,因为我的家庭是国民党家庭,因为那个学生搞活动要选一个,当时叫护校委员会,要赶走反动校长,要保护好的教师,他们要选个主席,我是不问政治的,为什么我被选成主席呢,因为学生选,一般是看成绩,他选高三的,没人干,高三马上毕业了,就要考大学。而高一以下的又带不起头,初中的更不行,一般是高二,选的是学习第一名。我当时是第一名就选成主席了,从此和政治就再也脱离不开了。我父亲也希望我成为个学者。当了学生头头以后,我原来一个中文老师,是东北人,把我发展成民盟会员。
他个人我不太了解。现在也不知道下落了,他反正是民盟会员,我入民盟那就是一句话。后来要抓我们,在国民党的外来派和地方派引起斗争,外来的就是军统,国民党县党部是本地人,是中统,不赞成说:“你不能对付地方士绅,这人是辛亥元老的儿子”,后来就闹到专员那去了,他叫许卓修,是钱大钧的女婿,很能干的人,安徽人,专员还是很有政治手腕,他请安康地区一个最有威望的老人,是前清的翰林,北洋时代旧文学造诣最高的,姓张,也是我的老师,家庭教师嘛。请这个人出面,叫家庭和这些老师们来劝阻我不要再搞这些事情了,张老师跟我谈了,也跟我父亲也谈了。
有一天,安康的专员许卓修,找了一个比较开明的士绅雷英齐(文革中他被枪毙了。西安事变时候,他是杨虎城的独立营长,后来到了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因为杨虎城又被免职回家,回到地方是个绅士)陪他,到我家来了,一看国民党的政客比共产党做工作可是高得多,到我家的客房。我父亲把我找来,是这么说的:“有人检举你在学校领导民盟会,我是不相信的,老先生是党国元老,家庭教育很好,你在学校是高材生,学校教育也很好,我不相信这个事情,以后注意一点,不要干涉校政,你功课很好,马上就要考大学了。”陪同他的雷英奇就插话了:“专员,中国民主同盟是合法单位呀,传桂他就是搞也是合法的,这不是正大光明嘛”。我也不反驳,也不说话。“按你的成绩,考大学你是没有问题的,我们还可以写几封信,推荐一下,西北大学的校长,西北工学院的院长,我们都认识,可以推荐你,地方也有责任推荐。”我知道他也是吹牛,在国民党时代推荐无效,还是应考,你一个小专员你怎么能推荐,除非是在中央组织部,给你设个特务,你不得不收,吹牛是安抚的。这件事情就撂下了。
我担任护校委员会主席,领导学生搞些活动,第一个活动就是反对反动校长,要把他赶走,进步教师优秀教师我们要保护,这都实现了。最大的活动就是响应“一二一”,一般都是大学响应,但是我们那儿就是中学也响应了。
当时安康也没有大学。高中是最高的。安康中学的校长是蒋文廉,中统特务,原来是西大的讲师,注册部主任。他在我们学校发展了六十多个“中统”。我们当时搞的最大的活动就是“一二一”运动,响应“一二一”运动,抗议“一二一”,屠杀进步教师学生。就游了一下行。学校开个会,发个声明。全学校大部分的学生参加了,我领着喊口号嘛:“强烈抗议国民党政府屠杀进步教师和进步学生某某某等”,再就是出墙报,墙报的名字叫“熔炉”,后来作为当时安康日报的副刊,我17岁是安康日报副刊编辑,把学校的报选一部分,在安康日报每周发一期,用“熔炉”做刊名,这期署名的主编就是骆传桂。当时安康报总编辑是安康中学的语文老师。
后来到西安考大学,那就是1946年中学毕业了,我休学一年,有一点病,大概是19岁,考大学那一年算是春风得意,七月份考,八月份发榜,我连考18天。给自己考了四个,替别人代考两个,一共六个,都考中了,还考了个武汉体育学院。我在学校一贯作弊,教育协会都知道。给女同学代考一次,她去贿赂排座位的人,把两个人排在一张桌子上,卷子一发下来就换下来。她答的什么?她胡答,我答的是她的试卷,她是我的同班同学,那时已经名花有主了,是天津人,在中学关系都很好。
这个女同学考的是陕西商业专科学校,后来在北京我们还有来往,她的丈夫不知道,我在北京工作的时候,我的另一个女同学把我带到她家去,她开始没认出来我。那个女同学是北京人:“你连他都不认识?他是替你考大学的”。当时她丈夫在面前,她没跟她丈夫说过作弊考试的事儿。体育学院怎么代人考呢?那个同学给那个对相片的人行了贿,我代他考文化课,他自己考专业,答卷子都是我答,对相片的人一对就不管了,不是那个人不管,这就是旧社会的作弊考试的办法。
我自己考的四所大学是西北大学法律系、西北工学院的电子系、复旦大学外语系、西北农学院水利系。为什么最后选择了上西大?因为西大开学早,西北工学院签的慢一点。我已经在西大法律系报名,前三名公费,西工是机械电器电机全部公费,我在西大法律系,学期维持了一年。我考上西工了,西工开学迟嘛,第二学年人家查出来了,不许跨校。
当时的想法不想过问政治,将来当个工程师,有保障了,当时工程师很好,大概一个人毕业的时候有几种选择,有几个单位要你,原来以为不问政治,后来不是这样,确实不想过问政治,就想当个工程师,以后还可以研究学问。
上了学校以后就不成了,工学院闹得更厉害,成天抗议,反内战,反饥饿,而且这个反内战是两面都反,对国共两党的内战都反,并不全都是共产党领导的,一个是自发的,从成员来看,民盟占多数,学生会主席,正职是民盟,副职是地下党,可他不暴露,一到游行示威的时候,打旗帜的站在前排的是民盟的,地下党是不暴露的,民盟都是公开的。反内战运动的中心在南京中央大学,地下学联也在南京,也在中央大学,中央大学的学生会主席叫梅振乾,后来也是地下学联的主席,南洋华侨,民主同盟,中央大学经济系四年级学生,副主席叫王世德,湖南大学的,梅振乾这个人被埋没了,因为他是民主同盟,反右派时自杀了。他解放后在南京银行,没有什么重要工作,地下党都当官了,他就是银行的一般职员。
反内战运动在西北是西工院带头的,持续时间最长,罢课时间也最长,我不是头头,我是印宣言传单,用油印机。后来地下学联决定,47年6月2号全国总罢课,当然国民党就知道了,国民党决定由6月2号零点开始全国抓人,叫你搞不成。6月1号天快黑了,我在西安,当时西工一年级有个建筑公园,现在是个中学,原来是西工分院,就是一年级和兼修班,二年级以上都在咸阳。我有个同乡叫李梦彪,他是国民党的国大代表,和胡宗南也有关系吧,他开个商行,又搞政治活动,中央代表当然搞政治活动,我常到他那儿去。陕南有些人也常到他那儿去,他的家比较富裕,来了就吃饭嘛。有一天胡宗南的长官部有一个上校参谋张宏谟,他是军统特务,原来是安康县党部的书记长,到他家去,说是今晚上零点全国抓人,我看到名单有你,你赶紧走,我说我得回去拿点衣服,带点路费,我身上没钱,他说:不能回去,你回去各个学校一通知,我们一个人都抓不到,都掉脑袋了,马上得走。就这样,我想办法通知了几个人,连我一共六个。
我通知几个中学生,还告诉几个大学生,我的同学只通知到一个,就是戴杰,山东人,他逃了以后,又考了清华,后来是北京市人大常委副主任。现在退了,七十多了嘛,原来他就是搞工会,后来提拔专业人才提拔成北京市委组织部长、常委、人大副主任。我通知的大学生只有这一个,其余都是中学生,当时没路费嘛,那个军统特务张洪谟说:我看我身上有没有,掏一掏没带钱,把戒指取下来说:上火车不要走车站正门,我给你指路,从道北铁索缺口钻进去,如果查票你跟他说,我没钱,到郑州下去把这换了,给你补票。这个特务关系,纠缠了多年。
后来我的朋友检举了我和张宏谟的关系,我的这个朋友是西工一年级学生,他是水利系,我们还是同乡。52年检举了我的这层“军统”关系。后来查了好多年,再后来找到军统的这个为我报信的人,他在西安交大附近的劳改皮鞋厂做皮鞋,大概经过几次提审,这个人都说的是实话:和林牧本人没政治关系,他父亲救过我,对我们家都有恩,我是报恩。而且那个劳改单位写的是这个人劳改表现很好,判的是无期徒刑。他后来是病死的,不病死可能减刑。国民党把人情没有摧毁,共产党把人情摧毁了。
我从郑州换了戒指,大概四千多吧,从郑州逃到南京,住到中央大学,住日本式的那种木头房子,夏天热得要死,后来从中大又逃到上海复旦。
在中央大学我接触的都是些搞学生运动的,民主同盟的人。同时还有同乡是地下党,叫王天敏,后来也死得很惨,他的外号叫“毛泽东的干儿子”。他在中央红得很,共产党的旗帜举得很高,反右派的时候死得很惨。王天敏原来是我中学的同班同学,他是陕南人,功课很好,他在中央大学水利系,解放后起先是治淮工程指挥部,后来是治黄工程指挥部计划处处长,管一大堆人,又是工程师,后来打成右派,而且是强劳,就在铁路边砸石子,黄委会在郑州,劳改不是劳教,强劳,那是比较重的,他给我写过信,让我到北京开会,从郑州路过某些地方的时候,给他带点吃的,他饿得不行。
我找过他,但没找到,他在铁路沿线砸石头,后来病死了,他的妻子也很惨,武汉水利学院的学生,国民党军官的女儿,他是极右分子,他妻子也受到牵连,工程师也被开除了,生活无着,她是湖南人,嫁了个农民,以后她又跟那个农民离婚了,带着她的儿子回到她丈夫的家乡劳动,一直到三中全会以后才来找我,我就给她找工作,我想水利工程师找个工作也不难,也不计较右派什么的。给水利厅写信,给水利厅打招呼,把这个女的用一下,原来是个水利工程师,但是水利厅一看是个老太婆,因为受折磨,年纪比我大。三中全会以后,我都五十一二了,她五十四五了,一看是个老太婆,人家不要,最后又回去了。
我在复旦大学还是很有趣,住在教师家里,国民党政府发现了内地有一批学生跑到上海,给上海大学下命令,不许收留外地学生,出了布告,复旦大学也只能把我们赶走,后来同学给我出个主意,你就明走暗不走,复旦住的也是日本式的木头房子,上面一层楼是不住人的,你把行李捆起来放到楼上去,人就跑出来,什么时候进去呢,晚上零点以后,我们就在马路上睡着坐着,大伏天睡到柏油马路上,一直睡到零点以后,复旦的传达一招手我们就从窗户跳进来,回到原来宿舍把行李从楼上拿下来打开睡觉,天一亮又把行李放到楼上又走。
吃饭怎么吃?我们六个人,三个人倒班,三个人去吃,然后三个人再去,第二批去,菜都是残羹剩饭了,这在上海当时都登了报了。苏州路桥,人力车上苏州路桥很陡,后面要有人推,推到桥顶,太太老爷们给丢几个钱,就干这个,结果干着干着又不行了。挨打,上海的流氓鳖三打,抢了他们的生意,后来在上海都登了报,大学生推洋车,被鳖三痛打。
后来就是三伏天睡柏油马路,很有热度,我内科外科都得病了,内科大概是虐疾,忽冷忽热,外科就是屁股上长了这么大个疮,七天七夜没有吃一点东西,也没有拉一点东西。后来同屋的同学,见我稍微好一点,把我拉到虹口一个红十字会医院,在那儿看病,来一个像护士长的高个女的,三十来岁吧。“我看你那样子,好像是学生吧。”我说是。“这个病要开刀,你有钱没有?”我说没钱,我是逃难来的。“我们是红十字会医院,我们商量一下看能不能给你免费。”
后来商量了免费,割了那个大的脓包,还有内科的都免费。这中间还有点插曲,我想在那儿找点饭碗,只有两个人可以找,一个是巴金,再一个找储安平,我是储安平的老读者,也通过信,他当时不是民主同盟的,他是无党派。能不能给我找点工作,当个校对嘛,他在书店卖书,三联书店嘛。储说,你先回去,我给你想想办法,后来我就回到复旦,他回信给我说,现在内地来上海的学生很多,像你这样的情况也很多,我很想帮忙,但是爱莫能助。后来因为这个事情,审查的时候查出来了,跟储安平的关系是怎么怎么。
那时写自传都是非常忠实的,什么都写。到上海逃了一趟,共产党最注意的,他们叫革命活动,我们叫民主活动,搞这种活动受打击以后的表现,看你是不是叛徒,逃难时查得很严的,都接触过什么人。
起先当然没问题,反右以后就查跟储安平的关系,到文革连巴金都捎上了,说我参加了巴金的无政府主义组织,我找巴金都没找到,而且巴金当时已经不是无政府主义了。储安平倒是见面了,不给我帮忙,我很有气:你算一个什么进步人士?后来我就想,能不能想办法介绍我们到新加坡找找民主同盟的胡愈之先生,一点路费没有,没办法,要有路费就好办,不要他推荐。
那时候坚决不到解放区去,从上海病好以后,上海也没什么希望了,往武汉走,轮船买了一个四等仓,就是没有仓,是个过道,到了武汉,找同学,住下来,也没什么办法。后来又接到西工同学的来信:你现在可以回西安了,不追究了。国民党时代就是这样,风头上抓你,就是叫你闹不起来。1947年9月回来上课了,到11月,国民党解散民主同盟,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组织,把张澜和罗隆基在上海软禁了。蒋介石下了命令以后,叫张澜宣布解散民盟,张澜宣布了,民盟中央在香港开会的时候,宣布张澜是叛徒,重新选举主席,我们是下边的人,我们跑不到香港去呀,唯一的地方是跑到解放区,因为民盟没有实力呀。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