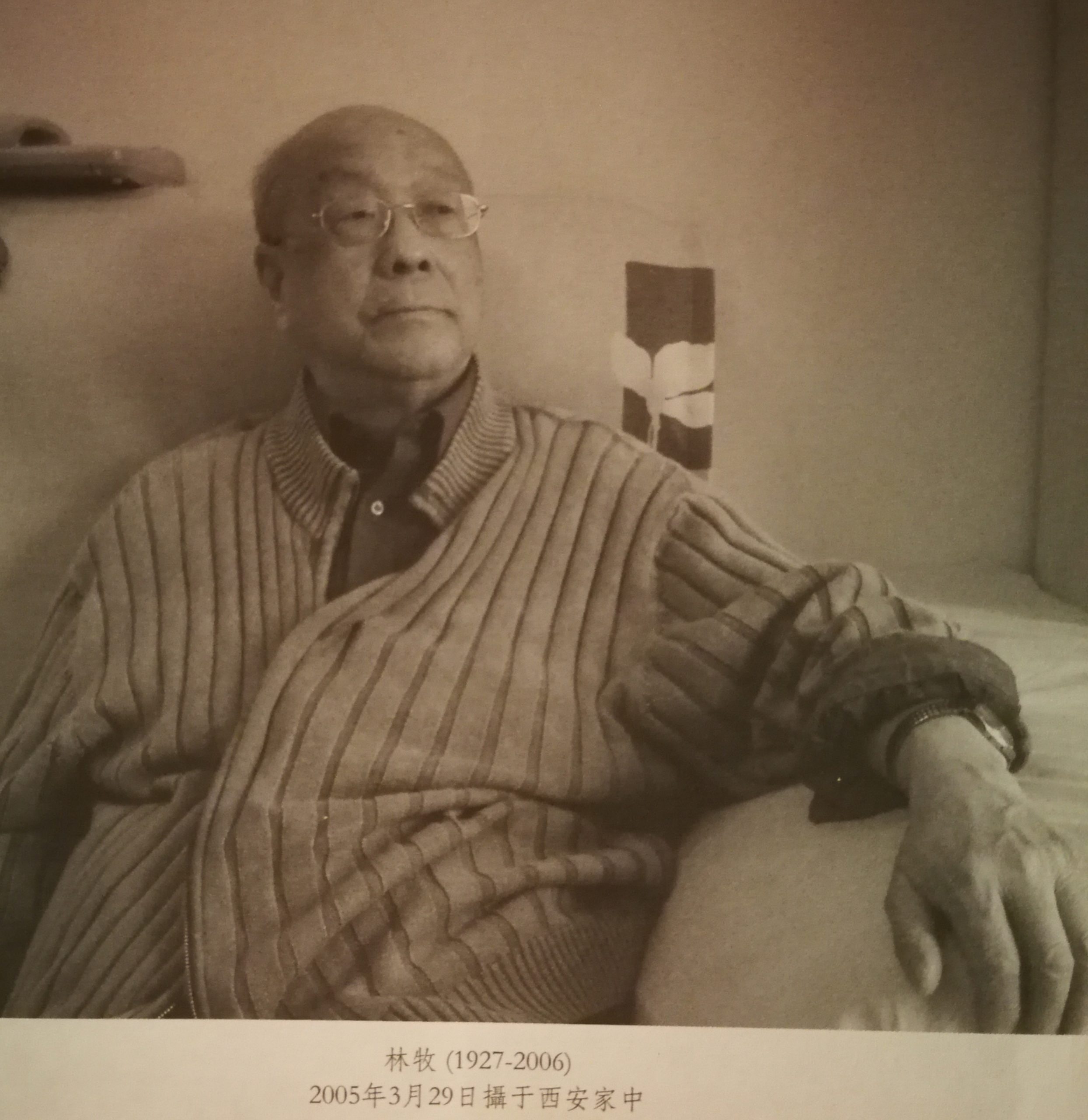八、我在两次学生运动中
我说:出了事我负责,敞开学校大门,让学生上街游行,那会是党委书记负责制
“六·四”前夕耀邦周围的人提出过“逼邓保赵打陈”的六字方针
汪峰亲口对我讲:杨尚昆说调军队不会对付学生
我在天安门广场发表声明的前天晚上梦见第一任教育部长张奚若对我讲了四个字:保护学生!
我没有违心检讨,最后一次被开除出党
到了10月6号,就碰上了学生运动,矛盾又上来,原来的校长,张启之很能干,也有学问。当时是校长负责制,我就不干什么事儿了,后来又恢复了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再后来就碰到十月份的学生运动。主题是反对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抵制日货,因为中日贸易逆差。另外要求国内还要反对太子党、反对任人为亲等。
李鹏发表讲话:要求大学生尽量不要出校门,各学校要承担自己的责任,把自己的学生都管理好,张启之也不愿意压学生,他的思想并不保守,他不愿意压学生,但是他怕负责任,跑了没人负责了。
我就负责了,我就说敞开大门放学生出去。叫青年教师和学生会干部,不要呼反动口号,不要搞打砸抢,不要叫人抓辫子,秩序好一点。西大学生到西工大找西工大的学生,西工大的大门进不去,后来学生都是翻门出来的。
后来教委就来施加压力,我说:这是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来人就把我告了,陕西省委派了个抓文教的常委,原来是交大的,来参加西大党委会,讨论这件事情。我当时讲了,这次的学生是我发动的,如果说学生有什么问题,都在我身上,由我一人承担。公安厅定的西大的三张反动大字报是错误的,不就是画了个彭真给日本天皇深深鞠躬嘛,另外一个是给胡耀邦提意见,胡耀邦在日本轻率地邀请日本三千青年到中国访问,结果人家到中国来胡闹了一阵,并没有邀请中国青年回访,对中国很没礼貌。还有一条意见,画了个北洋军阀的像,对学生说:你们好好读书,不要干涉国家大事。
我说这三张都不算。给胡耀邦和彭真同志提意见,宪法和党章有规定,对任何人都可以提意见,为什么对总书记和人大委员长就不能提意见呢,而且学生提意见是很有礼貌的,提你的官衔,叫胡耀邦总书记,彭真委员长,这算什么反动呢。要不我来跟耀邦说,学生给他提意见是不是反动,画北洋军阀,我们现在又不是北洋军阀嘛。我针对那个省委常委讲:只要我在西大当一天党委书记,就不许任何人到西大来压制学生,不许来撕学生的大字报,大字报可以动员学生自己撕毁,不许别人撕毁。我现在就要讲党委的一元化领导,然后又在干部教师大会上宣布,参加游行,甚至带头游行的学生不许追究责任,责任都在我身上。后来他们说全国只有这一家,然后我就开始辞职,十一月辞职,十二月又辞职,一个月写一次,始终没有批,一月份我就自动离职了。
当时辞职的原因就是为了学生运动。我不能执行现在这一套政策,我无力执行现在对待学生的政策嘛。自动离职后,我就住在军区的干休所,不管事了。西大不少著名的教授们一再登门劝我,千万不要离开呀,西大还得靠你,可我决定真的不干了。
后来我和西大几个教师、学生编了一套《中国通俗丛书》,一共编了三十几本,在西安和台北都出版了。
期间还办了个公司,失败了。也是用人不好,都是学校的那些中层干部。
87年、88年我都是在编书,公司是88年办的。
这就到89年了,我为什么到北京去呢,5月初,中国党史研究室和党史资料出版社,跟陕西省委联系,要赶七一前出一本纪念耀邦的书,他们要邀请我去干,陕西省委叫办公厅通知,我就去了。
开始我对学生们的那个运动还没介入,忙着编书,组织了那么一帮耀邦的老下级写文章。我自己也写,一方面编,一方面写,很快到了5月17号就编完了,书印出来了,在库房放着不许发行,六四以后就更不许发行。当时还不是说因为耀邦的事不许发行,因为参加编书的一批人参加六四了。
编书的间隙,晚上我也看看熟人,有一天到耀邦的老秘书戴云家里,耀邦的一些部下在那儿聚会,他们说你来迟了,我们对于平息这次事件,商量过六个字:逼邓保赵打陈。陈包括李鹏、姚一林等,我说你怎么能保赵呢,赵紫阳这个人两次对不起耀邦,他是个滑头。那些人说,你这样子想就不对了,现在耀邦死了,你不保赵谁来主持革命大局,只有他才能把这个事业继续,逼邓是不能反邓,只能逼,就像当年张杨提的逼蒋抗日一样,没有说反蒋抗日。邓不能反,只能逼,逼得他保赵,打李鹏、姚一林一伙,我说这样子我接受。
当时主要的人有耀邦的大秘书,后来是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还有耀邦周围的人,其实我也没起什么作用。
那是5月10号,还是11号,在静坐绝食前嘛。
我开始跟李洪林也没联系,顾不上。大概到了13号,我给李洪林打了个电话,我说我来给耀邦编书,住在招待所,他说戴晴搞了个组织签名,看你参加不参加,就是那个十二人签名。我说我没功夫来看,我不看也不好随便签名,我说都有谁参加,第一个是严家其,第三个就是戴晴,最后两名是李泽厚和刘再复,签名分先后,一个是我没看到,你叫我签不是成了第十三个了嘛(犹大),这我不干。再后来就是五一六会议,是人民日报理论部文艺部通知我的,理论部主任很老资格,我没去,十二个人签名,我没签名还说了句话,等我把我这个书编好了,我自己发表声明。书大致上编好了,就是16号,就交给中宣部了。我是17号上天安门的,我发的声明上写的是5月18号,写错了,应该是17号。
那天晚上我又做了个怪梦,我这个人怪得很,碰到大事就做怪梦。梦见谁了呢?张奚若,他是第一任教育部长,也是陕西人,以前我见过他的,梦中他跟我说了四个字:保护学生。然后很愤慨的用手一指,墙角就留下一个指印。
第二天我就上天安门了,我住在厂桥,穿过北海公园,北海公园敞开大门也不卖票,中山公园都是敞开大门。我步行去的,找李洪林联系,他在前门东大街,住在12楼,李洪林老婆在历史博物馆工作,她是专门给学生送水,李洪林他们很高兴:这下邓小平完蛋了,起码他的政治生命没了。我说恐怕不一定吧,军队的态度怎么样?军队没问题,三十八军军长拒绝清场,谁愿意冒这个天下大不韪。
我说:军队很难说,其他人很难说,我出来在天安门那儿转,遇到最精彩的游行队伍是新闻界,自己骂自己:人民日报胡说八道!中央电台颠倒黑白!我们再不愿欺骗人民了。再就是银行队伍,海外存款,铁证如山。四川人的游行队伍是“小平同志,四川人欢迎你告老还乡。”再就是首钢的标语尖锐得骂邓小平:小平、紫阳你还不动手!
我在那儿站一会儿,后来我就想看看绝食学生,往北大校区那边挤,挤不进去,一个北大学生不知道姓名,在那儿谈了谈,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是西大的,他说你是什么态度,我说坚决支持你们。你准备讲呢,还是怎么样?我说:我写。
然后我就在中山公园外边栏杆上坐下,学生给我纸,我花了一个小时写了两千字的声明。事后西大中文系的教师说:你那是传世之作,你不到现场你写不出来,今后恐怕也写不出来。写完后我就交给学生了,外电都播了,报纸上转载只有台湾。
随后我还在招待所住了几天,新认识了一些我过去不认识的人。5月21号,已经开始戒严了,军队介入。汪峰到招待所来看别人,顺便也看我一下,对耀邦过去的秘书表示关心,我就问他:汪老,中央怎么这样搞(调军队)?汪峰说:不要紧,出兵戒严不过是把学生控制住,不要发生大的问题,幸好现在没发生什么大问题。你放心,绝不会开枪。我说汪老你这个话,是从杨尚昆那听来的?他说:是的。因为他跟杨尚昆关系密切,当年到陕北他最早接触的红军干部就是杨尚昆,杨尚昆是长征先遣队队长,汪峰当时是副政委,他跟杨尚昆关系很密切。他说是的,我就放心了。后来家里打电话说台湾我的表孙女在西安等了我九天,要和我见一面。我请她到北京来,电话里她说北京路不通,只有你买飞机票回来,要不他们不能再等了。我在5月22号买的飞机票回到西安,和台湾来的亲戚聚会了两天,把他们送走。我又离开西安,这时已进不去北京了,那就25号了,我就转到了襄樊住着。准备绕武汉再到北京,去不成了,武汉车也不通了,武汉大学正在卧轨,实际上没有卧轨,是坐轨,连湖北大学校长也跟着坐轨,到那儿也不能动了。5月26号到的襄樊,从襄樊转到南阳油田了,我的外甥一家都在南阳油田,然后六四就发生了。
如果我不离开北京,肯定跟他们那一伙一起出国,后来他们在报纸上搞了个变相的通缉令,《中国法制报》、《经济日报》上都刊明:林牧在华伟集团公司有经济问题,速回来交待云云。后来正式通缉没通过。
在南阳有天晚上来了个政法干部,三十出头吧,他来跟我谈了谈,表示很同情,就说:我们欢迎你到我家里住,我用全家的生命保证你的安全。他父亲也是个地区干部,级别比较低。他还说:我的家就是陈胜的家乡,豫东太康县。
第二天就给我把票买了,买的到太康县的票。我在南阳油田的亲戚朋友,原来都同意到太康县去,晚上他们一商量:太康县是农村,很封闭,消息不灵通,而且你一个人,家里人从来不认识,这个人看来没问题是真心,可人家家里人,住时间长了,是不是很讨厌。现在你只能往南走,就是往出走,先回老家金华。
从南阳出发到浙江,路上查得很严,一到站武警就上车了,拿着相片对,肯定没我的相片,我不是被公开通缉者。我坐在乘务员席上,到了金华。金华这家人同我们并无血缘关系,可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现在已经和亲戚一样来往了。这家“亲戚”无微不至的关心和保护我。金华住的时间不长,又去杭州,杭州又住了几个月,为什么长期寄留在金华?火车不通。我起先想从金华转到广州,转广州就给《花城》的主编写了个信,说我想到你那儿去住几天,结果这老兄根本不回信。我又给广西师大桂林的老教授写信,说想到你们那儿去看看,他们都知道了,给我回了信,桂林离金华很近,说是桂林天气酷热,不利避暑。后来还想到海南找李晓东,西大历史系博士,跟我的儿子差不多。结果李晓东由于领学生游行被海南通缉,跑回西安了。
后来想在福建晋江一带找一个船,从台湾转走。结果又没弄成,根本走不成了。有段时间上当的不少,李小东在海南被学生骗了,说给他找好了船,结果一到海滩就被抓了。在看守所关了半年才出来。
我在杭州时,经常跑出去,也没人告密,要抓我的人他们始终不知道我在哪儿。一直到了1990年春节,我才决定回西安,你要抓就抓,春节后我就回了西安,一个私营企业接待了我,后来又把我转到化工厂。后来我干脆公开的回来。张保庆他们知道了,大概是4月份吧,叫原来省政府秘书长张振西把我约出去到一个咖啡馆谈了一回。因为我回来没有公开露面,张保庆找他谈:老林的问题说严重严重,说简单也简单,又没抓到他的手稿,几句话就完了。张保庆所以这么搞,由于上面有压力,一个是省委第一书记给他写了信:对林牧同志的问题,你们不要做得过头。汪峰的信是:对林牧同志,你们不要小题大做。
我敢做敢当,我做好事,又不是做坏事嘛,大概在1990年的5月8号,我给西大党委会和陕西省委写了一封信,大概这样几条:1989年5月18日,我在天安门发表的公开声明,是我经过深思熟虑的由衷之语,从起草、印发和传播,我承担全部政治责任,我不做违心的检讨,让历史去做出结论。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