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137)
赤色帝国覆亡之谜(90)
比亚勒在谈到苏联民众的参政情况时把苏共的组织状况也包含在内了。他说:
提出一个关于苏联人民参政的基本形式是比较容易的。卷入苏联人民参政的各界公民人数非常引人注目。先说党的组织,1978年,苏共拥有1638万党员,其中65.8万人是候补党员。而1964年这个党有1150万党员,这就是说,党员的人数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增加了42.4%。现在,女党员达到410.6万人,占党员总数的25%。目前,在(十月)革命前入党的只剩489人,在革命期间入党的只剩下2370人。如果说目前有12%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入党的话,那么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则是过去十年中入党的。
苏共有390387个基层党组织。1976年,从事宣传工作的干部有222.1万人,其中4.8%是专职的党、共青团和工会的工作者。此外,在苏联还有370万宣传鼓动员,其中180万人定期汇报政治情况。
苏维埃系统包括50561个基层单位,这些单位有210万名苏维埃代表,其中56.1%是非党人士。在这些代表中,工人和农民占总数的67.7%。在这些苏维埃中,设立了许多常设委员会,分别负责专门的监督工作;70%以上的苏维埃代表是这些委员会的成员。
苏联的工会有会员1.07亿,组成了688600个基层组织。它们由25104个理事会和委员会领导。共产主义青年团有3482.6万名团员,有177.9万个基层组织。青年工人占团员总数的57.3%。约有七百万人是所谓的工人纠察队——民兵辅助组织成员。
在乡村,最引人注目的组织是集体农庄理事会。在现在的2417个理事会里,有12.5万名集体农庄和农业组织的代表,其中6.4万人是集体农庄的普通庄员。此外,全国还有无数其他组织,诸如劳工科学组织和全苏发明家合理化建议者协会等,大约有几千万名成员。
这些数字意味着什么?它们在公民与政府联系方面能告诉我们什么呢?
首先,尽管数字很大,我们却不应被它所迷惑,认为绝大多数苏联公民都积极参与了“低级政治”。在苏联这种参与都是罕见、偶然而且可能是表面的活动。然而,人们也不应当忽视,参加这些活动的各种人确实有些人是比较积极的参加者。而且在各种活动中,积极参加的阶层还有部分重叠现象。
第二,被卷入或者参加的类型的意义也不是一样大的。实际上人们都知道,负责管理苏维埃代表机关、特别是全苏或加盟共和国一级的代表机关的活动,是有着一种合法化和自我维护的意义的。人们也知道,投票一事几乎没有什么意义,并不是什么激动人心、正规的和起作用的授权行动。
在人民参政的所有形式中,党员的参政形式显然是最重要的。党的活动的强大体制是整个参政系统的脊梁,归根结底是党的控制。
党员要定期参加党组织的会议,讨论高级政治和低级政治问题,定期参加党的思想教育学习。但是,重要的是,作为党员,就要担负起“社会政治义务”,就是要担负起一项经常的比较积极的任务,不仅要向党员、而且主要要向非党群众做工作,解释宣传党的观点。党组织的领导人对每个党员,都要根据他们的具体情况分配任务。这样的任务非常广泛,例如让一名党的新闻工作者到一个工厂做报告,让一名工人党员检查当地食堂的情况等。
我们这里试图要说明的是,作为党员,即使没有得到像占有行政职位的人所得到的权力,也会使人产生他是属于那个掌权组织的感觉,产生一种参加党是一种特权的感觉。这就是说,党员资格会产生一种与这种制度有着利害关系的意识。
比亚勒在上文介绍了苏共组织结构问题,接着这个话题我谈谈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的党建问题。
从1964年10月到1982年11月,勃列日涅夫一直是苏共最高领导人。但是,从这个时期苏共党的建设看,无论是党的建设思想还是建设实践都没有什么建树。如果说这个时期苏共党的建设有什么特点的话,那就是勃列日涅夫既吸取了斯大林时期搞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的教训,也放弃了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尝试,从而使苏共的党建模式日趋平稳和固化。经过长达18年的沉淀,苏共党建模式的积弊暴露无遗。人们在分析苏共瓦解的原因时,多是把视线放在戈尔巴乔夫身上,忽略了勃列日涅夫时期。而勃氏时期的苏共党建问题多多,应该深入探讨。
勃列日涅夫上台执政,继承的是在苏共历史上争议颇多的前任——斯大林和赫鲁晓夫的事业。由于赫氏对斯大林的批判在苏共党内和国际共运中引发的双重效应,正如毛泽东所说“揭了盖子,又捅了漏子”,以及赫氏不得法的改革尝试在苏共党内引起的强烈不满,从而使勃氏时期的党建思想和实践趋于保守和僵化。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这个时期继续沿用了赫鲁晓夫时期提出的全民党理论,同时对其进行了修正,使之更合乎传统的党建理论原则。最突出的是重新强调党的阶级性和先进性。
赫氏时期着力强调党的全民性,其意图在于改变党的活动方式,使之更具有开放性。勃氏上任后,一方面接过了赫氏全民党的口号,另一方面则在有关社会结构的分析和党的性质的论述中,致力于回归正统,反复强调工人阶级的主导地位和党的阶级性和先进性,强调党的全民性与阶级性的统一,并且总是把它们与党的领导地位和领导作用联系在一起。表面上看,这种理论较之赫氏时期既合乎传统的党建理论,又有时代感。但实际上这种理论脱离了苏联社会的实际状况,忽略了不同阶级或阶层的利益要求。所谓“在发达社会主义条件下,所有其他阶级和社会集团都接受了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和达到了工人阶级的水平”;“所有其他劳动阶级和集团,全体人民都转到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立场上来,接受党的思想、目标和纲领”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这种不合实际的理论,加上苏共高度集权体制模式的运转,加剧了党的职能与结构以及运行机制的矛盾和冲突,使苏共很难顺利地完成现代政党的一项重要功能,即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功能。
第二,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党建思想和实践与赫鲁晓夫时期相比,其显著特征是求稳抑变。
从赫氏和勃氏的作为看,如果说赫氏已经感受到了斯大林党建模式的弊病,并试图寻找病源,尝试医治,只是不能对症下药的话,那么勃氏则连探寻病源的主观愿望也没有,他所做的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缓解一下病痛而已。因此,勃氏时期不是针对斯大林党建模式的弊端和时代的发展需要,进行有效的改革,而是把苏共的党建方式和活动方式简单地从赫氏时期的有限改革中,使之法律化、制度化,从而使未被触动本质的斯大林模式以平稳的形式凝固了。比如:
为了加强苏共的领导地位和作用,勃氏上台后,苏共中央立即纠正了赫氏按生产原则把党分为工业党和农业党的做法,迅速恢复了过去按行政区划组织州、边疆区党委的做法。党和政府机构不再自上而下地分为工业和农业两部分。各级经济委员会和大多数全国委员会均被撤销,重新建立起更合乎传统的政府各部;并且在党中央设立了相关的部、局,数目比斯大林时期还多,有些部连名称都与政府部门相同,如农业部、建筑部、化学工业部、能源工业部等等,并把此举看成是“在建立各级党的机关方面恢复了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
勃氏为加强苏共的领导地位和作用所做的另一件事情是,在1977年通过的新宪法中,第一次用法律形式规定了苏共的领导地位。苏联宪法第六条规定: “苏联CP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是苏联社会政治制度以及国家和社会组织的核心。苏共为人民而存在,并为人民服务。” 勃列日涅夫在他所作的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说: “在制定草案时,我们立足于宪法的继承性,保持和发扬了列宁指出的社会主义宪法的特点。” 但事实是在列宁经手的1918年和1924年两部宪法中,从来没把党作为一种政权力量写进去。即使是斯大林经手的1936年宪法也没有明确规定苏共的领导地位。由于在过去的苏维埃宪法中从未有过这种传统可以继承,结果使得这个宪法第六条,不仅成了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抨击苏共搞一党专政法律化的口实,而且成为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反对派针对苏共的万箭齐射的靶子。
比亚勒在其著作中表达出苏共党员大都信服苏共是执政组织的论调后,又对苏共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及作用进行如下分析:
如果说党员资格确实能使人们忠于这种制度的话,那么研究一下党员在苏联社会及其各阶层中的相对比重则非常重要。我在这里只列举一些最有说服力的指数和有限的数据。苏共党员占苏联成年人总数的9.3%。一份统计材料表明,30岁以上,至少受过十年制教育的苏联公民中,党员大约占27%。几乎三分之一的完成高等学业的人是党员。在国民经济部门中工业的受过高等和中等教育的专业人才,三分之一以上是党员。
现在出现的这种现象,显然不是当年一群微不足道的骨干集团淹没在苏联人海之中的景象了。正是这种强大的、政治化的和被卷入的阶层的存在,成了这种制度在社会内部的合法性支柱。
无论如何,人们可以有把握地断言,非党群众积极地参加党务方面的活动的程度一般是要低于党员的。尽管如此,还是有千百万公民积极分子参加了他们所在街道、工作单位的政治活动。
一方面是苏联的参政制度,另一方面则是苏联新闻制度的封闭性和大规模的有倾向的宣传,这造成了我们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的一种现象: 在苏联,并不存在两种不同的政治教养(一种是社会骨干的,另一种是人民的)。而居统治地位的政治教育,既为社会骨干所接受,也为大多数人民所接受。
我已经设想,广大阶层的群众,实际上都已表明他们与苏联制度基本保持一致。而这种一致很大程度上是不知不觉和无形散漫的。所以,我不是说这就表明人们要为这种制度承担义务,准备投入自己的力量。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种接受,充其量也只是一种伴随着大量旷工、不遵守劳动纪律等消极行为的接受。所有这些行为,都说明他们对许多政策的不满,而最重要的是,这些行为说明劳动人民个人最关心的是他们自己的福利。真正有意义的是,对政治的漠不关心,即只关心“我到底能捞到什么”,而对抽象的正义和平等不闻不问,而且漠不关心又与基本上接受政权的政治公式同时并行,这就意识着一种可能得到承认的合法化的基础,而这个基础对这种制度的领导人来说是没有理由感到满意的。
现有的有关证据表明,各个政权在各集团和个人中合法化的程度,与这些集团和个人参加政治活动和管理社会事务的程度之间有直接关系。而且在现代社会,大部分合法化的问题,都与一些决策机构(而不是个人)的合法性有关,也就是说,拥有要求具体个人、集体和集团等采取某种同意行动的权利有关。这里主要的问题是,什么是使这些要求得到实现的决定性因素。我这里完全同意阿瑟.斯廷奇孔布的论点,其关键在于这些要求在其他权力中心的合法性,而不是它们在应当承担其后果的人民当中的合法性。
一种合法的权力或权威,必须以一系列后备权力源泉为后盾,这种权力源泉要建立在那种经常能够战胜反对派的权力上。各种合法性主张和从这些主张派生出来的准则的关键性作用,是使其他权力中心随时准备支持一个拥有某种权利的人的行动。一种权力的合法程度,要看掌权者能否依靠支持其政权的主张和准则,号召足够的其他权力中心作为必要时的后备力量,使其权力行之有效。这些后备力量,可能表现为一个人的权力在公众舆论中赢得的声望,或者表现为他的权力合法性的主张得到他的国民的承认。
我认为,共产党社会、专制社会以及民主社会的经验证明,政权在骨干中合法化的程度,无论从政权的生存,还是从政权的有效性来说,对政权稳定都是中心问题。这并不是说,政权在人民心中合法化的程度就不重要了。这里所要说的只是,与在骨干中合法化的程度相比,它在许多方面都是居于次要地位的。其中,有两个方面最为重要: 第一,只要一个具体的权力中心或一个具体的骨干的要求,被其他权力中心和其他骨干认为是合法的,那么即使其在人民中的合法性很低,甚至衰落,也威胁不到政权的稳定。第二,政权在人民中的合法性的衰落,且不说用语言或暴力表达出来,就是这种衰落本身也更多地是以骨干中的合法性衰落为先导或者与这种骨干中的合法性衰落相关联,很少在骨干中合法性增长的时候会发生人民中合法性的衰落。
从制度的稳定,尤其是从它的改革的潜力的观点出发,看来政权在骨干中的合法性的程度是更加关键的。而最重要的是,正是政权在骨干中的合法性的衰落或瓦解,才导致群众中这种合法性的衰落或者把人民的不支持转化为有效的人民的反抗。在东欧所发生的革命、起义、不流血的“春天”和“十月”,都是首先在共产党骨干内部爆发合法性的基本危机的。相反,在斯大林之后的时代,苏联社会骨干观点上的变化和他们的内部冲突,在大多数骨干中,或在起关键作用的一部分骨干中,并没有形成合法性的基本危机。
当然,苏联的政治骨干不是一个整齐划一的整体,他们结合了各种各样的利益、形形色色的观点和情感。在国内出现危机时和受到沉重压力的时候,他们趋于分化。但是,可以看到,一整套核心的态度和信念是坚强有力和坚定不移的,这些态度和信念渗透到整个骨干阶层。在谈论苏联社会中的集团和利益时,人们会注意到不同集团中互相抵触的关系的变化,这种趋势是可以理解的。这指的是一些基本上接受这种制度、而在它内部争夺利益的集团之间的一种关系,指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这些集团之间互相一致的关系比他们互相抵触的关系更为普遍、更为持久。
苏联社会的骨干集团就是苏共,它的组织形态必然会影响国家功能的发挥。勃列日涅夫时期在党建方面的第三个问题是因循守旧,继承了苏共那套适用于极权体制的封闭式党建思想,并使其得以完整地延续下来。同时伴随着极权体制而产生的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的泛滥,使苏共党内华而不实、言行脱节的风气盛行。
首先,在苏共的体制建设中,依然是重集中、轻民主,使极权制得以稳固维持,以致人们一提到苏共的党建模式,就会把它同高度集权、党政不分、行政命令、个人专权、个人崇拜、党的领导职务终身制、干部任命制、官僚主义等字眼联系起来。这些极权制模式的种种特征,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并无改观,有些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个时期在恢复列宁主义的旗号下,苏共的重集权、轻民主的党建传统进一步加强。人们虽然能够从这个时期苏共的文献和舆论宣传中,看到大量关于扩大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的言论,但很难从实践中找到加强党和国家民主制建设的行之有效的例证,相反,却可以找到许多加强集中的例证。如在苏联宪法中规定党的领导地位和领导作用;取消干部更新制和任期限定制;等等。
除此之外,勃列日涅夫还授予克格勃以极大的权威,军队的政治势力也在这一时期得到加强。因此,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政权被称为党、警、军三位一体的“铁三角”政权。对意识形态也加强了控制。同时,勃氏为巩固个人的权力,还采取了一些组织措施,如在苏共二十三大上,将中央主席团更名为中央政治局,把中央第一书记的职称改名为中央总书记,从而恢复了斯大林时期政治局和总书记那种至高无上的称谓。他还吸取赫鲁晓夫下台的教训,第一次在党章中规定“中央委员会选举苏共中央总书记”。总书记由中央委员会选举,这就意味着只有中央委员会才有权罢免他;有了这样的规定,勃氏的统治就比赫鲁晓夫要安全得多,因为在1964年10月,赫鲁晓夫是被中央书记处和主席团罢免,而后由中央全会确认的。而在1957年6月的那次危机中,在中央主席团以八票对四票的结果撤消赫鲁晓夫第一书记的职务时,是中央全会挽救了他。二十三大还恢复了从前被斯大林强化,而后被赫鲁晓夫取消了的“内务办公室”(总书记的秘书处),办公室主任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书记处书记契尔年科,办公室成员除一人之外全都是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或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从这一点来说,已经超过了斯大林时期,当年斯大林的“办公室”主任波斯克列贝舍夫只不过是一名中央委员。这就造成一种既成局面: 中央有关部门作出的有待政治局批准的一切重要问题都不能越过勃列日涅夫的“办公室”,而要预先得到它的同意。
就这样,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通过上述种种加强集中的措施,不仅使极权体制得以延续下来,而且更加巩固和完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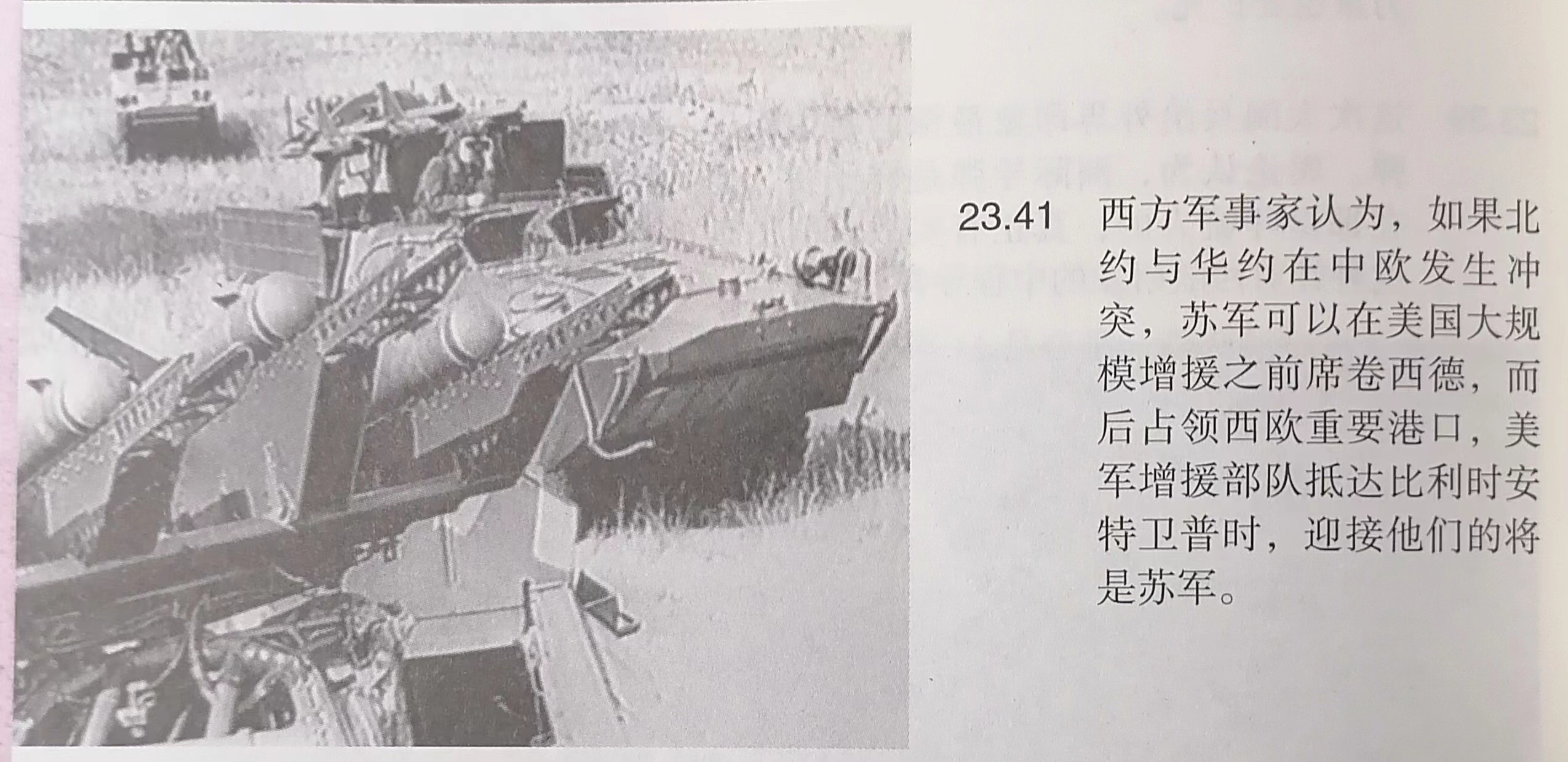
(未完待续)
荀路 2024年2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