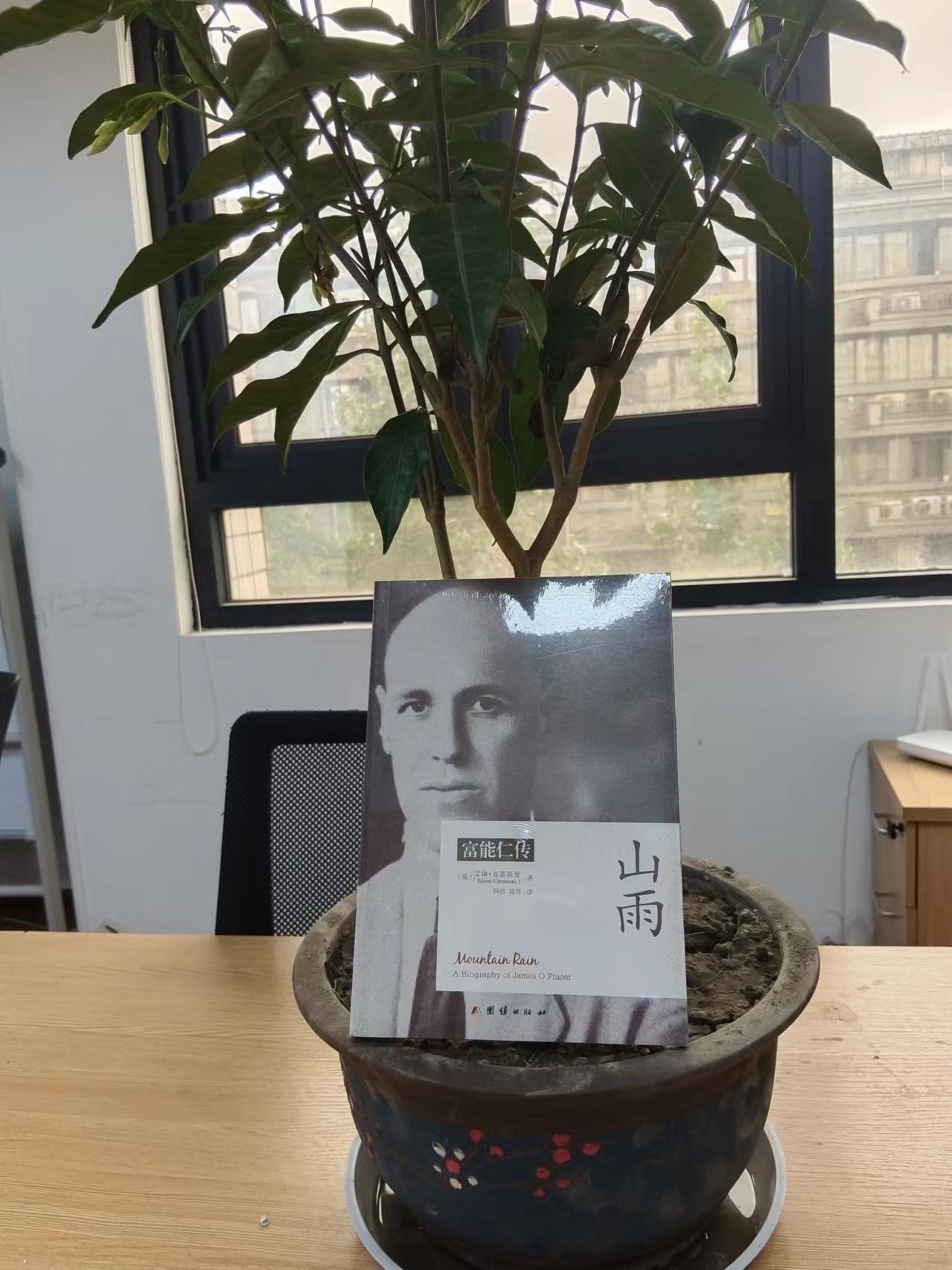问:据我们了解,您写了《用生命爱中国——柏格理传》,还翻译了一些传教士的传记,比如《客旅》、《山雨》、《多马·索恩传》等,可以看出您对传教士历史很感兴趣,为什么?您曾说过,希望“让这段令人感动、触动人灵魂的历史,长久、温暖地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中”,这是您笔耕传教士传记的主要原因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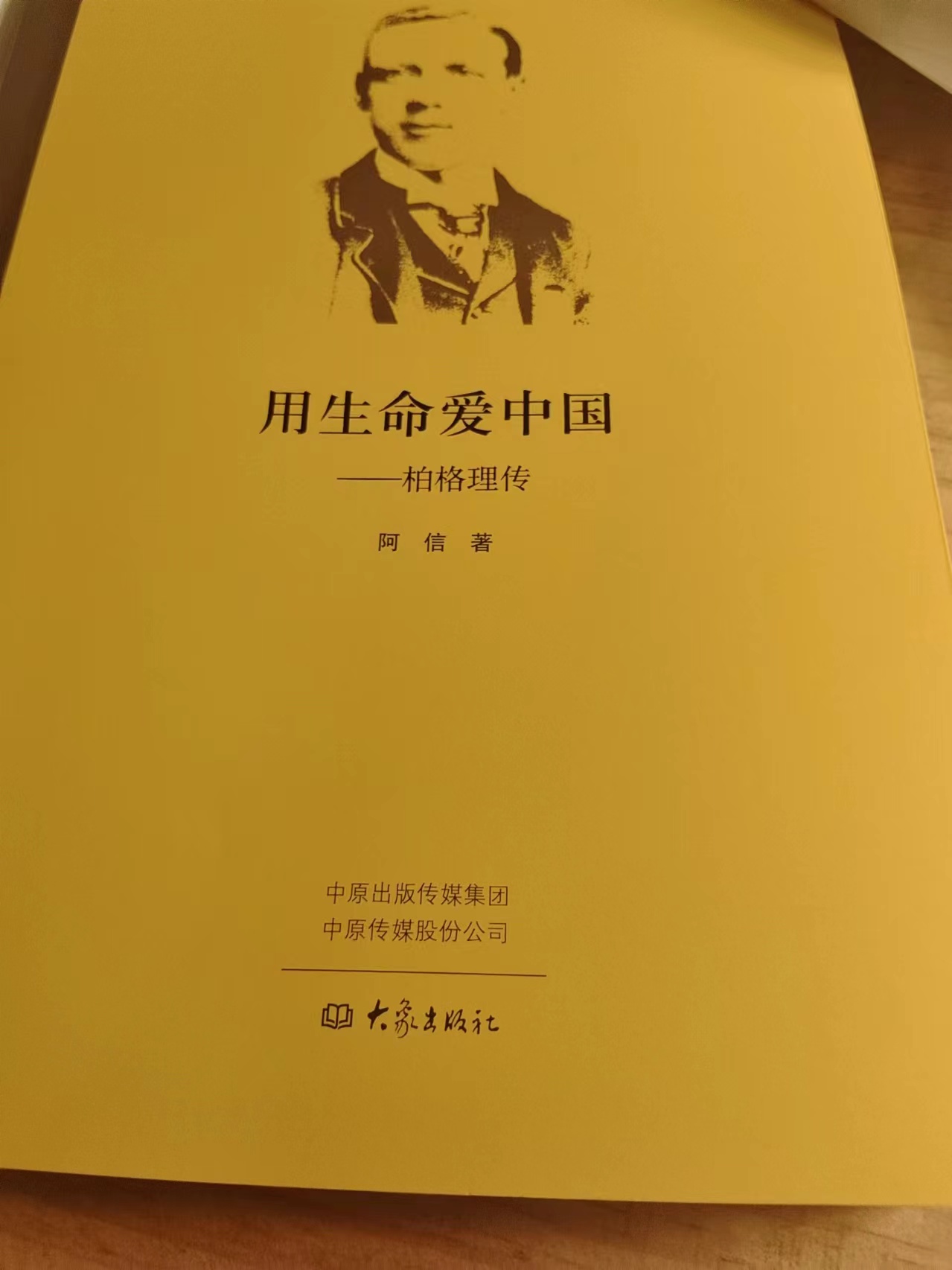
阿信:这段话更应该是结果。2005年是我的人生一个很大的转折点,当时我已经三十七八岁了,做生意遇到一些困难,情绪跌入低谷。我的一个大学同学说来贵州吧,树挪死,人挪活。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中国经济正强劲,房地产业欣欣向荣。如果直面自己,谦虚一点,不要那么好面子,找个工作不会有很大问题。但我被自我封闭起来了。于是跑去贵阳。
我相信那是上帝的带领,因为我去贵州的那一年,刚好是柏格理进石门坎一百周年。贵州教会的许多朋友组织人去石门坎纪念,我觉得莫名其妙,因为他们要来回开车三天时间,路上两天,当地一天,我想这些神经病跑那么偏远的地方去干嘛?完全不懂。有一天我在贵阳的一个书店里买了一本《中国国家地理·贵州版》杂志,其中有一篇中国社科院沈红博士写的文章《石门坎:“炼狱”还是“圣地”?》,我看了之后就想,我在贵阳待着都恼火,这个传教士从英国来,待在贵州和云南交界那个高山上,也没有不高兴,人家还是自愿的,这样一想,我就很喜欢柏格理,就找来他的书读,《在未知的中国》我读了好几遍,非常感动,我当时就起了一个信念,要把柏格理的故事告诉中国人。
记得2007动笔时,在网上查阅有关柏格理的资料,网页翻出来也就三、四页。现在资料很丰富,可以说我意外踩到了一个风口,这个风口完全是上帝赐给我的。人生有很多经历无法解释,我比较坚定的认为上帝在亲自拉着我的手,把我拉到贵州,把我从灰堆、逆境中提拔出来。我恐怕是中国第一个研究柏格理的基督徒,当然一些研究柏格理的前辈,比如张坦老师,后来信了主。我当时显然不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所以从我身上我知道上帝是不看人的;我也不是作家、不是翻译,但上帝就选中我,这是我这些年一直研究传教士的动力。所以,可以说,“让这段令人感动、触动人灵魂的历史,长久、温暖地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中”这段话,既是从2005年到今天为止我一直做教会史研究的原因之一,更是我认识柏格理之后的一个结果。
问:您在人生低谷时遇到柏格理,开始了大逆转,确实我们人生中有很多解释不了的事情,相信一定是神在引领。那您刚才提到您不是专业的写作者,也不是专业的翻译,肯定在翻译、写作的过程遇到很多挑战,记得您在《客旅》的后记中提到“常常累得手足酸痛,连欢乐的力气都没有”,给我们讲一件让您觉很很难、但很感恩的故事吧。
阿信:《客旅》后记中的感觉,我后来想起来很可能是我翻译《山雨》时的感受。翻译《山雨》过程中得了腰肌劳损,腰部很痛、躺着痛、趴在床上也痛,我记得趴在客厅长沙发的椅背上,手里拿着云南西部地图,顺着书中当年传教士所走的路线,核实地名,我拿的是中文地图,当时传教士用委码拼音标注地名,一些地名是没有变的,有些已经变了。刚开始翻译时,英文水平不高,《山雨》的英文原稿每一页大概都有几十个单词不认识,但这不是最难的,因为可以查词典。翻译过程中让我感觉最难的是对人名和地名的考证。
感恩的是有英文好的陈萍姐妹帮助我一起翻译。我翻译1~5章,关于怎么祷告那个章节是我翻译的。记得我当时腰很痛,翻译了很长时间。云南和缅甸的边境线是1962年才正式划定的,《山雨》里提到的很多地方今天很可能在缅甸境内,区分起来很困难。翻译过程中得到很多人的帮助,龙陵的余牧师是柏格理中国同工的后人,他沿着富能仁的宣教路线走了很多次;我还辗转找到傈僳族学者史富相先生的女婿李先生,记得他当时在怒江州委工作,我就打座机电话给他,那是这世界还没有手机。他送了我一本《史富相文集》,对我帮助也很大。我说付钱,他说岳父的事,不能要钱。
当时我有一个理想,力争把《山雨》这本书翻译成一本导游手册,所以我用了很大功夫、在人名地名的核实上,作了大量工作。但还是犯了一些明显的错误,最明显的就是对“怒江大峡谷”的误解。我现在知道,怒江从丙中洛到六库这一段称为怒江大峡谷,下面到腾冲大理这段,东岸是大理坝子,西岸是腾冲坝子,富能仁传福音的主要区域在腾冲和大理坝子。当时怒江大峡谷在地图之外,就是说不管是中国还是英国的地理学者都未进入这一领域,所以杨宓贵灵在《多走一里路,就是一台戏》中写到阿子打时,说他们夫妇走到了地图之外。我翻译时不知道,只要看到富能仁住地的旁边是深谷,我就想当然地翻译为怒江大峡谷。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现在很多弟兄姊妹一说起富能仁就是怒江大峡谷,真不知道重点是去了解福音历史还是游山玩水?这个错误大约是受我的影响。希望将来有机会再版时,可以把错误和容易误导读者的地方都改过来。
问:您写柏格理传记,又翻译富能仁传记,他们一个在贵州石门坎的苗族人中传福音,一个在怒江傈僳人中传福音,都是很有果效的,那您能不能简单评价一下这两位传教士,你心目中的他们是什么样子的?
阿信:我只能简单地说一下自己的感受,一开始我觉得柏格理和富能仁都很了不起,是传奇式人物,也是我们普通人可望不可及的,但经过多年对传教士的研究,当我进一步了解西方传教士的工作方法,了解到他们所处的宗教及人文环境时,我开始觉得出现柏格理和富能仁以及众多与他们一样的传教士实际上也不令人意外。
所以我觉得无论柏格理还是富能仁,首先他们都是神忠心的仆人,是被神差遣的;其次我非常欣赏他们的工作方式。富能仁一到傈僳地区,先拿笔开始记录傈僳人的语言,然后找一个人开始学习,他们主动地学习当地人的语言,而且有科学的记音工具,这是值得我们效仿的。而且,他们用简单的方式发明文字,让普通人很容易学会。西方传教士有一套非常科学的系统,很多我们觉得很厉害的工作,在他们其实是很普通的事,当时宣教机构就有这方面的培训,不难。西方文字是记音(拼音)文字,发明文字只是一个技术性的活路,和中国象形文字完全不同,这是深处中国象形语言中的人很难理解的。所以周有光先生说世界上其他民族的文字都已发展到字母阶段,独有中国还处于“古典文字”阶段。很奇怪不是?
我觉得要向柏格理、富能仁学习,这种学习不能停留在表面上,变成中国文化里面的崇拜,他们实际上跟我们是一样的普通人,都是上帝所钟爱的人,只不过他们被上帝特别呼召来到中国。如果我们把他们作为朋友、老师来看,我们才可以学习他们,更像他们。他们和我们相比,更大胆,不怕犯错。他们刚学会苗文、傈僳文,就开始翻译圣经,他们不怕出错,先翻译出来,再不断修订。
问:您在翻译过程中的这种看见对我们启发很大,学习传教士确实不能停留在表面,也不能变成一种崇拜。您曾经说过笔耕让您成为一个稍稍像样的一个基督徒,为什么这么说?您如何经历生命的变化?
阿信: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都要不断被神更新和改变。为了写《柏格理传》,我读了很多遍《在未知的中国》,我给柏格理编写了年谱,把柏格理每一年每一月做什么事情都罗列出来,因为不同的文献资料上有时会有不同的记载,我要把它们列出来,然后以我的经验和掌握的资料,来判断哪些可能是对的,哪些可能是靠不住的。在翻译《山雨》的过程中,一年多的时间,相当于有一个主的圣徒站在我的旁边,告诉我怎么做事、怎么思考、怎么敬拜、怎么祷告,所以,写作和翻译的过程就相当于柏格理、富能仁牧师活过来,每天给我做忠心服侍的榜样。正是因为这样的经历,也让我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写作和翻译都要精益求精,让活过来的传教士可以影响更多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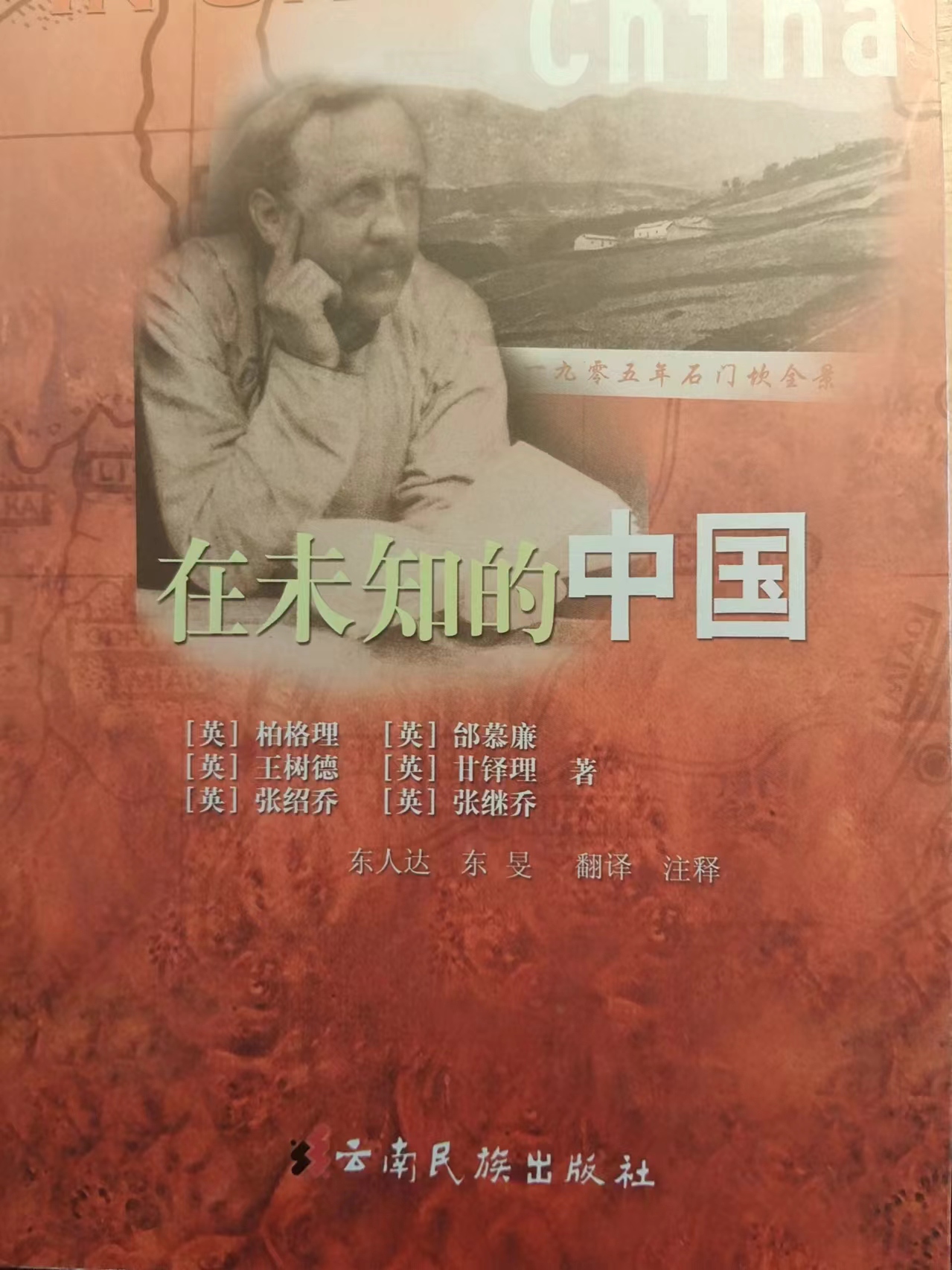
问:您说过前五章是您翻译的,我看到第五章有很大篇幅的祷告,印象很深,而且富能仁在滩岔这个地方灵命里面临很大的争战,他靠着信心的祷告胜过。那谈谈这一章的翻译对您有什么影响好吗?
阿信:影响非常大。可能腰肌劳损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记得这一章我大概用了一个多月时间翻译。富能仁当时面临很艰难的选择,因为在傈僳人中传福音果效不明显,争战又很大,他身心灵都跌入低谷,开始考虑是否听从内地会的要求离开怒江傈僳族地区。就在那个时候,突然沙漠里开了江河,傈僳村庄一家一家信主,神成就了富能仁的祷告,让他祷告的信心更强了,在人不成的事,靠着神的力量完全可以。我当时翻译时有点不太相信会有这么大的反转,因为那个反转完全不可思议,非常奇妙,所以,翻译过程让我从富能仁身上学到了信心祷告的功课。
问:您刚刚说在翻译的时候有一个希望,就是让传教士活过来,继续做事,继续说话,我感觉到翻译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是生命影响生命的过程,已经和这个传教士建立了很深的感情,那么,如果您有机会见到富能仁的后人,您最想对他们说的一段话是什么?
阿信:1949年之后传教士被驱逐出中国,这在世界宣教史上都是一件让人震惊的大事。我翻译柏格理的大学学长、多马·索恩传时了解到,他们教会先后在澳洲和加拿大宣教,两个地方的禾场丰收之后,选定的第三个宣教禾场是中国。当他们来中国宣教时,是英国、澳洲、加拿大三地基督徒同工一起来的,如果不出现巨大的变故,后来的历史应该是和中国基督徒一起再向外宣教。石门坎苗族其实已经开始给自己的苗族同胞宣教;怒江大峡谷的福音其实是宣教士和木城坡傈僳族弟兄姊妹合作的结果,最早去怒江大峡谷宣教到是四位木城坡一带的傈僳人。但这一世界福音潮流后来在中国中断了,我认为中国对整个世界的宣教起了非常大的阻力,这种阻力在世界宣教史上都是很严重的,以至于西方社会包括教会,很多人都认为宣教士在中国的宣教完全失败。
所以见到富能仁的后代,我想告诉他们,中国人记得他们的祖辈,他们祖辈在中国撒下的种子依然在开花结果。虽然他们在中国曾经受到不公正的对待,甚至误解,文革期间墓地都被摧毁,但是福音毕竟就这样传开了。我还想说的是,我们中国基督徒欠福音的债,我们应该尽我们的努力,去还福音的债。
阿信:作家、独立学者,主要从事中国传统思想研究,及近代宣教士赴华宣教的文献翻译。主要作品有:《用生命爱中国—柏格理传》、《山雨——富能仁传》、《客旅——瑞典传教士在中国西部的生死传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