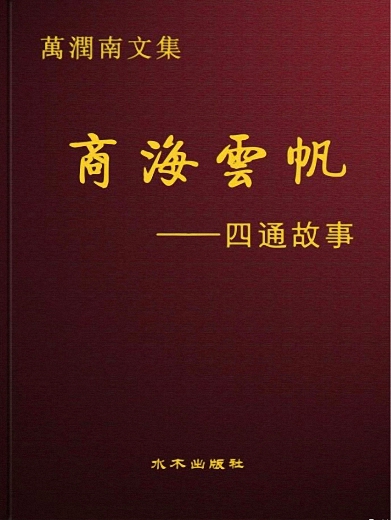第八章 商海布局
(56)广州行
商场布局,犹如下围棋。在长沙,我们“长”了一子;在新疆,我们“飞”了一子。1986年,我们在中关村根据地,又“提”了两子。
话说我原来的工作单位:中科院计算中心,也先后办了两家公司。一家在中关村,叫“鹭岛公司”;一家在珠海,叫“拱北新技术开发公司”。
珠海公司和港商合资办了一个“两头在外”的钮扣电池加工厂。所谓“两头在外”,是指原材料和产品市场都在海外。问题就出在这个“两头在外”。
这家钮扣电池厂,一直是负债运行,每个月都要从银行贷款。不到一年,累计贷款已达三百万元。给贷款作担保的,是中科院计算中心。不能如期还贷,银行就查封了担保单位的账户。这一下,计算中心炸开了锅。账号一封,不仅科研受影响,连发工资、付水电费都成了问题。所长冯康先生,一大清早赶到三里河院部。据说当时他脸色铁青,气得直打哆嗦。
在第一章《阳光灿烂》里提到,当年我一个只配“捡兔子”的低级研究人员,被破格成为为“点兔子”的,担当只有高级研究人员才能领衔的院重点项目。所长冯康先生对我们非常满意。说我们是“有任务、有手段、有团队,是最有希望、状况最好的一支队伍”。我说“为了老先生的这句夸奖,若干年后,我终于有机会报答了他”。
这一刻,就是这样的机会。
是老沈告诉了我这些消息。我们商量以后,决定出手相助。我带了一张三百万元的现金支票,主动找到了计算中心的领导。话,我说得很诚恳:“我是计算中心培养出来的,前年我出来办公司,关键时刻,领导支持了我。俗话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你们给我一个机会。这三百万元,先借给你们,马上存进银行,先把贷款还了。”
接着,我提议:“这样,你们把所里办的公司,都交给我们承包。如果今后这些公司的经营有新的亏损,由四通来承担。如果赚了钱,我们先还债务。把债还清之后,利润我们两家对半分成。”
这对计算中心来说,不仅解脱了眼前的困境,今后也是没有风险,只有利益。我相信,天下没有人会拒绝这样的提议。
1986年6月10日,四通和中科院计算中心正式签订了承包协议。
是珠海的纽扣电池厂,捅了一个三百万元的窟窿。这是一个硬茬。我把啃骨头的任务,交给了殷克。估计在那里会遇到什么三教九流的对手。而殷克这个家伙,自己就是一个三教九流。当然,我自己也喜欢打这样的硬仗。 1986年6月中,我、李玉、殷克、殷克的夫人李娜,我们一行四人南下,经广州去珠海。
途经广州,在酒席上,我们遭遇到了“正规军”,先打了一场硬仗。这一仗,堪称经典,可以千古流传。
军队,是四通打字机的一大客户。广州军区后勤部,是我们最早的经销单位之一。我和殷克一行途经广州的时候,谌受于正带着一批四通子弟兵,和他们在三寓宾馆联合搞MS-2400的产品展销。四通人一个个“嘴上呱呱的、手下哗哗的、脚下唰唰的”,让合作方赞不绝口。他们听说四通的老总到了,非常高兴,说部队首长晚上要设宴为我接风。
无酒不成席,这种场合,酒是免不了的。早就听说部队喝酒的场面很壮观,不让对方喝趴下,就不够意思;不把对方放倒,决不收兵。那天晚上,我真的见识了什么叫密集包围、轮番作战、梯队进攻。
部队首长是一位东北汉子,宴会一开场,他拿出一瓶五粮液说:“今晚咱们来这个,怎么样?”

我喜欢五粮液的口感纯正,香气浓郁,便赞了一句:“好酒!”
于是他满满地给我斟了一杯,是那种透明的玻璃杯,一杯大约有1.2两。待大家都倒上酒之后,我端起酒杯,站起来说:“来,我先干为敬。”接着仰脖一饮而尽,再把酒杯倒过来,以示无欺。然后说:“大家随意。”
接着,便挂起免战牌:“今晚,我们就不要比喝酒了,因为这样做可能对你们不公平……”
面对大家一脸疑惑,我语出惊人:“因为我对酒精没有反应。”
这一下,激起了他们高昂的斗志,看来,他们下定决心:今天一定要让我“反应”一下。
有人会说:见过吹牛的,没见过你这么吹的。但我确实有吹的资本。我先天能喝酒,平时不喝,喝起来却可以三杯不醉、五杯不倒,源于我得天独厚的身体条件。酒精,化学上叫乙醇,进入人体以后,有一种酶,叫乙醇脱氢酶,会脱去乙醇的一个氢分子,乙醇就转化为乙醛,乙醛伤肝;但人体还有第二种酶——乙醛脱氢酶,再脱去乙醛的一个氢分子,乙醛就转化为乙酸,乙酸会分解成二氧化碳和水,再排出体外。一喝就脸色通红的,是没有第一种酶。有的人貌似能喝,喝多了脸色发青的,是没有第二种酶。两种酶齐全的人不多。爹妈在造我的时候,没有一丝偷工减料,我是两种酶都不缺的少数人之一。喝酒对我们来说,其后果是排气和排水。说得粗俗一点:就是打嗝、放屁,出汗、撒尿。而且,只有我们才能从容地体会喝白酒的美妙:入口的绵甜、入喉的净爽、回味的浓香,这是一种从五脏六腑溢出的异香……虽然旁人闻到的可能是酒臭。李白斗酒诗百篇,苏轼把酒问青天,他们才思敏捷,超脱旷达,多半应该是酒的功劳。
第一次知道自己能喝,是在承德。当时我在铁路中学教书,邻居是学校工宣队的王师傅,平时好杯中物。一天他拎着一瓶一块二毛八的散装白酒,说一个人喝没意思,过来邀我同饮。我们用那种平时刷牙、喝水通用的大搪瓷缸,一人半斤,满满的一杯。桌上就摆了一小碟花生米,我端起搪瓷缸,像喝凉白开似的,咕嘟咕嘟就下去了半杯。他觉得工人老大哥不能在臭老九面前丢份,也照样一口气干了半杯。结果很悲惨,他当场就趴下了。我赶快把他的老婆,也是铁中的李老师叫过来,把王师傅扶回家了。而我当时却没有什么感觉,由此发现了自己的“特异功能”。
那天在广州,我捅了马蜂窝了,进攻像潮水般涌来。首长一挥手:一梯队,上!一个个精壮的小伙子,轮番过来劝酒。我都一一干杯。殷克也能喝,属于那种喝了脸色发青的,想过来救场。首长一努嘴:二梯队,上!殷克马上被另一批人包围了,无法靠近我的身边。
一波进攻过后,我神色怡然,在席上依旧高谈阔论。这时候首长一使眼色,第三梯队上了,都是老同志。其中有一位,上来要和我喝交杯酒,说:“我们全家都敬重你,我代表老伴,想和你喝一盅交杯酒。”然后就挎起了我的胳膊。这家伙,为了劝酒,把老婆都搭上了。这杯酒不能不喝,我笑着一饮而尽。
还有一位更绝的,过来先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纸,说:“这是医院的诊断书:晚期肝硬化。医生严禁我喝酒。但今天见到你,高兴!”然后干了一杯。我清楚他杯里的是凉白开,因为没有酒的那种透明度,但不便点穿,又跟着干了一杯。
李玉在现场紧张得无所适从,只好在旁边计数。根据她的统计,我先后一共干了二十二杯。最后,餐桌上菜肴满盘皆空,旁边的长桌上堆满了空酒瓶,全场鸦雀无声。我站起来,向大家拱拱手,道了谢,非常有尊严地走出了餐厅。
期间,我也不是一点“反应”也没有,我不停地擦汗、打嗝,还上过几次厕所。后来感到酒力有些上头了,便在意念中默想:“千万不能露怯!”顿时感觉像有一盆凉水,从头往下慢慢灌下来,脑袋又是一片清明。武侠小说里描写有人中了毒,可以用内功把毒素逼出体外,我相信这类说法。看来,我上辈子不仅是一位高僧,还应该是一位内力深厚的武林高手。有人说我会“吹”,咱索性把上辈子也“吹”一下。这辈子的事,有名有姓,还都可以查证。上辈子的事,嘿嘿,就查不清啦!
出了宾馆,凉风一吹,有些反胃。上了面包车,车门一关,离开了主人的视线,我便原形毕露,哇的一口吐了出来,弄得一片狼藉。回到下榻的宾馆,死死地睡了一觉。睡醒之后,起来冲了一个热水澡,便一切恢复到常态。第二天,我们驱车直奔珠海。
是啊,计算中心在珠海公司亏空了三百万,不是个小数,得先弄明白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