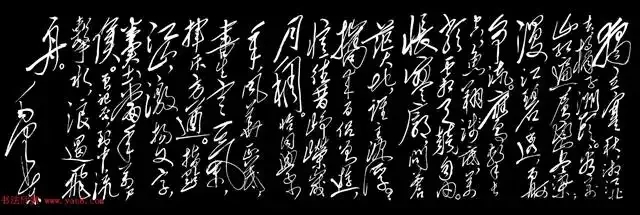三)这首词不是毛独自创作之证据
在近十年间,互联网上有人揭发,这首词不是毛独自创作,而是毛与青春时代的同学、同志游历岳麓山、橘子洲时的众人联句合写,据说毛的小学同学、萧瑜之弟萧三曾在延安发现:原作”肃立寒秋”,被改为”独立寒秋”,原作”欢歌百侣”,改为”携来百侣”。
这个揭发很严重,如属实,毛很卑鄙,是贼诗人,这个揭发者如果是萧三本人,可信性会大一些,由于揭发者无名无姓,不知是谁,该揭发就难以采信了。倒没想到,笔者买到一本由国学相当深厚的李奎宁编著、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印制庄重堂皇的《毛泽东诗词鉴赏大全》,其第一页有如下文字:
……据美国施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一书载,毛泽东在延安时,曾将其诗词七十多首汇集付印,题名《风沙诗词》,印数很少,只送给亲密的朋友。但由于战争环境,这本诗集未能流传下来……
其第17页又有如下文字:
这首词(黄琉注:指《沁园春· 长沙》)最早见于萧三著的《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北京新华书店1949年8月发行),后经毛泽东亲自审定,正式发表于《诗刋》1957年1月号……
这两段文字证明上述的“萧三证言”,并非空穴来风,为此,这个“萧三证言”挑起了笔者对这首词的创作者及创作时间的深沉怀疑,为解疑而想,竟是越想疑点越多。由于近十年间经已查实,四卷毛选中很大部分文章不是毛所写,而毛绝不客气、面不改色都当作自己的作品(包括稿费全部独呑),我们今天怀疑这首《沁园春·长沙》不是毛个人构思创作,因而不算过分。现在,笔者就纯粹从这首词的结构、用词手法来分析,足可证明这首词应该就是众人联句合写,不是单个人的构思创作。另外,查磡《毛泽东年谱》,笔者竟又发现这首词绝不是写于1925年,这就兹事体大了。
1、 经查,这首词最早公开发表于1957年1月号《诗刋》,发表时毛标明的写作时间为1926年,其后,官方查实毛1926年不在湖南,毛在湖南长沙的时间是1925年秋,当这篇词再版时官方遂求证于毛而给毛“订正”写作时间为1925年,毛如果声明该词并非即景 ( 即景自然亦即 “即时”,就算修改几个月或几年才完成,因诗意生于即景之时,循例也算即景)之作,而是追怀往事的游戏之作,或说明该词断断续续在1926年才写完,天下人也就无可质疑什么了,但毛无异议接受该“订正”,亦即毛表示该词是他1925年秋即时即景之作。
笔者认为,这个“订正”真是可圈可点,因为这首词如果真是毛所写,又是写于被紧急缉拿、必要化装亡命关头,毛不可能忘记写作年份。中共毛史、党史权威逄先知在其《毛泽东年谱 1893-1949》中写到:毛1925年8月底逃出韶山,在长沙藏匿数日,于9月初南下继续逃亡,途中住店时因恐惧而把所写笔记全部焚毁。毛记得而讲出这件事,可见“1925年秋”于毛何等凶险,印象何等深刻。如果这首词是毛所写而又写于“1925年秋”,写这首词之事和焚毁笔记之事,明显如一胎所生的孖生男女婴,由于构思、写成这首词所化的时间、心思,绝对远多于焚毁笔记的时间、心思,毛只记得“1925年秋”焚毁笔记,而“错记”这首词写于1926年秋,也就直如生下孖生男女婴的母亲只记得生下女婴,而把同时生下的男婴忘得一干二净,这怎么可能?毛之所以会“错记”,只能是这首词并非毛亡命关头、亦即并非 “1925年秋”所写。
2、 如果这首词是毛单独构思创作而又写于“1925年秋”,毛绝对没有必要隐瞒这首词是逃亡关头之作,因为公示这首词是逃亡关头之作,只会更显毛何等临危不惧,何等英武盖世,何等伟大神圣。1957年1月发表这首词时,毛没有说明这首词是逃亡关头之作,甚至直至1976年毛死之后二十年,官方及中国千百万毛诗词的狂热粉丝都只是轻描淡写说这首词是 “1925年秋,……毛离开长沙去广州……时所作”,并无一人留意及提到这首词是毛的逃亡关头之作➌,就凭这一点,已强有力证明这首词绝不是毛逃亡关头之作。在《沁园春· 长沙》词中,事实上也绝无丝毫逃亡的气味、色彩,官方给它 “订正”写作时间为1925年,应该是无意图的很机械之“订正”,官方绝未想到这个“订正”竟会使这首词成为“逃亡关头之作”,中共毛史权威逄先知未留意这个问题,料算是因他并非诗学专家。
3、 这首词不是1925年毛逃亡关头之作,那么会不会是1925年毛的非逃亡关头之作呢?经查,不会!《毛泽东年谱·1893-1949》141页至145页,记载毛1925年1月至8月在家乡韶山一带的活动甚详,毛根本没有空余时间去长沙。
4、 这首词究竟真正写于哪一年呢?查看《毛泽东年谱·1893-1949》及左中右许多部研究毛的巨著,笔者查实如下:
a)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五·四”运动,内除国贼,外抗强权,抵制日货,要民主的呼号震撼全国,毛没有参加声援北京学生“五·四”运动的纪录,但1919年7月毛的《湘江评论》刋物出版发行,其主调鼓吹无政府主义,不主张“有血革命”,它呼叫中国人要觉醒, 要“民众大联合”以救国。刋物出五期被禁,秋冬间,毛母病危,浸而至死,毛置之不理,无动于衷,毛忙于参予、策划查禁日货及“驱张(湘督张敬尧)运动”,运动遭张敬尧命令警方刺刀刺戳、棍棒痛殴后沉寂,12月毛与数人赴北京告状、求援。
b) 1920年,极器重毛的杨昌济1月17日 在北京病逝,毛参予治丧,杨开慧1月底随母兄扶灵返回长沙,毛逗留北京至4月11日才离开北京,去天津、曲阜、济南、南京游玩近一个月,5月5日抵上海,随后见陈独秀。恰巧这时苏共派来中国图谋成立中共的维辛斯基也抵上海访陈,毛得以旁听了密谋(这自然给斯大林留下深刻印象,这为毛后来崛起种下“因缘”),但毛这时只想搞“湖南自修大学”、“民众大联合”及“湖南独立”运动,无意参予组织共产党。7月初,毛离上海去武汉见恽代英等,至7 月7日才又回到长沙(《毛泽东年谱·1893-1949》第68页),拼力搞至年底,自修大学办成了,文化书社又开张了,他的“民众大联合”略见声势却烟消云散,他的“新民学会”会员也越来越散漫,“湖南独立”运动自然也无疾而终,对此他当时致向警予的信显示他气得要死。但由于这一年年初毛之父死,秋天他承继家产实质成了地主,兼且人不知鬼不觉独吞了章士钊给出的二万元救国钜款➍,他不可能苦闷、怅惘,事实上该年秋他一边和陶斯咏造爱,一边向杨开慧展开追求,并于年底和杨结婚。至于前途问题, “湖南独立运动”虽然失败,但当时他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祖师爷李逹比邻而居,又接受陈独秀、蔡和森的来信指教,他很快想到维辛斯基所说的必要组党才能牢笼同志乃高见,他因而不会怅惘。该年11月他已着手组织CY(社会主义青年团,独立于中共之外的党团,这与后来属中共管辖的共青团不同)湖南支部➎。
c ) 1921年,7月,毛在上海参加中共一大,返回长沙即大展拳脚发展中共组织,绝无苦闷迷惘情绪;
d ) 1922年 ,毛添丁,生毛岸英,发展组织工作又很见成绩,毛很振奋,绝无苦闷怅惘情绪;
e ) 1923年,5月毛被调去上海中央工作,参加国民党(与后来反共的国民党性质不同,当时苏共支持国民党超过中共千百倍),参予国共合作,毛声名鹊起,似鲤跃龙门;这一年秋冬毛不在长沙。
f ) 1924年1月,毛为汪精卫提携参加国民党一中全会,坐主席台,获孙中山钦点为后补中央执委,毛奉派赴国民党上海执委工作,他拼命卖力;颇有跳槽昄依国民党之势,大受他的死党好友、中共中坚分子们非议、不满,年底被踢出中共“四大”的代表名单,中共“四大”结果,是他又被踢出了中央委员会;这一年秋冬毛不在长沙。
g ) 1925年年初,毛在国、共两党上层遭冷落,情绪低落,精神崩溃,1月离上海,回到韶山养病兼搞农运,8月底,毛在湘潭农村指挥百余农民拿着锄头、棍棒强迫一土豪贱价卖粮,这等同破门强抢,为此省长赵恒愓闻报8月28日向韶山县发出电报密令:“立即逮捕毛泽东,就地正法。”毛得朋友郭麓宾报信,紧急化装医生当夜逃出韶山,抵长沙藏匿几日, 9月初南下广州;入医院留医半个月,再去投拜汪精卫,10月7日,由汪推荐,毛就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代理部长,月薪120 元。
h ) 1926年1月,国民党二中全会召开,毛的座位为十五号。曾上主席台作《宣传部两年经过状况》报告。3月20 日,中山舰事件爆发,蒋成功反制苏俄、中共之压迫, 5月,国民党《整理党务案》获通过,毛依该法案不得不辞去部长职,转而主办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毛该年秋冬不在长沙;7月9日,蒋中正就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誓师北伐;
I ) 1927年,国民党“清共”,毛参加武汉的中共“八·七”会议,旋即回湖南策划、组织“秋收起义”,忙得天昏地暗,接着上井岗山落草为革命山大王。
(以上未注明出处的,均可查看中共毛史权威逄先知编著的《毛泽东年谱》)
细看以上,剔除1925年,明显有苦闷、怅惘情绪的《沁园春‧长沙》,只能写于1919年秋天,词中的“忆往昔”,则是忆1913至1919年春夏的事,其中特别是 “新民学会”成立后的事。1919年秋天毛的《湘江评论》被禁,毛母病危垂死, “驱张运动”遭警方刺刀棍棒痛殴,这时毛又未了解马列主义,他崇拜的人是梁启超(主张“新民”)、泡尔生(主张“无政府主义”)、陈独秀(主张“民主、科学”),亦即他仍未找到人生方向,如此种种,他可算又穷又困苦。心境难免苦闷、怅惘。要说《沁园春‧长沙》写于1920年秋,可能性很微,因身怀钜款(详情见本文之后的附文)又一明一暗搂着两个美女(杨开慧、陶斯咏)谈情造爱者,怎可能会苦闷、怅惘( 参看张戎著《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P18)?
另须注意:1912年清帝退位至1920年,人们把那些凭借清朝廷而享有权势、在民国肇始仍在弄权者视为“万户侯”,以“粪土”视之是自然的,但1920年 至1925年,中国政坛已一批接一批涌现出很多举足轻重之新军伐新政客。比如孙中山、段祺瑞、吴佩孚、冯玉祥、张作霖、陈炯明、陈独秀、汪精卫、胡汉民、 蒋介石等等,“万户侯”实不足以涵括这些权势声威远超公侯的新军伐新政客。
另须特别特别注意的是:1920年至1925年,毛(包括“百侣”中的蔡和森、萧瑜、彭璜、罗章龙等等)的 ,活动很多,该等活动的重要性全都远远超过他读书时期的活动,其足迹且遍及长沙、北京、天津、济南、南京、上海、武汉、广州等等风云滚滚之地,毛的姓名未算响亮,但也可算是大时代涛头站立的弄潮儿了,而这首《沁园春·长沙》提到的事,都是1919年秋天之前在长沙发生的事(即成立“新民学会”及办《湘江评论》等),全词并无只字触及1920年至1925年的风云人物、大事件和毛自己(包括“百侣”)的活动,这应该也是这首词写于1919年而并非写于1925年的强有力的证据。
这首词的结构散乱,有众人联句合作的鲜明特色,完全不像是一个人的构思创作:
A、“怅”字把上阕斩为两截,涵意相反,欠缺转折的逻辑交待,单个人创作不可能如此构思;
B、 “曾记否”是设问语,在二人以上的联句作诗的环境中,被问者是参予联句作诗的其他人,这是明白如火的,这一设问因而就绝不奇怪,绝不突兀。但如果这首词是单独一个人所构思创作的,被问者是谁那就必须有所交待了,自古以来类似之问,创作者都会在诗词的题目标示写给谁,(比如标示“致萧三”、“致蔡和森及某某某” ……等等,)但这首《沁园春》的题目只是“长沙”,又起句即声明是“独立寒秋”,因而 “曾记否”就出现得莫名其妙,不知是问谁,单个人构思全篇词,不可能如此逻辑错乱。
C、这首词增加了三个平仄韵(秋。透、否),读起来琅琅上口,韵味很浓(不等于诗味很浓),外行人很容易被欺骗,以为读得顺就是条理畅顺,其实它的下阕的条理不顺,结构很奇怪,不合中国文法,请看:
|
上阕 |
文法结构(逻辑范畴) |
文理逻辑(叙述內容) |
|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桔子洲头。 |
起 |
说明登顶的人物、时间、地點点/p> |
|
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 鹰击长空,魚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 |
承 |
写所见景 |
|
怅寥廓, |
转 |
因景而动情 |
|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
合 |
抒怀 |
|
下阕 |
||
|
携来百侶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
我回忆起… |
|
|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糞土当年万戶侯。 |
我又回忆起… |
|
|
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
(我再又回忆起,而)你还记得吗… |
以表格分列出来,即可看出:词的上阕己完成了起承转合,其中转的环节仅一“怅”字,显得很单薄、生硬,但仍勉强通,至于整个下阕的文法结构则奇怪,难以裁定,下阕的文理逻辑(叙事内容)则是:
我忆起,……
我又忆起,……
我再又忆起,而你(或你们)还记得吗……
以 教学生作文来解说:当一个学生连续写完 “我一忆……,我再忆……,我三忆……”之后,这世界有教师会教导学生不必再写这“一忆二忆三忆”引发了什么,就算全文写完而交卷吗?可肯定绝无教师会这 么教导,而毛这首词明显就是写出“一忆二忆三忆”就全篇嘎然而终了。按常规这首词的下阕结构属于有头没尾。
不过,诗是一种很特殊的文体,写诗头尾可以颠倒,条理可以偶有错乱,为此坐实毛这首词有头没尾并不恰当。由于上阕的末韵句“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 浮?”很沉重,又未有解答,所以,这上阕的最末韵句可算作下阕的逻辑收结,或算是“一忆二忆三忆”之引伸倒射处。换而言之,整个下阕算是整首词转的环节和 合的环节中间的补充,它以“一忆二忆三忆”来隐晦回应上阕之怅问:“我(或我们)有这个主宰沉浮的可能,因为我(或我们)风华正茂……我(或我们)不把万 户侯放在眼里……”。(在此必要指出:这个回应上阕之“怅问”,依据文法、逻辑,只能是“很不服气的苦闷迷惘之问”,不能胡说为“怅问”遭冲击而变成 “豪迈之问”。)
不能指实下阕有头没尾,但这里却可以质疑:这种“引伸倒射”结构,是西式文法结构,大概是很刁钻的洋诗人才会玩出这种文法结构,中国古文学中很难找到谁曾以 这种文法结构来作文写诗,毛没受过西式教育,更极抗拒看新体自由诗,他所写的所有诗词、文章,全都循守中国的“起承转合”式顺序结构,绝无这首词的西式文 法结构,为此,说这首词是毛单个人构思创作,是讲不通的,而说这首词是好几个人联句拼凑,乱打误撞而撞合了这种文法结构(大致算是:起—承—合~转),则十分可信。
6、 当我们认定这首词是毛和同学集体所写而又写于“1919年秋”,本文前面把词中的“怅”问“谁主沉浮?” 解读为是问陈独秀(中共)将主沉浮,还是汪精卫(国民党)将主沉浮?自然不当,必要推翻,而另作新的解读行不行?行!新的解读如何呢?很简单:毛和他的同 伴们之怅问“谁主沉浮?”是怅问哪一个人(或其高见)将主宰沉浮?这种怅问在1919年是很正常、很普遍的,因为当时的北洋政府很脆弱,各省督军拥兵自 重,孙中山像一条流浪狗,中国是“一战”战胜国而巴黎和会居然要中国把德国在山东省的利益割让给日本,这成何体统?于是,究竟谁的高见可以救中国,,究竟 谁是救中国于沉沦的英雄,说实在是当时举国士子之怅问。改采这种解读,由“看”到长沙之美好之景而突然转换为“怅”,当然仍突兀,不畅顺,但这并非绝对, 事实上只要词题标示是好几个人联句作于1919年,那么“怅”字之转出,也就谈不上突兀,谈不上不畅顺了,因为1919年爆发“五·四”运动,是众所周知 的举国震撼、士子皆激愤怅惘之年。当然,改采这种解读,词的第一句必须是”肃立寒秋”而不是”独立寒秋”,”欢歌百侣”,也不能被改为”携来百侣”。
依 据以上六点,可以斩钉截铁裁定《沁园春·长沙》是好几个人联句拼凑于1919年秋,毛发表该词时注明写于1926年,不可能是“误记”,因为1926年秋北伐开打,长沙地区大军云集,中国天翻地覆巨变,经常全局在胸的毛不可能不知道,他随手而写出该词作于1926年,再后来又认同写于1925年,应该是下意识回避1919年,亦即毛纯粹是因内心有鬼,鬼迷心窍了:他不自觉地以为回避1919年这个他和好几个穷愁潦倒的愤青死党抱团取暖的年份,也就可以遮掩住该词乃几个愤青死党联句拼凑。不料这有如给贼赃贴上封条:“此地无银三百两”,不旋踵又给贼赃加写上“鼠辈润芝不曾偷”。
因为我们无法断定其中哪几句是毛所写,只好权且把它算作毛的作品,笔者重审该词,旨在给读者扫清迷雾,看透毛的真面目,并无剥夺毛的署名权之意,其实这首词 百份之百算是毛所写,并不能给毛增添了什么光辉,也不能显示毛有什么诗才,这一点读者耐心看下去即可明白。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