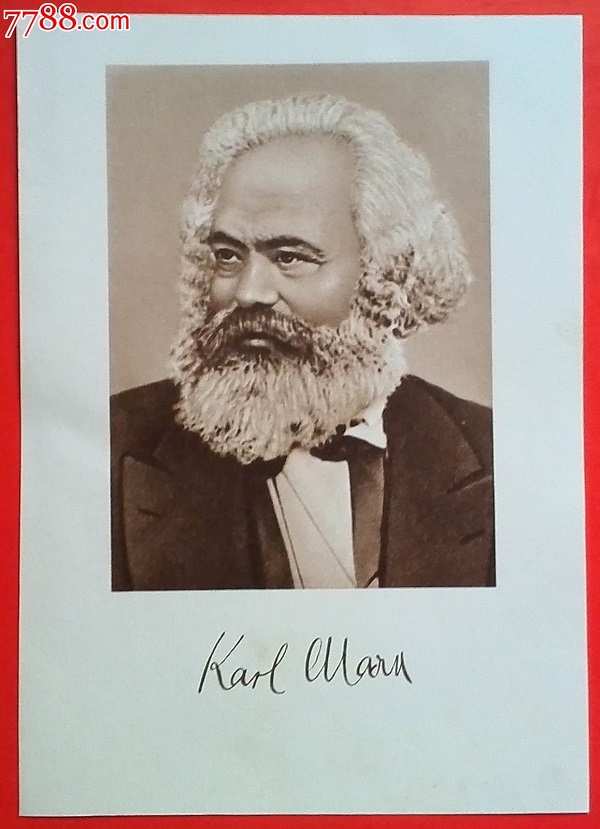——《共产主义神话与“新中国”.第二章》
13
马克思一直着期待欧洲大革命再次来临,并且总是乐观的认为革命就要来临。他之所以积极投入第一国际,即出于此,他欲打造一个庞大的国际性的革命组织,当革命到来时,投入其中,实行共产主义革命。
尽管马克思关于革命即将到来的预言,一再失实,然而1871年,革命真的到来了——巴黎公社起义。这是他久已盼望的革命,然而他是如何对待这场革命呢?
1870年,拿破仑三世向德国宣战。马克思以第一国际的名义发布了一个声明,主要内容是:谴责拿破仑三世发动战争;德国应战不应超过防御范畴。声明最后说:“法国和德国工人互通和平与友谊的信息。
单是这一件史无前例的伟大事实,就向人们展示出更加光明的未来。事实表明,同那个经济贫困和政治昏聩的旧社会相对立,正在诞生一个新社会,而这个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因为每一个民族都将有同一个统治者——劳动!”显然,马克思的乐观预言,与现实不搭界,属臆想。
1870年7月19日普法战争爆发,法国惨败;同年9月2日拿破仑三世宣布投降;9月4日,巴黎爆发起义,宣布建立第三共和国,成立“国防政府“。9月19日普鲁士军队包围巴黎。巴黎市民自发地组建了30万人的“国民自卫军”。10月31日,巴黎市民再爆发起义,旨在推翻共和制的“国防政府”,并提出巴黎自治的要求。关键时刻,布朗基号召人民群众支持政府,共同抗敌。起义无果而终。1871年1月28日,法国“国防政府”与普鲁士签订停战协定,放弃抵抗。而国民自卫军不接受政府投降,脱离政府,建立中央委员会,坚持抵抗。同年2月8日,法国国民议会举行大选,组建新议会,梯也尔被选为临时政府首脑。
1871年3月18日,梯也尔政府指令军队收缴国民自卫军占据的400门大炮,遭市民阻拦,指挥官勒康特将军下令开枪,但士兵拒绝开枪,转而哗变。混乱中,勒康特及另一名将军被杀。骚乱迅速蔓延。国民自卫军就势举行起义,占领市政厅及各要地。梯也尔带领政府、官员、企业家、贵族、军队、警察、教会等撤退到凡尔赛。巴黎为起义的市民所占领。3月19日,国民自卫队中央委员会发布公告,进行公社选举,让公社权力取代政府。3月26日,巴黎分区进行公社选举,96人当选为公社委员。公社委员会取代了国民自卫军的中央委员会。巴黎公社正式诞生。国民自卫军拒绝,并杀死了两名将军。梯也尔下令镇压,当巴黎爆发革命。马克思并未积极参与,而他和第一国际都是局外旁观者,对之没有什么影响。马克思在他撰写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中说“ 我们同他们一起为法国建立共和国而欢呼,但是同时我们感到不安……,这个共和国并没有推翻王位,而只是占据了它所留下的空位子。……组成这个政府的,一部分人是声名狼藉的奥尔良党人,一部分人是资产阶级的共和党人。”“ 由此可见,法国工人阶级正处于极困难的境地。在目前的危机中,当敌人几乎已经在敲巴黎城门的时候,一切推翻新政府的企图都将是绝望的蠢举。”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十七卷)可见,马克思在早是反对巴黎公社起义的。“按照奥地利社会主义者奥伯温德的说法‘在起义开始之后的两天,马克思写信给维也纳说它没有成功的可能性。”“看起来巴黎人似乎要屈服了。”(戴维•麦克莱伦《卡尔.马克思传》第七部分)
在巴黎公社存在的两个月中,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始终保持沉默。在巴黎公社成立的次日,马克思提议发布宣言《告巴黎人民书》,委员会让他负责,然而一个星期后,马克思说“已经不合时宜了”。直到巴黎公社覆灭的第三天。马克思才交给委员会一份宣言《法兰西内战》。(参见,同上)
马克思期待革命、盼望革命,等待革命时机之到来,然而当革命到来时,他则左右徘徊,置身其外。书房里的革命之堂吉诃德,成为了好龙的叶公。马克思是书房里的学者、知识分子、思想家,而绝非革命家。其无行为既无行的渴望,也没行的能力,多限于空想空谈。革命家是行动者,如布朗基、巴枯宁,无论对错,他们都为了其所认定的革命,抓住时机,舍生忘死,付之以行。比如此次巴黎革命中,当法军连连败北,布朗基便于八月中旬由布鲁塞尔赶到巴黎,策划武装起义,建立共和国。此举失败。9月初,拿破仑三世投降,第二帝国覆灭,第三共和国建立。当普军兵临城下,布朗基号召民众支持国防政府,保卫巴黎,一致抗敌;并组建国民自卫军,当选为169营司令。而当国防政府放弃抵抗,准备投降,布朗基则再次举行民众起义……;直至他被捕。
对于巴黎公社这样一场惊天动地的伟大“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仅是写了一篇评论《法兰西内战》。马克思作为共产主义革命的奠基人和领袖,面对这场革命,其反差是如此之大,可谓是全然“失职”。纵观马克思一生,除了1848年德国革命爆发后,其前去办了一年的杂志之外,未曾参加过任何实际的革命。马克思是共产主义革命的幻想家、虚妄家。马克思更像是诗人,生活在自己的幻想里,认定了一种意识,即不看现实。《共产党宣言》是他的共产革命的妄想;《资本论》作为一部经济学著作,成一家之言,亦有其独特的贡献,但是此著是先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然后按此模式建立其经济学理论。故此,马克思未能完成《资本论》,因为其理论的基本论点来于其意识形态,而与现实不能自圆。《法兰西内战》也是按照作者的共产主义革命的意识框架,去解释巴黎公社革命,而不合事实。与其说,《法兰西内战》是对巴黎公社事件的论证分析,不如说是作者借巴黎公社鼓励共产革命,并为之论战。
14
《法兰西内战》的光彩之处,是作者强烈谴责梯也尔政府对巴黎公社的残酷杀戮,特别是在巴黎公社的抵抗已被平息之后,梯也尔政府大规模摸底抓捕公社成员,并草率地处决,有学者统计估计有2-3万人被处决;数万人被监禁及流放。无论如何,如此残酷血腥的杀戮都是不可宽恕的。在巴黎公社被镇压后数日,马克思便面对“胜利者”发表严厉的抗议和谴责,这是他的亮点。但其基本论点乃是高扬其共产革命的思想。
1、简单化的阶级论
《法兰西内战》的第一句话就是:“1870年9月4日,当巴黎工人宣告成立共和国而几乎立刻受到法兰西举国一致欢呼的时候,有一伙钻营禄位的律师——梯也尔是他们的政治家,特罗胥是他们的将军——占据了市政厅。”之后又说,“巴黎战胜普鲁士侵略者,就无异是法国工人战胜法国资本家及其国家寄生虫。国防政府在民族义务和阶级利益二者发生矛盾的时候,没有片刻的犹豫便把自己变成了卖国政府。” 而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中,马克思这样论述《国防政府》“这个共和国并没有推翻王权,而只是占据了它空出来的位子。它不是作为社会的胜利,而是作为民族的防御措施宣告成立的。它掌握在一个临时政府手中;组成这个政府的,一部分人是声名狼藉的奥尔良党人,一部分人是资产阶级共和党人,而后者中间某些人的身上又在1848年六月起义时期留下了洗不掉的污点。……这个政府不只是从帝国那里继承了一大堆残砖断瓦,而且还继承了它对工人阶级的恐惧。”
当普鲁士大军围困巴黎,法国面临的是民族战争。在此,“国防政府”所代表的是法国国家、民族及全体人民,并非马克思所说仅代表奥尔良党人及资产阶级,新内阁就任宣言的核心是“拯救祖国”。
“国防政府”成立数日后,激进民间领袖布朗基即号召法国人民支持新政府,共同抗敌。他在《祖国在危急中》中,呼吁“在共同敌人面前应该消除一切分歧。”
马克思以阶级观看待民族、国家间的冲突,导致其对整个事件的偏见。他以为“工人”“无产者”是先进阶级,代表人类的前途,只有他们是好的,代表历史的进步;而任何国家的政权,无论是君主制的还是共和制的,都是坏的、反动的,都是阶级压迫,都应该被摧毁、剥夺,无论他们做什么,怎么做,都应该反对、谴责。
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的导言中说得更彻底:“实际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而且在这一点上民主共和国并不亚于君主国。国家再好也不过是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中获胜的无产阶级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有能力把这全部国家废物抛掉。”
马克思主义将人类如此困难、复杂的国家、民族、社会种种问题,简化为1+1的阶级论教条。按照这种教条,人民需要不断地造反、革命,凡国家政权就是阶级压迫,不论其好坏,即需要推翻,废除。如此,人类除了不断推翻国家政权之外,就再无其它事情该做。
1870年9月底,普鲁士军队包围了巴黎,一个月后,法国麦茨要塞,由巴赞元帅率领的17万法军,向普鲁士军队投降。俾斯麦断定:“只要巴黎几个礼拜没有咖啡和牛奶,便会不攻自破。”在普军围困中,巴黎走投无路,人们已经到了吃猫、狗,乃至老鼠的地步了,老人和孩子成批地死去。法国政府别无选择,于1871年1月28日,被迫和普鲁士签订停战协定,放弃抵抗,割地赔款。这本是国家屈辱无奈之举,但马克思斥责其卖国:“国防政府在民族义务和阶级利益之间的这一冲突中,没有片刻的犹豫便把自己变成了卖国政府。”(《法兰西内战》)原本是民族、国家之困境,马克思却将之视为本国家的阶级斗争。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中共对国民党的斗争采取的是同样模式,将国民政府暂时的防守或后退,斥责投降卖国,以维护大地主、资本家、官僚阶级统治。
1871年2月初,法国进行了国民议会选举,保守派大胜。在645个议席中,保守派占据了420席,共和派仅占145席,而最具声望的激进领袖布朗基则落选。这说明民意转向“恢复”秩序,革命诉求下降。以梯也尔为首的新临时政府,提出执政首要任务是:结束各派纷争的混乱局面,恢复和平与秩序。在当时的局势下,任何负责任的政府都会如此做,此是国家之大局,也是民意之所在。
马克思猛烈抨击了此届政府,包括对主要阁员,乃至对其私德。当然,其血腥镇压了巴黎公社,马克思难以抑制愤怒,可以理解。但是马克思指责其是“反革命势力”,复辟“昔日的千年王国”;“发动反对共和国战争”,“在外国侵略者的监视和卵翼下把对外战争变成一场国内战争——一场奴隶主叛乱”,(《法兰西内战》),则是主观臆断。
梯也尔政府之所以要收回大炮:一是防止激进的国民自卫军骚乱,爆发内战;因为在1870年10月,巴黎市民已经有过一次起义,加重了国家的危机和混乱;再是,防止国民自卫军用大炮攻击普军,破坏停战协定。况且国民自卫军已经脱离了政府的控制,成为巴黎一个失控的武装的政治及军事中心。在危机中,为了维护和平、恢复秩序,此乃政府必要之举,是国家、民族之大利;至于策略上是否得当,能否达到目的,另说。
而马克思谴责说:“巴黎投降了,和平了,这时新的政府首脑梯也尔不能不看到,只要巴黎工人手里还有武器,有产阶级——大土地占有者和资本家——的统治就时刻处于危险之中。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设法解除工人的武装。”“夺取大炮显然只是全面解除巴黎武装”,“武装的巴黎是实现反革命阴谋的唯一严重障碍。武装的巴黎是实现反革命阴谋的唯一严重障碍。因此必须解除巴黎的武装。” “于是梯也尔发动了内战”。(《法兰西内战》)梯也尔政府恢复国家和平与秩序之举,又被马克思解释为阶级斗争,并指责其为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而发动内战。
马克思以阶级论,将整部由普法战争所引发的巴黎革命事件,简化为工人阶级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间的阶级斗争。这种简化、教条化的意识模式贯穿了其后一个多世纪的世界共产主义革命与运动。
2、关于巴黎公社的性质
马克思热烈地赞颂了巴黎公社,将之视为工人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是新世界的曙光。他在《巴黎公社一周年纪念大会的决议》中写道“大会认为,英勇的三月十八日运动是把人类从阶级社会中永远解放出来的伟大的社会革命的曙光。 ”“……宣判了旧社会的死刑,不管旧社会的统治形式如何 —— 是君主制还是共和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十八卷)恩格斯在1891年《法兰西内战》的导言中说:“公社的最重要的法令,就是要把大工业以至工场手工业组织起来
……。这种这种组织工作,正如马克思在《内战》中完全正确地指出的,归根到底必然要导致共产主义。”
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说“这是使工人阶级作为唯一具有社会首创能力的阶级得到公开承认的第一次革命”,“工人阶级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满怀完成这种使命的英勇决心”,“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而为人所称颂。它的英烈们已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大部分公社委员,都是国际工人协会的最积 、最有见识、最刚毅的人物……这些人都百分之百地正直、真挚、聪明、忠诚、纯洁、狂热——正面意义上的狂热。” “我们的协会(指第一国际)只是文明世界各国最先进的工人之间的国际纽带。无论在何处、在何种形式或何种条件下,只要进行着阶级斗争,自然总是我们协会的会员站在最前列。”显然,马克思讲巴黎公社革命当作伟大的工人阶级革命,是共产主义革命的先声,甚至马克思将之当作是第一国际的革命。
“1871年3月18日清晨,巴黎被‘公社万岁!’的雷鸣般的呼声 醒了。公社,这个使资产阶级的头脑怎么也捉摸不透的怪物,究竟是什么呢?”马克思写到“公社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但是,无论廉价政府或“真正共和国”,都不是它的终极目标,而只是它的伴生物。”“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如果没有最后这个条件,公社体制就没有实现的可能,就是欺人之谈。生产者的政治统治不能与他们永久不变的社会奴隶地位并存。所以,公社要成为铲除阶级赖以存在、因而也是阶级统治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的杠杆。劳动一解放,每个人都变成工人,于是生产劳动就不再是一种阶级属性了。”“是的,先生们,公社是想要消灭那种将多数人的劳动变为少数人的财富的阶级所有制。它是想要剥夺剥夺者。它是想要把现在主要用作奴役和剥削劳动的手段的生产资料、土地和资本完全变成自由的和联合的劳动的工具,从而使个人所有制成为现实。” (《法兰西内战》)
马克思在这里,按照他的共产主义革命理论,来阐述巴黎公社;但这只是,他用巴黎公社来注释他的共产主义革命理论;而并非是巴黎公社原貌。
巴黎公社革命是市民革命,参与者的成分很复杂,包括店主、商贩、佣人、店主、雇工、游民、学生、主妇、知识分子、艺术家、职员、马夫、皮匠……。按照马克思共产主义革命的理论,“工人阶级”、“无产阶级”是指产业工人,而在这场革命中,产业工人很少。无论如何,都不能将巴黎公社定为工人阶级革命;此说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牵强附会。《共产党宣言》这样定义无产阶级:“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
1871年3月26日,巴黎进行公社选举,96人当选为公社委员。其中包括布朗基主义者、巴枯宁主义者、蒲鲁东主义者、激进的共和党人、改良派、雅各宾党人、社会主义者、女权家,还有工人、医生、记者、流亡者等等。这是一个庞杂的混合体,工人阶级既非主导者,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也并非是其纲领。
1881年,巴黎公社失败十年之后,马克思在致斐迪南•多梅拉•纽文胡斯的信中,全然颠覆了自己在《法兰西内战》关于巴黎公社的论断,说:“也许您会向我指出巴黎公社;但是,且不说这不过是在特殊条件下的一个城市的起义,而且公社中的大多数人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不可能是社会主义者。”(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三十五卷)显然,这段论述倒更合乎事实。
巴黎公社革命,更多地属于无政府主义革命。当然,这里的“无政府”并非是汉语的字面意义,而是指安那琪主义(Anarchism)。其强调个人自由与人际间的平等,反对国家、政府的权威统治,而主张社会群体的自治。
首先,巴黎公社是继承了法国大革命的精神:自由、平等、公民权利。巴黎公社中央委员会在1871年3月24日公报中宣布:“巴黎不想统治,但它向往自由。除了靠自己的榜样,它没有独裁的野心。……它通过确立自己的自由而为别人准备条件”(赵京《巴黎公社的精神》)自由、平等、公民权利,是法国大革命的精神遗产,也是巴黎公社的最终的政治要求,其起义,推翻现政府,废弃国家统治机器,均是为了实现此目的。
巴黎公社不同于法国大革命的之处,乃是创造了“公社”的社会组织形式。而“公社”正是蒲鲁东主义始终的社会梦想,废弃国家、政府、统治机器,在保障个人自由的前提下,人与人组织成互助的社群,自由、自立、自治。“公社”正是按照蒲鲁东主义的理想,而建立的。马克思如此热烈地赞颂“公社”,将之当为未来共产主义的原则和社会组织形式,是自由、平等、民主的最高形态。这也就是其称巴黎公社“为新社会的光辉”的原因。显然,就社会的终极形式,马克思回到了蒲鲁东那里。
那么,马克思和蒲鲁东主义的区别到底何在呢?主要有两点:一是武装暴力革命,二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也就是马克思批判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即“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法兰西内战》)无产阶级必须用革命暴力“摧毁”和“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以革命的暴力镇压、消灭旧势力的反抗。马克思认为,由于巴黎公社“浪费了宝贵时间”去组织民主选举,而不是迅速地去消灭凡尔赛的军队,而且也没有没收法兰西国家银行的资产;因而导致“公社”失败。何为“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这里说的很清楚。虽然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没有明确地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但是文章中表达了这个意思。1871年9月,也就是在巴黎公社失败数月后,马克思在《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中,说“在过去发生的一切运动当中,最近的和最伟大的运动是巴黎公社。巴黎公社就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关于这一点不可能有任何异议。”“公社未能建立起阶级统治的新形式。……必须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可能实现这种变革,而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工人阶级必须在战场上赢得自身解放的权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十七卷)
1875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特别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主要是吸取了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他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巴黎公社的第一条令是:“废弃旧的国家机器——包括废除征兵制,常备军、警察和法院。”这是巴黎公社的核心所在,是其最广泛地获得自由、民主、公民权利的前提。此理想可以理解,但是乌托邦的幻想。
蒲鲁东主义的合作社,保障个人自由,成员平等合作,实行自治,民主管理,这在许多国家已经实现。在欧美民主国家,有种种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但前提是有国家和制度的保障。如果此类合作社有效运作,真正做到保障个人自由,成员平等合作,实行自治,那么其规模就不能太大,而且其秩序的保障要依靠每个成员的道德自律。群体的规模越大,则道德约束的指数便越低,而越发地需要以强制的力量——如法规,来保证群体内部的秩序。再而,如果社群与它社群发生冲突,将如何解决?因此也还是需要高于其上的法律给予评断、裁决。人类原始形态,一个部落占有一片地域,自立自治,自然无需国家,但是如果其遇到强大外地的攻击,那么就需要联合其它部落共同抵抗。国家由此而形成。国家并不是人性所需,但却是人类生存现实所需。而国家一旦建立,就需要整套的国家机器,政府、军队、警察、司法、税收等等。其即是对国民安全及社会秩序的保障,也是对国民的负担、约束和强制。由自由而言,人受制于国家,由此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的废弃国家的观念有其道理。但是,在人类发展的一定阶段,起码是我们多能看到或预测的时间内,国家这一人类生存的形态尚是无法摆脱的。当然,在人类历史上,国家也正是人类无数灾难、战争的根源。国家不是好东西,但只能如此。我们无法设想,一旦废弃其国家,人类将是什么样子?大致会是无边的暴乱和杀戮。由此,巴黎公社本质上也还是乌托邦性质的,这乃是其失败的根本原因。
马克思与蒲鲁东主义之间还有一个差别,就是蒲鲁东主张小合作社,成员间能切实做到互助与合作,而马克思主张的是所有的合作社联合成一体,整个国家、社会组成共产主义公社。这等于说,推翻旧国家,砸碎其旧国家机器,然后建立一个名为“公社”的新国家,重新建立一套新的政府、军队、警察、司法、税收机制,而它的新的统治者则是“无产阶级”。群体一定形成到一定的规模,便需要制定法规,建立稳定的秩序,并需要具有经验的专门职业人员来管理,这就形成官僚阶层。理想中的,官员可以由民众随时免职,及选举新官员是没有可能的。特别是,按照马克思所说,这是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阶段。于是我们就回到了在前文章所引用的拉吉斯在《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的论述:职业革命家——革命领袖建立党,凝聚革命骨干,带领人民暴力夺取国家政权。他们代表人民统治国家,由此“创造”出一个“新阶级”——高于人民之上的掌有特权的统治集团,即官僚集团,其以集权方式统治国家、社会及人民。在“新阶级”统治下,人民不仅都沦为无产者,而且彻底丧失了自由。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