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陈子明先生是中国著名民主人士,曾经在1975年因为议论时政被开除学籍,并定性为反革命。1979年,他出任《北京之春》编委,并在1991年因被指是八九学运的“幕后黑手”而被中国当局判囚13年,虽然后来曾获保外就医,但随后也长时间被软禁家中。2014年10月21日,陈子明因病在北京去世。本访谈录是陈子明生前接受台湾中央研究院研究员陈宜中专访的内容。BBC中文网获得授权连载发表有关专访的全文。
陈宜中(以下简称“问”):您在1994年保外就医期间,提出了“中国政治反对派”、“理性、负责任的建设性反对派”概念。您还特别阐发了“民主运动要立足主流社会”。陈子华在〈我所知道的“社经所”〉(附录于《陈子明文集》第十二卷)中,曾对您的政治反对派理念做出概括,其中有段话是这么说的:“当前,政治反对派可以做以下五个方面的事情:政治对话、时政批评、立法倡议、历史撰述和筹备参选。反对派要积极主动地提出每一个时期国家发展的重大议题,通过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管道,展开严肃认真的政治对话。反对派人士要根据每一个人的兴趣与专长,自然而然地产生出自己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理论各个领域的发言人,对政府和执政党的各项政策以及现行体制的各个方面进行评论,公正地肯定其进步和成绩,不留情面地抨击其弊端和劣绩。反对派应着手拟定自己的外交政策、国防政策、经济政策、国土开发和环境政策、教育政策、科技政策、民族政策、宗教政策、港台政策,等等。反对派还应当帮助成立一个『学校教科书编辑委员会』,研究设计能够取代普通教育与高等教育基础课中人文学科现行教材的新体系和新教材。反对派人士要在中国的法制建设中发挥自己的独特作用,通过各种方式提出立法动议,拟定法律草案。反对派人士要珍惜自己的政治传统,积极撰写自己的历史和当代中国社会的历史。反对派要对改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修改选举法提出自己的意见,并制定近期和中远期的竞选纲领和竞选策略。”
我想,这应该就是“建设性的政治反对派”的具体所指?
陈子明(以下简称“陈”):这确实就是我的思路。陈子华的概括是根据我在1994年第一次保外就医时写的两篇文章:〈中国的民主:从说到做〉和〈1995年的中国政治反对派〉(载《陈子明文集》第四卷)。
问:您2002年出狱,2006年恢复政治权利后,不带头从事公开活动了。现在您是个体户?
陈:我现在没有去挑头做什么事,虽然也有人希望我做。我刚出狱时,刘晓波希望我挑头做,但是我说你做的已经挺好了,就不一定非得我来干。
是这样,我觉得在中国宪政民主运动的阵营中,应该要有多种可能性的备案。至于最后是谁出来,都是可以的。如果将来是台湾式的转型,就需要一种跟体制内有对话能力的、也有信誉的人,否则凭什么跟你对话?这个并不是你的问题,而是别人的问题。
我不会提很激烈的要求,但却是很坚定的人。只要是我提出来的事情,是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我希望能持续保持这样一个影响,就是说,搞政治的人是需要有信誉的,不能今天这么说、明天那么说,让人家都不知道你的意思何在。我陈子明就是三条:第一条,我是一个中国人,一个维护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人;第二条,我是一个坚定不移的自由民主主义者;第三条,我是建设性的政治反对派,我跟共产党的基本理念不一致,但我是可以对话的反对派。从1980年代、1990年代到现在,我的政治定位一直是这样。

宪政民主
问:您说“民主运动要立足主流社会”,这个提法似乎假设了一种非革命的民主过渡,就是一种比较渐进的模式,在过程中逐渐培育出中国宪政民主的思想力量、社会力量与政治力量,在所谓的“公民社会”中持续扩大阵地。
陈:我主张走一条立足于公民社会的宪政民主道路,这可以说在1980年代中期就确定了。当时,我对自己团体的性质有过描述。我在接受《新闻周刊》记者白凯柔采访时表示:我们愿成为促进中国知识分子分流(即不要挤在进体制当官的独木桥上) 和追求独立性的先行者。我们的基本目标是:扎根民间,推动中国公民社会的形成与发展,进而推动政治体制的变革。
我出狱后这几年,一些朋友凡是做了乐观估计的,说三年变化、五年变化的,到目前为止都是破产的,而且也都是被打压得比较厉害的。所以我是不会轻易说具体年头的。但是我又有一个看法:中国的变化是加速度的,不是均速的,而且愈接近临界点,变化的速度就愈快。由于是加速度的变化,所以看不清楚,好像暂时不会变,但是也可能很快就变了。
问:您在最近一篇文章中,重新阐释梁启超和章太炎的“革政”思想,说当前所谓的中国模式正在催化政治革命,而为了避免革命的代价,就需要“以革政挽革命”。您提出的“革政”思路,是否暗示修宪或立新宪?.
陈:现在已经不得不对宪法动手脚了。1982年的新宪法是主流文明以外的一部怪异宪法,这宪法本身不具有宪法的性质,它对于人民和政府的关系,政府各部门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都没有明晰的界定。我认为,州(地级市)这一级在中国发挥很大的作用,但是宪法上没有地级市。按宪法,中国现在只有省市自治区,下面就是县,然后就是乡镇。但比如说苏州,从财政来看,苏州市根本比青海和宁夏大很多,如今不可能再否定掉这个层级。财源都是往市集中,从县往上提,从省往下放,重点都放在市。市这一级再不承认,是不可能的。
我们当然要讲宪政的人权、限权、分权,但是也要讲国家建设的具体面、具体构想。这些年来,我两方面的问题都在讨论,包括一本五十多万字探讨地方自治和地方行政的专著(收于《陈子明文集》第七卷)。北京大学出版社曾想出这本书,我也准备用别的名字出,但是中宣部告诉他们这是陈子明写的,他们也就没敢出了。但是一章一章的,都在杂志上出了,很多人引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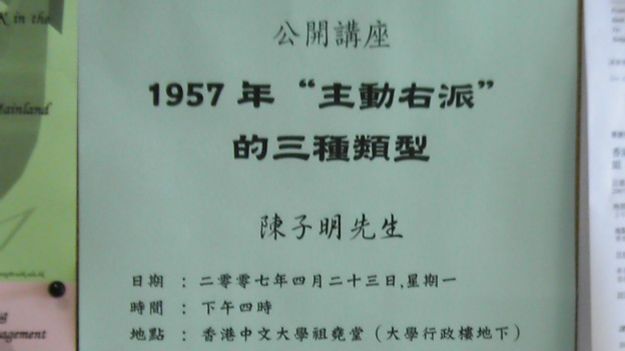
社会公正
问:您怎么看当前的社会公正问题?
陈:1997年秦晖的《天平集》出了以后,我写过一篇书评,我认为宪政民主派有必要强调社会公正,不要让这个旗帜被毛派给抢过去。我主张宪政左派和宪政右派形成联合阵线,主要也是针对这个问题。在宪政民主派当中,必定有些人更关注公正问题,有些人更关注自由议题,现在强求一致是没必要的。如果说政治局面发生变化,可以组党竞选了,那么,在形成竞选联盟的时候,就需要有更清晰的旗帜和口号。现在大陆还没走到那一步,还没有面临选举的问题。目前,宪政民主派涉及的话题多一点,涉及的面广一点,整个阵地就更宽阔一点。
问:您所谓的宪政左派跟宪政右派,以我理解,指的应该是在社会公正与经济公正问题上,有些人偏中左,有的偏中右,彼此之间总会有些差异,但都共同接受宪政的基本价值,包括法治、基本自由及其他宪政权利。可是,虽然您曾把部分新左派也列为宪政左派,他们却不见得接受宪政民主。
陈:这里头有个演变过程。我自己后来写文章也说过,2008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对于“新左派”的定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们2008年以后的东西,几乎完全是国家主义,没有任何左派的味,只能叫新右派,不能叫新左派。世界经济危机给了他们一些动力,让他们相信国家主义的路子是对的。
秦晖在一篇书评里说过,说我是有一些政治考虑的,所以比较强调联合的可能性。我不否认这一点。.
问:在更年轻的大陆自由主义圈子中,左右联合的提法似乎不太有吸引力。
陈:这些自由派应该说是学理派的,不太有政治考虑,也不去思考联合阵线的可能性。他们还是觉得,凡是理论上跟我不一致的,我就应该抨击他。
宪政当立
问:“宪政当立”的主张,在您的设想中,该如何兑现?
陈:“宪政当立”有很大的支持度,这样的呼唤已有十年以上的历史了。赵紫阳晚年谈宪政和议会民主制,谈反对派的必要性,说反对派政党的存在是中国将来不出现国家分裂的一个要件。这些问题,赵晚年都认识到了,而且也有所表述。李源潮和李克强当省委书记时,也曾经谈过宪政。现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层,接受宪政观念并不难,只是要在压力下才可能朝这个方向前进。这些年来,体制外的民运人士也好,异议分子也好,维权人士也好,对于“希望在民间”已经是很清晰了。就是说,即使体制内会有变化,它也是一种反馈。如果体制外的民间力量不够大,达不到某个程度,也不可能希望体制内会走在你的前头,主动去提出什么平反六四、修宪、开放竞选啊。
问:您所谓的修宪,是指朝向宪政民主迈出一大步的阶段性修宪吗?在2013年11月的三中全会之后,您怎么看“革政”(宪政民主变革)的前景?宪政当立,但是在当前时局下,该如何努力?我想这是海内外和两岸很多人的困惑。
陈:“革命”一词现在被滥用了,从技术革命到暴力革命,意思已经很不一样。我讲“革政”是要突出“政体革新”这个意思,就是要打破现行政体(极权也好,后极权也好,威权也好),实现建立宪政民主新政体的目标。“革政”不排斥任何手段,从明治维新式的到辛亥革命式的,到台湾民主转型式的,到东欧“天鹅绒革命”式的。
2013年11月的三中全会前后,我发表了许多评论文章,对之持否定态度。中共新领导人的毛式话语(群众路线等),关于六十年一贯制的话语,是拾了1990年代新左派转变成的21世纪新国家主义派的牙慧,是对1980年代的时代精神的一种背叛。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有人说,说一套做一套才是有智慧的政治家,但我认为这是文人一厢情愿的捧臭脚。反对普世价值的政治家,只会成为中国的希特勒。薄熙来就是前车之鉴。
中国民间社会现在应该要强调独立性。当执政者没有表现出“革政”意愿时,必须对之持坚决反对和严厉批判的态度,同时积极发展自身的实力,联合、扩大反对派阵营的社会层面。
修宪与立宪,这两种可能性都是存在的。关键在于社会力量的对比。

政治反对派
问:在中国大陆,部分年轻的自由派(或反对派)对体制内政改已不抱期盼,转而寄希望于毕其功于一役的民主革命。有些青年激进派声称自己才是真正的政治反对派,说要告别公民社会,这跟您的反对派理念似乎渐行渐远?您如何理解近来的这些发展和争议?
陈:由于中国官方日益保守化,一部分自由民主派的激进化就是一个必然的回应。宪政阵营有一个从偏左到偏右,从激进到温和的广泛光谱,我认为这个光谱愈宽愈好。只要激进派不把温和的宪政派当做主要敌人(这是一种列宁主义的做派,列宁把社会民主党的中左派考茨基视为最危险的敌人),我对他们的奉献和牺牲表示敬佩。
建设性政治反对派不是四平八稳的意思,政治反对派首先是反极权、反专制、反法西斯化。当执政者没有对话意愿时,反对派整天喊对话是没有用的,你要用实力来迫使执政者对话。当执政者被迫对话时,你要有接招的能力,这就需要你有治理国家的对案,否者就会出现俄罗斯的情况,转型后的政权落到前克格勃(KGB)集团的手里。
“告别公民社会”这个说法是错误的。王绍光、胡鞍钢反对公民社会,中宣部、国安部与政法委反对公民社会,你为什么要和他们站在一起反对公民社会?公民社会的发展壮大,是政治反对派发展壮大的前提条件。不能说长期处于社会边缘的人才是真正的、纯粹的政治反对派,只有当更加广泛的社会阶层(从农村上访者、城市维权者、民间宗教组织到律师、记者、学者、民营企业家……)纷纷成为政治反对派,你才能撼动现行体制。
台湾对大陆的影响
问:台湾在中国大陆的政治转型过程中,能起到任何积极正面的作用吗?这篇访谈主要是就大陆谈大陆,几乎一路都没有提及台湾。在访谈结束前,能否请您也对本刊的台湾读者说几句话?关切大陆政治转型的台湾读者愈来愈多,但普遍有一种自顾不暇的无力感。
陈:台湾在中国大陆的政治转型过程中,已经发挥了积极正面的作用,将来会有发挥更大作用的空间。
首先,台湾起到了榜样的作用。台湾的经济腾飞,是邓小平经济改革的借鉴对象之一。台湾的民主转型,给予大陆政治反对派许多宝贵的启迪。应当说,由于大陆当局的出版封锁,大陆民众对于台湾民主转型的经验教训还十分缺乏了解。
其次,台湾起到了援助者的作用。六四以后,台湾朝野始终在精神上支持大陆的民主运动,对于大陆流亡者也给予了一些实质性的帮助。
还有一点,台湾可以成为大陆政治转型的直接当事人,今后愈来愈多地扮演对话者的作用。中共从来都只跟有实力的人对话,而台湾是有实力的——既是国际民主大家庭的一员,也与大陆宪政民主派心心相映。台湾不要小看了自己。台湾自保的最好办法,就是提出“民主统一”,迫使中共放弃专政,制定符合普世价值的新宪法,或者回归中共曾经参与制定的民国宪法。台湾只要坚持自由民主的理念,在基本政治原则上不妥协,甚至采取更进取性的姿态,就可以在大陆政治转型中起到关键性的推动作用。
来源:BB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