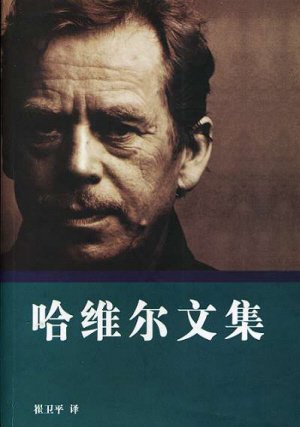他强调道德的政治,即他所说的“反政治的政治”,强调对具体人的尊重,“强调从恢复个人的尊严道德开始冲击极权主义无所不在的控制”,努力对荒诞现实进行解构,试图以理想的奋斗让政治回归人文道德的轨道。
在中国知识界文化界,提起捷克,大多数人可能知道卡夫卡或者米兰·昆德拉这两位文学家,剧作家哈维尔很少有人知道。知道的,很可能是仅作为政治家而且成功了的哈维尔。可以说,在当今世界的国家政治领导人中,曼德拉、李光耀和哈维尔(Vaclav Havel,1936-2011)是当之无愧可以冠之“思想家”的。哈维尔从剧作家、民运领袖到捷克斯洛伐克民选总统和捷克首任总统,他的一生大多数时间在被监视被监禁和自我流放中,对他来讲,专制政治下的现实社会是荒诞的,而自己的理想追求是坚定的和清醒的。他用戏剧表现荒诞的现实,批判剖析并思考,而用身体力行来探索未来国家生活的文明生态。由于相同的前社会主义背景,中国知识人读这本书会觉得格外亲切、格外深刻和格外有震撼力穿透力!
作为一个当代东欧专制政治体制下的“持异议者”,哈维尔在批判极权主义统治荒诞的同时,也深刻思考欧美现代民主体制的缺陷及某些“民主援助”的虚假性。他既是一个孤独的人文思考者,也是现实文明政治的探索者。他强调道德的政治,即他所说的“反政治的政治”,强调对具体人的尊重,“强调从恢复个人的尊严道德开始冲击极权主义无所不在的控制”,努力对荒诞现实进行解构,试图以理想的奋斗让政治回归人文道德的轨道。李慎之先生认为哈维尔“最大的功绩就在于教导人们如何在后极权主义社会尊严地生活,做一个真正的人”。徐友渔先生强调哈维尔“斗争的目的是人性的回归”。
捷克是个小国家,但我们从哈维尔的文字中感受到一个小国家小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强大的精神张力,以及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担当气魄!哈维尔书中言:“自信并不是自负。恰恰相反,只有真正自信的人或民族,才能倾听别人,平等地接受他人,宽恕其敌人和为自己的罪过感到悔恨”。(《1990年新年献辞》,p189)“我不采纳任何意识形态或教条主义,不管是左派的还是右派的,以及其他任何对于这个世界封闭的、事先准备好了的推论体系。与此相反,我总是试图独立地去思考,运用我自己的理性权力,并且极力抵制种种将自己束之高阁的诱惑。我感到自己随时准备接受有意思的和有说服力的每件事情,随时准备吸收新的观念和将它们纳入自己的世界图景”。(《我相信什么》,p204)“在某种意义上,那些围绕着有关国家建设技术性方面的混乱临时的活动,对于让我们偶尔记起国家的含义也许不无裨益,即国家必须保持真正的人性,换句话,国家必须是有精神、有灵魂和有道德的”。(《政治、道德与公民性》,p202)“而我最讨厌的还是将自己看着一个处于中心的人物,将自己置身于某个地形学上的位置是荒诞的,这更多地因为虚构的中心位置完全依赖于所采取的某个角度”。(《我相信什么》,p204)“我赞同‘反政治的政治’这种提法,也就是说,政治不再是权力的伎俩和操纵,不再是高于人们的控制或相互利用的艺术,而是一个人寻找和获得有意义的生活的道路,是保护人们和服务于人们的途径”。(《政治与良心》,p136)“恰恰欧洲和西欧,提供了和强加于这个世界的已经变成这种权力基础的这样一些东西:自然科学、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工业革命和类似于这种革命的那种幻想的抽象性,通过将‘本来的世界’赶到浴室而代之以对消费、原子弹、某些主义的崇拜。也正是欧洲――民主的西欧,今日正面对这种矛盾的输出而感到困惑”。(《政治与良心》,p128)“有人试图将我们在这个国家所做的事情,搬到民主社会政治辩论的语境中,通常是可笑的”。(《无权者的权力》,p70)“那些死守着传统议会式民主政治概念不放的人,他们迷信唯有这种‘久经考验’的民主才能保障人类永久的尊严及人在社会中的独立位置,依我看是非常短视的”。(同上p97)“像‘社会主义’一样,‘资本主义’也是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加以推广和庸俗化的一个概念,我看不出为什么我必须接受它,尤其是对这个概念不费力气地加以运用,是一种喜欢接受类似的意识形态标签而使生活简单化心理的典型,并且还和许多具有危险的文明现象联系在一起,它们并不在我的框架之内”。(《我相信什么》,p205)“我们的行星很小,是一块相当适合生活的地方。如果命中注定要在这颗行星上生活在一起的人们忘记了这一点,无视对人类同胞的爱乃是所有正处于竞争中的文化的核心戒律这一事实,那么,它就会成为所有行星中最荒诞的一颗”。(《在堪培拉国际出版俱乐部的演讲》,p254)
深刻的现实剖析和理性认识是哈维尔及这本书的最大特点和显著成就。哈维尔将他成年经历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家时代称之为“后极权社会”,(post-totalitarian system;《哈维尔传》的作者英国著名政治学者约翰·基恩则称之为“晚期社会主义”late-socialism;李慎之先生认为应该是later-totalitarian system,相对于earlier-totalitarian system,相当于中国的前汉与后汉之分)是一种“熵”的制度:“一种‘熵’的制度在其自身影响的范围之内,拥有一种增长熵的总量的手段,即通过抓紧它自己的中心控制,令自己更加坚如磐石,将社会禁锢在一件只有一种尺度控制的紧身衣中。伴随着在这个方向上采取的每一个步骤,它不可避免地也使自己的熵增殖”。(《给胡萨克总统的公开信》,p24)
哈维尔对后极权主义制度的特征这样分析和描述:“后极权社会的特征是缺乏正常的社会生活,因而无法预测任何意义深远的政治变化”。(p95)“后极权制度是现代人类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一个侧面,由于其极端性质,把问题的起源暴露得更加清晰。后极权制度的自动性不过是全球技术文明自动性质的极端表现,它所反映的失败不过是现代人类普遍失败的变体”。(《无权者的权力》,p96)“在极为简捷的意义上,可以说后极权制度建立在独裁统治和商品社会之间历史性遭遇所提供的基础之上”。(p61)“这个国家由千人一面的官僚们所支配,这些人声称坚持革命的意识形态,但却仅仅想着他们自己,他们已经不再相信任何东西,原来的意识形态已经变成形式化了的仪式,它给他们提供一种其内部联系的语言”。(《故事与极权主义》,p165)
哈维尔指出:这种制度下社会的核心特征是深层次的恐惧!“而今天的制度仅仅是建立在少数统治者自我保存的本能和被统治的大多数人的恐惧之上”。(同上,p28)“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制度被称之为专制制度,更确切来讲,是一种操控了经济、社会地位的政治官僚制度”。(《无权者的权力》,p49)“这里的基本原则是,权力的中心就是真理的中心”。(同上,p50)“这个制度为人民服务仅仅在这样的限度上,即必须保证人民将为它服务”。(同上,p54)
在《给胡萨克总统的公开信》中,哈维尔全面描述和深刻剖析后极权社会的恐惧与荒诞:“一个全都联合起来的社会给予其政府以全部支持。对任何不带偏见的观察者来说,我想其回答是不言而喻的:他们被恐惧所驱赶”。“因为恐惧失去自己的工作,中学老师讲授他并不相信的东西;因为恐惧自己的前途,学生跟在老师后面重复他;因为恐惧不被允许继续自己的学业,青年人入团和参加不管是否必要的活动;在这种畸形的政治信誉的制度下,因为恐惧他的儿子或女儿是否取得了必要的入学总分,使得父亲采用所有义务的和‘自愿’的方式去做每一次被要求的事。因为恐惧拒绝的结果,导致人们参加选举,给被推荐的候选人投票,并假装他们认为这种形同虚设的走过场是真正的选举;出于对生计、地位或前程的恐惧,他们不得不投票赞成每一项决议,或至少保持沉默;是恐惧使得他们经历自我批评、赎罪、不光彩地填写一大串丢脸问题的令人羞辱的行为。恐惧或许有人会告发他们,将他们驱逐出现存社会,他们通常在私下里表达他们真实的想法。在大多数情况下,使得劳动者以他们名义的所谓‘工作义务’,是那种恐惧忍受经济倒退、努力想改善自身和为了讨好权势者。实际上,同样的动机也隐藏在建立‘社会主义劳动突击队’的背后,存在于这种清醒地意识到它们的主要功能是在给上级的合适的报告中被提及。恐惧导致人们出席各种官方的庆祝会、示威和游行。因为恐惧被从正在进行的工作中驱赶出来,许多科学家和艺术家效忠于他们事实上并不接受的观念,写他们不同意的或明知是虚假的东西,参加官方的组织和参与他们认为是几无价值的工作,要不歪曲和删改他们自己的作品。在保存自己的努力中,许多人甚至报告恰恰是他们自己对被报告人做的那种事情”。(p8-9)
其次,人与制度关系方面的论述深刻而精辟:这本书的英文名称是《The power of powerless》,《无权者的权力》是这本书中最能体现哈维尔思想特色的文章。其实,人与制度的问题是后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人强调公民性和现代性,认为没有现代公民素质,再好的制度也发挥不了作用;而有人则呼喊没有制度的文明就不会有国民的文明。这个问题似乎变成了鸡与鸡蛋的先后问题。哈维尔在这方面的认识有助于提升现实分析。他将后极权主义制度称之为“压力等级制度”:“后极权主义制度的本质之一是将每个人纳入其权力领域,如此他们便不能意识到自身是人类成员,而可能放弃自己的人类身份而认同制度的身份,即他们也许变成制度普遍的自动作用的代理人和它既定目标的奴隶,他们也许加入到制度的普遍指令,他们也许被拖入和上其套圈,像靡菲斯陀勒斯对浮士德所做的那样。更有甚者,他们或许通过自己的卷入创造了一个普遍的规范,这样给他们的公民同伴施加压力”。(p59)“十分简单地说,每个人帮助其他人服从。在一种制度的控制中两者都是客体,但同时,他们又是它的主体。他们都是制度和它的工具的牺牲品”。(p58)“我们所有的人――当然是在不同程度上――得为这个极权主义机器的运行承担责任;我们当中没有人仅仅是牺牲品,我们也都是它的共谋者”。(《1990年新年献辞》,p187)“意识形态是与世界联系的华而不实的途径。它给人们提供那种有关身份、尊严和道德的错觉,同时更容易地将他们和这东西分开来。┅意识形态最初的辩解功能,成为提供给后极权主义制度的受害者和栋梁双方一种幻觉:这制度是和人类秩序及宇宙秩序相和谐的”。(《无权者的权力》,p52-53)“对他们来说,接受具有谎言并处于谎言之中的生活便已足够。由于这个突出的事实,个人巩固了这个制度,实现了这个制度,创造了这个制度,是这个制度”。(p55)“人类成员被迫和一个谎言生活在一起,但是他们之所以能被被迫因为事实上他们仅仅能够以这种方式生活。因此不仅是制度异化了人性,而同时,异化了的人性也支持这种制度,将其作为它自身无意识的意图,作为其自身堕落的一种堕落意图,作为人们丧失自身的一个记载”。(p59)“发达的极权主义赖以建立的操纵手段如此精致,如此复杂和有力,以致它不再需要谋杀凶手和牺牲品。甚至不需要因为有着一个更好前途的梦想而散布不满的火热的乌托邦建设者。‘现实的社会主义’这个名词,是这个时代自己杜撰出来的,它强调了这样一点:在这里梦想者已无容身之地”。(《故事与极权主义》,p163-164)
现代社会,制度与人已经没有天然的联系,所处的制度环境未必是自己或祖先创造的,很可能是别人移植或强加的。文明社会要求两者的建设与发展都应该以人道人文作为基础。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被公认为“十年浩劫”,然而,经历过的人都成了受害者,连发动指挥的也成了“被蒙蔽”的受害者!而绝大多数真正的无辜受害者却已不能说话了。对于今天仍然活着的“文革”经历者,也许本书中哈维尔的朋友、波兰民运领袖《选举日报》主编亚当·米奇尼克的比喻能给予启发:“如果你在妓院中工作了十年,你还将自己当作一个处女,这是不合适的”。(p297)
有人将思想家分为刺猬型和狐狸型,可以肯定,哈维尔绝不属于后者。作为“流放者的归来”、“魅力型领袖”,他书中以下论述是经典的,是需要思考辨析的。
“冷漠和放弃是人类跌入虚无的最严重的形式”。(《狱中书简》,p116)
“世界的迷失仅仅在我自身迷失的范围之内”。(同上,p119)
“一个沉默的伙伴,尽管你敢肯定当他开口时将像敲钟一样清晰,但却从来不能预言他什么时候开口和他将要说什么,他将比任何事先预料到的人原有能力搅动这个世界”。(同上,p121)
“现代化不应该由服务于‘科学世界观’的农学家或官僚所代表和推行那种非个人的客观科学,实际上那是一种妄自尊大、骄横、不可一世的粗暴侵犯”。(《政治与良心》,p125)
“制度、意识形态和党政机构剥夺了人们的良心、常识和自然的谈话及实际的人性的内容,这对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是一样的”。(《政治与良心》,p128)
“自由和民主包含参与,因而是所有人的责任”。(《1990年新年献辞》,p187)
“政治不仅仅是一门模棱两可的艺术,它更可能是一门坚持原则的艺术,一门改进世界和我们自身的艺术”。(《1990年新年献辞》,p189)
“人性的首要任务是为更为人道的生活创造条件”。(《无权者的权力》,p76)
“民主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因而是一种改进的能力”。(《在堪培拉国际出版俱乐部的演讲》,p252)
“几乎没有一种文化不是源自这样一种信念,即在我们不可及之处,还存在着一种更高的、神秘的世界秩序,一种万事万物源出其中的更高的意图,一种记录着所有事件的更高的记忆,一个我们大家全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负有责任的更高的权威”。((《在堪培拉国际出版俱乐部的演讲》,p249)
“再也不把文学拉到法庭面前受审”。(《后共产主义的奇特纪元》,p235)
“与极权主义制度相比,民主秩序本来就是非结论性、不确定、松散和不十分强有力的”。(《后共产主义的奇特纪元》,p225)
“从道德的观点看来,即使只有一个无辜的人成为这项法律的受害者,我也认为这是一项坏的法律。因此,准确地说,不能运用一种集体罪责的原则而只能判断每个人的具体行为”。(《后共产主义的奇特纪元》,p219)
“激情澎湃和唯理性的乌托邦不过是同一枚钱币的两面”。(《对沉默的解剖》,p151)
2015-3-18于峻修堂书斋
来源: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