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果兄很有个性,在纽约会上上台责问潘国平刘国凯等造反派:“你们知不知耻?”但这回读了他的回忆,原来他也有过一个“造反-逍遥”的转变,可是最后还是入了牢笼,关了三年,这就是共产党要缠你,你躲也躲不了的。他说“虽然当时我没有读过萨特的书,但已经提前进入了现代派”,我看“现代派”就是“精神造反派”。
再说我自己,我们原来在四川荣昌中学教书的华东师大毕业的“三学士”,和体育老师杨洪锦、徐启富(女)带了亲信学生刘长春、刘志华、陈德荣,组织了一个“红旗战斗队”远行串联,即如胡锦涛、万润南游山玩水,一路到了上海,我们就滞留不归,到了一九六七年二月,接到小亲信们来信说杨洪锦被捕,徐启富揭发了我们许多鸡毛蒜皮的事情,于是我们就害怕了,就从上海到北京去打听消息(而已)。
在地质学院碰上几千四川造反派,又在西苑饭店(国务院招待所)里吃白食,见到了宜宾反李井泉的老干部刘结挺张西挺,又看了斗争了五十四军参谋长耿志刚的热闹,有一个重庆工人把他的军帽上的红星扯掉,我检起来,后来还给他。耿志刚好像是个大学生,长相很象高文谦,他对我说:“要说受压,我在部队里就是受压的,镇反抓人不找我,到北京开会,就让我来遭罪。”那时部队里知识分子吃不开,文革后耿志刚先当军长,后来好像还当过一阵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后来,杨洪锦出了狱,已经是五月分了,回四川时有中央文革撑腰,我们也没想干个啥,可是那些保皇派很可恶,老缠着我们,说我们是“牛鬼蛇神翻天”,还老把杨洪锦哥哥在台湾当空军,扯上与我们有关系……事情就愈闹愈大了,不可收拾了……但我们最后是以“收听敌台”入罪的。当然,各单位,各地区都有乱麻一般的问题,我说自己,就如康正果、耿志刚都只说自己一样。我想每个人都不要有“冤枉”的思想,共产党这个绞肉机,今天绞这个,明天绞那个,是天经地义,理由过程都无一相似,反抗的动机也人人不同。
再说,人的觉悟过程也都不一样,正果说“我把申诉材料扔在王力的怀里,可是一直没有下文……我看透了……”,林彪、邓小平也有自己的过程,连“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解放军也是一样的,林彪叛逃,解放军的思想也一起叛逃了。最可恶的算是不要脸的王光美薄一波,要是当初他们被毛泽东枪毙了,也就不会活着歌颂红太阳了。
二○○六年六月二十四日
……
附:《康正果:一些老家伙没被打死的后果──十二人文革记忆(六)》
康正果:文革开始之前,我曾是个大学生,在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
我根本不存在红和黑的问题。我是一九五七年念初中。我被认为是个表现不好的学生。我从来没有想去参加政治运动。初中二年级,父母把我寄放在祖父家里,读了许多古书,还有许多解放前出版的书籍。
我在大学期间,写了三十六本日记,其中有对“九评”的感想。后来被同学揭发出来后,我把日记烧了。但就是因为这件事,我于一九六五年,被学校开除,罪名是焚毁反动日记。当然,还有反动言论,那是校方在同学中调查的。被开除后,我被打发到砖瓦厂劳动。那个厂是公检法的下属。去劳动不算是判刑,而算就业,即劳改释放后,安置就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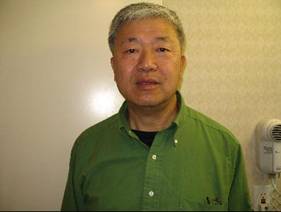
耶鲁大学资深中文教师康正果
文革开始时,我是个局外人,在一边看热闹。但我也关心文革。自从被开除后,我一直在找机会翻案。我不断上诉。文革发生对我来说,是个伸冤的机会。我不喜欢刘国凯,对文革抱以满腔的革命热情──我没有这样的热情。我像社会渣滓,我的方向是要翻案。在工厂劳动时,周围大都是小偷流氓,我与他们没有共同语言。
一九六六年开始砸烂公检法。当时,在西安有许多上海人,乘机杀回上海。还有临时工要转正,也造反。我看到各种人,冲着造反,或者跟着造反,为的是借机改变自己的处境。我也混水摸鱼地上访了。我十二月底到北京上访,住在接待站里。那里有许多上访者,不少是五十年代受了冤屈的。
我非常认真地写了个上诉书。本来,我对革命书籍没有兴趣。除了古书,我读的都是欧洲哲学和文学,按着哲学史和文学史读。包括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但是,为了写一个合格的申诉材料,我学了毛的书,我使用那样的语言。我以为只要用语得当,就可以获得平反。一月一日,周总理接见公检法系统的人。中央文革的人在场,王力也在。我把申诉材料扔在王力的怀里,可是一直没有下文。
我到开除我的大学里去看大字报。我想看看那些把我开除的人,如今还有什么话说。可是,我看到的大字报却说,“校方包庇反动学生康正果”。天哪,那些开除我的人,被说成是“包庇”我的。可见,不管谁当权,我永远是“反动学生”。从此以后,我看透了,变成了一个逍遥派。
我后来就躲在家里看书,翻译俄国文学。我曾想翻译《日瓦戈医生》。
我是在报上看到批判勃列日涅夫的文章时,知道了此书。我写信给莫斯科大学,想要此书翻译。可是,信被截获。第二年,我被抓。
在做逍遥派期间,我过着真正的逍遥日子。我看了许多厂里同事们偷出的禁书,比如《金瓶梅》的原版,还看了许多中外名著。除了读书,我还有其它快乐事情。西安有许多地下舞会,也有许多交际花。在那段无政府状态的时间里,舞会和交际花全都出现了。我在《出中国记》的自传中,有几章专门写这段生活。我们跳舞,欣赏古典音乐。那段时间是我最快乐、最自由的时光。
现在想来,当时有许多人造反,是想通过改变社会来改变自己。可我却是完全立足于自我解放。虽然当时我没有读过萨特的书,但已经提前进入了现代派。我被抓后,关了三年。出来后,被下放到农村。我的妻子是在农村找的,是个农村妇女。
我现在对文革的看法,可能是其他人都没说过的。在我看来,历史上,前一代人所建立的文化,通常都是随着那代人的死去而消失的。比如欧洲,一战,二战,都是因为当时的人死去后,那样的文化消失了。
现在是二战后出生的人在当政,比如克林顿,小布什。
我想说的是,文革,被打死的人都是值得同情的。但是,又正因为文革没有把那些老家伙全都打死,包括思想左倾的老知识分子,所以才导致今天的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没有获得很大的进步。想想看,要是文革中所有死去的人依然全都健在的话,那么中国社会还要保守,还要糟糕。我觉得可惜的是,没有把所有的老家伙全打死,比如王震,薄一波等等。郭小川也一样,假如活下来会很左。如今,重要的是,每个个人,抢救自己的个人记忆。每个人都应该摆脱现在那种文革研究史,摆脱这样那样的争论。大家回到个人的经历中,谈自己做了些什么,想了些什么。个人的经历,会对文革研究带来更加深化的成果。
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