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普•席斯金(Fhilip Shishkin)《不安的山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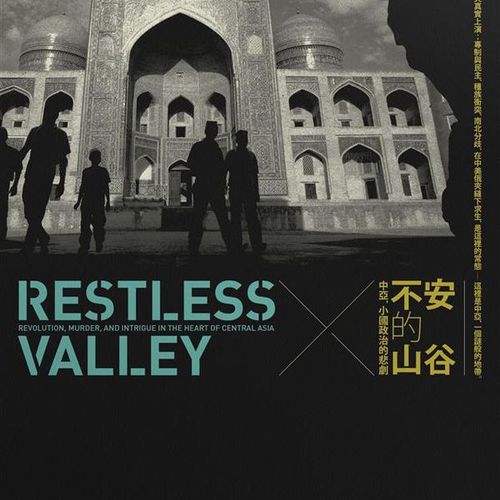
二零一六年九月二日,七十八岁的乌兹别克总统卡里莫夫猝死,这个帝王般的“终身总统”自从乌兹别克一九九一年独立之后就一直控制该国政权,长达四分之一世纪之久。这个国家有形式上的选举,每次选举卡里莫夫都获得九成以上的选票。国际社会批评说,乌兹别克的选举“既不自由,也不公平,选民没有选择的权利”,而反对派候选人也承认加入只是为选举制造表面民主形象,自己的选票其实也投了给卡里莫夫。
卡里莫夫死后,乌兹别克前途未卜。有政治评论家指出:“卡里莫夫实行既反美又反俄的奇特政策,酷似齐奥塞斯库生前的罗马尼亚。由于该国的极端组织即使在威权政府打压下仍然比吉尔吉斯的同类组织强大得多,卡里莫夫以后的乌兹别克肯定会沦为暴力活动的主要输出者。”卡里莫夫这个血腥屠杀人民、家族宛如吸血鬼的独裁者,却是中国政府在中亚最亲密的盟友。与西方媒体对卡里莫夫的负面评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媒体对其死亡的报道充满赞誉之词,认为乌兹别克是中亚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中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并特别提及二零一三年习近平访问中亚,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立即得到卡里莫夫的赞成和支持,卡里莫夫明确表示:“乌方愿积极参与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促进经贸往来和互联互通,把乌兹别克斯坦的发展同中国的繁荣更紧密联系在一起。”实际上,“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卡里莫夫彷佛是一面镜子,照出了习近平的原形。
在地理上,中亚比非洲和南美离中国更近,却更让人感到陌生。中国人对这个地区惟一的兴趣就是,当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的西进政策之后,认为那边蕴藏着无限商机。早在一九九零苏联即将解体之际,波兰作家卡普钦斯基就写下了一本气势磅礡的《帝国》,其中有专门的章节描写中亚地区。他观察到因苏联强迫中亚耕种棉花而导致的环境急剧恶化,以及这些地方普遍存在的独裁、暴力和毒品泛滥。在苏联还没有解体时,该区域的“有效统治”就提前瓦解了。卡普钦斯基发现,木伊那克这个“曾经一度坐落在赋予生命、美丽的阿姆河流进咸海的地方”,如今沦为“一个令人难过的集中营”,那裡现在既没有河流也没有海洋,城裡植物枯萎;狗都死掉了,半数的居民离开,留下来的则无处可去。他们不工作,因为他们是渔夫,而那裡根本没有鱼。当地人的绝望情绪令人毛骨悚然:“碰上没有强风的日子,人们会坐在小板櫈上,靠着他们老旧房子摇摇欲坠的破牆。要是对靠坐在墙上的人笑,他们只会变得更加阴沉,而女人会用面纱盖住脸,真的,微笑在这裡看起来是个错误的表情,笑声听起来则像是用生锈的钉子在玻璃上刮搔般尖锐刺耳。”这个城市宛如整个中亚地区的缩影。二十多年之后,中亚的溷乱、停滞、种族和宗教冲突无丝毫的改善,甚至更加恶化了。
美国资深採访记者席斯金多年爲《华尔街日报》撰写关于中亚地区的报道,他在报道杰作《不安的山谷》中,细密而生动地呈现了中亚这几个后缀带有“斯坦”名词的小国不为人所知的真相:革命与背叛,独裁与屠杀,贪婪的国际资本与俄国、美国、中国三大若隐若现的国际势力的操纵,黑帮、毒品贩子、激进伊斯兰教士与渴望自由的女性、爲人权而战的律师、爲良心而写作的作家,彼此冲突争战,看不到尽头。《不安的山谷》如同《帝国》的续集,引人入胜,发人深省。
这裡只有奴隶主和奴隶,没有公民社会
一九二四年,史达林将突厥斯坦地区分为五个卫星国:土库曼、塔吉克、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哈萨克。作为统治多民族的帝国,苏俄跟中国一样对“以夷制夷”的技巧非常娴熟:故意製造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冲突,然后莫斯科高高在上地扮演最高仲裁者的角色。在划分国界的的时候,苏俄将国界划成犬牙交错状,让本来都属于广义的突厥民族的几个民族国家互相敌对和仇视,从而不可能联合起来反抗俄罗斯人的统治。
苏俄在二战前期佔领波兰领土时,製造了惨绝人寰的卡廷惨桉等屠杀事件,消灭了波兰的知识分子、中产阶级,以此摧毁波兰的民族记忆,使波兰成为苏俄永远的附庸国。一个没有精英阶层的国家,不可能成为有独立意志的国家。苏俄在波兰的统治策略,也在中亚各国使用,卡普钦斯基写道:“在史达林统治期间,大批的农人、伊斯兰神职人员,以及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成爲镇压的受害人,后者被俄罗斯人所取代,也被当地的激进分子和官僚所同化。”之后,莫斯科打造了一个听话的本地权贵阶层,而其代表人物就是“在每个加盟共和国首都矗立着一位高官,也就是当地党部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按照东方传统,他会在位到死为止”。
苏联解体之后,中亚各国在苏联留下的“前共产党人-社会工程学派官僚集团”的统治下,始终没有找到合理的国家建构方式。这些大大小小的独裁者,都採取一种拜占庭苏丹式的统治方式,他们不称国王,也不再保留共产党书记这个臭名昭着的职务,而沿用民主国家国家元首的称呼“总统”。每一个总统背后,都有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乌兹别克的民众连麵粉等基本食品都得不到保证,卡里莫夫的女儿却以时装设计师的身份旅行世界,拥有顶级时装品牌,并重金请到国际歌星爲其生日派对演唱。
这些中亚国家都没有形成稳定的公民社会,在通常情况下,民众被独裁者视为顺民或奴隶;惟有革命发生的时候,一夜之间变成暴民。充满诗意的鬱金香革命,除了少数领导者有建立民主国家的愿景之外,大部分参与者都是趁火打劫之徒。席斯金在鬱金香革命当天,在被民众攻陷的总统府附近的百货商店中,看到一群群的劫匪。不少人来自偏远乡村,从来没有见过现代化的百货公司,警方的撤离让他们可以为所欲为。席斯金幽默地描写了一个双手抱着一大堆从商店裡抢来的女性内衣的暴徒,还兜售说:“你想买些内衣吗?算你批发价。”这个细节注定了鬱金香革命不会有好的结果。果然,靠鬱金香革命上台的领导人,比被推翻的前任领导人更贪婪和暴虐,五年之后,人们又发起一次革命将其推翻。翻身的奴隶以难以想像的速度蜕变成了奴隶主。那么,哪一次才是最后一场革命呢?没有人知道。
吉尔吉斯作家艾特玛托夫《一日长于百年》中,描写一种中世纪奴役俘虏的办法:将俘虏五花大绑,然后去到沙漠烈日之下,并用一块骆驼皮盖住他们剃光头髮的头壳。随着骆驼皮在太阳底下缩紧,挤压烘烤着俘虏的头,这就是像中世纪的脑叶切除手术。俘虏不是死亡,就是忘记自己是谁,失去了反抗的意志力,成为理想的奴隶,或是极权政府的人民。艾特玛托夫将这种人成为“曼寇特”(Mankurt),而这个字后来也用来比喻没有思想、卑躬屈膝地对权威效忠的人。艾托玛托夫写道:“他就像一头安静的野兽,十分顺从也十分安全。他从未梦想过要逃离。对于任何一个奴隶主而言,最恐怖的事就是奴隶起义。每个奴隶都是潜在的反叛者。曼寇特是惟一的例外,反叛与不服从的观念完全不在他脑子裡。他不懂那样的激烈情绪,因此根本没有看守他的必要,更不需要怀疑他心存不轨。曼寇特就是像狗一样,只认他的主人。他不与其他任何人往来。他的梦想全都简化成填饱肚子,没有其他的考量。可是他盲目、勤奋且毫不犹豫地遵守命令。”这种人就是中亚各国居民的一种象徵符号。
为什麽同样是此前遭到苏联吞併的国家,波罗的海三国很快就融入欧洲文明世界,而中亚各国至今仍在专制独裁的泥潭中挣扎?因为它们分享的是不同的文化和信仰传统。影响中亚最大的是三种东方的文化和信仰传统:首先是来自阿拉伯的伊斯兰专制主义,其次是来自俄国的斯拉夫专制专制主义,第三是来自中国的儒家专制主义。中亚国家很不幸地在西、北、东三个方向被黑暗的伊斯兰世界、俄罗斯和中国所包围。这三大东方专制主义如同三道咒语,紧紧地束缚中亚国家的发展。
比天安门屠杀更残暴和更被忽视的安集延屠杀
二零零五年,中亚和东欧国家爆发颜色革命,乌兹别克的安集延地区也发生了民众的大规模抗议示威。卡里莫夫以铁腕方式炮制了安集延屠杀,他嘲笑逃亡的吉尔吉斯总统阿卡耶夫没有胆量杀人,“你不敢杀人,还有什么好说的?”吉尔吉斯总统阿卡耶夫是半弔子的独裁者,他不敢发动一场屠杀,宁愿接受被推翻和流亡的命运,不敢杀人是他对祖国惟一的贡献;而乌兹别克总统卡里莫夫跟中国的暴君毛泽东和邓小平一样,是彻头彻尾的独裁者,杀人毫不手软,他们深知自己干过足够多的坏事,如果不杀害、囚禁、恐吓更多的人,自己就有可能被推翻,并被送上审判席和绞刑架。所以,杀人是他们精心算计之后的理性的选择,而不是突然爆发的疯狂之举。
中国媒体在给卡里莫夫的“悼词”中,特别讚扬这个独裁者当初如何果断地控制住局势:卡里莫夫“御驾亲征”乘专机抵达骚乱地区;迅速在当地机场建立临时指挥部;视察当地强力部门,下达实施紧急措施命令。在记者会上,卡里莫夫表示:“把乌兹别克斯坦的骚乱事件与乌克兰、格鲁吉亚和吉尔吉斯的事件等同起来是不对的,我本人坚决反对任何所谓的革命。”当时,中国迅速认同乌兹别克政府对事件的定性:“乌兹别克斯坦是中国的近邻和合作伙伴……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将一如既往地支持乌兹别克斯坦及本地区各国为维护国家和地区安全与稳定所作的努力。”对于十多年前在北京杀人如麻的中国政府来说,在安集延杀人的卡里莫夫如同一名亦步亦趋的学生。
如果把各个时代、各个国家的屠杀放在一起类比,有人也许会发出不太妥当的追问:是希特勒的屠杀更残暴,还是史达林的屠杀更残暴?是柬埔寨红色高棉的屠杀更残暴,还是北韩金家王朝的屠杀更残暴?永远找不到关于“之最”的答桉,只能说明对人性黑暗面的评估找不到尽头。跟北京的天安门屠杀相比,乌兹别克的安集延屠杀更加悲惨:北京“六四”屠杀发生时,正好有到中国採访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访华这个重大国际新闻的庞大的记者团队,他们意外地经历和记录了这场屠杀。中共当局无法遮蔽那麽多公开发表的照片和录影。而乌兹别克原本就处于被世界所漠视的中亚,安集延又是一个偏远的、交通不便的城市,少有外国记者光临,屠杀发生之后国际媒体的报道相当有限。而且,美国由于阿富汗战争的需要,在乌兹别克设有军事基地,对卡里莫夫的批评相当克制,欧盟和整个西方也是如此。
乌兹别克是一个警察国家,当地有笑话说,电视上举行中亚各个民族身穿民族服装的选秀,乌兹别克的民族服装是让人毛骨悚然的警服。不过,由于腐败、低效和懒惰,这个警察国家的漏洞很多。席斯金计划去安集延採访,从塔什干去安集延的公路被封闭了,他被警察赶回去。然后,他灵机一动,乘坐飞机飞到离安集延很近的另一座城市费尔干纳,再租车赶去,果然成功。由此,他感叹说:“在一个警察国家,无能是一种美德。”中国的维稳工作比乌兹别克高效得多,中共在新疆屠杀维族人之后,将新疆全境封锁,乃至切断电话、手机和网络等全部通讯。席斯金若是想到新疆採访,恐怕“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在安集延,究竟有多少民众遭到屠杀,至今仍然是一个谜。据席斯金的採访,当地的一位医生说,她在一所校园裡看见了五百具尸体,“许多人死状悽惨,头上中弹、腿上受伤,全身伤痕累累。那裡看到的不是血迹,而是一滩滩的血水”。一个失去儿子的妈妈说,她在医院看到了七百具尸体,她一路上发疯似的寻找儿子,“路边堆着好多尸体。有的尸体的内脏、脑浆都跑了出来。有一具尸体手抓着一条麵包,还有一具则躺在脚踏车上面。”
安集延屠杀的死难者至今死不瞑目,元凶卡里莫夫没有像伊拉克的萨达姆和利比亚的卡扎菲那样可耻地毙命,而是体面地死去。但未来在实现转型正义的乌兹别克,他终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那些“用针挖井”的人权捍卫者
本书的大部分章节,描述了中亚各国阴沉、溃败、痛楚的现状,让读者心情沉重。但是,作者也给出了这个区域的另一条出路,比如吉尔吉斯经过第二次鬱金香革命之后,有一群一直爲民主自由奋斗的律师、记者、NGO工作者加入过渡政府,废寝忘食地工作,希望在这个国家建立起现代的政治、经济制度,让人民可以安居乐业。
旧政权製造的惨案逐一受到调查,真相浮出水面,凶手受到惩罚。数年前,吉尔吉斯知名反对派记者帕夫尤克收到某基金会发来的一封电邮,告知他获得了一项奖金,邀请他到哈萨首都克阿拉木图领奖。帕氏赶到约定的酒店,第二天就传来噩耗:他的手脚被胶带綑绑,被从酒店六楼扔下,五天后死亡。新政府成立之后,重启对此案的调查,最后暗杀行动的策划者被绳之以法:那是一个身材矮胖、脸孔极其丑陋、理平头、眼睛小而冷酷的男子,吉尔吉斯安全局资深探员伊斯曼库洛夫。此人在哈萨克的法庭上被判处十七年徒刑。与此同时,在吉尔吉斯首都比斯凯克的一条街道上,树立起了行走中的帕夫尤克的塑像,他的採访包背在右肩上,左手拿着一台录音机。塑像下的铭文写着:“献给以文字散播自由的那些人。”
而在乌兹别克,酷刑仍然泛滥。受刑者之一的穆萨耶夫揭露说,他遭受了一种在业内被称为“北方之光”的酷刑:他被固定在一张凳子上,头部不断遭受敲击。他描述说:“刚开始,你觉得头非常痛,接着眼前的一切都变成红色的,就像有鲜血从你的眼睛上灌下来,然后你看到黑白条文。过了一会儿,你的身体好像整个移到头裡面,你感到头痛欲裂。再来,你觉得自己的灵魂想要脱离你的身体,你想要撕裂身体,帮助灵魂离开,可是却感觉不到身体的存在。”乌兹别克当局继承了苏联时代的传统,酷刑被“外包”给监狱中经验丰富的囚犯,不需要警察和狱卒亲自动手,即便被揭发,他们也可置身事外。最后,穆萨耶夫被迫签署认罪书,被判十五年重刑。这种境遇,与今天中共统治下饱受酷刑折磨乃至家人被扣爲人质的人权律师、NG活动人士、独立作家和记者们何其相似!中共统治者比中亚的统治者更为成功的是,用经济繁荣的泡沫来掩饰中国社会的种种乱象,而安心发财、循规蹈矩的一般民众,少有机会遭到安全人员的骚扰——像雷洋死于警察暴力那样的事件,在大多数人看来只是“运气不好”的“偶然事件”而已,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中国跟中亚国家一样,都还没有踏入“法治国家”的门槛。
即便如此,反抗者仍然没有屈服。美国的压力让NGO组织阳光联盟的领导人乌马洛夫提前出狱,赴美与家人团聚。人权活动家伊克拉莫夫评论说:“监狱裡有好多人:最优秀的商人、作家、记者、人权捍卫者、宗教思想家。设法释放他们很重要。即便只有一个人出狱,那也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他使用一句乌兹别克的谚语来形容他们的工作:“那就像拿针凿井。”如果用中国的谚语来说,就是精卫填海、夸父追日。再次被中共判处重刑的中国民主人士胡石根也有与之类似的“推牆”理论,所谓「宁可十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天安门学生运动领袖之一的周锋锁评论说:“‘推墙’这个说法非常好。在中文‘推特’上,最流行一句话就是‘推倒这堵墙’。其实这堵墙更重要的存在于中国人的心中,就是中共用暴力和谎言建立在每个人心中的恐惧,这个墙推起来比实体的墙要难很多。”
晚近一个世纪以来,总体而言,作为普世价值的民主自由,在全球不断拓展。尽管在某些地区的民主转型出现困境和逆流,但并不意味着专制独裁就能成为另一种普世价值。流亡欧洲的乌兹别克诗人、反对运动领袖苏利,在捷克旅行期间,遭到国际拘捕令逮捕,乌兹别克政府企图以莫须有的罪名引渡他。捷克短暂拘押他之后,将其释放。曾经被关在同一座监狱的捷克前总统、也是诗人和剧作家的哈维尔前来与苏利会面,哈维尔以自身的经历鼓励苏利,正如他全力支持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一样。我们有理由相信,苏利和乌兹别克的明天,刘晓波和中国的明天,会像哈维尔和捷克的今天这样充满光明。
来源:RF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