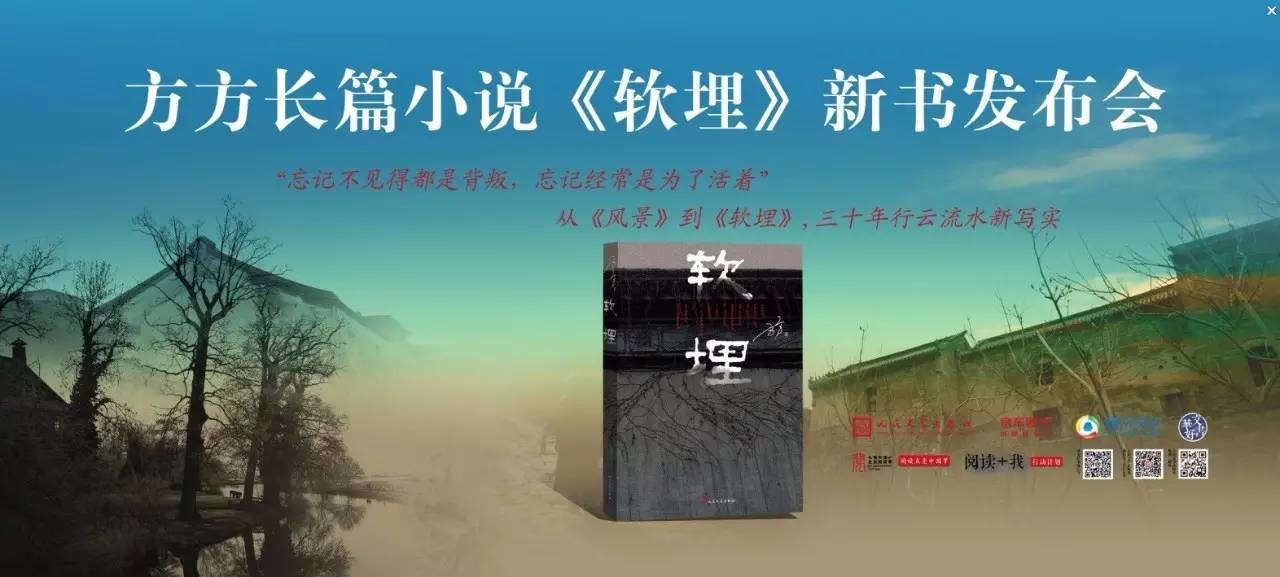第四章
第五章
21. 灰光里的台阶
丁子桃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在坠落的过程中越来越重。心脏仿佛也被无数细丝一根根缠紧,呼吸也由此而困难。她已无力挣扎,准备呼出最后一口气,然后放弃自己。便在这时,她听到轰的一声巨响。随之而来的,是全身骨头的嘎嘎声,她顿觉自己四分五裂。
好久好久,她缓过了劲来,意识到她的坠落已然停止。她想,恐怕是坠到底了吧。四周仍然暗黑如漆.她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亦不知自己是生是死。她不由问自己,我死了吗?我是不是已经死了?
问罢,她记起母亲曾经说过:“只要活着,就会有痛。一旦死了,痛就没了。”那个画面,仿佛浮在了眼前。小小的她正在绣屋里学着绣孑L雀尾羽,突然被针扎了手。看着鲜血从指尖流出,她呜呜地哭着。母亲走过来,看了一眼,教训她,然后说了这样几句话。她知道这是母亲年幼时,她的父亲常用的训斥语。母亲的家在成都科甲巷开绣坊。她的父亲是远近著名的绣工。她家里专绣宋画,以供富人收藏和雅玩。母亲自小就学了一手好绣活。出嫁时,特意提了一个条件:夫家必须辟一间绣屋。她的父亲一口答应了母亲的要求。此一刻,绣屋和绣架上垂挂的绣品,也都晃在了眼前。母亲站在绣架边,一手整理绣品的边缘,一手用指尖抚着绣好的图案。母亲低着头说:“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没了记性。这样,痛没痛过也不知道。”
她挪动了一下自己,觉得浑身剧痛。于是想,这么说,我还活着。我还会痛,并且我还记得。
她的耳朵也开始变得灵敏,隐然听到阵阵呼啸,似来自很深远的地方。这是一份无边无际的深远,她被这声音环绕,一层又一层,有如打包,被紧紧地裹住。她觉得自己就在这深远之中,又觉得这深远距她遥不可及。她并未有一丝的害怕,却有着无限的疲惫。于是她闭上了眼睛。她甚至不知自己是醒着,还是睡着。
时间一直按它的方式行走。或许是一天一年,也或许是一百天一百年。黑色的浓度突然弱了。有淡淡的灰光浮在顶上,这光里像飘着柔纱。透过这层纱,丁子桃向上望去,有一格一格的线条沿着灰光的来处逐级上升,如同阶梯一样分布均匀。她慢慢地数着。一直数到了十八,她便看不清了。
她想,十八层,为什么正好是十八呢?这是什么意思?
22. 不,不是这样的!
忽有寒风袭来,只一阵,便吹透到骨。她打了一个哆嗦,哆嗦间,突然就想起许久以前,她坐在湖边的小竹亭里,看秋水涟漪,湖鸥飞翔。湖面起了风,她有些寒意,于是自念道:“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
有人给她披上了一件衣服。这衣服温暖了她的心。
丁子桃想,是谁呢?是谁为她披上了衣服呢?她想不起来,不禁大声问道:“谁?你是谁?你为什么要为我披衣服?”有个深厚的男声回答说:“是我。我是陆仲文呀。我担心你受凉哩。”
丁子桃说:“陆仲文,你到哪里去了?我怎么好久都没有见到你?”
陆仲文说:“我正想问你呢。你们到哪里去了?我爹娘呢?我奶奶姨娘呢?还有我姑我哥呢?慧媛妹妹呢?你们都到哪里去了?还有我的小汀子?我怎么找不到你们了?”
丁子桃呆住了。他们都到哪里去了?她四处张望着,想看看有没有他说的那些人。那都是他和她的亲人。
四周空旷,灰蒙蒙的,仿佛浓雾将她深深笼罩,就连陆仲文她也看不到。丁子桃说:“你在哪?仲文你在哪?”
陆仲文的声音变得格外遥远,丁子桃甚至不知道它来自哪个方向。这声音说:“我在找你们。你们在哪里?”
丁子桃想,我在哪里?这是什么地方?
她再次看到灰光里的十八层台阶。蓦然间,她有顿悟,莫非自己真是在地狱里了?正像二娘当初所说:你就该下地狱。
她伸出自己的手,想看看上面有没有血。但她看不到。她能感觉到自己的手在哪里,眼睛却什么也看不见。这双手,她突然对它心生厌恶,有一种觉得它非常肮脏的念头,甚至恨不得它从未存在过。
丁子桃想,为什么呢?发生了什么事?她扬起双手,相互拍打了一下巴掌。有清脆的叭声传到她的耳里。这声音惊到了她。然后有很多的叭声响在她的耳边,而她的手却僵硬着并未动弹。在不绝于耳的叭声里,一些面孔浮了出来。她的手,正一张张地对着这些面孔打耳光。那些面孔她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他们呆滞地望着她,任她的手掌在自己脸上挥舞。
四周有欢呼声,还有金属的撞击声。一个尖锐的声音夹在中间响起:“你会下地狱的!阎王老子不会放过你的!”
丁子桃突然叫了起来:“不,不是这样的!”
她对自己说,不,不是这样的!我不应该下地狱。留在地狱里的人不能是我。我得出去,告诉仲文,告诉二娘,也要告诉所有人,事情不是那样。不是他们所看到的那样,也不是他们所想象的那样。
这时候的她,突然有一股信念:她要出去。她一定要出去。她要告诉所有人,包括那些热烈并冷酷地看着她的人。她要说,曾经发生的那一幕,并非她的本意,也与她无关。就算她要重新回到的地方仍是地狱,她也要把这些说清楚。
于是,她开始向上爬了。
23. 地狱之第一:河流里的嘶喊
一点一点地爬着。丁子桃不知道自己爬了有多久。她爬上了第一个台阶。她站立起来,抬头向上望着,心想,对我来说,这是我的第十八层哩。可是,她问自己:“我要告诉人们什么呢?我又要从哪里讲起?”
她发现自己有满腹的话要说,却又无从说起。
瞬间她被河水淹没。身边到处是石头。激流把她从这块石头推向那块石头。她拼命挣扎,努力地想要攀住一块石头。但河里的石头光滑无比,每一次抓着,又迅速被另一股激水冲开。
她一直嘶喊着,喊得声音几近沙哑:“汀子!汀子!”
汀子还在船上。他被蓝花的包袱皮裹着。他睡着了。她记得他酣睡的小脸上,还挂着笑意。他的小腿蹬开了包袱皮,脚上的花鞋露了出来。那鞋子是她亲手做的,鞋面上绣有两条小金鱼。
陆仲文走的前夜,一直抱着汀子。父子俩逗着笑着。陆仲文说:“叫爸爸。”
汀子便说:“叭——叭。”
陆仲文大笑,边笑着边把汀子举了起来。汀子在他高举的时候,撒起了尿。尿落在了陆仲文脸上。他哇哇地一通乱叫,把汀子递给了她。他跑出屋洗脸时,屋外传来好多笑声。陆仲文洗过脸,换了衣服,转进来拍着汀子的屁股说:“小坏蛋,这是你给爸爸的送行礼物吗?”
她也笑,然后说:“当然。这是我们汀子留的记号哦。”
陆仲文要去的地方是香港。走前又说:“我会挂念你和我们的小汀子,我会尽快回来。孩子全靠你照料了。爹娘虽然不需你费心,但有什么事,你也关心一下。”
她说:“放心吧,我会的。还有小茶和富童帮我哩。”
陆仲文说:“富童喜欢小茶,想要跟她结婚哩。你不反对吧?”
她笑道:“怎么会反对?我巴不得哩。富童自小跟你,小茶自小跟我,他们也般配哩。以后他们有了娃儿,正好跟我们家汀子搭伴儿。”
陆仲文走时,她抱着汀子,随着马车,一直送他到县城。
现在呢?汀子到哪去了?船呢?船在哪里?
而她在水流中。就像一块活动的石头,被随意地冲刷和推动。这是一块很奇怪的石头。它似乎在抗拒无休止扑来的水头。它时滚时顿,轨迹混乱。两岸阒无人声,连风刮树叶的声音都很弱小。与水撞石头之声相比,它仿佛根本就不存在。她的意识还是清晰的。河水不时没过头顶,她每次张口,都被流水呛回。那些声音便扑转向心里,这是她仅剩下的两个字:汀子!汀子!她的狂喊几乎震炸了她的心。甚至,两岸的高山,也被她的喊叫所撼动。
水流更快速地推着她到河的下游。轰轰的撞击声越来越强烈。她以为这是她喊叫的回声。她甚至分不清天和水。她亲爱的儿子汀子,你在哪里呢?她费尽全身力气,都看不见他。
她浑噩地扑腾,手指触到一件流动的东西。她一把抓住,发现是一块木板。她抱着木板时,突然认出,这是她家的船,是富童划船的木板。瞬间她清醒了:船被岩石撞散架了吗?那么,她的汀子呢?躺在船上的小汀子呢?这个问题一经提出,她就知道自己已毫无生趣。于是她双手一松,把一切都放下了。
没有了汀子,我活着做什么。这是她被水流卷走时的最后一缕念头。
24. 地狱之第二:船在水中旋转
丁子桃筋疲力竭。她不知自己在做什么,只是有喘不过气的感觉。
暗黑之中,她闻到一股清新气。是水的气息。她想,难道我已经到了河边?
突然,她就看到了富童。富童从船上跳下,朝她跑来。她的双脚已经站在了水里,他拦在了她的面前,喊道:“你怎么了?黛云姐!你要到哪里去?”
她呆望着他,没有反应。富童拉着她到了船边。他跳上船,然后伸出手,把她拉了上去。富童说:“怎么来得这么晚?陆爷说了,要在天亮前赶到湾道村,松表哥会去河口接你们;汀子没事吧?嗯,睡得很香哩。小姐呢?陆爷说你们一起走的,她在后面吗?是不是要等下她?再晚,会被人发现的。”
她的脑子一团糟,低声说了一句:“没有别人了。”
她抱着汀子,坐了下来。她神情恍惚,已然没有了自主意识。仿佛她只会服从,只会按别人所说的去做。
船迅速离了岸。后面无人追赶,划船的富童松了口气。富童说:“陆爷昨天中午就让我泊在这里了。我走的是碉楼下面的暗道,你也是吧?这条暗道没有人知道。陆爷说这是以前他爷爷修的,不到紧急时刻,从来不用。陆爷还说让我随你们一起去找仲文哥,一路上也好照应你们两个。为什么只有你?慧媛小姐留在家里要是也被拉出去斗争该怎么办?”
她嗯了一声。她不想说话。她心里憋着很多的东西。这些东西混乱地拥挤在她的五脏六腑。它们兀自在里面喧嚣和翻腾。她很难过,想要呕吐,却又吐不出来。
富童又说:“不过,听说金点是工作组长。他跟慧媛小姐关系一向好,想必不会找小姐麻烦。”
她突然叫了一声:“你不要提他!”
富童吓了一跳,船抖了一下。他低声嘟哝了一句:“你怎么了?”嘟哝完又说,“我自小跟仲文哥一起长大。我陪他去学堂上学,他在先生那里念书,我就坐在外面等他。回转时,仲文哥就把他学的字教给我认。”
她开始讨厌他了。她真不想说话,也不想听他说。她只想自己静一静。
水流很急,推着小船,瞬间钻进了山间。两岸高山夹峙,河窄石乱,水头时猛时缓。得幸富童在这河上走过多次,知石知水,他持篙灵活地点着两侧突起的岩壁,船便在他的调度下,轻巧地拐弯抹角,一路向前。
汀子在她的怀里睡着,仿佛知事,整个夜晚,他都不吵不闹。她的衣服穿少了,后背凉飕飕的,只有她怀里的汀子,浑身热烘烘的,令她的前胸充满温暖。
富童说:“汀子好乖。明天得让他知道,他坐了一夜富童叔的船。”
她依然无语。富童是个孤儿,自小便被她的公婆收养。公婆家还收养了另一孤儿,叫金点。他年长一些,便随家里长工一起干活。富童年龄小,一直是她丈夫陆仲文的陪伴。两人一起长大,情如兄弟。
富童不介意她的无语,依然自顾自地说着:“陆爷说,仲文哥会留在香港。我送到你们即回转。我从香港回来,黛云姐,你说我要给小茶带点什么?”
她一脑子的混沌仿佛被“小茶”二字撕开了缝,有亮光照射进来。她下意识地重复了一句:“小茶?”
富童说:“是呀。小茶喜欢你平常系的花围巾,我要不要给她也买一条?”
天色已经放亮了。阳光在山的后面。河在两山之间流着,流在大山的阴影里。风从外面进来,即刻便阴冷。
突然间,她放声哭了起来。她说:“都死了。他们都死了。”她的哭声压住了水声,在山间回荡。
富童大惊,问道:“死了?谁死了?”
她边哭边说:“全都死了。”
船在水里晃得厉害,富童叫了起来:“为什么要死?怎么会死?是谁?谁弄死了他们?按说,大门关严了,外人进不来呀!”
她把头埋在怀里的汀子身上,哭道:“是汀子爷爷要大家一起死。村里传话说,天亮就斗争陆家,要斗三天。斗完还要分人分房子,这是金点的决定。”
富童怔住了,默然地划着船。过了一会儿,他突然叫着:“这不关小茶的事吧?小茶是穷人,小茶不是地主家的人。小茶不姓陆,她不用死对不对?”
她开始冷静了,抬起头来,说:“小茶是自己要死的。听人讲,小茶被分给了麻叔家的老二。小茶死活不肯。但她晓得,不肯也不行。分到谁家就是谁的,不然就活不成。”
富童停止了划船,船晃得厉害。富童喊道:“小茶是我的人。说好了要嫁给我的。我也是穷人呀!麻叔还有间屋,我连屋都没有呀。黛云姐,你不要哄我!”
她哽咽道:“是我亲手埋的小茶,她就埋在西墙芭蕉树下,和紫平埋在一起。她们挨着肩膀躺着。”说着她又哭了起来,“我埋土时,总觉得小茶好像还有气……”
富童说:“你怎么可以让她死?你怎么可以埋她?”
她哭着说:“不埋怎么办?天亮了能让阳光照她的脸吗?”
富童吼了起来:“你怎么下得了手?小茶不是你的人吗?她拿你像亲姐一样,你怎么不救她?小姐不走,你可以带她一起逃呀?船还可以坐下一个。你怎么不带她走?”
她从未见过富童如此,心道你一个下人,竟敢这样跟我说话?便冷冷道:“我不埋她又能怎么样?你以为她能嫁给你?”
富童哭了起来:“黛云姐,我和小茶一向拿你当亲姐,你怎么可以这样?你怎么这么狠心?”
她正要开口骂他,一个下人,居然敢如此冲撞她。未及开口,她突然听到水里有咚的一声,抬头时,已经不见了富童。船立即在水中晃了起来。她尖叫道:“富童!富童!”
富童的声音从水面上滑了过来。
富童说:“你别怪我,我管不了你。我要回去找小茶……”
水流急推着小船。船身不时撞上岩壁,她吓得大叫,回应的却只有她自己的声音。她慌忙放下怀里的汀子,抓起富童扔下的竹篙。她听不见富童的声音,只听见水声如吼。她手忙脚乱地想要把船弄稳。但她从未与水打过交道,亦不知道如何划船。
水却更急了,推着船从一块岩石撞上另一块岩石。她一脚不稳,跌到船边。来不及等她想什么,船便翻了。她跌下水时,叫了一声“汀子”。
此后,她脑子里什么都没有了,只有汀子。
25. 地狱之第三:山路上的狂奔
丁子桃看到了山路。看到了自己的奔跑。
路很弯曲,两旁是低矮的植物,间或一段乱石相夹,一眼望去,像是有人随意抛下的一条布带,扭曲伸展,一直通到树林深处。一个人在她的耳边不停地下命令:黛云,你要……黛云,你必须……这声音让她心乱如麻。
现在她知道了,这个黛云,正是自己。
她的父亲喜欢《红楼梦》里的黛玉和湘云。他说,黛玉之聪和湘云之憨,女儿有此两样,便会有福。他从这两人中各取了一字,她便成了黛云。她的父亲喜欢藏书,喜欢写写画画。家里的东厢房有三大间,几乎都是父亲的书房。有一间是父亲用来写字画画的。父亲写字时,时常拖着长长的声音叫她:“云儿……过来,磨墨。”父亲的易砚是黛云喜欢把玩的,说黄不黄,说绿不绿,上面有俩人在下棋。伸手抚摸,光滑冰凉。但她不喜欢磨墨。磨得手酸,并且每次者会弄脏她的衣衫。她的母亲也不喜欢父亲使唤她去磨墨。母亲认为这应是姨娘分内的事,母亲只希望她留在绣屋。母亲希望她能学到她的绣技。但父亲还是喜欢叫她。父亲说:“我家云儿磨得好,浓淡适中。只要云儿磨墨,我的字画,品格就都出来了。”说完父亲还要说,“我还是要用上次那块曹素功墨。”
但在这奔跑的时刻,她耳边的说话人不是父亲。父亲一向语气绵软而随和,现在这声音却透着强硬和霸道。
山路漆黑异常。天空非但没有月亮,连星星都没有一粒。黑云深浓到看不见边缘,也看不清层次。黛云背着孩子,在路上且走且奔。她似乎不需要看路。她的脚自己会知道路在哪里。
就是这样什么都没有的夜晚,却有人一直在上空说话,仿佛是在为她指点迷津:进了碉楼,楼梯下堆着损坏的木头花窗,搬开它们,后面有一扇小门,这是我爷爷当年挖的暗道。这暗道通向山后。你从暗道钻出,洞口有茅草,出了茅草,是茶园。穿过茶园,找见两棵老樟树。树后有一排篱笆。翻过篱笆墙,朝南走十步,可以看到一条石头小路。路在坡上绕,你顺着路走,不要图近,两边的乱石会伤脚。小路直通到山下,你就顺着这小路往前跑。它拐弯你也拐弯,它进林子你也进林子,它爬升你也爬升。不要离路,一直跑到头。尽头边是河,富童会在那里等你。越快越好,天亮如被人抓到,你和孩子恐怕都会没命。
这是公公陆子樵的指示。他严厉而决绝,不容分辩。
山里并不安静,各种怪声在她的四周叫嚣。她跑过之处,偶尔会激起群鸟呼啦啦惊飞。在夜里,它们的翅膀,响彻四野。但她已然没有了对它们的恐惧,比这些怪声更大的恐惧压倒了它们。
她跑。狂跑。没命地跑。她明白,被人抓到,她真的会没命。她的父亲母亲和全家人凄凉的面容,还有他们的哀号、他们的惨叫,以及夜间村人细述他们惨死的过程,都像鞭子抽着她向前奔跑。几个月前,她还与父亲和母亲一起坐在且忍庐餐房吃饭。尽管浮财已然交尽,下人也都解散回家,家中几近贫寒。他们一家自炊自饮,为母亲做了顿寿面。可父亲说,一家人能坐在一起,并且还是坐在自家的且忍庐里吃饭,也算万幸。且忍庐是她祖父盖的。当初盖房时,因为屋后的远房大伯,嫌他们盖得高了,三番几次前来吵闹。吵一次,她的祖父便锯一次梁。一周里,连锯了三次。连族中其他人都看不过去了,想联合起来帮她家出头。她的祖父却说,且让且忍吧,邻里不可为仇。何况一笔难写两个胡字。屋盖好后,祖父取名为“且忍庐”。尽管他家的房屋低了,日子却越过越好。而高梁大屋的远房大伯家,三个儿子为家产打架,一打数年,及至这一辈,倒是把家败掉了。她的父亲说,看看,能忍便是福。且忍庐住着她家近十口人。她进城读书之前,一直生活在那里。这是她人生最亲切的地方。
孰料那一顿饭吃罢不几天,她与她的亲人们便阴阳两隔。她想,爸爸呀爸爸,你听爷爷的话,且让且忍一辈子,忍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你用了这么多办法,仍然被枪毙了,还连累了妈妈、二娘和哥嫂,一大家子人都因你们的且忍且让而死。你这样的忍又有何益?
她的心已经被她的所想痛碎了。
耳边渐有水声传来。瞬间她觉得她已闻到了水气。然后她看到了河流。再然后,她看到了富童。
此时的她,已然筋疲力竭,但她停不下步伐。仿佛她此生就是为了奔跑而活。她见到了水,心知自己已到河边,她意识到应该停下,却收不住自己的腿。她踉跄着,一直朝水里跑去。
富童冲上前拦住她。富童叫道:“你怎么了?黛云姐!你要到哪里去?”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