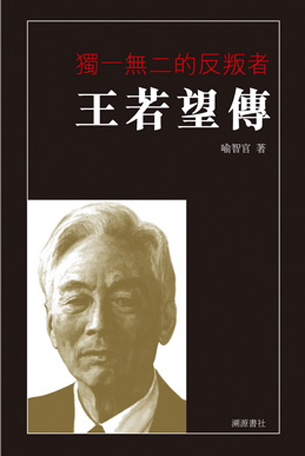(一)
十月刚过,一个年轻人来到编辑部,说是要找一篇十天以前寄来的文稿,题目叫做《伤心沟》。他发现还需要修改。对自己的创作如此认真,并且亲自上门,我们当然乐意照办的。
文稿还没还给他,我问了一句:“你用的什么笔名呀?”这一问,年轻人显得慌张,张口结舌,没有回话。我对他起了疑心。我看到他有一种胆怯羞涩的表情,更加证实了我对他的怀疑。我觉得不应冒冒失失把这篇文稿还给他:也许他不是“伤心沟”的作者。
“你是这篇文章的作者本人吗?”我在“作者本人”四个字上加重语气。
年轻人显得很窘,他从挎包里掏出了一封盖有T县长征公社革委会印鉴的公函。我打开公函一看,上面写着:
“兹有我公社小学教师焦克义同志给你刊写的一篇《伤心沟》,他本人觉得有些事实不符,需要修改,希将该稿交来人带回。”
我研究了这封公函,更增加了我的疑宝:如果作者本人觉得需要修改。只要寄一封信就可以了,何必要出公函?T县离上海有四百多里路程,还要专派一个人到上海来取?这一系列的疑问,使我对这篇《伤心沟》格外重视起来。我已经意识到这篇小说里面有非同小可的斗争。于是我从容又坚定地说:
“这封信我留下了。稿子刚来没几天,还没有看。等看完后再退给他本人就是了。
青年人显出很焦急的神情,说:“能不能让我捎给他?”
他越是焦急,这就更加坚定了我的主意.这篇作品不能交到他手里,这是保护一个作者的创作自由的问题,决不可掉以轻心。
我把《伤心沟》原稿粗略地看了一遍,写的是关于公社里兴修水利,发动青壮劳力挖了一条河,题材是很有现实意义的,作者笔下的党委书记也还有典型性的。要说有缺点的话,就是在结尾处没交代明白,这条《伤心沟》的结局是继续挖下去,还是撒手不干了。还有一个缺点,是由于作者太拘泥于事实,有点像“特写”,不像小说。
三天以后,那个青年人又来了。我说:“我们要把稿退给作者本人。”
同时,我想从他那里了解关于这篇小说受到公社领导如此重视的原因。但是他却一点不说,一味强调作者要取回原稿,最后他向我提出:“你们能不能给我写个条子,说明你们打算用还是不用,我好回去交差。”
看来,他空手而回是不好跟上面交差的。于是我用编辑部的公用信笺写了如下的话:
焦克义同志的来稿,系一篇小说。看来并非真人真事,本刊是否刊用,俟研究后再决定,希对你公社的业余作者加意培养与爱护。
此致
敬礼!
这个青年人拿到这张信纸后,临行时还悄悄地问:“那篇稿子能用吗?”我说:“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决定的。”
年青人走后,我又重新把《伤心沟》看了一遍,从这篇《伤心沟》里,我听到了被压抑的上万农民的呼声,触摸到一个青年教师热辣辣的一颗心。心想:作者寄这篇稿子时一定是经过了思想斗争和拿出了最后的勇气的吧!
我产生了想探究真相,洞察底蕴的愿望:是不是抓住这篇小说的纠葛,索性到现场去走走,深入一下生活。
四天以后,我带着《伤心沟》的原稿,到了那个公社的领导机关所在地。
公社里的大小干部,忙着招待我,给最上等的香烟,茶叶也是高档的。他们并不要看我的介绍信,只是问了问姓名,开口都是用“作家”称呼我,倒弄得我不好意思。没多大工夫,原先那个去过编辑部的青年来了,看到我,他显出几分紧张,几分尴尬又有几分羞涩的表情。他一时不知说什么话才好,只是问了句:“你怎么自己来啦?”。
我把他看做是唯一的老熟人,对他说:
“我这次来是想访问一下《伤心沟》的作者,研究怎样把这篇稿子修改好。”
他听我这么说,红着脸,越发说不出话来。幸亏在他旁边还站着一位负责政宣的干部,此人名叫张彦红,四十岁光景,穿一双白帮的网球鞋。张彦红马上含笑回答说:“今天不早了,作家一路上够累了,先歇息吧。”
于是那个青年乘机走开了。我向张彦红提出想见见你们的党委书记。他说:“不巧,党委徐书记到县上开会去了。”
我说:“我想找焦老师谈一谈。”
他有点为难的神色,说:“好,我去通知他。”在他离开我之前,他又问了一句:“叫他来是商量修改那篇稿子吗?”
我“嗯”了一声,他又进一步试探我:“你们是不是打算发表出来。”
我又“嗯”了一声,他就走开了。
晚饭后,我跑到街后一个农民家里。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农民工坐在长櫈上打草鞋,我走上前去,先敬他一支烟,问道:“你这是打草鞋吗?”他端详了我一会,然后说:“可不是,开河很费鞋,穿上这草鞋不打滑。”
“你们挖的是一条什么河呀?”
“挖一条没有水的河。”这语言跟焦克义的小说差不多。
“当初是谁的主意挖这条河的呢?”
老农民放开打草鞋的手,猛吸一口烟,说:“总是上级罗,我们当老百姓的,上级叫下海掏龙王爷的心肺、上天采月宫里的桂花,一个号召,我们不是也得去吗?”
正在这么讲着的时候,张彦红闯进来了,他一见到我,很抱歉地说:“我替你找过焦老师了,真不巧。他在三天以前到专区参加集训去了,要半个月才得回来。”然后,他又说:“你也真是分秒必争,不早点休息去!”
我说我找个老大爷随便谈谈,张彦红连忙对老农民介绍说:“这是上头来的作家,专门采访挖河的工程来的。”
老大爷马上接过话来说:“是啊,这条河的工程可了不起,我们这个公社连续三年得过大寨先进红旗咧。”
“能不能再讲得具体点?”
老大爷想了好久,才想出这么一句话:
“听说五年的工程,可以在地球上绕两圈咧。”
张彦红纠正他说:“是指挖出来的土方,可以绕地球一圈,没有两圈。”
“对,只有一圈,我记得当初还是听你说的,你看我这个胡涂脑筋!绕地球这一圈,就整整干了五年哪!”
由于有这位政宣组长在一旁,估计这个老农民不会再掏出心里话来了。于是,我只得怏怏地回到公社的宾馆去。
宿舍外边是两尺宽的走廊,我一时不想睡。在走廊上看看乡村小市镇的夜间风光,当我朝下俯视时,我看到楼下有一个人影在晃动。过了半个多小时。我惊奇地发现这个人影还在,我从他的背彤认得出:他便是去过我们编辑部的那个年轻人。
(二)
第二天由张彦红陪我去看那条人工河。我们俩出村没多远。后面跟来了一大帮男女老少,足有三、四十口人。我以为这恐怕是领导的意图,“运动群众”运动来的。心里想:今日个不知又要搞什么名堂。
走出村不到四华里的地方,就看到迎面横着一条大沟,足有四丈宽,沟底里已有没膝盖深的水;沟的两岸栽着低矮的杨柳。张彦红指指不远地方架在沟上的钢板桥,很得意地说:“这是农村最新式的桥。”
我们沿着河岸向最新式的桥走去。岸边可以看到当年农民扔在这里的许多草鞋。还有一半埋在上土里的防滑用的草袋,不成形的破箩筐,以及民工做饭而熏黑了的土坑。走近桥堍,在《伤心沟》一文里描写的用大块铁皮做的标语牌果然耸立在两岸,连那上面的语句都是照抄不误。那些摹豪言壮语虽然字迹模糊,但依稀可辨,上面写着:“兴修水利,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三年苦战,幸福万年!”递有一条是:“学大寨,流大汗,建设干顷丰产保收田!”不过我注意到有一块标语牌上,有谁用钉子画了个不规则形的乌龟,这是没文化的人表示愤怒的原始艺术。如今这些花了不少钱做的标语牌似乎成了嘲讽这个“伤心沟L的纪念牌坊。
跟踪我的农民人数在增加,当我们来到最新式的钢板桥上,站在桥上的社员就很多,张彦红站在最高处吆吗,他说:“你们跟来做什么?场院上的活儿你们不去好好干。有什么好看的?我陪作家参观这个水利工程,难道你们还没看够?”那态度的严厉和粗暴,跟对我的恭敬和客气判若两人。
一个农民大声地说:“我们就是要听听专家的意见。”
另一个青年农民针锋相对地说:“是的,我们没有看够,可是我们做够了!”
又是一位妇女的声音:“专家,你说吧!挖这条死水沟有什么意思?养蚊子还是养金鱼?”
“今年高低不挖了,咱再也不要那个倒头红旗,人么做煞!”
这时我才知道我原先的猜想是错了,这些情绪激昂的群众是把我当成了专家(一字之差),自发地跟踪我视察并提意见来的。
这些激愤的话把这位政宣组长弄得面红耳赤、狼狈不堪。他又一次地大声吆喝:“阿龙,快把他们带走,不要在这里瞎起哄!”我注意到这个阿龙是个紫红色脸膛的老汉,他的背有点驼,肩上背着一个粪篓子,他走出人群拉开嗓子嚷嚷起来:“有话回去说,现在兴民主,不要在首长眼前罗嗦啦!”
这个老汉可真有威信,他这么两句话,在桥上站着的男女社员就陆续往桥下走。这时一个年轻的农民挨近我身边,恳求地说:“你是专家,我们来就为的听你一句话,今年冬天这条河还挖不挖?”
我说:“我不是什么专家,这方面我是一窍不通。”
群众感到失望,渐渐走散了,我跟张彦红沿着“伤心沟”朝南走,这位政宣干部一路上给我做思想工作,他说:“伤心沟这个讲法是用心不良,是地富分子的污蔑,想破坏我们学大寨。所以在农村,阶级斗争还是复杂的,头脑里少了这根弦,就会分不清是非。”
我反问他一句:“刚才在桥上讲话的全是地富分子?”他不加思索,背诵如流地说:“这说明地富的言论毒害了不少人,而这些人又都是极端个人主义,他们怕做集体活,看不到全局,怕到河上干累活。嗯,在说话的人里头,那个女的,出身就不大好,她的外公是富农,娘家的叔叔是小业主,所以,对挖这条‘兴无河’有看法,说怪话,对他们不作阶级分是不行的。”
我们沿着“伤心沟”往北走,快走到深沟的尽头,才看到那里有一条东西向的河流,政宣组长介绍说:这是被当地人称作月牙河,是供给兴无河的水源。我站到月牙河口一看,连我这样对水利一窍不通的人,也看出兴无河的规划是盲目的,完全违反科学。原来月牙河是长江的支流的支流,由于月牙河沿岸建设了不少工厂,又开拓了许多水浇田,本来有限的水量就越来越欠缺。以致到了秋后,月牙河的水位就下降到可以赤脚过河的程度。五年前动工的兴无河指靠这么一个穷困的邻居供给水源,那真叫做缘木求鱼,陆地行舟。
这位政宣组长还不断地给我打气说:“你以为水源不足吗?那不要紧,长江之水天上来,每隔三年五年总耍发一次大水的,等我们把这条沟挖好,只要放进一次水,让它灌满,两头用水闸控制,这就好派用场了。毛主席说:困难的过去和胜利的到来,常常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如果我们半途而废,不但把农民群众五年的劳苦付诸流水,而且对不起党,对不起国家,对不起四个现代化。”
我不想再听他的这番宣传,便把话头引到《伤心沟》的作者身上,他昨天讲的焦克义到专区集训去了,这恐怕又是耍诡计,不让我见他的面。于是我说:“请你把焦克义去专区的地方告诉我吧,这回来乡下,我一定要见到他。”
他看见我的态度很坚决,却慢腾腾地说:“这个人不找他不妨事,他又不是什么大人物。他完全是想出风头,喜欢耍耍笔杆子,专替地富分子讲话的人,此人不是反革命,起码也是右派。寄给你们的那篇伤心沟,不就是一份现成的证据吗?”
我微笑着说:“就该给他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咯,是吗?”
他没有听出我话里边带着嘲讽的意味,这时我们已经离开兴无河,往小镇上走,他一边把脚步放慢,一边说:“当然,反党反社会主义,这决不是寃枉他,他破坏农业学大塞,破坏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伟大运动。这个人成分也不好,祖父是地主,作风呢,也不正派,喜欢跟在女学生后面甜言蜜语,依我看,这个家伙,戴顶坏分子帽子也够格了。”
我仿佛又回到了“四人帮”的统治时代一股冷气从脊梁一直冷到脚跟。
从张彦红的谈话里,我感到了焦克义遭迫害的不祥之兆,这就更增加了我的怀疑和不安。在第三天的夜晚,我决心去访问焦克义的家。
这是前后两进房子的宅院,焦克义果然不在家,接待我的是他的年轻的妻子,她跟焦克义都在一个学校里做教师。她见到我,非常惊恐,当我说明来意,并把《短篇小说选》等书放在桌子上,作为赠送给焦克义的礼物时,她仍旧用怀疑、害怕的眼光瞟着我。而对桌子上的礼物,她连眼睛都不屑看一下,仿佛那是一堆会引爆的违禁品似的。我一副热心肠,碰着这么一个冷面孔,心里真不是滋味。我只得自己找座位坐下来,讲了这样的话:“焦克义老师给我们写的稿子很有意思,很真实,他的写作是完全正当的。请你相信,再不会有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了。今后再也不许可像四人帮那样随便抓人、关人了。你把真实情况告诉我吧。
她这才含着眼泪说:“请你不要再提那篇闯祸的小说了吧!这篇文章,还没寄出去时,克义就给了几个好明友看,那些人全说这篇文章写出了我伲心里要说的话,不知是谁把这里头的意思捅出去了——那《伤心沟》的题目就怪刺激人的。这一下政宣组长忙起来了,要克义交出那篇文章,说是不拿出来就要抄家。我吓得发抖,他还是不肯把作品交出来。我父亲把克义骂了一顿,说他不知好歹,什么文章不好写,偏要去揭这块烂疮疤(她学着当小学校长的父亲的口气),你自己找死是你的自由,你可晓得还要拖累一家子?几十年来,为了写什么东西,弄得家破人亡,还见得少吗!如今稍微松动点,你骨头又痒了。这么说着,克义才肯把底稿交出来,总算没有抄家。
“事情并没有完结,张彦红这号人鬼得很,别的能耐咱不知道。追查反动言行啦,批斗人,贴大字报,整人啦,他可是精明极啦。他从邮局的一张挂号底本里,查出寄往你们这个刊物的单据,就把克义叫到革委会去,训了两次,第二次去了很久很久的时间,我以为他这次怕是回不来了,我连牙刷、毛巾、被窝都收拾好了。没想到晚上他回来了,脸色苍白,晚饭也没吃。他对我说,毛病出在那张挂号单上,头一次投稿,总怕稿件失落,又以为挂了号,编辑部会重视一点,就为的这张挂号单子留下了祸根。张彦红一定要他写信去讨回那篇《伤心沟》,克义这个强牛就是不肯写信,他说宪法刚刚公布,保障公民的通信自由,写得明明白白。
“这样他就跟张彦红顶牛,一直顶到夜里八点钟,他还是没有写信。要不是《四人帮》打倒了,像他这种脾气,老早被关到县监狱里去了。
“大前天晚上闯进来两个民兵,又是张彦红带来的,说是公社为了克义的安全,要他到N县去避风头,到那边还是做老师。规定一个月之内不让回家,也不许跟家里通信。我临时替他收拾了几件替换衣裳,还带了一只脸盆、一只网篮,却把毛巾、手帕、袜子、肥皂也忘了。就这样连夜把他押走了,就像押送一个犯人。
“我猜想他确实是蹲牢监去了。当克义走了以后,政宣组陶同志特别关照我:克义到哪儿去以及前天晚上的事,不许对任何人讲,所以你晚上闯到我这里来,这是大犯忌。你拍拍屁股可以一走了之,我这里的日子可不好过哩!对不起,你对克义的一片好心我领情了,如今你还是早点走,我真怕给他们的人碰见。”
我这才明白,克义在夜间失踪,为的是我下乡来害了他,我怀著有罪责的沉重和激愤的心情连忙起身告辞,克义的妻子指着放在桌子上的那几本书,坚决地说:“你赶快拿走,一张纸头也不要留,抄起家来有嘴也说不清。”她的这几句话好像鞭子在抽打我的心。我痛苦地只得收起可怜的礼物。
她最后说了两句:“求求你,那篇《伤心沟》真伤透了我的心了。千万不要登出来,要是登出来,就毁了我一家子了!”
我回答她:“请你相信,四人帮毕竟完蛋了。真是无法无天,我一定要把他弄出来。”
当我走出焦克义家的门不远,果然看到一个人影子远远地站在门外的枣树后头,我咳一声嗽,那个人影子露出一个头来,我认得出那个人是曾到上海去的年轻人。
(三)
《伤心沟》里有一段描述的拆迁户的生活,给我很深的印象,我提出要去看看拆迁户的村子。张彦红一再地劝说我不要去了,但他却违拗不过,只得陪我一同前往。
原来在《伤心沟》一文中写到,为了挖这条笔直的沟,毁掉无数的农田还不算,处在这条沟上的十多个村子还得全部拆毁。为了安置几千无家可归的农民,就临时搭起无数的窝棚,他们把这些窝栅叫做“大寨院”。
我亲自看到了“大寨院”是什么样子:下面是用土基(没有经火烧过的砖坯)砌的墙,上面盖的芦席,考究一点的是覆盖着油毛毡,为了防止大风把芦席和油毛毡吹跑,便把一些砖头、石块压在屋顶上。拆迁户从老家搬出的家俱、缸盆,放不进窝棚里,就在屋旁另造一问低矮的芦席棚,作为贮藏室。
我来到“大寨院”的一家,有一个老妈妈正在拉风箱生火,一阵阵呛人的烟雾弥漫了整个窝棚,使得我们没法走进去。还有一位中年妇女,在筦筐里拣赤豆,大概是她的儿媳妇,我先给老妈妈打招呼。她眯细着被烟雾熏出泪水的眼睛,从头到脚看了我一遍。我便坐在她身边的矮凳子上,问她:“我是来看望你们的,老妈妈,在这里过得好不好?”
老妈妈打量了我好一会儿,便说:“我是一半埋在土里的人了,好也过,不好也过。”她一只手还在拉风箱。
“你原来住在哪个村里的?”我问。
“徐家塘。那是我们祖祖辈辈的村子呀!提它干什么,五年前早踢蹬平了,连一根青草也不留。”张彦红发觉这个老妈妈说话带出牢骚。心里直叽咕,便对我说:“另外找一家吧,这个老妈妈光知道心疼老祖宗那点房子。”
他越想引开我,我越是不肯走,我坐在矮凳上不动,继续与她说话。老妈妈抬头望了望这位张同志!似乎她刚才没注意在我的身后还站着一个人。当她认出这位张同志是公社的干部,却引出了如下一大篇的话语。
她先问了我一句:“你是不是省里的?你要是省里下来的官,我告诉你吧,当初是他亲口讲的,说是拆毁了我们的村子,给我们另造个二层楼的大寨院,保证上一代的跟年轻一代的分成两大间,.这是不是你讲的?”说到这里,老妈妈把我撂开了,把睑转向张彦红。张彦红想溜,又溜不走,只得硬若头皮挨骂。
“我们想把原来房子的木头、门框拆下来,在这里搭个临时的房子,你们不让,说是这些木料要留着去造大寨院咧,一切归了公。等了你们一年,二年,三年,头年才过门的新娘子生的小孙孙都快五岁了,你讲的那个大寨院还不见动工。你讲的那个大寨院呢?是一只空心汤团。把我们骗到这么个倒霉地方,大雨大漏,小雨小漏,想不到我年过五十,还要摊着这一步苦运!你说,这不是活受罪吗?”
在筦筐里拣赤豆的儿媳妇一直没作声,这时她插言道:“你说这些有啥用?房子早拆掉了,你今日诉苦,明日去闹,也还是没有房子。我们这里不是也叫大寨院吗?不方便的就是两代人挤在一起。爹爹的好多奖状镜框一块也没地方挂。”
正巧那位叫阿龙的老汉挎着个粪筐走进来.他看到张彦红跟我,马上放下粪筐,招呼着往屋里坐。这时老妈妈用嘲弄的语气说:
“我们这个窝棚怎么好招待大干部呢,白天里头黑糊糊的,烧柴的烟直呛人,一只象样的椅子都搁不下。”
阿龙从口袋里掏出半匣香烟来,一定要我点一支,一面说:“叫你们好等吧!”
我说:“我是随便走走,不一定找你。刚才跟你老太婆谈得很有意思。”
这时儿媳在一旁说:“刚才妈妈又为了房子的事情给这位省里来的同志诉苦了。”
阿龙的脸涨红了,好象做了亏心事似的,很抱歉地朝张彦红望了一望,说:“她就是唠叨,为那个房子她不知唠叨多少遍了。”他又转身朝着老妈妈说:“我们要想到解放以前吃不饱饭的那种日子,房子住得宽敞有什么用?我们现在住的大寨院就不错嘛,大前年闹地震警报,好多住瓦房的都羡慕我伲大寨院咧,我们这个房子就是不怕地震,真有地震也压不死人!”
我苦笑了,阿龙的这番解释给张彦红解了围,他夸赞着阿龙阶级觉悟高,又要引他讲出挖兴无河的好处来,阿龙也果然回答得很得体,他说:“兴无河只要有水,不管水有多少,就是胜利,不能行船也好,罱河泥嘛!”于是我们告辞了出来。
在路上,张同志称赞阿龙老汉说:“阿龙真是个人红心红的贫下中农。他有眼光,有见识,他能够在工程没完成以前就看出优越性来。他是地道的贫下中农,连续四年评上学大寨先进劳模。他是我们公社的标兵!”
(四)
我经过深思熟虑以后,决定全力以赴的为援救焦克义而奋斗。第一个步骤就是向张彦红放空气:如果再不把焦克义放出来,我就要告到省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去。这一着果然有效,空气一放出去,使得党委书记改变了避不见面的初衷,同意跟我见面了。
我由张彦红领着,来到公社办公楼,我看到这位徐书记头顶秃了一半,浓眉大眼,是个短小精悍的六十岁上下的人。他很有礼貌地接待了我,并且向我道软,说是他没能亲自陪我到兴无河边去看看。
我们谈话时,张彦红同志坐在一旁,党委书记则坐在圈身椅里。我开门见山,带着不满情绪对他说:“我这次来就是想见一见焦克义同志,你们把他弄到什么地方去了?”
徐书记象个得胜将军似的神态,微笑着说:“听说你想到纪律检查委员会告我状,这没有什么。每个人有他自己的民主权利嘛!我们并没有把焦克义隔离或是送公安局,这个政策界限我们还是掌握的,我们只是给他换个工作环境,防止他在错误的道上走得更远。让他到N县做代课老师,这是违犯哪一条政策呢?”
“他就是写了那篇小说,这是什么错误,为何要采取这种组织措施呢?你们的公社出了这么个人才,做领导的应该高兴,用心培养……”
他没等我说完,就接着说:“像焦克义那样把我们党看成眼中钉,我们不能培养,这是个阶级路线问题,这是大方向,含糊不得。”
我说:“在你们的培养下,只能产生鹦鹉,恐怕产生不了作家。”
徐书记也有点来火,冲着我的话说:“我宁愿要鹦鹉,也不要乌鸦!他那篇《伤心沟》,你看过的,他在那里面把个公社党委书记写成个什么样子了啊!写得阴险、专制、好大喜功,瞎指挥,简直成个土霸王了。这会给读者什么影响呢?”讲到这里,他把圈身椅转向张同志,几乎是向他求救的神情,说:“你可以出来说明嘛,我是不是这样的人?”
张彦红赶快作证:“这完全是焦克义恶意揑造。”
徐书记嘴里吐出唾沫星子,决断有力地说;“这篇稿子不发表出来万事皆休。要是刊登出来,一切后果得由你们编辑部负责。”
我发现了他心理上的弱点:他最怕这篇文章刊登出来,我偏要说准备发表。他有领导整个公社的权,我们编辑部也有发表某一篇文章的权。我说.“这是一篇小说,它其中的公社书记并不是真人真事,可以指的是你,也可以不是你。作者可以自由创造他的人物。只要他写的东西基本上符合现实生活。就可以发表,焦克义的文章还是有可取之处的,我这次下来是了解一下事实的真相。我坦率地告诉你吧,我认为他写的故事是真实的,没有什么夸大,而且还遗漏了一些应该写进去的人物。”我把眼睛望了一下张彦红,他好像触了电似的不知所措。
徐书记像被火烫着了一般那么不安和焦躁,大声地问:你们编辑部一天耍收到好几百篇文章,什么文章不好登,偏要登这种非驴非马的东西?“
我的嘴边露出微笑,这时我倒变成了得胜的将军似的,对他说:“你们如果不把作者放回来,这不又是一篇你自己提供的现成的小说题材?”
他的半秃的前额沁出汗来,气咻咻地说:“我们并没有把他关起来,本来,要是四人帮掌权时期,像他这号人:”只要党委一个条子,他就乖乖地进去了,没有还价!“
我说:“你们是用两个民兵把他押送走的。”
徐书记用手抹一抹前额,从椅子上站立起来,疑惑地问张彦红:“怎么会有民兵押送?我们没有这么干嘛!”
我睁大着眼睛看着张同志,他结结巴巴地说:“为了保护……他的安全,我是派了两个民兵,押送到N县教育局,不用民兵生怕半路出什么事。”
张彦红的“坦白交待”使徐书记火冒三丈,他大声责备政宣组长:“你办事总喜欢做得过头!你们弄惯了,从前碰到阿五、阿六、张三、李四不听使唤,动不动就是派民兵。如今四人帮倒了,你还是动用民兵。这就把人民内部矛盾升级到敌我矛盾,这确实是违反政策。”这番话训得张彦红手足无措,涨红着睑不停地说:“是,是。这一点是做过头了。”
看样子,一个发火,一个认错,不像是做戏做给我看的。
徐书记关照张彦红:“那就这样吧,打个长途电话,把焦克义叫回来就是了。让他回来。不相信一个教师能翻得了天。”
张彦红起身出去,一面战战兢兢地说:“打电话怕说不清楚,派个人去吧。”当他走出门以后,徐书记对我说:“这个人还没转过弯来,过去遇到每个大转折,他转弯最快,这一回工作重点大转移,他就跟不上了,一点不知道新的政策,真没有办法!”
然后他用很亲密的语气说:“你们真看中焦克义的文章?能不能把那篇稿子放在明年开春以后再发表?当然,最好换个题目,因为《伤心沟》这个名字这里方圆几十里的人都晓得,兴无河这个名字反而没人叫。”
我问:“为什么要拖到明年发表呢?”
“给你说实在的吧,今年年底整个专区要评比大检查,要是这篇《伤心沟》一登,我们保持了五年的大寨先进单位岂不完全泡汤了?这不仅关系到我们一个公社,还关系到整个县呢。四邻公社要是得知这篇稿子是我们公社的人写的,他们不但要撬掉我们的先进牌子,还要骂我们吃里扒外,你想想,这个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咧。”
“只要把焦克义叫回来,他那篇稿子晚一些时发表也可以。”我刚说完,张彦红回来了,他怯生生地说:“我打发陶福海骑自行车去的。”然后他转向我说:“我们一点没有难为他。”说罢,他又坐在原来的位置上。
这时我又进一步向徐书记讲了这三天来所得的印象,我说:“我看你们挖这条河,一开头就干得盲目,违反科学,违反人民利益。你们不要将错就错了,应该结束这场劳民伤财的工程了!”
徐书记把圈身椅转向窗口,背朝着我,这也许是表示对我的轻蔑,也许是在思考我的意见呢。大约过了五分钟,他的身子转过来了,他的脸色是温和而又诚恳的。他说:“你这个高见我在开工第三年上就看出来了。那年省水利厅来了一个专家视察了一番,便对我们说:”毛主席指示我们修地球的,可不是要我们破坏地球哪!“他说江南是水网地区,湖泊、池塘很多,而耕地很少,你们缺的不是水,而是土地。他还说挖这条河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反而把地下水的走向搞乱了,他说这条河不过是聋子的耳朶——空摆设。当时县委、公社骂他是摇头派,没有一个人理睬他。只有我承认他讲得有道理。因为第三年上兴无河两岸的庄稼明显地减产。那时候已经是骑虎难下,我一个人也是孤掌难鸣。不把河工完成,不仅是县委书记刘海文的失败,也是我们党委的失败。我们为它做了多少宣传呀!纸张笔墨消耗掉多少呀,还开过几次现场会呢。(我立刻联想到矗立在河两边的铁皮做的那么多标语牌和花了几万元架起最新式的早桥。)
徐书记的这段话对张彦红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他的信仰,他为之辛辛苦苦连续干了四、五年的伟大事业,连同他所吹嘘挖出的土方足够绕地球一圈的宣传,一同崩溃了。他冻僵在椅子上,就像没有剥去包装纸的一根棒冰。
徐书记的话也使我感到吃惊,我预先不晓得他是这样的人。一下子我们之间的距离、猜疑消失了。我进一步建议道:
“过去干错了,那责任完全可以推到四人帮头上,如今拿出勇气来,向群众说明做错了,群众也能谅解的。从今冬开始,索性把伤心沟填平它,不更好吗?”
徐书记皱了一下眉头,眼睛里几乎有潮湿的泪水,说:“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所有挖上来的土方,这几年全给运去烧了砖瓦。如果要从外地运泥巴来,到哪里去弄那么多的土,而且运输的劳力不会比挖河花的人工少哇!不但如此,当年我们发动农民挖河,是理直气壮,情绪昂扬的,如果现在花力气来填平它,老百姓挑一筐土就骂你一声娘,你受得了吗?那几千口人的拆迁户就要吵着要还他们的老房子,你受得了吗!”
我说:“既然有困难,那么,今年先停下来,不要在膏药上面再贴膏药了。”
徐书记很为难地说了下面的一席话:“我们一个公社扭不转这个局面。前不久我们的县委书记布置今冬明春开河大会战的任务,还对天盟誓说了豪言壮语:我们要再接再厉.把地球挖穿也耍挖出水来!你看,事情已经弄得这般僵,胳膊扭不过大腿呀!”
当我知道焦克义确实回了家,我才放了心,但我没有去看望他,也不把原稿退给他,因为我生怕又引出一些是非来,有可能连累他一家遭遇不幸,我必须竭力避免。至于“伤心沟”留下的后遗症,徐书记都无能为力,我一个外地的编辑有什么能力挽回这个局势呢?我决定回上海去。
(五)
过了一个月以后,焦克义又寄来了《伤心沟》的尾声,正好给我这个故事做个结束。
原来阿龙打听到我是为焦克义的一篇文章才到他们公社来的,阿龙老汉就去找焦老师。两个人谈到今年还要开挖“伤心沟”的事,阿龙说:只有发了疯的人,才主张再挖下去。焦克义怂恿他到专区去上告,阿龙说:到专区去不顶用,要上告,就得告到省里去。于是焦克义跟阿龙,还约合了三个人。自带盘费去了省城,最后找到了水利厅。出来接待的人正好是两年前到过“伤心沟”视察的那个专家。阿龙一面讲着“伤心沟”坑害了农民的情况,一面从包袱里把一大迭先进个人和劳模奖状、奖牌撒在桌上,说:“正是这些奖状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如果真是干了为国为民的好事。我得到国家的奖励当然感到光荣,可是我干了这些年,干的什么呀!每次的现场会上,总要叫我照着张彦红起草的稿子一本正经地发言,其实全都是骗人的假话。这些奖状使我不好做人。”
后来才晓得这个水利专家靠边站了十来年,不久才任命他做水利厅长的。他说,马上派个专家小组下去调查。过了一个多星期,上面果然派来了四个人组成的调查团,调查团下乡勘察了五天,最后由水利厅正式通知县委:停办这项水利工程。
焦克义的来信最后写道:“今年我们这个县的农民总算过了一个”囫囵年“(春节时全家团圆,没有欠债,不出劳役,没有病痛,欢欢喜喜过年,叫做囫囵年)。大家兴高彩烈,只有县委书记不大高兴。说什么,不挖这条河,今年评大寨先进拿什么来评比。我们的徐书记跟我们一样高兴,还允许我们五个人上告的旅费在公款里报销哩!”
他还在信里说,“如今,发表那篇使我伤心的小说已无大碍。不过.考虑到我们的方针政策常常变更,今天肯定了的,说不定明天就推翻,所以在发表时还是不要用真名真地点,尤其是白纸黑字的东西。”我是遵照他的嘱咐,拖到今年春夏之交才刊出这篇《伤心沟》的。我这篇纪事不过是伤心沟和我这篇《代序》里所用的县名,公社名都是虚构的,连焦克义也不是原来的姓名,请勿妄加猜测。
——原刊于一九八零年六月《上海文学》
【编者注:为纪念王若望先生,本站特转此文。文章的观点,并不代表本站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