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四十年前农村往事录
《饥饿引发的变革》在第三章《青山遮不住:农村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深入展开》中揭露了大量极左路线在农村造成的灾难,同时也披露了广大农民发出的强烈愤懑。请看以下报道:
各地农民发出愤怒的质问
“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横行,″学大寨“运动的强硬推行,给农民的生产生活造成深重灾难。在当时的高压之下,农民敢怒不敢言。到1978年,他们胆子开始壮了起来,对那些”左“的做法发出一声声愤怒的质问。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共河北省沧县县委错误地把农民的自留地,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和“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来批判,先后将全县绝大部分社员的自留地收归集体耕种。广大农民对此极为不满。“四人帮”垮台后,沧县县委仍不解决社员的自留地问题。
1978年3月上旬,全国五届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的新宪法公布了。宪法第七条明文规定:“在保证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人民公社社员可以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在牧区还可以有少量的自留畜。”沧县广大群众高兴地说,新宪法说出了咱们的心里话,这回县委该按国家的根本大法办事了。一些社队开始把集体经营的自留地分给了社员。大褚村公社大褚村大队第九生产队开会商量后,一人分三厘菜地,谁种就归谁。事过两天,公社党委书记陈某得知此事,马上打电话给县委副书记韩某报告。韩某立即让县委“学大寨办公室”派人前去调查。接着,韩某在一次电话会议上说:“关于自留地问题,宪法公布后又有的分了。县委初步学习了新宪法,认为自留地集体经营是对的,符合大方向,有利于集体生产。凡是重分自留地的,就是复辟倒退,就是留恋资本主义!”
沧县县委的做法激起了广大群众的极大愤慨。社员气愤地说:“是县委大,还是宪法大?”有的社员说:″县委这样干,上不听中央指示,下不顺民意!“还有社员说:″现在是两头清楚,中间糊涂!”有一个大队党支书对公社领导说:“社员经营自留地符合新宪法,反正我们按宪法办事,你们要是怕的话,就领着俺们去找县委,俺敢和他们辩论!”民心不可违,尽管县委一再下禁令,许多社队干部仍然不理他们那一套。到5月底,全县已有6个公社50多个生产大队把自留地分给社员自己去经营。
拖了一段时间后,最后还是县委认输。
“宪法大还是县委大”?这虽然是个不言而喻的问题,但充分说明在现实的社会环境下谁才是主宰一切的无上权威。沧县县委之所以敢无视宪法权威,是因为他们知道在宪法之上还有“王法”一一上级党委权威。该文披露,在新宪法公布以后,沧县当地的上级党委制定了一个《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规定”中关于自留地是这样说的:″自留地可以集体经营,也可以个人经营,已经集体经营的要积极种好,一般不再变动。“沧县县委看到上级党委的”规定“,感到上级党委对自留地的经营方式明显地倾向于集体经营。因此,下面的领导干部即使认为”规定“不符合宪法精神,但也不敢不执行。他们宁可违背宪法和得罪群众,也要看着顶头上司的脸色行事。这其中的利害关系人所共知,在此就不多说了。该节文章还报道,有一次,沧县县委学大寨办公室向县委汇报新宪法公布后广大社员强烈要求把自留地分给社员个人经营时,县委的一位领导说:″咱们还是听上级党委的吧!”县委当然小于宪法,但宪法能大于党委吗?
另一声责问发自湖北省的钟祥县。责问是愤怒的,但口气又有几分幽默。那里的农民问:“摸鸡笼子是社会主义吗?”
事情是这样的。有段时间,钟祥县农村中刮起了一股“摸鸡笼子”的歪风,半夜三更,社员家鸡笼子被一些干部摸了,鸡被杀掉。农民们对这件事非常气愤。有的人在鸡笼子里放上镰刀,结果前来“割资本主义尾巴”的人摸鸡不着反而把手割破了,一时间传为笑谈。
“四人帮”垮台后,一些社队的社员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摸鸡笼子”是社会主义吗?社员养鸡是资本主义吗?旧口公社建新大队历来都有饲养家禽的习惯,1973年,这个大队社员养鸡3900多只,平均每户养鸡13只,年收入四五十元。然而,″四人帮“极左路线的追随者却把社员养鸡诬蔑为给资本主义”供氧输血“,是″留恋小生产”。他们大搞所谓″割资本主义尾巴“,要把包括养鸡在内的社员家庭副业统统砍掉。从1974年冬天到1975年春天,当地有人提出”鸡头不能超过人头″,“剁鸡头,革鸭命,房前屋后砍干净(砍树)”的口号,并且挨家挨户地“摸鸡笼子”,核对鸡头,多养了的都要处理掉。几天时间,全大队社员养的3900多只鸡,被处理掉两千多只,真是搞得“鸡犬不宁”。
在建新大队批判“四人帮″的社员会上,73岁的老大娘胡元珍说,我们老太太养几只鸡,把鸡蛋卖给国家,家庭增加了收入,也支援了社会主义建设,有什么不好?我们增加这收入,可顶大用场了,称盐打油,看病买药全靠它,不愁零花钱。胡元珍大娘谈到,1977年,她家养了18只母鸡,卖鸡蛋收入70多元,解决了一家七口人的零用钱,还给儿媳、孙子添了三套衣服。她气愤地说,社员怎么能缺少这项家庭副业?”四人帮“不安好心,把社员养鸡说成是发展资本主义,他们就是想把我们社员搞穷。
1977年,建新大队三百多户社员共养鸡4800多只,平均每户16只,全年向国家交售鸡蛋18000多斤,收入12000多元,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年。
这个小故事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今天的读者看了可能会哑然失笑,感到不可理喻。然而,当年却是中国农民们必须面对的严酷现实。
其实,坦白地说,说“四人帮”肆意破坏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实在是有些冤枉。因为当时无论是谁,只要他服膺毛的权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他都得“斗私批修”,坚决铲除一切资本主义的东西。“四人帮”以及追随者之所以挖空心思搞极左的东西,目的完全是为了遵照毛的旨意实现毛的理想一一乌托邦社会主义。这本书的作者为尊者讳,将中国农村不尽如人意的问题推给“四人帮”,出于无奈,但情有可原。但是,问题多了,时间长了,难免不能自圆其说。其实,大家看了以上叙述都会明白,当时农村的问题症结在于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四人帮”是毛的忠实追随者,说他们是“破坏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是罔顾事实。事实是,在毛定于一尊的情况下,“党的政策”本来就是如此!
在中原大地,河南的农民也在责问:为什么不让我们种生姜?
……记者访问了河南省蔬菜公司,据他们统计,1959年全省生姜产量2400万斤,可调出200万斤,出囗若干万斤。近几年来,市场上却买不到生姜了。问题出在哪里?
有关部门提供的大量事实证明,“四人帮”是破坏生姜生产和供应的罪魁祸首。
河南的生姜,数博爱县上庄公社生产的“清化姜”品质最好。在五十年代,这个公社生姜种植在三千亩以上,年产生姜一千多万斤,是我国著名的商品姜生产基地。由于“四人帮”的破坏,到1976年,全公社生姜只种了75亩。
上庄公社的社员按捺不住内心的怒火说,种姜是个苦活,可是为种姜我们却惹来戴不完的帽子,挨不完的棍子,受不完的窝囊气。你种点姜,有人就攻击你“金钱挂帅”,搞资本主义。近几年来,一是卡面积,全公社10579亩地,规定种粮面积不得少于9900亩。二是停止供应种植生姜用的饼肥。一卡,一停,哪里还能多种生姜?
浙江省吴兴县的农民在责问:为什么砍掉我们的桃树?
这一呼声是通过一封读者来信在《浙江日报》上发出的,接着新华社、《人民日报》转发了这封信,使全国人民都听到了他们的呼声:浙江省吴兴县便南公社潘店大队农业学大寨工作组违反党的政策,强行砍了社员自留地上的桃树。这封来信立即在浙江省农村广大干部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还有一声惊人的责问来自海南岛。1978年,新华社记者在海南见到这样一个荒唐的场景:东方县发生了一件所谓火烧“资本主义”的咄咄怪事:该县板桥公社文质大队干部胡作非为,放火把一些社员割的茅草烧了。
割茅草历来是板桥公社一些生产队的集体副业,也是许多社员家庭的一项副业。附近莺歌海盐场等企业每年都要用这些地方的茅草搭盖工棚、仓库。文质大队的一些干部往年就把一些社员割茅草当作资本主义来批。10月19日,文质大队的干部们开会决定:火烧“资本主义”。当晚,大队干部们就到野地里社员的茅草堆上点了火。他们从夜晚一直烧到第二天下午。社员们看到自己的辛劳成果化成灰烬,不禁发出责问:这把火烧的真是“资本主义”吗?
福建省的农民们在发问:雨量充沛、四季常青的福建省,为什么前几年经济作物产量大幅度下降?对此,新华社一名记者通过调查作出回答:“四人帮”一伙把多种经营,搞各种副业当作资本主义倾向加以批判,结果是″以粮为纲,全面砍光“,给全省的多种经营带来了严重的灾难。
福建省搞“全面砍光”的第一把刀是用“夺粮”的口号取代了“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
第二把刀是把发展经济作物统统作为“资本主义”来批判。福州市建新公社建中大队过去种植香料作物八百多亩,号称“百花园”。可是竟被作为“溅满封、资、修毒汁”的“黑样板”,说他们种植的香料作物是“封、资、修的温床”,硬是强迫群众把香料作物统统砍掉。农民含着眼泪,举刀砍向那些长了几十年的白玉兰树……就像建中大队那样,批呀,砍呀,整个福州市郊区的香料作物被砍伐殆尽。结果,这些社队收入锐减,有的由原来的富队变成了穷队。歪风所及,有个时期,福州市每人平均一两蔬菜都供应不上。城镇居民说,难道只有这样才算是″社会主义“吗?
内蒙古自治区纯朴的牧民们实在难以弄明白:我们养牛马羊给国家贡献皮、毛、肉、奶,国家给我们供应口粮,怎么能算是″吃亏心粮“呢?
″牧民不吃亏心粮“,是″四人帮”横行时提出来的一个极为荒谬的口号。
要牧民种粮,就要弃牧开荒。内蒙古牧区多为干旱草原,在这里开荒,常常是“第一、二年收点粮,第三、四年变沙梁”。结果是开垦一亩粮田,沙化三亩草原。伊克昭盟近20年开荒导致沙化600万亩,流沙侵吞草场1200万亩,这对草原资源是一个严重的破坏。收了眼前小利,造成百年大害。……
看了以上报道,让人触目惊心的是,中国农村在二十多年里似乎被一伙犯罪分子所统治:农民失去人身自由,不能自由择业迁居,养的鸡鸭被抢走,种的蔬果被损毁,花草树木被砍光、烧光,动辄被批判斗争,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贫困匮乏,社会福利天方夜谭。在这种社会环境下生存,还得对统治者歌功颂德,感激涕零,真是难为亿万农民群众了!
这是一段不堪回首的社会历程!不客气地说,这是与人类文明社会之路背道而驰的歪门邪道!如果让几个美国农民、法国农民、加拿大农民、澳大利亚农民、日本农民、印度农民、荷兰农民……在七十年代来中国当一段时间的人民公社社员,没准这些人会疯了的!当时的中国人民自以为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正确指引下”,沿着“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胜利前进呢。现在回想起来,只要是理智健全、思维正常的人,有谁会认为那是一些正常现代文明社会的现象呢?如上所述,那些社会现象是多么可悲、多么可怜、多么可笑、多么可恨啊!
现在我再次发问:当你了解了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村的情况,你还怀念毛时代吗?你还赞颂毛的路线吗?你愿意在那种社会环境下生活吗?
再接着往下看吧!
湘乡农民不堪重负引起中央重视
湖南省湘乡县历史上曾是一个农业发达地区,然而在农业学大寨运动深入开展的七十年代中期,这里的农业却连续四年徘徊不前。
是什么阻碍着这里的农业生产发展呢?
1977年冬天,中共湘乡县委在揭批“四人帮”整风运动中发动群众找问题,终于找到了农业上不去的原因:这些年来四面八方向农民伸手,造成了农民不合理负担过多过重。农民不堪重负,哪里还有生产积极性?
湘乡农民负担来自各个方面,中共湘乡县委作了分析归纳,大约有以下八个方面:
第一,有的单位无偿地平调生产队的劳力、资金和物资,大搞非生产性建设。这几年,有的单位讲排场,摆阔气,刮起一股大兴土木、修建楼堂馆所的歪风。……
在大搞这些非生产性基建中,有的严重违反财经纪律,任意占用农业和社队企业的生产资金;有的搞乱摊乱派,拉走生产队的劳力、资金和物资;有的甚至不惜占用耕地,毁田建房。……
第二,有些单位和社队铺张浪费,吃喝成风,有的干部违法乱纪、贪污盗窃,任意侵吞社员的劳动成果。有的单位以协作、开会、检查之名,请客送礼,大吃大喝。
第三,非生产人员、非生产性用工、非生产性开支大量增加,各种摊派名目繁多,干部劳动少补贴高,农民不合理负担加重。1976年,太平公社非生产性人员平均每个大队有28人,占总劳动力的10.2%.同年,这个公社的各种非生产性用工达317315个,占全公社总用工的14.6%,平均每个劳力负担88.8个。这个公社的各种摊派费用共达61642元,平均每户负担21.9元。
第四,国家各级有关部门在兴办农村文教、卫生、交通等事业中,也把大量费用转嫁给生产队负担。……
第五,有的干部职工,长期拖欠生产队的钱,也是造成社员分配不能兑现的一个重要原因。1977年,全县国家干部职工拖欠生产队钱、粮的有6548户。有的干部职工欠生产队的钱不还,却盖了房子,买了自行车、手表、收音机,社员意见很大。
第六,发展社队企业,调用生产队的劳力多,付给的报酬少。1976年全县社队企业单位调用生产队劳力33325个,付给生产队的报酬平均每个劳动力为82元,到队的日工值只有一角五分钱左右。
第七,农田基本建设战线过长,过多地调用了社队的劳力和资金。从1975年以来,全县每年农田基本建设用工都在2000万个以上,比前十年的发展速度增加两倍。……
第八,一些工业部门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扎根不牢,有的支农产品价格高,质量差,数量不足,支农产品成了“害农产品”。农民说:“卖了耕牛买铁牛,买了铁牛变死牛,真是坑农。”
湘乡县委的报告说,由于上述情况,形成了“上下左右向生产队伸手,四面八方挖生产队墙角”,增加了农民负担,严重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面对这种局面,基层干部和群众呼声强烈。他们说:“如今是县里调、公社要、大队叫,生产队急得跳,不知队为基础的政策要不要。”有的说:″我们生产队像一棵棕树,今天你剥,明天他剥,剥来剥去,只剩下个小小的芯子了。“有的说:”现在上面办事是笼统一万三,大家来负担,搞得生产队像五月的萝卜空了心。“
中共中央在批转湘乡县委的报告时,加了一个很长的按语,说“湘乡县委提出的问题,是一个在全国相当多的地方普遍存在着的严重问题。”特别突出地要当地解决好农民″增产不增收,多劳不多得,分配不兑现“的严重问题。并把湘乡作为减轻农民负担的典型,向全国颁发了中共中央1978年37号文件。
农民负担问题由来已久。湘乡只是冰山上的一角。农民负担为什么重?原因是“上下左右四面八方”都向农民伸手,农民不得不就范。为了平息农民的不满情绪,当年中共中央特地发文严厉地重申反对一平二调、乱摊派。但这只能收到一时之效,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的根源是体制问题:统治者的权力没有任何有效制约,被统治者的权利得不到任何有效保障。
在民主宪政国家是不可能发生类似湘乡这种“乱摊派”的行为的。在民主国家农民虽然是个体经营,但农民的利益一旦受侵害,首先会有农民协会出面为此而抗争,农民还可以寻求法律和社会舆论的帮助和支持。况且,在发达国家,农民不但不需要向国家交税纳粮,国家反而向农民发放补贴。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又有谁会向农民伸手呢?没有各地议会的同意,任何组织都无权向民众伸手要钱。作为中国最大社会群体的农民阶级,几千年来一直处于无权无势的地位,他们的生存状态当然也就可想而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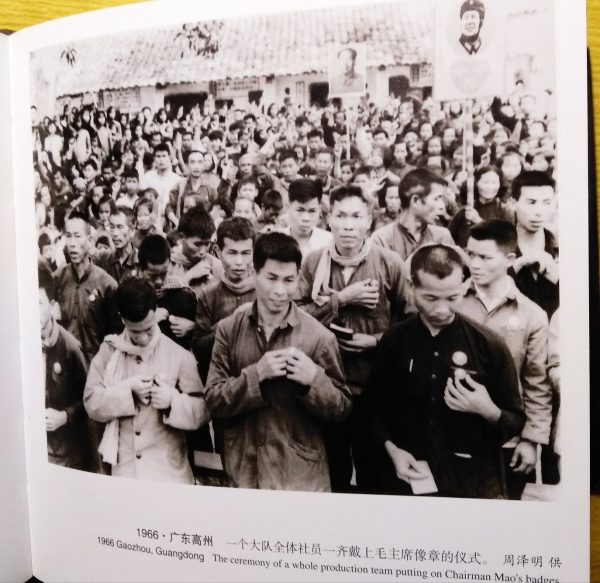
(未完待续)
荀路2019.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