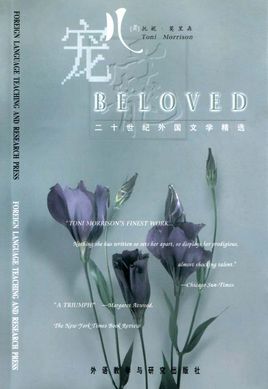第5章
第6章
“太太?你怎么啦,太太?”
塞丝走到一把椅子旁,拾起一张床单,尽她胳膊的长度抻开来。然后对叠,再叠,再对叠。她拿起另一张。都还没完全晾干,可是对叠的感觉非常舒服,她不想停下来。她手里必须干点什么,因为她又记起了某些她以为已经忘记的事情。事关耻辱的隐私,就在脸上挨的耳光和圆圈、十字之后,早已渗入她头脑的裂缝。
“他们干吗吊死你的太太?”丹芙问。这是她头一回听到有关她妈妈的妈妈的事。贝比·萨格斯是她知道的唯一的祖母。
“我一直没搞明白。一共有好多人。”她说道,但当她把潮湿的衣物叠了又叠时,越来越清晰的,是那个拉着她的手、在她认出那个记号之前把她从尸首堆里拽出来的名叫楠的女人。楠是她最熟悉的人,整天都在附近,给婴儿喂奶,做饭,一只胳膊是好的,另一只只剩了半截。楠说的是另一种不同的话,塞丝当时懂得,而现在却想不起来、不能重复的话。她相信,肯定是因为这个,她对”甜蜜之家”以前的记忆才这么少,只剩了唱歌、跳舞和拥挤的人群。楠对她讲的话,连同讲话时使用的语音,她都已忘记了。那也是她的太太使用的语言,一去不返了。但是其中的含义—却始终存在。她把潮湿的白床单抱在胸前,从她不再懂得的密码中分辨着那些含义。夜间,楠用完好的那条胳膊抓住她,在空中挥动着另一截残肢。”告诉你,我来告诉你,小姑娘塞丝。”然后她这么做了。楠告诉塞丝,她妈妈和楠是一起从海上来的。两个人都有好多次被水手带走。”她把他们全扔了,只留下你。有个跟水手生的她丢在了岛上。其他许多跟白人生的她也都扔了。没起名字就给扔了。只有你,她给起了那个黑人的名字。她用胳膊抱了他。别的人她都没用胳膊去抱。从来没有。从来没有。告诉你,我在告诉你,小姑娘塞丝。”
作为小姑娘塞丝,她并没有什么感觉。作为成年女子塞丝,她感到愤怒,却说不清楚为了什么。贝比·萨格斯的强烈愿望仿佛海浪冲击着她。浪过之后的寂静中,塞丝看着坐在炉边的两个姑娘:她的有病的、思想肤浅的寄宿者,她的烦躁、孤独的女儿。她们看起来又小又远。
“保罗·D一会儿就回来了。”她说。
丹芙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刚才,她妈妈站在那里出神地叠床单的时候,她咬紧牙关,祈盼着故事早点结束。丹芙讨厌她妈妈老讲那些与她无关的故事,因此她只问起爱弥。除此以外的世界是辉煌而强大的,没有了丹芙倒更是如此。她因自己不在其中而讨厌它,也想让宠儿讨厌它,尽管没有丝毫的可能。宠儿寻找一切可乘之机来问可笑的问题,让塞丝开讲。丹芙注意到了她是多么贪婪地想听塞丝说话。现在她又注意到了新的情况。是宠儿的问题:”你的钻石在哪儿?””你的女人她从来不给你梳头吗?”而最令人困惑的是:给我讲讲你的耳环。
她是怎么知道的?
宠儿光彩照人,可保罗·D并不喜欢。女人开始成长时,活像抽芽前的草莓类植物:先是绿色的质地渐渐地发生变化,然后藤萝的细丝长出,再往后是花骨朵。等到白色的花瓣凋零,薄荷色的莓子钻出,叶片的光辉就有了镀金的致密和蜡制的润泽。那就是宠儿的模样—周身镶金,光彩照人。保罗·D开始在醒来后与塞丝做爱,这样,过一会儿,当他走下白楼梯,看见她在宠儿的凝视下做面包时,他的头脑会是清晰的。
晚上,他回到家里,她们仨都在那儿摆饭桌时,她的光芒如此逼人,他奇怪塞丝和丹芙怎么看不见。或许她们看见了。如果女人们中间有一个春情萌动,她们当然能看得出来,就像男人一样。保罗·D仔细地观察宠儿,看她是否有所察觉,可她对他一点也不留意—连直截了当的提问都常常不作回答。她能做到看着他连嘴都不张。她和他们相处已经有五个星期,可他们对她的了解一点也不比他们发现她在树桩上睡着的那天更多。
他们在保罗·D到达124号当日曾经摔坏的桌子旁就坐。重新接好的桌腿比以前更结实。卷心菜都吃光了,熏猪肉油亮亮的踝骨在他们的盘子里堆成一堆。塞丝正在上面包布丁,嘟囔着她的祝愿,以老练的厨子惯用的方式事先向大家致歉。这时,宠儿脸上现出的某种东西—她眼盯塞丝时攫住她的某种宠物式的迷恋—使得保罗·D开口了。
“你就没啥兄弟姐妹吗?”
宠儿摆弄着勺子,却没看他。”我谁都没有。”
“你来这儿到底是找什么呢?”他问她。
“这个地方。我是在找这个我能待的地方。”
“有谁给你讲过这房子吗?”
“她讲给我的。我在桥上的时候,她讲给我的。”
“肯定是早先的人。”塞丝道。早先的那些日子里,124号是口信和捎信人的驿站。在124号,点滴的消息就像泡在泉水里的干豆子—直泡到柔软得可以消化。
“你怎么来的?谁带你来的?”
现在她镇定地看着他,但没有回答。
他能感觉到塞丝和丹芙两人都后退了,收缩腹肌,放出黏糊糊的蛛网来相互触摸。他决定无论如何也要逼逼她。
“我问你是谁带你来这儿的?”
“我走来的,”她说,”好长、好长、好长、好长的一条路。没人带我。没人帮我。”
“你穿着新鞋。你要是走了这么长的路,怎么从鞋子上看不出来?”
“保罗·D,别再挑她毛病了。”
“我想知道。”他说道,把刀把儿像根旗杆似的攥在手中。
“我拿了鞋子!我拿了裙子!这鞋带系不上!”她叫嚷着,那样恶毒地瞪了他一眼,丹芙不禁轻轻去摸她的胳膊。
“我来教你,”丹芙说,”怎么系鞋带。”她得到了宠儿投来的一笑,作为奖赏。
保罗·D觉得,他刚抓住一条银亮亮的大鱼的尾巴,就让它从手边滑脱了。此刻它又游进黑暗的水中,隐没了,然而闪闪的鱼鳞标出了它的航线。可是她的光芒如果不是为他,又是为谁而发的呢?他见过的女人,没有一个不是为了某个特定的人容光焕发,而只是泛泛地展示一番。凭他的经验而论,总是先有了焦点,周围才现出光芒。就说”三十英里女子”吧,同他一起等在沟里的时候,简直迟钝得冒烟儿,可西克索一到,她就成了星光。他还从未发现自己搞错过。他头一眼看见塞丝的湿腿时就是这种情形,否则他那天绝不会鲁莽得去把她拥在怀中,对着她的脊背柔声软语。
这个无家无亲的姑娘宠儿,可真是出类拔萃,尽管把二十年来遇见过的黑人琢磨个遍,他都不能准确地说出为什么。战前、战后以及战争期间,他见过许多黑奴,晕眩、饥饿、疲倦或者被掠夺到了如此地步,让他们重新唤起记忆或说出任何事情都是个奇迹。像他一样,他们躺在山洞里,与猫头鹰争食;像他一样,他们偷猪食吃;像他一样,他们白天睡在树上,夜里赶路;像他一样,他们把身子埋进泥浆,跳到井里,躲开管理员、袭击者、刽子手、退役兵、山民、武装队和寻欢作乐的人们。有一次,他遇到一个大约十四岁的黑孩子独自在林子里生活,他说他不记得在别处住过。他见过一个糊里糊涂的黑女人被抓起来、绞死,因为她偷了几只鸭子,误以为那是她自己的婴儿。
挪。走。跑。藏。偷。然后不停地前进。只有一次,他有可能待在一个地方—和一个女人,或者说和一个家在一起—超过几个月的时间。那唯一的一次差不多有两年,是同那个特拉华的女织工一起度过的。特拉华是肯塔基州普拉斯基县以外对待黑人最野蛮的地方,当然,佐治亚的监狱营地就甭提了。
同所有这些黑人相比,宠儿大不一样。她的光芒,她的新鞋,都令他烦恼。也许只是他没有烦扰她的事实令他烦恼。要么就是巧合。她现身了,而且恰好发生在那天,塞丝和他结束了争吵,一起去公共场合玩得很开心—好像一家人似的。可以这么说,丹芙已经回心转意;塞丝在开心地笑;他得到了许诺,会有一份固定的工作;124号除净了鬼魂。已经开始像一种生活了。可是他妈的!一个能喝水的女人病倒了,给带进屋来,康复了,然后就再没挪过窝儿。
他想把她撵走,可是塞丝让她进来了,他又无权把她赶出一所不属于他的房子。打败一个鬼是一码事,可把一个无助的黑人姑娘扔到三K党魔爪下的地方去,则完全是另一码事。那恶龙在俄亥俄随心所欲地游弋,极度渴求黑人的血,否则就无法生存。
坐在饭桌旁,嚼着饭后的金雀花草,保罗·D决定安顿安顿她。同城里的黑人们商量一下,给她找个地儿住。
他刚刚有了这个念头,宠儿就被自己从面包布丁里挑出来的一颗葡萄干噎住了。她向后倒去,摔出椅子,掐着脖子翻来滚去。塞丝去捶她的背,丹芙将她的手从脖子上掰开。宠儿趴在地上,一边呕吐,一边艰难地捯气。
等到她平静下来,丹芙擦去了秽物。宠儿说道:”现在去睡吧。”
“到我屋里来,”丹芙说,”我会在上边好好看着你的。”
没有比这更好的时机了。丹芙为了设法让宠儿和她合住一室,都快急疯了。睡在她上铺并不容易,得担心着她是否还会犯病、长睡不醒,或者(上帝保佑,千万可别这样)下床漫步出院,像她漫步进来时那样。她们在那里可以更随便地说话:在夜里,当塞丝和保罗·D睡着以后;或是白天,在他们俩都没到家的时候。甜蜜、荒唐的谈话里充满了半截话、白日梦和远比理解更令人激动的误解。
姑娘们离开以后,塞丝开始收拾饭桌。她把盘子堆在一盆水旁边。
“她什么地方得罪你啦?”
保罗·D皱了皱眉头,没说什么。
“我们为丹芙好好地打了一架。也得为她来上一回吗?”塞丝问道。
“我只是不明白干吗摽在一起。明摆着,她为什么抓着你不放,可是你为什么也抓着她不放,这个我就搞不懂了。”
塞丝扔下盘子,盯着他。”谁抓着谁不放关你什么事?养活她并不费事。我从餐馆捡回一点剩的就行了。她跟丹芙又是个伴儿。这个你知道,我也知道你知道,那你还牙痒痒什么?”
“我也拿不准。是我心里的一种滋味。”
“那好,你干吗不尝尝这个呢?尝尝这个滋味:有了一张床睡,人家却绞尽脑汁琢磨,你每天该干些什么来挣它。尝尝这个滋味。要是这还不够,再尝尝做一个黑女人四处流浪、听天由命的滋味。尝尝这个吧。”
“那些滋味我全清楚,塞丝。我又不是昨天才出娘胎的,我这辈子还从来没错待过一个女人呢。”
“那这世上也就独你一个。”塞丝回答道。
“不是俩?”
“不是。不是俩。”
“可黑尔又怎么你啦?黑尔总和你在一起。他从不撇下你。”
“没撇下我他撇下谁了?”
“我不知道,反正不是你。这是事实。”
“那么他更坏,他撇下了他的孩子。”
“你可不能这么说。”
“他没在那儿。他本来说他会在那儿,可他没在。”
“他在那儿。”
“那他干吗不出来?我为什么还得把我的宝贝们送走,自己留在后头找他?”
“他没法从厩楼里出来。”
“厩楼?什么厩楼?”
“你头顶上的那个。在牲口棚里。”
慢慢地,慢慢地,花了尽可能多的时间,塞丝挪向桌子。
“他看见了?”
“他看见了。”
“他告诉你的?”
“你告诉我的。”
“什么?”
“我来这儿那天。你说他们抢了你的奶水。我一直不知道是什么把他搞得一团糟。就是那个,我估计。我只知道有什么事让他崩溃了。那么多年的星期六、星期天和晚上的加班加点都没影响过他。可那天他在牲口棚里见到的什么事情,把他像根树枝一样一折两断。”
“他看见了?”塞丝抱紧两肘,好像怕它们飞走似的。
“他看见了。肯定的。”
“他看见了那些家伙对我干的事,还让他们接着喘气?他看见了?他看见了?他看见了?”
“嘿!嘿!听着。你听我说。一个男人不是一把该死的斧头,去他妈的砍掉、劈掉、剁掉日子里的每一分钟。是倒霉事找的他。他砍不倒这些事,因为它们属于内心。”
塞丝踱来踱去,在灯光里踱来踱去。”地下联络员说:最迟星期天。他们抢走了我的奶水,可他看见了却没下来?星期天到了,可他没到。星期一到了,可还是没见黑尔。我以为他是死了,才没来;然后我以为是他们抓住了他,才没来。后来我想,不对,他没死,因为他要是死了,我该知道;再后来,你过了这么多年找到这儿来,也没说他死了,因为你也不知道,所以我想,好吧,他不过是给自己找到了更好的生路。因为要是他在附近的什么地方,就算不来找我,他也肯定会来找贝比·萨格斯的。可我根本没料到他看见了。”
“事到如今,又有什么关系呢?”
“假如他活着,而且看见了,他就永远不会迈进我的门。黑尔不会。”
“他崩溃了,塞丝。”保罗·D抬眼看着她,叹了口气,”你全知道也好。我最后一次看见他的时候,他正坐在搅乳机旁。他涂了自己一脸的牛油。”
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她因此而心怀感激。一般来说,她能马上看到她耳闻的画面。可是她没看到保罗·D讲的事情。脑子里什么都没出现。小心翼翼、小心翼翼地,她跳向一个适当的问题。
“他说了什么吗?”
“没有。”
“一个字没说?”
“一个字没说。”
“你对他说话了吗?你什么也没对他说?总得有句话!”
“我不能,塞丝。我就是……不能。”
“为什么?!”
“我嘴上戴着个马嚼子。”
塞丝打开前门,坐在门廊台阶上。没有太阳的天空变为蓝色,可她依然能辨认出远处草地上黝黑的树影。她来回摇着头,听凭她那不听话的大脑摆布。它为什么来者不拒、照单全收呢?不拒绝苦难,不拒绝悔恨,不拒绝腐烂不堪的可憎的画面?像个贪婪的孩子,它什么都抢。哪怕就一次,它能不能说一声:不要了谢谢?我刚吃完,多一口也塞不下了?我塞满了他妈的两个长着青苔般牙齿的家伙,一个吮着我的乳房,另一个摁着我,他们那知书达礼的老师一边看着一边作记录。到现在我还满脑子都是那事呢,见鬼!我可不能回头再往里添了。再添上我的丈夫,他在我头顶上的厩楼里观看—藏在近旁—藏在一个他自以为没人来找他的地方,朝下俯看着我根本不能看的事情。而且不制止他们—眼睁睁地让它发生。然而我那贪婪的大脑说,噢谢谢,我太想再要些了—于是我又添了些。可我一这么做,就再也停不住了。又添上了这个:我的丈夫蹲在搅乳机旁抹牛油,抹得满脸尽是牛油疙瘩,因为他们抢走的奶水占据了他的脑子。对他来说,干脆让全世界都知道算了。当时他要是真的彻底崩溃,那他现在也肯定死了。要是保罗·D因为咬着铁嚼子,看见他却不能救他或安慰他,那么保罗·D肯定还有更多的事能告诉我,而我的大脑还会立即接受,永远不说:不要了谢谢。我可不想知道,也没必要记住那些。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做呢:比如操心,操心明天,操心丹芙,操心宠儿,操心衰老和生病,更不用说爱了。
可是她的大脑对未来不感兴趣。它满载着过去,而且渴望着更多的过去,但不给她留下一点空间,让她去想象,甚至去计划下一天。浑似那个野葱地里的午后—那时她能看见的最远的未来仅仅是一步之遥。别的人都发疯了,她为什么不能?别人的大脑都停了下来,掉转身去找新的东西,黑尔肯定就是这样。那该有多么甜蜜啊:他们两个,背靠牛奶棚,蹲在搅乳机旁,心不在焉地往脸上猛扔冰凉的、疙疙瘩瘩的牛油。感觉牛油的滑腻和黏稠—揉进头发,看着它从手指缝中挤出。就停在那里,会是怎样的解脱啊。关上。锁住。挤牛油。可她的三个孩子正在去俄亥俄的路上,躺在毯子下面嚼着糖水奶嘴,那是什么牛油游戏都无法改变的。
保罗·D迈出门槛,抚摸着她的肩膀。
“我没打算告诉你那个。”
“我没打算听。”
“我没法收回来,但我能把它搁下。”保罗·D说。
他想对我开讲了,她暗忖道。他想让我去问问他当时的感觉—舌头让铁嚼子坠住是多么难受,吐唾沫的需要又是多么强烈、不能自已。那个滋味她早就知道了,在”甜蜜之家”以前待的地方她就一次又一次地目睹过。男人,男孩,小女孩,女人。嘴唇向后勒紧那一刻注入眼里的疯狂。嚼子卸下之后的许多天里,嘴角一直涂着鹅油,可是没有什么来抚慰舌头,或者将疯狂从眼中除去。
塞丝抬头朝保罗·D的眼中望去,看那里是否留下了什么痕迹。
“我小时候见过的那些人,”她说,”他们套过嚼子后看上去总是那么疯狂。谁知道他们因为什么给他们上嚼子,反正那一套根本行不通,因为它套上的是一种从前没有过的疯狂。我看你的时候,却看不见那个。你的眼睛里哪儿都没有那样的疯狂。”
“有把它放进去的法子,就有拿出来的法子。两个办法我都知道,我还没想好哪种更糟呢。”他在她身旁坐下。塞丝打量着他。在昏暗的日光里,他瘦骨嶙峋的古铜色面孔让她的心趋于平静。
“想跟我讲讲吗?”她问他。
“我不知道。我从来没讲过。跟谁都没讲过。有时候唱唱,可我从来没跟谁讲过。”
“说吧。我听得了。”
“也许吧。也许你听得了。我只是不敢肯定我能说出来。我的意思是,能说得准确,因为并不是嚼子的问题—不是那么回事。”
“那是什么呢?”塞丝问道。
“公鸡,”他说,”路过公鸡时,我看见它们那样看着我。”
塞丝笑了。”在那棵松树上?”
“对。”保罗·D同她一起笑了,”上边肯定落了有五只公鸡,还有起码五十只母鸡。”
“”先生”也在?”
“一开始还没看到。可是我走了不到二十步就瞧见它了。它从栅栏上走下来,坐在木盆上。”
“它喜欢那个木盆。”塞丝说着,心中暗想:不好,现在停不下来了。
“可不是吗?像个宝座似的。知道么,是我把它从鸡蛋壳里提溜出来的。要不是我,它早憋死了。那一只老母鸡走开时,身后跟了一大群刚孵出的小鸡崽。就剩下这一个鸡蛋了。好像是个空壳,可后来我看见它在动弹,就把它敲开了,出来的就是”先生”,脚有点瘸,一身的毛病。我眼看着那个狗崽子长大,在院子里横行霸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