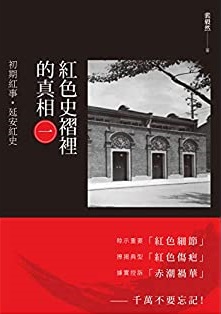《红色史褶里的真相》第二辑:延安红史(12)
 汁液仍浓的《斗争十八年》
汁液仍浓的《斗争十八年》
久关「铁屋」,2005年首访香港中大一整月,第一次与闻「红色叛徒」司马璐。稍后,得知这位逃出大陆的司马先生1952年在香港出版回忆录,与刘绍唐《红色中国的叛徒》齐名。近年,本人专力研究延安一代,很想一阅这位被延安逐出者的自述。无奈搞港版书不易,读到他的《斗争十八年》,已是2010年初冬,还是寒山碧先生赠我的复印本。
司马璐其人
司马璐(1919~ ),出生江苏泰县海安镇(今海安县)贫家,9岁丧父,13岁丧母,仅读两年私塾三年小学。一度颠沛流离,入布店、杂货店为徒,15岁入报馆为服务生。1935年,进入上海生活书店并加入共青团。因投稿《大公报》副刊获载,对文化产生兴趣。这一时期,他因参加中共地下工作被捕,但未泄露机密,1937年出狱并加入中共,「七·七」后赴延。中组部长陈云亲自谈话后,送枣园「敌区工作干部训练班」,给予的鉴定:
有组织能力和斗争经验,但具有浓厚的个人英雄主义,个性强、骄傲、缺少劳动观念,组织锻练炼不够。(页68)
这已经属于相当不错的「组织鉴定」,可送秘密工作训练班。后再入中央党校,后分配《新华日报》延安办事处主任、边区医院文书。1939年,司马璐在延安被捕审查(因在与陈果夫有关系的图书馆工作过),停止党籍,同年7月遣送离延,在延安总共生活一年半。离延后,派入国军骑兵第二军「开辟」,一度自拉武装打游击,不久被新四军彭雪枫部兼并。司马璐再回骑二军,因红色履历被军长何柱国「礼送」。1940年8月,司马璐抵渝,再次加入中共,联系人徐冰,任朝鲜义勇队总队长秘书。
1941年,司马璐秘遣浙皖;1942年初脱离中共——「召回自己的灵魂」。1944年组建「中国人民党」(最初七十余名青年,后有大批袍哥[1]加入),办《人民周报》;1948年在沪组织「和平民主同盟」,呼吁国共停战,走第三条道路。
1949年5月,上海易手后,潘汉年两次召见司马璐,在上海有名的「五层楼」宴请,问他要「人民党」名单。(页267~269)1949年圣诞节,司马璐逃港,办刊《展望》,彻底反共;1953年10月出版回忆录《斗争十八年》。2002年,83岁的司马璐与86岁的戈扬(七十年前青梅竹马)在美结婚。这对「延安青年」用暮岁婚礼向世人表示:皈依民主自由。
杯水主义
延安男女盛行「杯水主义」,青年女性因紧俏(性别比例18∶1)而昂然于群。抗大副校长罗瑞卿死缠司马璐女友夏森,强行约会,关门不让走。夏森在日记中哀叹:
罗校长啊,你为甚么一定要纠缠我呢?女人,女人,女人到那里都是一样啊!
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招待所住着一位孕妇,说不出肚子里谁是「孩子他爹」,勉强说出办事处里两名男性,人家又都不认账。(页40、100、131)
一般女同志被派出工作,除了少数以外,差不多始终只做些男同志的辅助工作,她们多半以「临时太太」的身分,由党暂时配给某一个男同志。这是革命工作呀,她们当然只得服从,她们时而被调开,时而又配给另一个男同志。在这些女同志的工作期间,「临时太太」造成多少悲剧,女同志们流了多少眼泪,出现了多少辛酸的故事啊!(页132~133)
红色恐怖
《斗争十八年》记载了传主15~33岁的经历,重点为1935年进入中共阵营后的「红色感受」。限于篇幅,本文只能撮选「最精彩」的一二事实。
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司马璐受命自渝赴皖,以屯溪为中心展开皖南浙西的地下活动,顶头上司闽浙赣三省特派员「老头子」(司马璐称「柳英」,即刘英),他向司马璐描绘中共红色恐怖:
每一个高级的负责同志都提醒我们,不仅要提高对党外的警惕性,而且要提高对党内同志的警惕性,他们随时在相互之间需要「了解」,当然也一样需要「了解」。……一个愈像忠实可靠积极的同志,愈要当心他。(页192)……没有一个同志是绝对可靠的;为了革命,任何手段都是合理的。(页198)
刘英向司马璐介绍江西清肃AB团(反布尔什维克英文首字母):
今天看着一批同志审判别人,明天又看到那些昨天审判别人的人,又在被另一批同志审判,一批批一批批绑出去杀了。我敢说这中间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冤枉的,但是我也敢保证党的政策是绝对正确的。(页193)
仅仅这样的悖论就令人毛骨耸然了。一位前几天还在灌刘英辣椒水的干部,竟也以AB团罪名被处决。「老头子」接着论证三种人必须杀:一、接受党内审查时顺竿自诬招供者,这种人意志薄弱,本质易于动摇;二、受冤屈而激怨者,此类人忠诚度不够,容易成为叛党分子;三、乱用AB团名义杀人者,这种人「当然党也是一并杀了」。由于怀疑一切,你越是忠实积极,越可能遭组织上「关心」,「杀了干净」。(页193~194)
屯溪事件
屯溪某布店是中共联络站,李老板夫妇连伙计不过四人,但开饭时总坐满一桌。不过虽然吃在一张桌上,彼此不通问也不介绍。另一联络站为王大嫂处,专门用于个别谈话。王先生据说长年在外跑单帮,其实是中共华东局派来的一对假夫妻,租好房子后,王先生就奉命调往别处,王大嫂就成了「老头子」的情妇。
一次,司马璐请王大嫂递一张条子给「老头子」,遭到一阵训斥。司马璐辩解:「王大嫂是我们自己人。」老头子歇斯底里暴跳起来:「谁是自己人?谁?谁?」(页196)
「老头子」还告诉司马璐,上海平日杀共产党最起劲的巡捕,说不定就是共产党员,因为「他们不多杀一些共产党员是没法取得上面的信任的,多死几个自己的干部有什么关系,何况这也是对党的一种贡献呢。」上海闻人虞洽卿秘书的康生,就是利用巡捕房里的眼线,避免了一场倾覆大祸。(页197)
一次,几个联络站的安全信号全撤下,原来一位自制炸药的本地同志失手,发生爆炸,被邻居当成汉奸扭送警察局。由于此人知道几处联络点,只得全体「紧急搬家」。三天后,「汉奸」出狱,听说他家里花了点钱。「老头子」判定是国民党的反间计。几天后,「汉奸」失踪。司马璐问「老头子」:「是不是我们把他干了?」最初,「老头子」推托不知道,后对司马璐讲了一套理论:
你知道吗?革命是需要残酷的,昨天的同志,可能今天就是我们的敌人。……错杀一个,没有什么了不起,一个人有什么关系,革命是多么一件大事。(页200)
但那位「自制炸药」同志的家属却向地方当局要人,警察局当然不知下落,家属却盯着:「先前被你们关过,现在继之以失踪,还不是你们干的吗?」此时,「老头子」布置屯溪中共地下党员发动地方绅士出面,控诉国府残杀青年,油印传单写得十分凄惋,声称这次事件是「国民党的又一滔天罪行」。而国民党也把所有宪警训斥一顿。
最可怕的是:
依照我们党的纪律,像老头子这样的负责干部,被捕后即使不死在国民党手里,释放后组织上也会立刻派人去把他干掉的。(页213)
如此进步
「屯溪事件」后不久,「老头子」再次开导年轻人:
当发现一个同志不可靠的时候,最好是能够通过敌人的手把他干掉。因为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既可以为我们组织上除去隐忧,又可以增加我们的政治宣传资料。否则的话,只好我们自己动手了,不过,那总是不得已的。……你为什么近来老是不说话了?!
我以为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只应该知道执行组织上的命令和你的指示,多说话是没有用的。
那对极了,所以我很信任你,你确是党性强,一天天有进步。
这位「一天天有进步」的青年党员,最后竟写下这样的「叛党言论」:
共产党人所关心的不是抗战的胜利,而是如何加重这些腐蚀的因素,加速这个社会秩序的破坏,动摇抗战的基础,打击政府的威信,以便于他们准备革命条件。(页169)
在敌人的伪组织机构中,大量地充斥着我们的同志,他们藉日本人的刀,去屠杀国民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人员,甚至我们党的组织也经常与日本人的特务机关交换情报。据我直接知道,上海两次破获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和一次江南日本人对忠义救国军的围剿,都是我们党在日本人合作之下的杰作。……做汉奸也是革命,听说好多大汉奸都是我们党的同志,比如像袁殊(当时的伪中央宣传部长)……(页210~211)
司马璐还在回忆录中「揭发」了老头子等中共高干在杭州嫖妓。(页209)
技术问题
游击队员瞿飞几年躲在山里,实在太苦,此时调来做白区工作,负责管钱的财务,「真是到了天堂哪!」几杯老酒下肚,他向司马璐透露游击队如何解决经费问题:
其实,只要发得下狠心,找钱也不难。打土豪是个办法,可是现在不行了,不过你要是指他是个通敌的汉奸,他就没有话说了,反正是不必经过公审的。或者还可以把游击区以外的有钱的绅士拖进来。……武装走私也是个办法,伏击敌人的运输车辆也是个办法,不过那总是太危险了。最有效的办法是直接向老百姓抢……
那不是使老百姓要对我们发生反感吗?
你真是又太书生之见了,这完全是技术问题。比如说,我们先派一部分同志化装土匪去抢了,等到老百姓报告到我们队里来,我们就立刻派一支部队追上去。这时,我们那些奉命抢掠的同志,已经满载而归,从另一条路归队了。这样,老百姓不但不会对我们有反感,我们地方党的组织,还要发动老百姓对我们慰劳呢!(页202~203)
这位游击队员还向司马璐透露了另一「万万说不得」的筹款途径——印制假钞,「你不见我们党里拿出来的都是一叠叠的新钞票吗?还不是这么哗啦哗啦发出的?!」(页204)
最后觉悟
早在延安,司马璐听了刘少奇的课就认识到:
做一个共产党员,最好根本不要有「思想」,或者一直不用「思想」。否则,不是带来许多烦恼,就会发生「思想问题」。
果然,司马璐这段话遭到揭发,挨了总支书猛批。
我的确已经是一个乖巧的共产党员,绝不提出疑问,小组会的时候,听着上级所讲的再发挥一番。我竭力克制自己的理智。明天党是另一个讲法,我亦复如是。我认为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是应该如此的。……我们的党性坚强的程度,就全看我们牺牲「自我的意志」,当一个把「人的尊严」磨得差不多了,就成为一个标准的共产党员了。(页82~86)
司马璐通过事实认识到:
甚至我们自己的同志间,也互相吃掉对方的部队。党的中央没有什么是非可说,他永远是相信力量就是代表真理,有更多的枪杆子的一方面总是对的。(页220)
1950年底,司马璐逃港,揭露中共竟与日寇有勾结,共同破坏沦陷区三青团组织与围剿忠义救国军。(页211)游击队与地方党组织有矛盾,游击队便将与地委关系密切者秘密处决或作战时开枪打死。「人民内部矛盾」就如此解决了。(页206)此外,辣椒水之类江西苏区就灌过自己人了,老虎凳延安也有人坐了,假犯人混狱骗供之招也用上了。江西苏区整肃AB团乱了枪法,灌他人辣椒水的行刑者,没几天也因「AB团」被处决。[2]
红色叛徒最后认识到:
这许多年来。我的一颗纯洁的心一天天受到损伤,我贡献了我的青春给这个理想——我过去把他看得如何的崇高和伟大。如今,他的光芒在我面前已经全部变得漆黑,这个追求,今天已经彻底的幻灭了!(页221)
他对中共的最后认识:
这个党是一个完全以命令支配党员行动的党,军事化的党,特务化的党。每个党员,毫无保留地毫无还价地服从党的纪律。党的基本政策就是「杀人越货」四个大字。(页225)
一些信息
抗战胜利前后,一个小共干都敢当面训斥章伯钧。一次,王炳南教训章伯钧:
你们民主同盟,国民党凭什么要买你们的账?还不是因为我们有五十万大军和一个强大的共产党?!
从当年小共干训斥到后来的老子党,脉络清晰呵!中共创始人之一的张申府之所以与中共搞不好关系,就是不买一些小土共的账。(页241)
司马璐延安枣园「敌工培训班」同学陈健民,昆明国府后勤机关工作人员,中共地下党员。一天,党命令他逮捕某人并立即处决,事后再向政府公布此人为图谋不轨的共党分子。当陈健民遵命将此人逮捕,一看,原来也是枣园同学——会唱山歌的矮个子李毓兹。经过交谈,原来昆明中共组织经费十分困难,李毓兹奉命抢劫昆明大商号源昌公司。事后才知道这家公司有龙三公子股份,龙云追缉甚力,限期破案。昆明中共地下组织这下慌了神,因为中共在西南的活动全靠龙云掩护,现在抢了人家公子的公司,一旦破获,如何得了?至此,陈健民才明白组织命令他捕杀李毓兹,竟是为了灭口!他把自己「任务」告诉老同学,两人相拥而泣。最后,陈健民送了一点路费给李毓兹,嘱他走得越远越好。陈健民自己提一只小箱,悄悄逃至重庆。(页246~247)
中共接手政权前夕,利用升官发财,勾引过某些民主党派。这些民主党派也确实有人在打共军进城后洋房汽车的脑筋。(页261)民主社会党魁张君劢身后的高方中,上海易手暴露出中共社会部小头目身分。中统上海办事处行动大队长王大超,曾镇压民主运动,原来是中共地下党员,这会儿主持审讯「反革命」案件。(页263)此外,当年信息屏蔽,形成诸多隔膜。如司马璐以为萧军已被整死。(页254)包括香港还有不少人惑于中共「宽大」钓鱼政策,做着「靠近」梦。(页278)
对大陆读者来说,这本写于半个多世纪前的回忆录,汁液仍浓,仍可读出许多惊叹连连的内容。值得引述的历史反思是:「我们全靠飞机大炮去阻止共产党,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的精神阵线却早就崩溃了。」(页258)包括《大刚报》总社长毛健吾都认为中共「也是一种理想」,不听司马璐劝阻,执意北上回大陆。(页279)国共之争,中共胜在思想,这是国民党与自由知识分子1949年后才绞拧出的「历史经验」。司马先生也因意识到思想武装的重要性,决心后半生从事自由文化工作。(页281)
司马先生对中共的某些判认经得起时间检验:「共产党人一向总是以自己的行为标准去理解别人。」(页275)「任何一种幌子,任何一种理想,任何一套好听的名词,如果受到独裁者个人的意志所支配,那一定就要走样了。」(页280)文革后中共步履蹒跚的改革,雄辩证明红色逻辑「此路不通」,只能羞羞答答卷起当年的革命理论,恢复资本主义旧制,但还撑着架子,政治上仍不肯认输,名之「改革」。然而革命人民这回明白了,谁都会在心里问上一声:
既然重走资本主义道路,那么,马列主义的意义呢?赤色革命的价值呢?
2010-12-17~19于沪
[1] 袍哥:晚清民国川渝地区民间帮会,其他地区称哥老会,与青帮、洪门为三大帮会组织。辛亥后,川渝成年男子大多加入或间接受「袍哥」控制,今天仍有诸多留痕。
[2] 司马璐:〈斗争十八年〉,亚洲出版社(香港)1952年,页119~120、192~194。
原载:《开放》(香港)2011年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