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转胜章
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十三团阀门厂被定为营级编制,原先的一连改编为以铸造为主的一连和以加工装配为主的五连。一连的领导班子也进行了调整,指导员赵兴福被调去参加地方军管,申胜章调来担任副指导员。为了安慰从部队刷到兵团的现役干部,一般都要给他们提一级,这位副指导员在部队大概是文书一类的排级干部。
第一次见到申胜章是在全连大会上,他中等身材,面容消瘦,虽竭力摆出英武之态,仍难掩几分猥琐。此人不苟言笑,也很低调,经常感慨“连伯达同志都说自己是个小小老百姓,那我们咧,算什么?就是草民”。他给我的最初印象就是一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样子,非常普通甚至平庸的一个人。记得在一次董连长主持的生产调度会上,申胜章不但一言不发,还摆出一副昏昏欲睡的样子。会议最后安排连首长分工,当时生产分为白班和夜班,董连长希望申胜章能够分担一部分,他却似醒非醒地说了句“我负责思想政治工作”,引起董连长极大的不满。
没过多久,申胜章由副指导员提升为指导员,像是从惊蛰中复苏,整个人立刻变了模样,工作中一反常态,异常积极认真,说话也不再轻声轻语,变得干净利落,毫不拖泥带水。
我们连的工作环境是比较恶劣的,为了便于搬运,铸造车间的门窗都被拆除,冬季北风肆虐,苦不堪言。一天恰逢申胜章来车间巡视,一位兵团战士说了一句“指导员,冷啊”,指导员却回了一句更冷的话:“冷?使劲干活就不冷了。”真是令人拍案叫绝。
 指导员,冷啊… …
指导员,冷啊… …
冷?使劲干活就不冷了。
除了浇注时高温的灼烤,粉尘也非常多,尤其是混砂、退火等工种,即使戴防毒面具也无济于事。记得有一次混砂班竟然把农药误当作膨润土使用,当铁水浇入砂型时,刺鼻的浓烟升腾而起,大家掩着鼻子开玩笑说,这下把肚子里的蛔虫都熏死了。
混砂班的班长路彪对工作环境的恶劣曾提出意见,在全连大会上遭到申指导员的痛斥,上纲上线到对抗毛主席“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教导。
在日常生活中,申指导员也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时刻抵御着无所不在的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他最擅长的本领就是从空气中嗅出阶级斗争的味道。
有这么一根神棍整天在头顶晃来晃去,我只能小心谨慎地蜷缩在说不尽的注意事项里,更何况我明显地感觉到他的目光中含有一种强烈的敌意。我听说不久前他对我的评价是“思想复杂”,后来很快演变为“路线斗争觉悟低”,照此发展,迟早还会继续升级。
紧躲慢躲还是没躲过去。那天,我正在宿舍里下围棋,申指导员走了进来,他冷眼旁观一言不发。为了打破尴尬,一位兵团战士小心地赔着笑脸说:“指导员,您也来一盘?”申胜章却像是受到了莫大的侮辱,先从鼻孔里发出令人不寒而栗的哼声,又狠狠地甩下一句“扣子棋,我从来不搞这套东西!”说完后头也不回,夺门而去。留下满屋人面面相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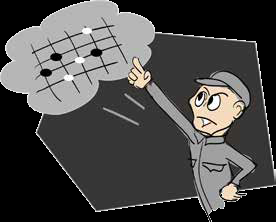
在全连大会上,申指导员就“扣子棋”事件大发雷霆,在他眼里,下围棋竟然是在对抗毛主席和林副主席。
本来大家在工作之余打扑克下象棋甚至搓麻将都是很常见的事,申指导员平时也熟视无睹,“扣子棋”的封资修指数也不比那几样高,为什么偏偏令他如此深恶痛绝,这个疑问我一直搞不明白。毛主席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但是在指导员身上我却清清楚楚地看到了无缘无故的恨。
申指导员用颤抖的声音愤怒地质问:“林副主席指示我们要用百分之九十九的时间读毛主席的书,难道林副主席也错咧?!”
指导员甩出一连串的惊叹号,我在下面一声也不敢吭,心中无数匹草泥马奔腾而过。其实林副主席的原话是“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中,我们要百分之九十九地学习毛主席著作。”根本没有要求大家把百分之九十九的时间都用来读毛主席的书,否则还有时间工作和休息吗?
1971 年4 月,我偷听敌台的问题再次被抖落出来。

建国初期偷听敌台并不是什么十恶不赦的行为,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有几位解放军飞行员收听了台湾的广播后陆续驾机叛逃,引起高层震怒。林彪有过一个关于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的讲话,其中有坚决禁止收听敌方广播的内容,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也曾发布过禁止看黄书和听敌台的通知。尽管法律条文中并没有把偷听敌台列为罪行,但谁会把法律当回事呢?“文革”中偷听敌台足以构成非常严重的罪行,许多人甚至因此被拉去打靶。而我的那场风波恰好发生在“一打三反”运动中,任何问题一旦沾上运动的包,性质立刻严重许多,运动就像拱猪中的草花10,一旦染红,立刻加两倍甚至四倍计算。
“一打三反”的内容是打击反革命,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浪费,说是“一打三反”,其实最主要的还是“一打”。这场运动已经开展了将近一年,大家都以为要平淡收场了,我的问题却被揭发出来,按申指导员的说法,“运动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董连长事先知道我遇到了大麻烦,却也爱莫能助,但是他仍然向我作出暗示,使我有了一些思想准备。
申指导员精神亢奋,表示不获全胜决不收兵。连里成立了领导小组,并举办了“一打三反”重点学习班,成员除了我之外,还有陈斌儒、马文然和周明善。其中老陈只是挂了个名,马文然也只是被谈话一次,周明善受到不小压力,我则是重中之重,被责令老老实实交代问题。问题的关键是偷听敌台这个罪名实在太大,我承受不起,既然被逼得毫无退路,只能负隅顽抗。
我的确没有老实交代自己的问题,至今毫无愧意。申指导员的判断没有错,我确实偷听过敌台,而且不止一次,但是我接受了以前的教训,每次都非常谨慎,指导员绝对不可能找到任何直接的证据。这就是我顽抗甚至反击的本钱。也就是说,指导员猜中了问题的要害,但要想完成致命一击,却无法抓住把柄,只能靠诬陷。
我首先要了解对手究竟掌握了多少材料,一切行为都要围绕这个目标。
学习班的第一天,一排的排长郑宝善找我谈话,他是领导小组成员之一。别看他名字中有一个善,实际上绝非善茬。他满脸狠色,双目炯炯,死死盯着眼前的猎物,没有任何寒暄铺垫,起手就是先声夺人的当头炮,大声对我说:“你的思想根源由来已久,要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一件一件老实交代,休想蒙混过关,也别跟我来那套里格儿楞。”我心里立刻一沉,知道麻烦大了,他们肯定已经知道了我在学校期间发生的事情。郑排长接着又弹了一番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之类的陈词滥调,他是复员老兵,以严厉著称,动辄大喊大叫,却不是口蜜腹剑的奸诈之徒。我希望尽快和幕后的主帅对垒,不愿和他这个先锋多作纠缠,索性以硬碰硬,回答说:“排长你不要虚张声势,有什么问题摆到桌面来。”郑排长勃然大怒,眼珠子瞪得溜儿圆,我亦毫不退让,双方都喊出了最高分贝,第一次谈话就这样谈崩了。随后郑排长向申指导员辞掉了这个苦差事,一去不返。后来听别人说郑排长其实对我并没有敌意,交手之后,竟然产生惺惺相惜之感。
郑排长硬攻无效,申指导员只好亲自上阵。我经历过几次挨整后,已非吴下阿蒙,既然如愿逼出对方boss,索性放手与之正面对决。申指导员像一只猎犬伺机撕咬,而我像一只兔子以命相搏,兔子垂死挣扎的求生欲望自然远远高过猎犬对美味的垂涎欲滴。比意志,我不会落下风。
 下面这些是我对你的看法,你认为呢?
下面这些是我对你的看法,你认为呢?
1. 对政治学习抓得不够紧
2. 团结同志不广泛
3 . 为人不直爽。
与郑排长相比,申指导员的花样要多一些,他并不是一味斗狠,而是先营造出一个比较轻松的环境。他表示想和我谈谈心,交换一下意见。他对我提了三条意见,第一条是对政治学习抓得不够紧,我心中暗自好笑,除了毛主席,谁敢拍着胸脯说自己对政治学习抓得足够紧呢?对这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我也不忍推辞,痛快地承认了。
第二条意见是团结同志不广泛,我觉得这条意见看似和缓,却暗藏机关,隐含着我搞小集团的意思。申指导员一反常态的和蔼早已令我更加警惕,我估计他采用的是先易后难,稳扎稳打,逐步紧逼突破的战术,我希望打乱他的节奏,便略带讥讽地回答说我的确团结同志不够广泛,尤其是未能和领导搞好团结,所以才有今天的局面。申指导员大概认为我会吞下这枚钉子,没想到我竟然作出反击,他沉默了一两分钟,提出了对我的第三条意见:为人不直爽。这其实是针对我不肯老实交代问题的一种委婉说法。
这条意见的杀伤力已经比较明显了,我当即要指导员举出实例,他自然是张口结舌,我叹了一口气,说我就是因为直爽过了头才被人抓住把柄,居然还被认为不直爽。其实我是很感谢他提的这个意见,使我趁机很直爽地发泄了一通不满。
申指导员很是恼火,口气也严厉起来,他要我交代问题,我一口回绝。我的立场是只回答问题,绝不交代问题,万一交代了对方仍未掌握的东西,岂不是给人家提供攻击自己的炮弹?几个回合下来,指导员终于失去了耐心,亮出底牌,将四位兵团战士写的揭发材料逐条念来。

事情的发展总算进入了我预设的轨道,我稍稍松了口气。
告密是很卑劣的,为人们所不齿,但是当年的政治伦理却大力提倡这种行为,理由是组织上永远是正确的,如果朋友的言行是错误的,知情人应该把这些情况向组织汇报。按照这种价值观和行为逻辑,毫不留情地揭发才是对朋友真正的帮助和爱护。揭发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主动揭发别人,另一种是在组织的压力下被迫提供一些材料。显然前者的觉悟和智商高于后者,后者受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毒害,囿于哥们义气,不知道检举揭发是对朋友的教育、监督、挽救。到现在我仍对揭发我的一些朋友们表示理解甚至真诚的感谢,他们向组织实事求是地说明情况无可非议,只要不胡乱编造,就不会带来太大的麻烦。从一些揭发材料中,可以看出他们也尽了很大的努力设法减轻对我的伤害。
不出所料,揭发材料中绝大部分都是含糊其辞的猜测,所谓的证据翻来覆去就是那么几条,根本没有什么像样的东西。如×××说我曾在夜里戴着耳机听收音机;×××说有一天满屋的人都在听敌台,其中可能有我;×××说有的人曾经用我的半导体收音机听敌台。这类问题都不难解释。夜里戴耳机听广播是为了避免打扰大家休息;既然满屋的人都在听敌台,请从中多找几位来证明其中有我,这应该很容易吧;我的一些物品如收音机照相机等经常被别人拿去使用,我并不知道去向,有时好几个月后才送回来,我最后见到自己的收音机竟然是在垃圾堆里,原来是马文然为了组装电视机把它的零件拆了。别人用我的收音机听了什么,我又应该负多少责任呢?
还有×××说我和陈斌儒某个下午在宿舍里听敌台,我的半导体收音机的拉杆天线早已经坏了,白天根本是收不到敌台的,这种揭发就是在帮我解围,我甚至怀疑是不是揭发人在玩无间道。还有一些揭发我唱黄色歌曲之类的无稽之谈更是于我毫发未损,并成为我反击的弹药。

其实我并不十分担心所谓偷听敌台的问题,我坚信做得滴水不漏,我担忧的是自己平时的一些言论很容易授人以柄。例如我曾经对当时的一首歌曲“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表示不屑,而这首歌的歌词正是源于毛主席的讲话。我还说过冬天的太阳和夏天的太阳给人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这句话其实是从林汉达先生的书里看到的。这类东西如果上纲上线,杀伤力也是非同小可。对于类似的指控,我一概推说不记得,既不承认,也不否认,为将来留有余地,这是一年前被赵兴福指导员算计后得到的宝贵经验,此时派上了用场。
申指导员认为抓到了我的破绽,穷追不舍地问:“你的记性特别好,这是出了名的,怎么会不记得呢?”我回答说:“是啊,我的记忆力很好,为什么会毫无印象,我也觉得有些奇怪,应该是根本没有这回事吧,要不然让揭发我的同志来帮助我回忆一下?”
指导员心里很清楚,揭发人背后写材料虽然可以很积极,但没有几个有当面对质的勇气,这个难题他始终无法解决。我抓住这处软肋,再三提出当面对质的要求。我早有打算,如果有什么人胆敢来胡说八道,我一定要把他也搅进来,不惜倒打一耙,演一出杨子荣舌战小炉匠。
几天后,申指导员忽然换了一副面孔,满脸洋溢着政工干部的诚恳,对我说“你的成绩是主要的,大家有目共睹,你现在的问题仅仅是别人在偷听敌台的时候,你没有能够及时制止,这不是什么大问题,不要有顾虑。你如果再坚持不肯承认,组织上就只好把材料交给群众,让群众下结论,群众说什么,就给你定什么,那样事情就大咧,你愿意把事情弄大吗?”他耐心地教导我一定要相信组织,要对组织忠诚老实,要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当老实人。虽然指导员破天荒地对我使用了肯定句,但为时已晚,无法打动我,我也随机应变,装出一副受了委屈的样子回答说,我是非常相信组织的,现在的问题是组织不相信我。

这件事折腾了很久,后来双方都筋疲力尽,申指导员也拿不出更多的东西,总是唠唠叨叨地老调重弹,对这点破事我已经解释了许多遍,索性一言不发,不再回答。指导员说:“组织上苦口婆心咧,跟你说了那么多话,好像没什么用咧,不知道你听进去没有,也不知道你在想啥咧。”这个事我可不能告诉他,如果他知道我在想啥咧,会气得七窍生烟。因为他的那一套谆谆教导我实在听不进去,他说出的每一句话在我耳朵里都变成了一个词“放屁。”在他滔滔不绝的时候,我却在心里背围棋定式,如果赶上心情不好,就把他全家轮流问候个遍。
有一天,我看到申指导员严肃认真的样子,忽然忍不住笑了起来。指导员拍案而起,狠狠地盯着我,目光射出彻骨的寒意,他厉声说道:“你嚣张不了几天咧!”每个字都掷地有声,激荡着一股扑面而来的狠劲。
他接着宣布:“其他同志偷听敌台就是你指使的,你是敌我矛盾,你是抗拒从严,不承认也没有用,只要有两个人证明就能定案,这是党的政策。”
令我震惊的是我的罪状中还有工作中弄虚作假,拉拢后进同志,搞阶级报复等十分荒诞的条款。
瞬间我的身体一阵发软,内心忽然涌现出深深的恐惧。本来我以为指导员的底牌已经出尽,凭借这点材料根本搞不出多少名堂,那些道听途说的罪证也无法落实。谁知道他根本不在意什么材料和证据,而是直接端起屎盆子迎面泼来。
我们连的司号员王维新是包头知青,外号王老肥。有一次指导员和手下的亲信在连部商量如何整所谓“连长的人”,恰巧被老肥听到,感到非常震惊,他认为指导员只知道争权夺利,没有一点共产党员的味道。老肥平时与我并无来往,却特意来告诉我。因此我对指导员已不抱任何幻想。
申指导员把自己的道德底线拉到大腿根以下,非要置我于死地。事已至此,已经没有任何道理可讲,羊无论如何辩解没有弄脏河水,狼是不会听的。回旋余地已经被这次谈话压缩到了零点。
申指导员软硬兼施,我软硬不吃,这并不是我足够坚强,而是我别无选择。如果把揭发出的问题上纲上线,按当时的标准,随便列出几条就死有余辜了,我总不能洗干净脖子请人来砍。在一些问题上我确实没有说实话,也不为此内疚,说实话也要先掂一掂脑袋的分量,也要分场合。地下党员被捕后说实话就是叛徒,我拼命给自己找出各种理由。
事后证明,我当时的做法是明智的,如果我顶不住,材料会当作成绩上报,处理也会很重,无异于自掘坟墓。我硬着头皮顶住,申指导员如果将没有做实的材料上报,不但无功,还可能受到无能的申斥。指导员从我这里无法直接突破,就把时间和精力用来搜集我在学生时期的材料,从而错过了最佳时机。
过了一段时间,学习班实在办不下去了,我的问题也暂时没有结论,于是向我宣布,因革命工作需要,调我去三排九班。实际上是撤了我的质量检查员的职。我觉得自己原来就是干翻砂的铸工,现在干回老本行也无所谓,如果这就是对我的最终处理,这个结果已经令我喜出望外,但我强烈地感觉到这只是第一步,实际上我已经有了更坏的思想准备。
申指导员不明白我为何敢于与他对抗,以为我依仗父亲撑腰,他高屋建瓴,以一种不容分说的气势当头棒喝:你父亲的情况我们已经了解了,他单位里的两派群众在许多问题上观点不一致,但一致认为你父亲是走资派,你父亲很早就是国民党空军的反动军官,虽然三八年去了延安,但不算参加革命。甚至还给我父亲戴上了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帽子。
连我父亲的问题也调查了,看来申指导员绝不肯善罢甘休,我的心情十分沉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事已至此,也只好等待申指导员痛下杀手。

从那时起,我一直在等待某个夜里一群人一脚踢开屋门猛扑进来,一边晃动着手铐一边厉声呼喊着我的名字。我从床上慢慢地挺身起来,不卑不亢地伸出双手,还要给惊恐的同屋战友们一个许云峰或江姐式的微笑。这个场景已经在我的脑海里预演了无数次,连先迈哪只脚都设计好了。
夏天的一个上午,有人通知我去连部。到了连部,看见我的父亲正在说着什么,申指导员在一旁毕恭毕敬地连连点头。父亲见到我后很生气,要我认真学习,改正错误,不要有抵触情绪,还强调说领导是帮助你,绝不会整你。申指导员的脸痉挛般地抽动着,挤出一堆尴尬的笑容,忙不迭地说:“是的,是的,我们不是故意整你,你能有多大油水?”
大概是申指导员搞的外调惊动了父亲,他得到消息后赶了过来。在送父亲下山的路上,我介绍了事情的来龙去脉,父亲沉思片刻,警告我说:“如果事情是这样,这个指导员是一个品质非常坏的人,你一定要多加注意。”
经过父亲的一番旁敲侧击,事情似乎有了一点转机,但我仍不敢乐观。有人曾悄悄告诉我,申指导员仍在暗中了解我父亲的情况,父亲当时仍未安排工作,而是到包钢参加劳动,但是已恢复组织生活,这些情况令申指导员摸不着头脑,有些犹豫。
等了许久的第二只靴子最终未能落下。当年9 月,林副统帅折戟沉沙,以自己和妻、子的性命,向红太阳作绝地反击,头颅掷处,好一似汤浇蚁穴,火燎蜂房。
九一三之后,“文革”的局面逆转,大河上下,顿失滔滔。申指导员嘴里平时总是把林副主席像口香糖一样嚼个不停,此时就像泄了气的皮球,再也没有了往日的精神。看到指导员脸上挂满了梦想破灭后的无奈与惆怅,我终于确信,这一劫,过了。

1974 年,我有一段时间住在连部办公室,夜深人静时,曾几次暗中打开文件柜,我想全中国也没几个人看过自己的档案吧。我屏住呼吸,打开厚厚的口袋,里面装满了“一打三反”时收集的各种揭发材料。看来当时申指导员真是下了血本。负责外调的是一位女生排的排长,她和她的手下曾到我的母校呼和浩特二中外调,成果颇为丰硕。看到揭发材料中熟悉的姓名和胡乱编造的罪名,我不禁哑然失笑,甚至有几分得意。仅仅过了三年,我的那些言论已经有很大部分被历史无情地证实,再也没有资格充当恶毒攻击的罪证了,剩下的部分也将继续减少杀伤力,越来越拿不出手了。我的那些所谓的罪名已经成为历史笑柄。多年后有写过揭发材料的同学向我表示歉意,其实当年我并没有对朋友们产生丝毫怨恨,这些往事已经成为饭桌旁的笑料,当年的反动观点都成了先见之明,也成为今日吹嘘的资本。
1979 年初我返回北京,临行前厂部的杭乃树将我的档案袋递给我,叮嘱一番后笑着说,“阀门厂的档案数你的厚。”我用手指弹了弹沉甸甸的口袋,笑着回答:“我的光荣历史全在这里了,不会弄丢的。”
几年后我入党时,支部书记沈富海负责外调,我请老沈谈谈看了我的档案之后的读后感,老沈奇怪地看着我说:“你的档案非常干净,除了两张表格,什么都没有,找不着什么感觉啊。”当年辛辛苦苦搞来的材料已经了无踪迹,我竟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
来源:微信公号:老鼠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