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鼠攀头
在兵团的日日夜夜,伴随我们的还有动物。
听到有人批评我们是喝狼奶长大的一代,心里很不是滋味,但是当年我们有时确实是极其残忍的。记得刚到兵团那年冬天,有人抓到了一只麻雀,大家准备把它浇上汽油点燃后放飞。章新建自告奋勇,他的哥哥是一位老大学生,当时正好来兵团探望新建。他一把拉住弟弟说:“新建,难道你真的要当凶手吗?”他说得几乎声泪俱下,我们却哄堂大笑,心里想这样的书呆子不来一番脱胎换骨的改造怎么得了。



等到自己年龄大了,特别是家里收养了几只流浪猫之后,对动物的情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小时候听到贫下中农因偷杀地主的狗吃,结果被地主逼得为狗披麻戴孝,真是恨死了地主,现在却觉得这个贫下中农也够可恶的。
不过我们在兵团似乎没有遇到什么可爱的动物。
很早就听过张果老倒骑驴的故事,一直以为毛驴是很温顺的动物,黔驴之技无非是叫几声而已,谁知满不是那么回事。我们连有一头用来运输铸件的毛驴,脾气倔而且十分奸诈。北京知青于振奎外号“窝头”,伺候毛驴的差事不幸地落在这个老实人头上。窝头一天到晚满头大汗地跑来跑去,逢人就问:“看见我的驴了吗?”
当地有一句俗话“毛驴是个鬼,不是胳膊就是腿”,如果有人骑它,它会连撂带挤,千方百计把人掀翻在地,使人吃尽苦头。有时大家举行骑驴比赛,成绩最好的也只能坚持几十秒,只有武存恩例外。
武存恩是来自内蒙古萨拉齐的知青,外号“沙鸡”,一头酷似马拉多纳的自来卷标注了某种独特的血统,格外引人注目。刚到兵团时,苑再励略施小计,沙鸡呆头呆脑地把一副没有钥匙的狗牙铐戴在自己手上,结果越挣扎越紧,表演了一场号啕大哭。
沙鸡平时总是咋咋呼呼,吆五喝六,一副大大咧咧的样子,其实十分精明。他的双腿力量极大,和人过招时,用腿夹住对手是其必杀绝技。他骑在驴背上,毛驴很难挣脱,他一发力,会把驴夹得拉稀。

与不肯配合的驴相反,马是非常任劳任怨的,怎么骑甚至站在马背上它都不闹情绪,总是一副逆来顺受的样子。六连的几匹马吸引了许多男知青,有一次叶鲁玺等几位知青偷偷地骑着马去昆区看电影,半夜里在回来的途中被团首长当场擒获,好像还被关了禁闭。我没有骑过马,只是在马文然的忽悠下骑过一次没有戴嚼子的骡子,骡子比毛驴还坏,我根本无法控制这个畜生,最终的下场是后脑勺重重地磕在马路上,立马晕菜,诊断结果为轻度脑震荡。
自己饲养的动物尚且如此,那些不速之客就更不友善了。
阀门厂大院的南门外有一片树林,我们去昆都仑召火车站时经常路过此处。这里常年栖息着许多乌鸦,飞起来遮天蔽日。它们有时会突然同时排泄粪便,像下雨一样,令人猝不及防,无处逃避。乌鸦的粪便中不知含有什么成分,沾到衣服上会留下难以清除的痕迹。
 乌鸦还可以原谅,毕竟也有可能是我们侵犯了它们的领地。苍蝇就不同了,有一句电影台词“你像苍蝇一样令人无法容忍”,到底是哪部电影已经忘记了,这句话却记得很牢,而且深有体会。
乌鸦还可以原谅,毕竟也有可能是我们侵犯了它们的领地。苍蝇就不同了,有一句电影台词“你像苍蝇一样令人无法容忍”,到底是哪部电影已经忘记了,这句话却记得很牢,而且深有体会。
 苍蝇的数量非常多,而且具有挑衅性,尤其是成群的苍蝇爬在脸上让你无法入睡,婶可忍,叔不可忍!我们每天睡觉前,都要打开门窗,拼命挥舞着毛巾,企图把苍蝇赶走,这套动作被戏称为“红绸舞”。即使是白天,苍蝇也围着人的脑袋转。叶鲁玺打牌时比较认真,最烦被打搅,每当被苍蝇激怒,就把敌敌畏倒在报纸上点燃,然后关闭门窗到室外等候。在弥漫的毒烟中,苍蝇拼命向外冲,撞得门窗的玻璃乒乒作响,过十几分钟后进屋能扫出半簸箕死苍蝇。
苍蝇的数量非常多,而且具有挑衅性,尤其是成群的苍蝇爬在脸上让你无法入睡,婶可忍,叔不可忍!我们每天睡觉前,都要打开门窗,拼命挥舞着毛巾,企图把苍蝇赶走,这套动作被戏称为“红绸舞”。即使是白天,苍蝇也围着人的脑袋转。叶鲁玺打牌时比较认真,最烦被打搅,每当被苍蝇激怒,就把敌敌畏倒在报纸上点燃,然后关闭门窗到室外等候。在弥漫的毒烟中,苍蝇拼命向外冲,撞得门窗的玻璃乒乒作响,过十几分钟后进屋能扫出半簸箕死苍蝇。
和苍蝇的无理取闹相比,有些家伙的目的倒是很明确:吸你的血。刚到兵团后,虱子悄然而至,有许多知青平生第一次见到这种东西,不知所措,也有的知青见多识广,记得一位包头知青一边用牙咬沾满虱子的衣领,一边恶狠狠地说:“你咬我,我也咬你!”
咬人的还有臭虫。1958 年2 月12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提出要在10 年或更短一些的时间内,完成消灭苍蝇、蚊子、老鼠、麻雀的任务。1958 年消灭了20 多亿只麻雀,两年后麻雀被伟大领袖亲自平反,顶替麻雀四害位置的就是臭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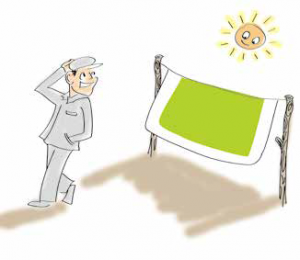
起初我们的宿舍里几乎没有臭虫,记忆中只有马文然遇到过几只。有一段时间他擅自搬到其他地方住,结果挨了咬。班长要求他搬回来,他回答说“苛政猛于臭虫也”,表示拒绝。后来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来了许多。臭虫十分贪婪,人被咬后奇痒难耐。它们以几何速度繁殖生长,夜里一开灯,只见密密麻麻到处都是,满墙为之变色,臭虫争先逃避的刷刷声清晰可闻,随便一接就可以装满半个信封。有的知青把床移到屋子中央,四面不靠墙,以为可以躲避,但是臭虫很聪明,它们会爬到屋顶再空降而下。
有一个包头知青体型干瘦,外号叫马干(记忆中似乎叫马建杰),这样的身体条件还要供应臭虫,自然格外不能容忍。他向卫生室要敌敌畏灭虫却遭到拒绝,理由是五好战士评比期间必须防止有个别想不开的知青喝敌敌畏自杀,除非有领导的特别批准。马干只好向指导员田振国申请。田指导员以同样的理由一口回绝。马干一怒之下将满满一信封臭虫悄悄撒在指导员的床垫子上。第二天,田指导员的被褥就晾在了室外,马干躲在一旁暗自拍手称快。
指导员被咬,问题的性质就变了。厂里终于下了决心,对宿舍进行了整修。原来屋顶只有一层荆笆,这次加装了吊顶,并且用药粉和水泥、白灰拌在一起,将墙壁彻底修补粉刷。臭虫以为人人平等,结果冒犯了领导,遭到灭顶之灾。
狗也犯过同样的错误。兵团战士养的狗都很奇怪,只要一见到复员老兵,平时再老实再窝囊的狗也会狂吠不止,甚至扑上前撕咬,似乎有不共戴天之仇。有一次一只狗误咬了团里一个什么人的裤腿,结果所有的狗都被勒令处死。
 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老鼠。我们遇见的老鼠可能是田鼠的变种,连尾巴算上有一尺长,和我童年时在昆明常见的老鼠大小相当。云南的老鼠每年咬伤甚至咬死的婴儿数以千百计,这里的老鼠虽不至如此凶残,但也胆大妄为。有一次团篮球队打比赛,观众围得水泄不通,篮球场上居然冒出一只老鼠向大家示威。更令人恼火的是,夜里睡觉时,经常有老鼠在头上脸上跳来跳去。于是大家创造出“上头”这个词,和猖獗之极是同一个意思,但是显得更加生动。
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老鼠。我们遇见的老鼠可能是田鼠的变种,连尾巴算上有一尺长,和我童年时在昆明常见的老鼠大小相当。云南的老鼠每年咬伤甚至咬死的婴儿数以千百计,这里的老鼠虽不至如此凶残,但也胆大妄为。有一次团篮球队打比赛,观众围得水泄不通,篮球场上居然冒出一只老鼠向大家示威。更令人恼火的是,夜里睡觉时,经常有老鼠在头上脸上跳来跳去。于是大家创造出“上头”这个词,和猖獗之极是同一个意思,但是显得更加生动。
为了对付老鼠,大家想了很多毒辣的办法。北京知青傅家三容貌超凡脱俗,仿佛穿越几万年时空而来的山顶洞人,他说话时舌头有些僵硬,令人想起《列宁在十月》中那个闹着要去抓列宁的密探。家三是公认的能工巧匠,他制造出一种能连续捕捉三只老鼠的捕鼠器,构思巧妙,但是实际上只要有一只老鼠被捕,其他的同伴绝不会继续上当,真是辜负了家三的手艺。
捉老鼠成为生活中的乐趣。一天夜里三排捉到一只老鼠,全排的人都从被窝里爬出来,最喜欢鼓捣电器的马文然拿来一个老式电话上的手摇发电机和一套变压器,老鼠被电得频频摇头,另一位北京知青何涛惊呼:“和宾努一样啊!”宾努亲王是西哈努克流亡政府的第二号人物,当时住在中国,在新闻记录片中经常出镜,不停地摇头正是他的招牌性动作。
大炉班的知青也别出心裁,有一次他们下夜班后捉来许多老鼠摆在门前的路上,然后泼上水冻成一个巨大的方阵,第二天早上出操时,路过的女知青吓得连声惨叫。

最残忍的方法是用雷管将老鼠炸得尸骨无存。时间长了,大家对老鼠的兴趣逐渐减少,捉住后就直接淹死,再后来懒得动手捉,索性和老鼠和平共处。我们宿舍内常有一只相貌特异的老鼠出没,大家给它起了个外号“瘦脸”,偶尔几日不见,还有些挂念。
实际上人类对老鼠的了解是很肤浅的。有几个人知道老鼠有为同伴收尸的传统呢?刚开始听到时,我还不大相信,后来验证了一次,用电线将死鼠捆在床腿上,第二天早上发现电线被咬断,死老鼠已经不见了。单凭这一点就足以让与同类相残其乐无穷的人羞愧,我们和老鼠相比,究竟哪个更文明?
记得有一年苏联的一些科学家建议把狼列入受保护动物名单,被《红旗》好一通狠批:看苏修已经堕落到何等程度。
傲慢自大的人类感觉不到其他动物的体验,也不知道它们也有自己的心灵,我们已经愚昧到何等程度。
来源:微信公号:老鼠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