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非常遗憾的是,在文言诗歌翻译尚未达致成功就为白话文运动所阻断,等到阻力稍退正待重新开始时,一批劣制译文丝毫不顾文言诗歌翻译的应有发展路径,竟将之拖向倒退之途。”
使用文言翻译,散文取得了比诗歌更大的成就,林纾和严复是苏曼殊远远不能比肩的。虽然白话文运动强劲地阻断了文言诗歌翻译的进展,但继续摸索其成功的路径,仍非徒劳无益。今日,我们比苏曼殊的时代具有了优势,不必仓促译写,而大可以在历史的经验之前先做一番冷静的反思。文言诗歌翻译的欠发达,也正是通过反思才看到的。不过,我们似乎轻率地把文言的特点当成了缺点,进而将之逐出翻译的领域,反思也就中止了。值得反思的地方很多,这里只谈文言散文和诗歌的不同特点,以见在翻译中散文更容易成功,诗歌更需要慎重。
中国的文言从口语脱离,逐步形成自身的法则,并以法则的秩序性建构出封闭的审美程式。这些程式根基于对古典的追摹,从而保持与日常世俗的疏离,成就一种“古雅”的美感。虽然程式的固化容易扼杀天才的创造力,但如王国维所指出,“古雅之能力能由修养得之,故可为美育普及之津梁。” 长期处于“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明史·李梦阳传》)的熏染下,天才的创造也必须被这些程式所轨约。桐城文法和江西诗法,分别归纳了古文程式和古诗程式的“共法”,唐宋以下,几乎没有人逾越过。
刘大櫆在《论文杂记》里强调了文法和诗法的不同,他说:“昔人谓‘杜诗韩文无一字无来历’。来历者,凡用一字二字,必有所本也,非直用其语也。况诗与古文不同,诗可用成语,古文则必不可用。故杜诗多用古人句,而韩于经史诸子之文,只用一字,或用两字而止。若直用四字,知为后人之文矣。” 同是根基于对古典的追摹,文法仅仅要求用字有所本,也就是说,必须使用大家所共同遵循的典范书面语,却不得直接使用现成语句。所谓只用一二字而止,不得直用四字,就是这个道理。诗法就不一样了,可以直接使用现成语句。为什么呢?因为诗歌要讲究对仗。对仗就需要两个句子,如果这两个句子都是现成语句,必然有不一致之处,倘使它们之间产生出一致性,就造成了一种类似惊异的美感。钱钟书明白这个道理,他说:“律体之有对仗,乃撮合语言,配成眷属。愈能使不类为类,愈见诗人心手之妙。譬如秦晋世寻干戈,竟结婚姻;胡越天限南北,可为肝胆。” 这样一来,诗法和文法之间就有了不同,诗法增加了一项使用现成语句的要求。
在翻译中,诗法自然显得比文法困难,怎么找到合适的现成语句,既要翻译出原意,还得自成对仗,无疑是个更高的要求。所以,文言诗歌翻译很少采用格律严密的近体诗,多数是要求相对宽松的古体诗,这样就回避掉了那项增加的要求,而只须遵守一般古文的用词规范。文言诗歌的美感特色因此大为削弱,其成就不及散文,也在情理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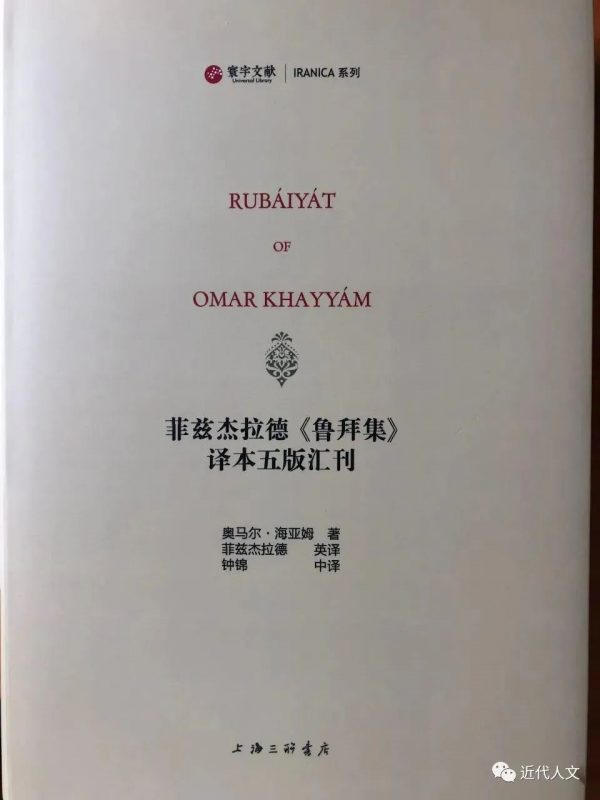 对这一点有所认识,文言诗歌翻译才可能进一步发展,以致渐趋成功。但非常遗憾的是,在文言诗歌翻译尚未达致成功就为白话文运动所阻断,等到阻力稍退正待重新开始时,一批劣制译文丝毫不顾文言诗歌翻译的应有发展路径,竟将之拖向倒退之途。我举出的例子是傅正明的《鲁拜集初版新译》。这是他本人自称“继五卷本《鲁拜诗词新译五百首》(唐山出版社,2015年)之后又一研究、翻译《鲁拜集》的力作。”(见译序)这位译者的履历挺辉煌,“198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学专业,获文学硕士学位,现居瑞典。”主要著作有论著三种,长篇小说一种,译著二十多种。
对这一点有所认识,文言诗歌翻译才可能进一步发展,以致渐趋成功。但非常遗憾的是,在文言诗歌翻译尚未达致成功就为白话文运动所阻断,等到阻力稍退正待重新开始时,一批劣制译文丝毫不顾文言诗歌翻译的应有发展路径,竟将之拖向倒退之途。我举出的例子是傅正明的《鲁拜集初版新译》。这是他本人自称“继五卷本《鲁拜诗词新译五百首》(唐山出版社,2015年)之后又一研究、翻译《鲁拜集》的力作。”(见译序)这位译者的履历挺辉煌,“198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学专业,获文学硕士学位,现居瑞典。”主要著作有论著三种,长篇小说一种,译著二十多种。
但辉煌的履历并不一定产生辉煌的译作,尤其当你看不到真正的辉煌之时。文言诗歌翻译《鲁拜集》的辉煌自非黄克孙译本莫属,傅正明在《明报月刊》2020年第一期发表《略谈鲁拜集第一首的迻译》一文,对之进行了批评。原因是因为他认为,诗中“‘光箭’意象隐含抗击社会黑暗的政治意味”,而黄克孙忽略了这个隐喻。他顺便讽刺了一下我的集唐译文,我最后一句集张籍诗“朝光瑞气满宫楼”,他说“形神俱离”、“粉饰太平”,颇有上纲上线的味道。
在谈这个评论之前,最好先看傅正明自己的译文:“东君醒看寒星瘦,出海红轮溢暖流,光箭满弓驱黑夜,金锋直射苏丹楼。”说它惨不忍睹,大概一点不过分。不要说江西诗法、桐城文法的要求,甚至连正常达意的要求都做不到。我结合傅正明《鲁拜集初版新译》这部自称的“力作”,归纳出五点不足,逐一来看他这首的译文。
首先,最基本的格律往往不能遵守。格律主要是两点,一个押韵,一个平仄。因为旧体诗翻译的难度,押韵从一开始就比较宽松,允许在平水韵的使用上“出韵”,钱钟书在《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一文中,就说到这首译诗“出韵两次。” 我也不为难傅正明。只是他有些时候出得太离谱,比如初版第59首:“悄悄溜了封斋月,重临独立陶工舍,陶工舍,土坯幻影,眼前身侧。”“舍”字只有在当“释”的意思讲时才读入声,作房舍讲,绝不读入声,这个字押到入声里就离谱了。至于平仄,他不合的地方就太多了。最有意思的是,他书后附有“中国古典诗词格律,以《鲁拜集初版新译》代表作为例”,(嗯,自己称自己的译作为“代表作”,可与“力作”媲美。)明明白白标出平仄,竟也公然不合。为节省篇幅,只举一例。《如梦令》第三句“⊙仄仄平平”,他填的是“天使携家珍”(初版第42首),“携”字当仄而用平。这一首“金锋直射苏丹楼”,三平脚,“苏”也是当仄而用平。其实,这个很好调整,“苏丹”,旧译有“素丹”、“素檀”、“算端”,随便换一个就行了。格律都不能娴熟掌握,还得我专门提到,实在太委屈了。
其次,用词不符合文言规范。这也有两点,一是不能准确使用典范的书面语,二是不能达意。傅正明的古典词汇显得极其贫乏,几乎很少能写出具有旧体独特古雅美感的句子。比如,初版第3首:“晨鸡初唱东方白,便闻酒肆敲门客:‘店主快开门,晓光催旅人,花开片刻落,月满三天缺,他日上冥船,重逢无后缘。’”全篇是彻头彻尾的“老干体”句子,好在还能勉强达意,尽管限于格律,“月满三天缺”别扭了,“上冥船”笨拙了。而很多时候被格律限制得太无奈,只能生造词句,连达意都做不到了。初版第5首,也就两个字押韵,(傅正明的七绝多数首句不入韵,倒是不算错,但他押韵的水准也就可见一斑了。)结果把句子写成这样:“水榭玫瑰又竞肥”,让我头脑中不停地回响“名花倾国两相欢”。而初版第6首这句“黄腮欲治醉红酡”,谁要能读懂,我还真是佩服了。我只能告诉他,“治”当动词用时,读平声。现在我们再看“光箭满弓驱黑夜”,也就习以为然,不会觉得这表达太难受了吧。
第三,不能娴熟化用古典的现成语句。造成如此的原因,一是掌握的现成语句有限,二是缺乏“使不类为类”的运用技巧。初版第17首,直译是:“他们说狮子和蜥蜴正侵占/杰姆西王欢呼豪饮的宫殿”,傅正明译为“蛇盘狮吼古龙宫”。指代君主的宫殿,自可有无数的用词,偏找一个指称神话中龙王宫殿的用词,其古典掌握之差只能令人摇头。初版第15首,原诗的意思:不管是勤俭的还是奢靡的,最终都得沉埋地下,不会像金沙一样被再次挖出。傅正明译作:“龙蛇同路归黄土,能否出棺看世风。”前一句化用《庄子》“一龙一蛇”,代指勤俭的和奢靡的,没有问题,后一句陡然接以口语,忘了和前一句呼应,也就引起质疑:莫非龙蛇归土还有棺材?初版第9首他有两句:“濯足渭河头,濯缨泾水秋。”在注释自道出处,可见其得意,但内行是绝对不会如此化用的,其水准正从自鸣得意中见出。不能“使不类为类”,其实还不如不用成语。那这一首第一句的“东君”,用《楚辞》的成语,其实指代的就是太阳,却和第二句的“红轮”没有明确的关合。不能娴熟地进行化用,在傅正明的译本里是个普遍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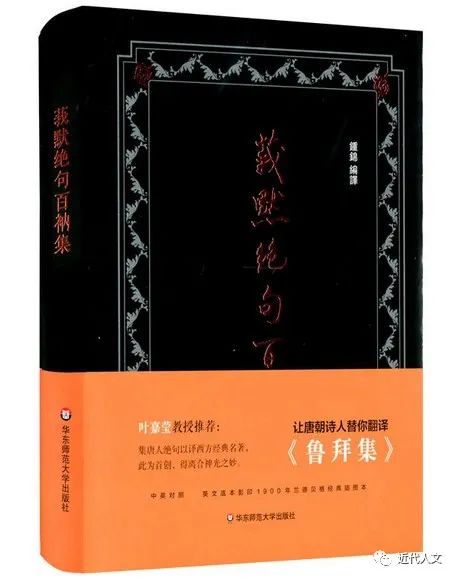 第四,作为译作经常增入不必要的辞句,或是游离于原诗,或是违背原诗。我们并不否认,黄克孙,甚至菲兹杰拉德自己的翻译,都大胆地进行了创造,所谓“宁为活麻雀,不作死老鹰”。但他们如此做,能够使原诗更符合自己民族语言的审美习惯,表达出更好的效果。傅正明如此做,却是前述三点不足在翻译上的综合体现。先看黄克孙的例子,第31首直译是:“我从地心飞升,将第七门穿过,/稳踞在土星的宝座。/许多疑惑都已在路上解开,/只除了那人类命运的最大之惑。”黄克孙译:“骑鹤神游阿母台,七重天阙拂云来。玉皇仙籍偷观尽,司命天书揭不开。”这样的创造,其美学效果不说自解。而傅正明呢?初版第68首:“纵使我埋骨成灰,/也要把葡萄的网罗向空中抛飞。/不会只有一个路过的信士,/将被它不知不觉地牵回。”他居然译作:“身后遗芳若网罗,破棺酒气罩枝柯,路经坟地朝香客,醉倒如同堕爱河。”我实在不能理解,即使对“朝香客”有无比的恼怒,也不至于平添“堕爱河”这样近似污蔑的比喻吧?诚然,波斯很多作品借爱欲寓意,但菲兹杰拉德并不认可,他在译序里指出:“不管这些意象的神秘意义对于欧洲人是多么显而易见,但它们即使被波斯的平信徒所引述,也不会不脸红。”我们没有理由相信,这首诗有任何可能暗示了“堕爱河”的意思。如此翻译直接背离原诗的主旨,我想不出任何缘故,只能猜测傅正明大概唯有“爱河”一词可以在这里来押韵了。这第一首的“出海红轮溢暖流”,就是游离于原诗的例子。菲兹杰拉德译文有四种版本,没有任何一版有“出海”的意象,第二版则明确说“太阳在东山的后面”。波斯的地理位置,大概也不容易有“出海红轮”的景象。傅正明在《明报月刊》自己讲:“让大海托出红轮,为的是着一‘溢’字以暗示贯穿在珈音哲学中的流溢说。流溢说,也可以译为照射说,把万物视为神的余光流溢或照射的结果。”即使有贯穿在珈音哲学中的这个思想,我们也不应该替珈音处处补充完备,何况这个暗示的手法根本没有必要,难道太阳从东山升起不一样照射或流溢吗?在我看来,他的说法只是为他的游离找借口而已。
第四,作为译作经常增入不必要的辞句,或是游离于原诗,或是违背原诗。我们并不否认,黄克孙,甚至菲兹杰拉德自己的翻译,都大胆地进行了创造,所谓“宁为活麻雀,不作死老鹰”。但他们如此做,能够使原诗更符合自己民族语言的审美习惯,表达出更好的效果。傅正明如此做,却是前述三点不足在翻译上的综合体现。先看黄克孙的例子,第31首直译是:“我从地心飞升,将第七门穿过,/稳踞在土星的宝座。/许多疑惑都已在路上解开,/只除了那人类命运的最大之惑。”黄克孙译:“骑鹤神游阿母台,七重天阙拂云来。玉皇仙籍偷观尽,司命天书揭不开。”这样的创造,其美学效果不说自解。而傅正明呢?初版第68首:“纵使我埋骨成灰,/也要把葡萄的网罗向空中抛飞。/不会只有一个路过的信士,/将被它不知不觉地牵回。”他居然译作:“身后遗芳若网罗,破棺酒气罩枝柯,路经坟地朝香客,醉倒如同堕爱河。”我实在不能理解,即使对“朝香客”有无比的恼怒,也不至于平添“堕爱河”这样近似污蔑的比喻吧?诚然,波斯很多作品借爱欲寓意,但菲兹杰拉德并不认可,他在译序里指出:“不管这些意象的神秘意义对于欧洲人是多么显而易见,但它们即使被波斯的平信徒所引述,也不会不脸红。”我们没有理由相信,这首诗有任何可能暗示了“堕爱河”的意思。如此翻译直接背离原诗的主旨,我想不出任何缘故,只能猜测傅正明大概唯有“爱河”一词可以在这里来押韵了。这第一首的“出海红轮溢暖流”,就是游离于原诗的例子。菲兹杰拉德译文有四种版本,没有任何一版有“出海”的意象,第二版则明确说“太阳在东山的后面”。波斯的地理位置,大概也不容易有“出海红轮”的景象。傅正明在《明报月刊》自己讲:“让大海托出红轮,为的是着一‘溢’字以暗示贯穿在珈音哲学中的流溢说。流溢说,也可以译为照射说,把万物视为神的余光流溢或照射的结果。”即使有贯穿在珈音哲学中的这个思想,我们也不应该替珈音处处补充完备,何况这个暗示的手法根本没有必要,难道太阳从东山升起不一样照射或流溢吗?在我看来,他的说法只是为他的游离找借口而已。
第五,翻译够不上“信达雅”的任何一个标准。这是前述三点不足在翻译上的必然结果。初版第73首是众多名家争相翻译的名作,按说不该出现不信不达的情况,傅正明居然也做到了。直译是:“啊,我爱,要是你我能跟他协力/去掌握万物所有的可悲设计,/我们难道不会把它砸碎,/再重新塑造,使它最接近心中所欲?”他译作:“唤醒意中人,借得光明手,合力掀翻老地球,重酿心仪酒。利剑断愁丝,新法离窠臼,打碎皇冠造大樽,浮海同佳偶!”原诗是去掌握宇宙万物的整体设计,岂止仅仅掀翻一个老地球?掌握了设计之后,砸碎旧的,塑造新的,极有革新的魄力。傅正明呢?他“离窠臼”的“新法”,不过是“重酿心仪酒”,“打碎皇冠造大樽,浮海同佳偶”,珈音的消极抗争手段成了终极目的。如果他去读读菲兹杰拉德译序里关于珈音的“酒”的论述,大概会明白些。这是不信。“重酿心仪酒。利剑断愁丝,新法离窠臼”,三句之间,没有任何过度衔接,好像在打碎皇冠之前,先要把自己的句子打碎。这是不达。坦率地讲,就傅正明的译文品质来说,要求“雅”,实在近于说梦了。再看这个第一首,原诗说,太阳驱散了群星和黑夜,再把金光之箭射向苏丹的塔楼。第一句“东君醒看寒星瘦”就失信,仿佛太阳只是慵懒地醒来,旁观着寒星一点点黯淡下去,原诗的力度丝毫没有体现出来。傅正明自己讲的“唤醒的诗学”,光明战胜黑暗的文学母题,在第一句中就减色了。其它三句之不达、不雅,前面都已谈过,不再赘述。
这五点不足,都能体现在这第一首上,并非偶然,他的译作几乎每一首都有这些毛病,只是我不能一一列举。明眼的读者估计已经看出来,傅正明根本达不到写旧诗最基本的要求,真的不明白,他为什么还强自己所难要用旧诗来翻译呢?
 了解了傅正明的文言诗歌翻译能力,再看他对黄克孙的批评。自然,“诗无达诂”,傅正明一定要把《鲁拜集》第一首理解成“隐含抗击社会黑暗的政治意味”,没有什么不可以,但以此为唯一标准衡量别人的译文,就显得武断了。如果直译,是这样:“醒来啊!太阳已让群星逃散,/从夜域之中,在他的前面,/连夜也一起驱出天际,再举/光之长矢射中苏丹的塔殿。”我们理解为太阳光辉普照也没什么问题,照射不一定就是射击。因此,黄克孙用了中国的意象:“羲和骏马鬃如火,红到苏丹塔上云。”那样奔放的想像,是纯粹中国式的天才趣味。出在二十多岁的少年笔下,我真是佩服,忘了指责他羲和是御龙而非驾马。这样的诗才,我认为不是傅正明的水准可以妄议的。顺便替我自己辩解两句。我集张籍诗“朝光瑞气满宫楼”的译文,自是对诗歌的一种理解,傅正明可以表示不满。但他忽略我自己不用集句的译文,就显得有些深文罗织。我的译文是这样的:“东君长矢举遥空,直迫星芒夜色穷。为唤人间新睡觉,金光看射素檀宫。”你还能看出“粉饰太平”的意味吗?
了解了傅正明的文言诗歌翻译能力,再看他对黄克孙的批评。自然,“诗无达诂”,傅正明一定要把《鲁拜集》第一首理解成“隐含抗击社会黑暗的政治意味”,没有什么不可以,但以此为唯一标准衡量别人的译文,就显得武断了。如果直译,是这样:“醒来啊!太阳已让群星逃散,/从夜域之中,在他的前面,/连夜也一起驱出天际,再举/光之长矢射中苏丹的塔殿。”我们理解为太阳光辉普照也没什么问题,照射不一定就是射击。因此,黄克孙用了中国的意象:“羲和骏马鬃如火,红到苏丹塔上云。”那样奔放的想像,是纯粹中国式的天才趣味。出在二十多岁的少年笔下,我真是佩服,忘了指责他羲和是御龙而非驾马。这样的诗才,我认为不是傅正明的水准可以妄议的。顺便替我自己辩解两句。我集张籍诗“朝光瑞气满宫楼”的译文,自是对诗歌的一种理解,傅正明可以表示不满。但他忽略我自己不用集句的译文,就显得有些深文罗织。我的译文是这样的:“东君长矢举遥空,直迫星芒夜色穷。为唤人间新睡觉,金光看射素檀宫。”你还能看出“粉饰太平”的意味吗?
言归正传,现在谈谈我对傅正明批评的意义。文言诗歌翻译渴盼有进一步的发展,我在文章开篇,从学理严肃分析了原因。但一批劣制译文的出现,给了批评文言诗歌翻译最好的借口。郭延礼坦率地说出:“翻译外国诗歌用中国古典诗体,又用文言,很难成功。”傅正明的“力作”,恰恰印证了郭先生的论断。我真心期待文言诗歌翻译真正踏上成功之途,转变人们固有的偏见。因此,我希望达不到写旧诗最基本要求的朋友,应该更谦虚地对待如黄克孙的译文,不要信口妄议,也不要率尔操觚。这样尽管不能保证自己能够进步,至少眼光会变得好一些,不再发表和出版“力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