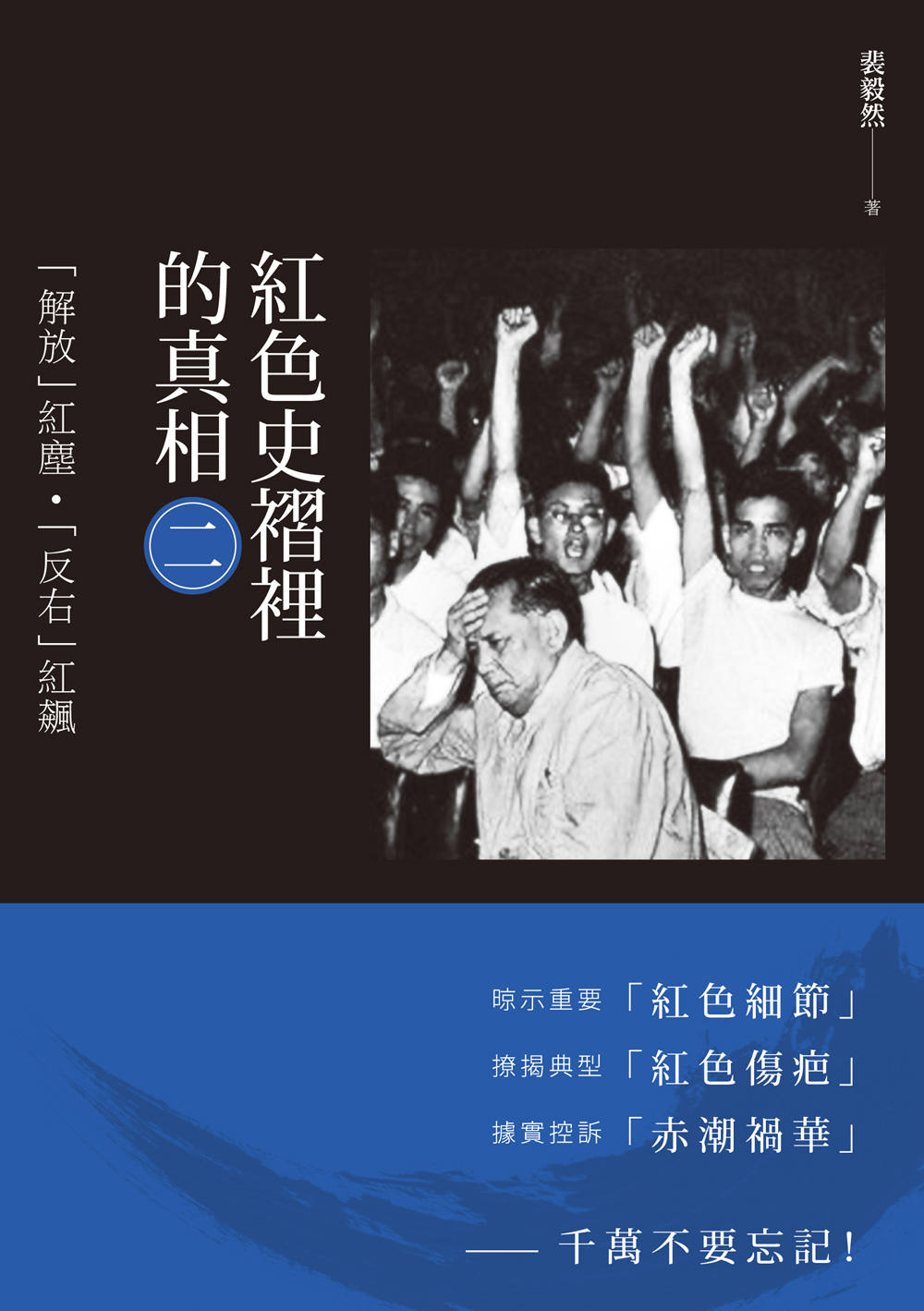《红色史褶里的真相》第四辑 :“反右”红飙(4)
傅作恭之死
近读西北民族学院女教师和凤鸣惨烈回忆录《经历——我的1957年》(敦煌文艺出版社2001年,钱理群书评载2004年5期《随笔》),不想读出一段鲜为人知的情节。国军反水将领傅作义八弟——傅作恭(1903~1960),居然也是“右派”,1960年3月饿死于甘肃酒泉夹边沟劳教农场。细细说来,傅作恭之死,还有一些悲上加悲的深层原因。
傅作义(1895~1974)兄弟十人,以“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排名。八弟作恭1945年毕业于金陵大学森林园艺专业,赴绥远见二哥作义,谈了建设家乡的理想。无奈内战风云正紧,二哥忙于军务,虽然欣赏八弟学成有志,也只能安排他到河套经营一家农场,为发展农业做点事。
1949年后,中共任命傅作恭为农场场长,但他的许多想法不合上级意图,无法伸展抱负。加上老粗管老细、外行领导内行,科班出身的傅作恭当然很有些看法,也不习惯红色政治环境下“必须听党的话”,心情很不爽。他向二哥倾吐抱怨,傅作义通过一起反水的老部下邓宝珊(甘肃省长),1952年安排傅作恭到甘肃省农林厅。
傅作恭性格耿直、脾气暴躁,到了甘肃农林厅仍不适应,尤其反感1958年“大跃进”的瞎吹牛,认为甘肃在经济、物质、技术等各方面都不具备上马引洮工程,得罪了甘肃省委,认为傅作恭的意见乃是阶级敌人向党进攻,补划“极右”,送入夹边沟劳教农场。
傅作义获讯,十分难过,又无能为力,虽知老八弟妹潘翠竹在兰州无工作,带着五个孩子很困难,但怕别人议论“搞特殊”,不便多寄钱,只能让她带着孩子回老家农村“自食其力”。傅作义对晚辈说:
老八女人和孩子在农村就是要让人同情哩,我不好多寄钱给他们,绝不能显得一个右派家里比别人强。
潘翠竹苦熬苦盼,巴望二哥救出丈夫。不料竟等来一张死亡通知书——“患病死亡”。[1]
中共夺国之初,摆出“联合政府”的样子,安排一些“民主人士”入阁。水利部长傅作义,当然明白自己的地位,一切尊重中共党组。另一位粮食部长章乃器也是“民主人士”,每件事都要问清中共意见才签字,公认工作做得最好,经常得到毛泽东、周恩来表扬。[2]傅作义虽为部长,实权却握于副部长李葆华。李葆华乃李大钊之子,1962年初升任安徽省委书记。文化部长茅盾(非党员),常务副部长周扬(党组书记),“日常工作对茅盾敬重,部务会议都是请茅盾主持,不过实际工作都是他(按:周扬)负责。”[3]
傅作恭这条山西大汉,一米八以上,身材魁梧,国字脸,浓眉大眼,一表人才。但个大消耗也大,一到夹边沟,伙食粗质恶劣且供量不足,吃不饱肚子,活路又繁重苛沉,很快体力透支,身体迅速垮下来。从没吃过苦的人,哪受得了这份里外夹攻的折腾消耗?傅作恭只得向二哥傅作义写信告急,述说饥饿难耐,劳动太重,顶不住了,盼望援救。傅作义接信,不相信弟弟所言,认为这是诬蔑党的改造政策,往社会主义脸上抹黑,义正词严地回信训斥弟弟,要他老老实实接受改造,云云。为此,傅作恭遭到农场狠狠批斗,他绝望了。
傅作恭死前,连续八天清晨五点半起床背草篼,第五天拉稀,实在背不动,难友高尔泰(1935~ )向管教赵来苟求情:
傅作恭是真不行了,我看见他拉的黑屎!
此时,夹边沟大批“右派”饿毙,都知道拉黑屎是“不行了”的信号。然而,这位管教却说:
我拉的也是黑屎!谁叫他当右派?他如果不是右派,就到北京住他哥哥傅作义的公馆,想吃什么吃什么,谁能管到他头上?傅作义与人民为敌,杀了不知多少人。傅作恭从国外回来,也不是个好东西!(按:一直误传傅作恭是留美水利工程博士)
于是,傅作恭被逼背着草篼继续挣扎走了十几里路,实在走不动,向赵来苟抱怨:
我实在走不动了,在资本主义国家,有事还允许申辩嘛!
赵来苟大怒:我看你就是资本主义!
赵硬要傅作恭负重前行,傅作恭腿上没劲,寸步难行,无力迈步,赵来苟便叫其他犯人用草绳套勒着傅作恭的脖子,前后各拉一根绳子,逼着傅作恭背着草篼一步步挪走,傅作恭往前倒,后边的人拽一下绳将他拉起,若往后倒,前面的人拽一下绳再将他拉起。三天后,傅作恭走到背草篼处再也站不起来,领工的管教舍不得多费劳力抬他,找来一只草笆子,把傅作恭放上去,由一名劳教分子用绳子拉着,“多快好省”地将傅作恭一路颠簸拉回住地。前兰州医学院教授、“右派”刘逢举过来一看:“已经死了两三个小时了!”
1960年底,全国大面积饿死人已是“公开的秘密”,无法再捂盖子,北京只得派出检查团分赴各地视察“灾情”。甘肃检查团由监察部长钱瑛带队,团员公安部副部长王昭及部分“民主人士”。水利部长傅作义向周恩来请行,随团前往甘肃。深秋一天,检查团来到酒泉夹边沟农场,场部听取汇报,傅作义插问:“这里有个傅作恭没有?”吕教育股长答道:“可能已经死了。”傅作义再问:“请问埋在哪里?”场长刘振宇推托责任:“听说他可能跑了。”傅作义忍无可忍,怒目圆睁——
你这哪是共产党做事?国民党死了人也要交代清楚。你说他跑了,他50多岁的人怎么跑?再说他就是有些右派议论,没有别的问题,他为什么要跑?
毕竟,手足情深,66岁的傅作义深负愧疚。到达夹边沟后,当他了解到这里严酷的生存条件,回想弟弟的求救信,自己非但没援助,还严词训斥,能不垂首饮泣吗?
据可靠消息,“夹边沟农场原来有劳教人员2800多人,能够回来的只有六七百人,是个零头。”
和凤鸣的《经历——我的1957年》,记录不少饥饿细节:吃生麦胀死、100公斤清漆被全部喝光、煮食人腿、草根树叶、老鼠蚂蚱、生食牛脑牛肉、刨吃死人内脏骨头、尸体被吃得只剩下一副骨架一颗头颅……
饥饿中的人际关系难以想象——
哪怕举步难艰,也要自己挣扎着去打,如果让别人去打饭,代打饭的人就有可能不顾一切后果地打了饭抢吃个净光。对挣扎在死亡线的人来说,哪怕是被吃掉一两口也是不行的呀!因为这和了许多碱菜子的面条虽然不值几个钱,许多奄奄一息的生命却全靠它来维持呀!每个挣扎在鬼门关上的可怜人,谁都绝不放弃能带来生的希望。任何微乎其微的可能,即便是碗边上的半根面条、半口汤、半片菜叶。我们同屋的四个女伙伴,一向都是自己打自己的饭。
当时全国粮库并不是没有粮食,农场也并不是必须将粮食限定于每月15斤,让这么多人去熬度鬼门关,因为“在管教干部心目中,劳教分子饿死若干个,又算什么?!”[4]
[1] 崔增印:〈傅作义与右派八弟傅作恭〉,《炎黄春秋》(北京)2010 年第7期,页39~40。
[2] 章立凡:《君子之交》,明报出版社(香港)2005年,页146。
[3] 张光年:〈回忆周扬〉,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页8。
[4] 和凤鸣:《经历——我的1957年》,敦煌文艺出版社(兰州)2001年,页364、371、289。
初稿:2005-2-21;增补:2010-7;
原载:《开放》(香港)2005年4月号(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