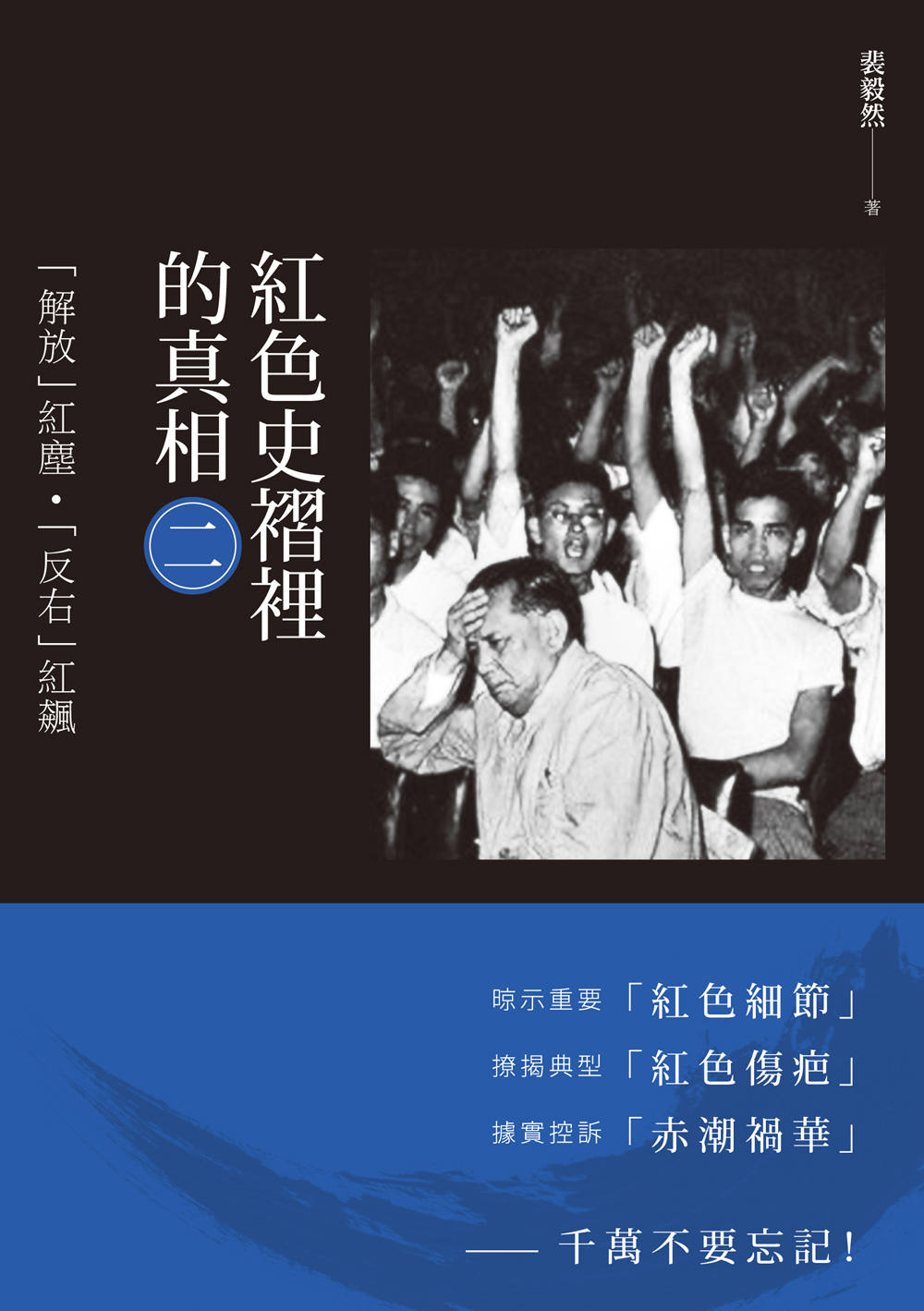《红色史褶里的真相》第四辑 :“反右”红飙(7)
浓春时节送壮士——与张元勋深谈北大学生“右派”
2013年4月15日傍晚,京友Email:张元勋先生12日去世,追悼会都开过了。急忙上网查询,证实噩耗,电叩曲阜张宅,向马姨(张妻)吊唁,得知元勋先生最后状况。过年时还好好的,三月起的病,无法起身,不久生了褥疮,每次翻身不易,临终前早上连米汤也不愿喝,12日13点51分走的人。吃得苦头不大,没在医院折腾,享寿八十,“善终”于家,也算最后的“好报”吧!曲阜师大文学院、老干部处主丧,14日追悼会,近千人出席。
笔者与元勋先生有一段接触,起因是我在香港购得他的《北大1957》。为研究北大“右派”,多次叨扰,函电交驰,积有数年。张先生与我座师周艾若先生相熟,得知我在研究现代知识分子,读了港美刊物上的拙文,大力支持,向我提供一系列“北大细节”。2009年10月下旬,借参加曲阜师大文学院主办的学术会议,登门拜访元勋先生。
见到元勋先生,大吃一惊。胡杰光盘《林昭之死》中那条老而弥坚的山东大汉,一头白发,面颊消瘦,躯体枯槁,寂坐客厅,旁立拐杖。2002年,元勋先生患上凶险的食道癌,体重160斤减至120斤,垂垂一病翁矣。1933年出生,不过76岁。2009年10月23日下午、26日上午,两度入寓访晤,元勋先生精神尚济,思路清晰,忆力强劲,表达流畅,向我详述北大学生“右派”种种逸闻,一一录下,回沪后整理成文,呈先生过目审定,投给港刊《开放》。其时,《开放》编辑部顾忌“右派”团结,访谈稿压下未刊出。如今,人逝事远,这篇拙稿既作为资料也作为悼文,追思元勋先生。
处理等级 = 当年表现
元勋先生说:他们那几届当年留校的,并非学习优秀,但绝对得是“左”派;北大学生“右派”林林种种,嘴脸不一,须具体辨析,不宜笼统视为纯一整体。
辨别右派当年的表现,很简单,只须看看他的处理等级即可得知。共产党论功行赏、论罪行罚,这种要害处,一点都不会搞错的。尤其那些“著名”右派,罪大罚轻,何故?均因“立功”矣!
寥寥数语,对研究“反右”则是一把辨析右派门类的入门之钥。一尺在握,等级可裁。学生“右派”,虽然同为受害者,但也内情复杂。
1957年5月19日,张元勋与沈泽宜以诗篇〈是时候了〉点燃北大“五·一九”运动。20天后,《人民日报》“六·八”社论。风向一转,沈泽宜迅速转身,反戈一击,立功获赦,7月20日全校大会上发表长篇泪书〈我向人民请罪〉。北大数学系学生“右派”陈奉孝忆文〈北大整风反右运动回顾〉:
沈泽宜第一个在全校大会上做了检讨,并宣布跟张元勋绝交。[1]
2015年6月9日,陈奉孝先生来函确认:沈泽宜不仅在大会上检讨,而且还检举揭发。沈泽宜处理等级最轻——留校察看一年。仅仅行政处分,随届毕业,拿到毕业证,分配工作,每月领薪。另一著名北大学生“右派”谭天荣因毛泽东钦定“当反面教员”,未开除学籍,北大花圃劳动。如此“轻处理”,当然事出有因。6月12日,谭天荣反戈一击发表声明:与《广场》编辑部脱离关系。其后,谭天荣之所以被劳教,并非政治而是刑事。张元勋指说谭天荣一向自称“现世享乐主义者”——不要家庭不要子女只要自己,属于“三天不打,上房揭瓦”的不安定分子。谭在北大花圃劳动,以为风头已过,故态复萌,某晚熊抱人家姑娘,揪至党委。“右派”还如此不老实,老账新账一起算,以流氓罪送劳教。张元勋在曲阜,谭天荣在青岛,居一省而从无来往,“毕业后就没见过面”。
对学生“右派”的处理,根据情节、表现也分六类:最重的“情节严重、态度恶劣”,判刑;其次为劳教;再次保留学籍劳动考察;下面是留校察看、行政处分,最轻“情节轻微,态度很好”,只戴帽不处分;沈泽宜本为第一种“情节严重”,因反戈一击有功,最轻处理——只戴帽不处分。[2]
陈奉孝、张元勋等被构织“现行反革命集团”,陈奉孝“首犯”,判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张元勋判刑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贺永增判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赵清和林树果被判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谭金水反戈一击有功,教育释放。张元勋刑满后,押送山东劳改煤矿,挖煤四年;再押至山东济宁劳改农场,进行“劳改后”,直至1977年“政策性松动”;44岁结婚;1979年11月北京中级法院平反。
元勋先生对同校“右派”陈奉孝十分认可,对笔者说:“陈奉孝人品不错。”
陈奉孝回忆录中:
投机不成蚀把米,这种人在北大的整风反右运动中我遇到过,在监狱、劳改队里我也遇到过,尽管这种人是少数,但确实存在。坦白地说,我并不认为当年被打成“右派”的人,心灵全都是高尚的,尽管他们也受了委屈,也应该平反。
另一名因检举揭发而获轻处理的北大学生“右派”谭金水,所有同案判刑4~15年,惟他“有立功表现,教育释放”。而从事所谓“组织活动”的过程中,谭金水是“最积极一个……许多主意都是他出的”,被他出卖的陈奉孝:
我才知道原来是谭金水把我们出卖了!这真出乎我们意料之外。……为了争取宽大处理,却把我们都出卖了。我能不恨他吗?[3]
林昭恋情
林昭近年名声鹊起,事情多起来。前些年,避居美国的其妹彭令范抱怨:
怎么一下子冒出这许多姐夫?
张元勋虽然对沈泽宜印象极差,但仍据实告知笔者:林昭恋情,只有与沈泽宜与甘粹实有其事,其他都是胡扯。与沈泽宜,还是林昭主动追沈。林昭个矮肤黑,并不漂亮,衣饰亦不合时,既缺少“江南佳丽”传统风韵,也不具备“阳光女孩”现代风采。沈泽宜当年可是浪漫倜傥的江南小生,对林昭不屑一顾。至于谭天荣,虽然谭讲他与林昭如何如何,纯属谎言。林谭相认于1958年以后,同在北大苗圃劳动才相识,此前并不相识。鸣放初期,林昭对谭的狂妄十分厌恶,谭近年连续撰文称述与林相识于1954年,一派谎言。
我问:“您怎么知道林沈之间的私密?”张答:“因为我们是好朋友,无话不谈。”再问:“既然林昭连这种事都对您说了,那你们之间……”再答:“我们之间确实没那层意思。只因在《红楼》编辑部共事而有交往。”
2013年6月,笔者再次访学香港中大,才读到陈奉孝先生的《梦断未名湖》,内有一段——
听张元勋讲,林昭原本不是右派,她与张元勋有一段恋情,张被打成右派后,团组织叫她与张元勋断绝关系,她不但不与张断绝关系,而且多次为张鸣不平,就这样一步步升级成了右派,进而成了“反革命”。她坚贞不屈,受尽折磨,最后被逼疯了。六八年被枪毙前,张还冒充是她的未婚夫前去探过监,结果张回到就业的劳改农场后被关了禁闭。[4]
可惜已无机会向张先生证实这一“有趣”细节了。
张先生十分反感将林昭说成“才女+美女”,他说林昭既非美女,更非“江苏省状元”,乃一调干生。1950年代高考不公布成绩,更没有“状元”之类名堂,“江苏省状元”从何说起?至于说林昭“北大第一才女”更属荒唐,此六字本身就十分模糊:“第一才女”指“全校第一”还是“全校女生第一”? 此六字来自沈泽宜的“创造”。张元勋先生说:林昭原本很左,应该算是那种“红苗子”,历次运动都积极参加,反右初期也很左,她的反思是逐步展开,渐渐深入。
痛斥沈泽宜
张先生语笔者:“一些人在等我死!因为我是他们底细的知情人。”2005年春,沈泽宜得知张元勋患癌症,打电话至张家,张先生接的电话。沈问:“张元勋家吗?”“我就是张元勋。你是谁?”“我是沈泽宜。”“哦,什么事?!”沈即挂断电话。
张先生说沈乃打探虚实,“想知道我是否死了”。张先生再告知:香港首版《北大1957》前夕,沈闻讯跑来曲阜,央我手下留情“放他一马”,我心一软,对他当年积极反戈的告密甚有保留。不料他对我载录其〈请罪词〉仍不满意,频频电话纠缠,指责我“不够朋友”。2008年《北大1957》修补版,“这回不再留情,一概照实录出”——
望着在讲台上表演着的沈泽宜的作态,他似乎从“末路”中又得到了一次“中兴”!不管是什么姿态,他似乎都很自赏自恋,正是声色俱佳!要的就是这么一种“爆炸”效果!……〈是时候了〉的那个“争名于前”的“诗人”,竟首先自辱、卖友求赦,立于危岸、袖观无数落水者——这叫做“欺世”,也叫做“盗名”!……其实沈泽宜确确实实地不应该是“右派”,但也不是“左派”,因为这二者令他扮演,皆不会演好,皆不酷似,他最合适的角色是“风派”!……风性难改,乃欲易辙嫁左,这正是他愈演愈丑、愈演愈劣的秉性的表现![5]
2015年6月11日陈奉孝先生潍坊来函:
当年北大“右派”大都对沈泽宜有这样的看法(按:指“风派”)。沈当年在北大非常喜欢出风头。
谈及沈泽宜至今独身,张元勋谓之:“此为其本性所致!”1985年,北大校友会,几位老大姐劝52岁的沈泽宜“实际一些”,赶紧找伴,不要再讲究文化和漂亮什么的,能生养后代即可,终究得防老。
沈一嗤鼻:
庸俗!我都坚持到今天了,一定要找个年轻漂亮、会唱歌跳舞、会写诗会浪漫的姑娘!
老大姐们被激怒了:沈泽宜,你改不了!那你去找吧!
张元勋告知:
沈泽宜现在并非无人照顾,他来我家时亲口对我说,现在有保姆母女俩侍候他,他认那女孩为干闺女,并把她弄到嘉兴师专中文系学习。
林昭如在,沈并不会要她的—— 一个76岁的老太婆!
也巧,1994年秋笔者在杭州教过一位湖州师院中文系女生,她得知我认识“沈老师”,一脸诡秘:“对沈老师,我们可是集体回避哟!”我在电话里向元勋先生不经意提起,张先生对“集体回避”四字留忆深刻,说是对沈最简洁的评语,随口告知沈泽宜的一段“师生恋”。
必须交代一下,笔者与沈泽宜先生亦熟,也有一些来往。2005年初,其时Email尚未普及,我初次访学香港,为沈泽宜带稿子给《开放》。2006年,曾携妻专赴湖州探访。但这次曲阜访张,张元勋先生既然这么说,我只能照实录出,恳望沈先生见谅。同时,我还得说:1989年5月沈泽宜先生数天在天安门广场,以老学长身分支持“八九学运”,封从德回忆录中说他们在广场上受沈影响很大。
声名走响
近年,《北大1957》、狱访林昭,张元勋在港美知识界声名渐起。1966年,张先生刚出狱即赴沪探监林昭于提篮桥,北大学生“右派”之惟一,元勋先生此生最大亮点,港评:“燕赵遗风”。眼前的张先生廉颇已老,伤病缠身,令笔者无法不生风霜之叹。赠元勋先生一本拙著,题词:“永远铭记您1957年的支付”。
元勋先生还告知或值记录的当年高考细节:1954年,他以青岛一中毕业生参加高考,文科考四门:语文、政治、外语、史地。四档志愿(每档一个专业,可报四所学校),第一档第一学校为第一志愿。录取通知书只通知录取与考取学校,没有成绩。录取名单仿旧时登报,他从报纸上得知录取北大,后才收到北大通知书。落榜者则无音讯,没有后来的“安慰信”。
三天后再访张寓,元勋先生告知翻阅所赠拙着《历史皱褶里的真相》,说书中所写的太平天国暴行是真实的。他幼时听祖母说过“长毛贼杀人放火”,当时哄吓孩子都说“不要哭,长毛贼来了!”张先生家乡妇女怕长毛强奸,带着草秸编席躲难于海滩,长毛骑兵上不了海滩。
“北大右派”,张先生终身为之“特殊关注”。在曲阜,张先生自然是“重点人物”(有可能Number one),尤其关注他与海外的来往,电话、信函……有关方面都有“兴趣”。一日划“右”,终身另类啊!
历史无情亦有情,林昭、张元勋的“五七支付”终究还是化为社会前进的推力,拥有我辈“后来者”。元勋先生的《北大1957》成为最珍贵的“实录”。林昭的愿望实现了——
我随时都会被杀,相信历史总会有一天人们会说到今天的苦难!希望你把今天的苦难告诉未来的人们![6]
元勋先生走了,又少了一位“右派”。中共至今仍未赔偿“右派”22年的苦难——补发工资,文革后对“走资派”则是全部补发的。这位在中共红尘里苦熬一生的“五七壮士”,无法在自己的土地上说出最后的话,《北大1957》只能出在香港。一声长叹,多少怅恨付东风!元勋先生,走好,继承遗志已有人。
[1] 陈奉孝:《梦断未名湖》,劳改基金会•黑色文库编委会(华盛顿)2005年,页349。
[2] 王书瑶:《燕园风雨铸人生》,劳改基金会•黑色文库编辑部(华盛顿)2007年,页217。
[3] 陈奉孝:《梦断未名湖》,劳改基金会•黑色文库编委会(华盛顿)2005年,页127、61。
[4] 陈奉孝:《梦断未名湖》,劳改基金会•黑色文库编委会(华盛顿)2005年,页354~355。
[5] 张元勋:《北大1957》(增补本),明报出版社(香港)2008年,页313~314。
[6] 张元勋:《北大1957》(增补本),明报出版社(香港)2008年,页401。
初稿:2009-11- 4~5; 修改:2013-4-16,再增补:2015-6
原载:《开放》(香港)2013年5月号(初稿)
补记:
2015年6月9~11日,陈奉孝先生就上文真实性数函电复笔者,并同意将其回复整理收录于下:
裴先生:您好!
您对张元勋的采访基本正确,张的回答也基本正确。张元勋与沈泽宜的矛盾始于《广场》刊物出版之初。当时,大家选张为主编,沈为副主编。此后,沈便很少再参与《广场》的事。反右后期,沈在全校大会上痛哭流涕做了检讨和检举。
张写的回忆录初稿拿给我看过,除个别地方有记忆性错误,内容基本属实,但他对沈泽宜和谭天荣用了许多讽刺挖苦的语言,我建议他出版时删去。我劝他只把事实如实写出来就行了,照你现在这样的写法,肯定会引起你们三人的矛盾,亲痛仇快,何必?我们是对历史负责,不是写小说。他口头答应了,但出版时仍用了原稿。不出我预料,此后他们三人便打起笔墨官司。他们三人都到过我家,都希望得到我的支持。我谁也没支持,只劝他们不要再这样互相攻击下去, 他们不听我的劝告,我也就不再过问他们之间的事了。大体情况就是这样。
沈泽宜出版回忆录后寄给我,但他很大程度上是为自己辩解,回忆录中多有不实之处。
陈奉孝
2015年6月9~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