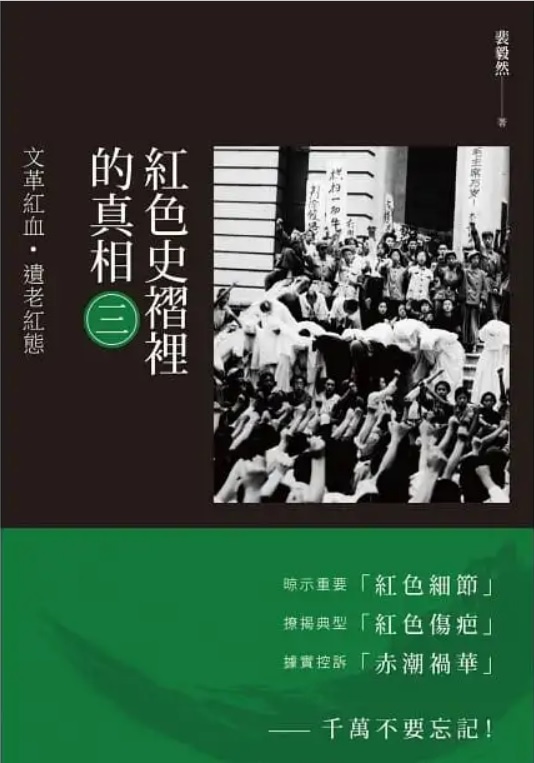《红色史褶里的真相》第五辑 : 文革红血(2)
不要自由要监狱——刘文忠宁愿“二进宫”
2008年1月4日,寒冬午后,上海闸北苏州河边“两岸”咖啡店,第一次见到61岁的刘文忠先生。他刚刚读了拙文〈文革狂涛中的知识分子〉,指着其中一句——“文革中,监狱成为最安全的地方”:”
这句话很准确,你怎么知道的?
他知道我并无入狱经历。我答:“看来的。”是夜,阅读他所赠回忆录《风雨人生路》(《反文革第一人及其同案犯》首版),读到他第二次主动要求入狱,一下子明白了他何以有此一问。
刘文忠(1947~ ),刘文辉九弟,左腿残疾,1966年9月29日帮三哥誊抄万言〈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10月1日赴杭州投递,11月23日晚与刘文辉一起被捕。1969年1月下旬押回原单位——上海徐汇五金厂(街道企业),管制三年,监督劳动,戴帽“反革命”,各类“牛鬼”中罪行最反动、性质最严重,每月只发生活费18元。
还不如“里面”
刘文忠“六进七出”——早晨六点进厂,晚上七点离厂,一进厂先向群专队报到,然后押着一个个车间转过去批斗,人尽可辱的活靶子,高潮时每天揪斗四五场。以前和睦亲密的工友,一个个对他毒骂恶打,似怀深仇大恨,口口声声:“我们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群众!”
批斗频率低下来后,派给他最重最脏最苦最危险的活,尽管他拖着残腿,仍是“牛鬼蛇神劳改队”主力。不久,增派三项八小时外“光荣任务”——打扫最肮的男厕所、清理冲床车间早晚两班废料、打扫两个车间与男浴室。
每天开工前,刘文忠得清理昨天晚班废料、搬运今天日班用料;傍晚,工人下班,他打扫厕所、浴室,19点才能完活。午休时,工人阶级休息,他则进牛棚接受训话。加班、挨批,不到20点不准回家,有时得拖到21点。如批斗耽误干活,须加班干完才能回家。他是厂里任何人都可差使的“免费劳力”,随时随地都可进行“帮助”——侮辱批斗。
天不亮逃出自己居住的里弄,晚上街灯齐亮后悄悄回家。我真像见不得“光明”的鬼……怕见到一切熟人、同学、朋友、邻居。[1]
最初,22岁刘文忠认为外面总比监狱好,虽受各种侮辱,任何人都可呼来唤去,到底多一点自由,只要努力干活,总可少受摧残,得一点同情。然而,“我还是个不知深浅的青年”。
一天,打扫女厕的女“牛鬼”生病,张姓女造反队员(破鞋)喝令刘文忠顶班。刘无奈,只得进去打扫。弄干净后,张氏进去如厕,出来后又喝令:“呒没打扫清爽!再去打扫!”刘文忠只得进去,三四张血淋淋月经纸抛散在地,顿时胃翻恶心。明明刚打扫干净,“革命破鞋”恶作剧丢撒月经纸,喝令单身未婚的刘文忠“一张张捡起来”,忍无可忍,刘文忠双目射出仇恨:“下流,你不要逼我!”转身拎起扫把走出女厕。张氏一边拉开上衣弄乱头发,一边呼喊跑向群专队:“非礼啊非礼!反革命要杀人啦!”群专队冲进车间,二话不说捆起刘文忠,押到食堂,召开紧急现场会——批斗“现反凶犯”。
刘文忠反绑双手,两名群专队员各摁一臂,请他“坐喷气式”。破鞋敲响开场锣,哭诉“现反”如何在女厕非礼自己,如何用扫把打她,还威胁要杀她。厂里大多数人都不相信老实厚道的刘文忠会“铤而走险”,加之腿残,怎会去惹这位女煞星?但“革命破鞋”乃区造反派头目姘头,没人敢替“凶犯”争取申辩权。
很快,“凶犯”脖挂十几斤重铁牌,上书“反革命行凶犯”,双膝跪在三角铁上,皮带、棍棒交杂拷打,一边喝问:“为什么用仇恨的眼光看人?!”“‘不要逼我’,什么意思?!”“阶级报复!想杀人放火烧厂房!”
无休止的揭发、无休止的污蔑,我像一个古罗马奴隶跪着,任凭宗教神权与奴隶主们的谩骂毒打。造反派们怀着妒忌邪恶的凶眼,用手拳用木棒戳我胸肌腹肌,恨不得把我身上的肌肉一块块刮割下来。
“革命群众”的揭发值得列述一二——
一“群专”女队员:刘文忠早晚在车间打扫卫生,无人时边打扫边锻炼身体,拉门框引体向上、凳上练腹肌,一边练还一边吃胡萝卜,好开心,根本不像管制分子。
一女工:这个反革命每晚冷水擦身,肌肉练得像运动员。“革命破鞋”立即扒开刘文忠上衣:“看这反革命雪白滚肚!”“一顿要吃八两饭!”“反革命凭什么长肌肉?是不是想复辟?!”
最恶心的一幕上演了:“革命破鞋”从女厕掏来一桶脏水,从刘文忠头上浇淋而下,“搞臭他!搞臭他!”这还没完,“革命破鞋”将那几张刘文忠不肯捡拾的月经纸塞进塑料袋,悬挂他头上。刘文忠浑身发臭,满腔怒火,拒不答话,批斗者持一木板撬嘴捅牙,“凶犯”顿时满口淌血,膝下又是坚硬无比的三角铁,瘫倒在地。革命群众也累了,只得收场,规定刘文忠今后“三不准”:
一、不准练身体,见一次斗一次;
二、不准用仇恨眼光看人;
三、不准一顿饭超出四两。
斗争别人既可表现自己,更可保护自己,无数次批斗中——
那些相识的朋友也上来打我,打得我越凶,越说明“划清界限”。……二年多前曾和睦相处的工友同志们,怎么一下子变得个个对我不相识又怀着深仇大恨了?他们许多人变成了残酷无情的暴徒,开口毒骂我,动不动毒打我……学得比法西斯还法西斯。他们口口声声称自己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群众”,可他们武装起来的是什么思想?什么主义?……我虽然一脚走出关押人体的监狱,但另一脚又踏进了无时无刻不在摧残我精神、摧残我肉体的更大的社会监狱![2]
国人沦为文盲、法盲、流氓。捐出陆机〈平复帖〉及杜牧、范仲淹、黄庭坚书法作品的张伯驹(1898~1982),年近七旬,批斗大会上被拉着绕场爬行。[3]
刘文忠有时哼哼革命歌曲〈宝贝〉,被问唱〈宝贝〉什么意思?是不是想女人了?!又被批斗两个多小时,挨了三四耳光。
一直支撑他的爱情幽火也熄灭了。那位兄弟厂女统计(手微残),托小姐妹退还刘被捕前所赠《普希金诗集》,内夹短信:
好好改造,重新做人。——曾经喜欢过你的人。
来人转告:
你人品教养都使她很喜欢,但她不理解你为什么要走这条自取灭亡的路![4]
家里冰如窟
三哥刘文辉是被镇压的“特反”,老爸“历反”,刘文忠“现反”,一门三“反”,刘家上下三十余口人缩瑟于“无产阶级专政”铁拳之下。
最麻烦的是没地方住。刘父原住日晖四村12号二楼16室(15平米),江南造船厂收回,已近八旬的刘父扫地出门,蜷缩楼梯转弯处(一周)。12号一楼4室24平米(大小两间),大姐一家六口挤16平米大间,父母、他住10平米小间,父子睡地铺。这还是派出所强制大姐夫“收容”岳父、九弟,大姐夫本不愿家里住进两个“反革命”。
刘家乃里弄出名的“关·管·杀”——“关押”(九弟)、“管制”(刘父)、“杀掉”(三哥)。家人面前,刘文忠也抬不起头,全家因他心惊胆颤。大姐一家对他这个“小舅舅”既怜又怕、既疼又防——
大姐一家,由于我与辉哥出事使他们遭遇打击,恐怖阴影笼罩心头,对我既怜悯又惊惧。一个活生生的反革命兄弟天天住在他们家里,尽管我不声不响每天早出晚归,睡铺也是夜摊早收,仍使大姐一家提心吊胆。姐姐、姐夫更害怕他们年幼的孩子会受我这个小舅舅的坏影响而招来危险……他们年幼还弄不清所谓“反革命”、“管制分子”的全部内涵,但几年来由于我与辉哥(三舅舅)的事,使他们遭受别人的歧视、辱骂,同学的欺侮、挨打……所以自我回家与他们同住,他们处处同小舅舅保持距离,露出惊惧疑虑的眼光,不敢越雷池一步亲近我。整个家庭中,没有欢乐,没有笑声,只有担心惧怕,全然成了一间冷气扑面的小牢房,时不时听见老母亲与大姐在暗中长吁短叹嘤嘤泣泣。[5]
刘父早被折磨成一具“活僵尸”。刘母得知幼子释放,从陕西赶回,她知道“管制”难熬,怕幼子再走老三的反抗之路。母亲知道大女婿一家对她很孝顺,她隔在中间,幼子会好过一些。刘文忠回家第一天,老母就警告:
你大姐夫一家是无奈接纳你的,你千万不能再学老三,否则我只有死给你看。
日子一长,九弟在家里处境日益尴尬。同一屋檐,形同陌路。里弄口遇见同学发小,对方像见瘟神迅速避开。岁月似煎,度日如年,想想何必出狱?回来干什么?家里的拖累者、社会的抛弃者,自由还有什么意义?一天,红十字会采血车来厂,他上前捋袖亮臂,群专队员马上责问:“怎么,想打人?”“不,献血。”群专队员一声冷笑:
你的血是“牛血”,有毒,不够献的资格![6]
宁愿“二进宫”
到处是揭发,动辄受监督,连累家庭、祸害亲戚,他觉得真不该出狱,情愿二进宫。天无绝人之路,命运十分眷顾。1971年6月10日,突然将他叫到办公室,两位市里的“公检法”要他揭发第一看守所同监獄犯言论,严正告知:
给你好好考虑一星期,坦白交代就不一定进去,可以继续留在单位接受管制改造。单位为你讲了好话,你这两年半在厂里改造基本还算老实,不然今天就抓你进去,警车就在厂门口等着。
原来,刘文忠在第一看守所私下说过攻击文革的“反动言论”,牢友最近揭发出来。“公检法”给他坦白检举的立功机会,否则立刻搭进去。刘文忠必须“狗咬狗”,卖友才能自保。
下班后,24岁的刘文忠钻入街边小花园,抱头苦思几个钟头:三年管制已熬剩半年,要他揭发的那位难友胡懋峰1970年3月已枪毙,保牢自己不算“叛变”。不过,监牢固为地狱,外面“管制”也等于下油锅,与其在外面活受罪,还不如“二进宫”,进去安耽。第一看守所讲的“反动话”、办的“读书会”不是死罪,最多加判五年。
监牢里面固然是地狱,外面受管制也天天遭油煎……我已经不是初入监的“亚瑟”了,深知坦白仍会从严,还不如抗拒到底“二进宫”。
他决定不揭发,不要“立功赎罪”,既然“东山老虎要吃我,西山猛狮也要吃我”——人民专政天罗地网,与其在外面连累全家,还是识相点,“抓住机会”进去。“进去”好处也不少:一可避开批斗,牢监里都是犯人,脚碰脚,反而平等,灵魂相对清静;二可为全家住宿减负,自己也有合法铺位;三则监狱里有不少高知,可上免费大学。[7]
他拒绝“从宽”,要求“从严”:“还是进去吧!”仅仅要求抓捕在厂里进行,不要让母亲与小外甥看到他“吃铐儿”。终于,他重游旧地,回到老地方——上海第一看守所。由于“二进宫”,且态度恶劣——同室狱犯已揭发,还顽固对抗“无产阶级专政”,1972年8月2日重判七年。先押市监狱,1975年初押往安徽白茅岭劳改农场,蹲足刑期,1978年6月9日获释,仍留白茅岭农场“二劳改”。
刘文忠吃牢饭九年三个月,管制两年五个月,劳改农场“二劳改”九个月,总难期12年5个月。他自嘲在狱中读了大学、硕士、博士、博士后。
主动“二进宫”,戏份甚足,为深挖刘先生当时真实心态,笔者特发专邮咨询刘先生。刘先生答函:
对四类分子特别是反革命管制分子的斗争场面与摧残程度,远远超过监狱大墙内。在外面,除了能吃饱肚子、呼吸到新鲜空气,所遭受的人格侮辱、精神折磨远甚于大墙内,而且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看不到尽头。特别是亲属,他们为我遭受到的压力,大墙内我眼不见为净。可管制生活天天挤在一起,我犹如钉十字架的感受。两年多期间,我除了心痛,流不出一滴眼泪,对遭受的迫害充满仇恨,甚至产生与折磨我的人同归于尽的念头,或像辉哥提倡的去人民广场自焚。此外,当时整个中国就是四类分子的大监狱,无法出逃,没有户口也无法生存,惟有再进监狱。我当时认为进监狱是我精神思想的解放与避免灵魂拷打的“出路”,特别进上海巿第一看守所,与政治犯同牢是我渴求的一个解脱。
读完刘先生的故事,十分佩服他的“不要自由要监狱”,很想残酷地对他说:“你真了不起!如果在外面,一定自杀成功!”
1979年3月15日,刘文忠平反。16日,上海高院派车从安徽白茅岭接回,按满师后月薪36元补发5400元(12年5个月)。半年后,拨给不远处大木桥路江南二村一楼三室,折抵没收同面积日晖四村12号二楼16室,刘家居住之窘得解。
1982年1月6日,刘文辉也艰难平反(经北京最高法院过问),国家赔偿1000元安葬费,说是“要体谅国家困难”、“文革平反已结束,国库没钱了。”[8]
补充资料
1967年6月22日,李立三俄妻李莎押入秦城监狱——
铁门“咣当”一声,关上以后,一种莫名其妙的轻松感萌生在心中,我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心想我再也不会被揪斗,再也听不到红卫兵的喊声了!秦城死一般的寂静比起批斗会上的狂喊尖叫总要强一些。
同日,李立三(1899~1967)受不了被冤“苏修特务”,成功自杀。1980年3月20日李立三追悼会,彭真主持、王震致悼词,胡耀邦、邓小平出席,抚恤金也仅千余元。[9]
1967年6月10日,1926年入党的女特工黄慕兰(1907~ )再入秦城,很庆幸“二进宫”——
狱中的医疗卫生条件依旧,医生护士的态度亦仍很好,为我治好了被打断的肋骨。我觉得软禁在此,倒是使我免受外面“文化大革命”风暴冲击折磨之苦,乃是对我们的一种保护措施。[10]
再补充一点“黑五类”文革生活。天津一位拥有二十间旧房的小业主,“四清”没划上资本家,一直没定成分,但也不是“红五类”——
我们家这么一来,点儿就低了,一下子街道邻居全变样,好赛他们无形中点儿高了。……遭白眼、挨骂,有时吃着饭一块砖头飞进来,玻璃窗粉粉碎。我们也不敢言声。你能说嘛?你能找谁说去?我母亲被同院一个小伙子拿拔火罐把脑袋砸得呼呼流血,我14岁小弟弟叫同街一个小子拿砖头把后脑袋砸破,缝了九针。当时满脸的血呀,看不清鼻子、眼睛、嘴。我们是人呵,哪能受这侮辱,叫他们骑脖子拉屎,连头还不许抬抬。打到派出所,可你家里有问题,你就没理,完事还得叫我们认错。挨打时反驳几句也算错,算挑事儿。……为嘛人都变成这样?为嘛我们受这个?我可说句粗话了——都为了操他妈的“文化大革命”。[11]
1949年后,大陆成了一座大监狱。每逢重大节假日或什么特殊日子,五类分子就集中“学习”。1972年,某公社将五类分子关了两个多月,释放时要家属交21元(伙食费、看守费、灯油费)。一位右派知道家里拿不出钱,打算就在里面熬下去算了。因为,就算出去了,说不定哪天还会再抓进来。公社政法头头问他:
政府放你,为何赖着不走?想把牢底坐穿?
我是想走,实因交不出21块钱。
你对交钱走人有什么看法,谈谈!
交看守费、灯油费,我还没想通。是你们抓我来,又不是我要借这里落脚。
你这家伙真不老实!我们枪毙犯人还要家属交子弹费哩,难道是犯人要我们毙了他?!我们按毛主席教导办事,绝对正确。你听着:“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你反对我们收费,说明我们做对了。[12]
还有一则“里面比外面强”。复旦新闻系学生右派姚福申(1936~),1968年说了一句“我们想要出去,只有等报上出现黑框框”(按:老毛死),“恶攻伟大领袖”反革命罪,判刑七年,安徽白茅岭“两劳”农场召开公判大会,送回上海提篮桥监狱服刑——
农场里每次批斗都要实行体罚并直接动手殴打,似乎不如此不足以显示其革命热忱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干部们很少亲自动手打人,但他们是批斗会的组织者与指挥者。只要管教干部念毛主席语录:“对于反动派,你不打他就不倒。”那班“积极分子”便立即心领神会,拳足交加。“牛鬼蛇神”们每天都要挂着侮辱人的牌子生活和劳动,牌子上的细铁丝嵌在头颈里入肉三分,每个被批斗的人谁不曾有过求死之心?我想每一位被批斗过的人都可以为我上面的陈述作证。然而文革期间上海提篮桥监狱比起劳教农场要相对文明些。虽然也经常开批斗会,但动手动脚的现象较少,也远远没有农场里那样凶狠,更没有喊“你不打他就不倒”在一旁指挥的干部。……我很庆幸自己被判了刑,脱离了地狱般的劳教农场,我以自己亲身经验证实了“劳教不如劳改”。
……
因为劳改农场属于监狱一部分,经费开支纳入国家预算和决算,劳改犯生活有最基本的保障。而劳教农场则属于自负盈亏的地方国营农场体制,国家一般不再给予补贴。其高压强制的管理手段和毫无希望的终身圈禁生活,无法激起就业者(按:劳教者)的积极性,所以在当时情况下,无论生活条件还是劳动强度都远比劳改生活艰苦。[13]
在劳改农场躲过红卫兵暴力的劳教犯杜高(1930~ ):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我们幸运地从“专政对象”变成了“保护对象”……红卫兵几次要来冲击这个右派劳教队,都被公安局挡回去了,说有命令“不准冲击监狱和专政单位!”……如果真的让红卫兵冲进来,那我们只有等着被他们打死。我们被封锁起来,与世隔绝,反而得救了。[14]
附记:
1993年10月29日《新民晚报》:一支中外探险队在西部沙漠发现绝世老人锺剑锋。1969年,锺剑锋无法忍受“成分”,逃进沙漠24年,不知世事沧桑。[15]
[1] 刘文忠:《风雨人生路》,崇适文化出版公司(澳门)2005年,页180。
[2] 刘文忠:《反文革第一人及其同案犯》,崇适文化出版公司(澳门)2008年,页237~243。
[3] 张传彩:〈父亲张伯驹的人生沉浮〉,《各界》(西安)2015年第12期(上半月),页23。
[4] 刘文忠:《风雨人生路》,崇适文化出版公司(澳门)2005年,页206。
[5] 刘文忠:《风雨人生路》,崇适文化出版公司(澳门)2005年,页207。
[6] 刘文忠:《反文革第一人及其同案犯》,崇适文化出版公司(澳门)2008年,页269、264。
[7] 刘文忠:《反文革第一人及其同案犯》,崇适文化出版公司(澳门)2008年,页267~270。
[8] 刘文忠:《反文革第一人及其同案犯》,崇适文化出版公司(澳门)2008年,页390。
政府偿额,刘文忠先生2015年6月17日确认。
[9] 李莎:《我的中国缘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北京)2009年,页314、339~340。
[10] 《黄慕兰自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北京)2012年,页360~361。
[11] 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年,页244~246。
[12] 李普:《李普自选集》第三册,柯捷出版社(纽约)2010年,页176~177。
[13] 姚福申:〈世事茫茫难自料〉,张大芝等主编:《阴晴雨雪旦复旦》,香港华泰出版社2008年,页305、309。
[14] 杜高:《又见昨天》,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4年,页169。
[15] 景凯旋:〈一个革命话语的产生〉,《随笔》(广州)2009年第5期。参见向继东主编:《遮蔽与记忆》,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页151。
初稿:2008-1-24~26;补充:2015-10
原载:《往事微痕》(北京)第117期(2014-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