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89)
——赤色帝国覆亡之谜(42)
埃莱娜•唐科斯在其《分崩离析的帝国》(1978年出版)中指出苏联在政治上有歧视少数民族的地方,并以苏共党员中民族成分的比例为依据说明问题。为了进一步说明这方面的问题,唐科斯用事实和数据指出:
党的组成更平衡一些是否就意味着较平等地参与政治决策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考察一下中央和地方党的权力机构的组成情况。
作决策的中央机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书记处)的组成很不平衡,非俄罗斯干部的比例很小。
在中央委员会,82%的成员属于占全国人口73%的斯拉夫民族集团。这种差距在党的两个最高机构中更加明显。在政治局,16名委员中只有两名属于非俄罗斯民族,6名候补委员中有3名属于非俄罗斯族。至于书记处则根本没有非俄罗斯民族的成员。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和10位书记都是斯拉夫人,他们都是中央集权政策的代表。
因此,必须考察一下政治局中少数民族成员的情况。他们为什么在苏共党内占有引人注目的地位呢?他们在政治局中是作为民族干部的代表,还是作为中央的地方政策的代表?他们的生平清楚地说明了他们的这种地位。在政治局委员中,有一位名叫库纳耶夫的哈萨克人,还有一位名叫谢尔比茨基的乌克兰人。
库纳耶夫在1939年27岁时才入党,自1964年以来担任哈萨克共产党第一书记,是斯大林时期培养起来的哈萨克政治高层的真正代表。苏联的大清洗毁灭了所有在十月革命后涌现出的民族优秀分子。大清洗结束后,各民族出现了一批先是从事技术工作、接着从事政治工作的干部,库纳耶夫就是其中之一。在斯大林时代,他在国家机关工作,六十年代初才转到党的机构中任职。1971年作为政治局委员而跃居于特殊地位。
谢尔比茨基属于另一种情况。苏共二十五大时,他年已58岁,此后一直在党的机构中任职。他年青时在共青团工作,后来又在乌克兰各级党组织中担任领导职务。这种双重的经历使他得以完全控制了乌克兰各级权力机构。在乌克兰他似乎是勃列日涅夫的代表,负责保证勃列日涅夫在乌克兰的影响。他似乎远不如他的哈萨克同事代表民族利益。那么,二十五大晋升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的阿塞拜疆人阿利耶夫又如何呢?
阿利耶夫是阿塞拜疆共产党第一书记,但他首先是安全部门的一位人物。1941年他18岁就进入了内务人民委员会,并一直持续到1969年任阿塞拜疆共产党第一书记时为止。他过去一直在中央和地方安全部门中任职,最后在1967年至1969年担任阿塞拜疆克格勃主席。除了这颗新升的明星外,在政治局候补委员中还有另外两位地方代表:白俄罗斯人马谢罗夫和乌兹别克人拉希多夫。马谢罗夫从1944年开始,先后在白俄罗斯共青团和CP机关工作,1966年苏共二十三大时进入政治局。拉希多夫是乌兹别克CP第一书记,曾长期在乌兹别克党和国家机关任职,自1939年22岁入党以来,一直官运亨通。但1961年二十二大进入政治局后却久不升迁,成了任期最长的候补委员,而且是继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和苏斯洛夫之后政治局中资格最老的人物之一。
通过对党的最高权力机构的组成状况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看法:
——首先,这一级机构根本不能反映苏联国家的情况,甚至也不能反映苏共的民族组成情况。在这一级机构中,俄罗斯人、其次是斯拉夫人占绝对优势。书记处的组成情况也是证明。
——有些民族在政治局中比其他民族占有更多的席位。例如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在政治局中的席位就比中亚和各穆斯林共和国多。相反,党员人数在全党占的比例超过其人口在全国占的比例的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在政治局中却没有席位。波罗的海各共和国在政治局中也没有席位。这表明,用“党员在全党占的比例”这一标准来衡量某个民族是否真正参与决策机构是靠不住的。
——值得注意的是,七十年代初人口的流动对领导机构的组成没有产生丝毫影响。这些机构的组成几乎是一成不变的,新的兼职的政治局成员都是俄罗斯人(罗曼诺夫兼任列宁格勒市委第一书记,乌斯季诺夫元帅兼任国防部长)。
——值得注意的最后一点看法是关于各民族参与政治生活的主要领域、即“高干阶层”的情况。在苏共中央制定的一份名单上,列出了属于高干阶层的三万到四万个职位。分配这些职位的是苏共中央中专门分管干部的机构。而在党的执行机构中央书记处里没有其他民族的领导人,这就意味着其他民族不能参与挑选负责苏联重要部门的干部的重大决定。在政体的另一极即共和国共产党书记处内,各民族在挑选干部问题上能起多大作用也是值得怀疑的。
唐科斯在用许多数据和事例说明苏共组织存在民族歧视现象后,最后指出:
最近的历史表明,在长期实行实用主义的不连贯政策后,中央政权制订了明确而又连贯的战略:严格控制非俄罗斯共和国各级政治干部、行政干部和技术干部的选择。控制程序的统一和政体的极端严密性似乎是当前全国一体化政策的特点。
苏共高层为什么要严密控制少数民族的党组织呢?唐科斯在《苏共是全民党吗?》一节的开头就点明了这一问题的症结所在:
在维护全国平衡方面,苏共所起的作用比国家机器的作用更为暧昧。列宁总是把他的党设想为一个阶级的、即无产阶级的,因而是超脱民族利益和民族分歧的特别组织。1917年以前,他拒绝了建立一个能体现全俄各民族特殊性的工人阶级组织的意见。但是,十月革命以后,随着联盟国家的诞生,同时重建了政党。在每个加盟共和国内,也成立了共和国CP。于是,隔阂便从此开始产生了。
这些共和国的共产党实际上是苏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本身并没有高于该地区各级党组织的权利。这些党组织的党员都是苏共的正式党员,共和国党组织似乎只是一种并没有任何特定内容的特殊的称号。这些党组织的作用只是要通过它们的存在表明苏联的联邦制,地方上的党员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没有任何独立性。从其宗旨来说,共产党是一个团结统一的组织,而不是多样化的组织。
不要多样化,更不要多元化;要团结统一,不要分离分散。为此,苏共当然要严密地控制全社会,那怕是自己的党组织。
唐科斯在议论了苏联的政治问题后,又议论了苏联的文化问题:
二十年代的苏联,其特征仍是革命空想主义,这是不应忘记的一个事实。尽管这种空想遭到打击(强迫各民族合并就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但布尔什维克仍坚持建立平等社会的幻想。从政治上开始实施的民族平等也开始向文化方面发展。所以,二十年代的国家计划强调要发展“所有”民族的文化,首先是发展各民族的语言。
为贯彻本地化政策所需要的干部应当是民族干部,因为他们熟悉本民族的文化。这一政策还有一些离奇可笑之处。有时会碰到这种情况,即在二十年代建立苏联时命名的某个民族实际上没有自己的语言,或者已经习惯使用别的民族的语言。然而,苏维埃政权却硬性规定,作为行政单位的每一个民族都必须拥有并使用一种自己的语言。例如,在已同时使用几种语言的白俄罗斯共和国,当局规定了一种正式的白俄罗斯语言,即便大多数居民都必须到学校上学才能学会这种语言。更离奇的是,政府还组织一些语言学家把只有几百人的小部落才说的一些地方方言变成书面的文字语言。
尽管很穷,苏维埃国家却把大量的力量和费用用于这种文化发展,有时甚至去无中生有地生造文化。当时本应该尽快地以最简便的方式进行扫盲,而他们却用大量的时间和资金去印刷有时只有几百个读者的课本,去培训教育这些未来的读者的教师。但是,这条“路线”是既定的和不可更改的。每个民族都有权使用“它自己的”文化,因而也就有权使用“它自己的”语言文字。不过,注定要实行这条路线的平等主义也是有其政治目的的。
承认每一个民族有平等的文化权力,这可以分化靠特殊的连带关系联系在一起的一些大部族。高加索和中亚的穆斯林民族就是例子。它们从本世纪初就一直试图以共同的语言为基础联合在一起。现在,在已确定的边界内,每个民族必须使用本族的语言。这样,文化平等主义就可以打破那些泛土耳其主义或泛穆斯林主义的梦想。之所以要打破这些梦想,是因为这些梦想如果一旦在苏维埃加盟共和国内得以实现,那就会形成一些民族共同体和具有危险压力的文化来反对政治上的集中制。
发展民族文化也带来了一些严重的不利因素。那种单纯的民族教育只能加强民族意识,与最终的统一目标背道而驰。所以,“民族文化”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概念,而是斯大林全面确定其含义的具有双重内容的概念。从“形式”上来说,特别是从语言上来说,这些文化是民族的,但从其“内容”上来说又是社会主义的。各民族通过语言代代相传的东西不是各民族本身的遗产,而是一种新的、各民族所共有的遗产,即社会主义及其价值和目标。只有这样的民族文化才能完成其使命。它能平息民族感情并使之得到满足,同时也能使其逐渐向一种新的、共同的思想意识转变。对斯大林发明的这种文化和解,列宁并没有表示反对,因为这种和解把目前的任务(满足民族情感和割断泛民族主义的连带关系)和长远的目标(逐步归于一种共同的带政治性的文化)结合起来了。在这中间,教育代替了强迫。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听取了列宁提出的警告。
然而,如果不实行控制政策,这种文化平等主义是行不通的。从原则上说,民族干部和民族文化必须满足民族的要求并逐步地减少这些要求。但这些东西也会导致截然相反的后果,导致出现狂热的民族感情。为了把平等限制在对各民族进行教育的范围内,苏维埃政权从二十年代开始就釆取了许多控制措施来作为这种平等权的平衡手段。这些控制措施有:国际主义的党对代表民族利益的共和国的控制;加盟共和国对州和区的控制;加强中央与地方的联系,从经济上加以控制;特别是还有文化上的控制。这最后一种控制就是: 赋予专门领导文化活动的CP组织以决定之权;用中央确定的共同的社会准则来取代支配每个特殊社会单位的社会准则和习俗。
二十年代苏联实行的自由主义加控制的民族政策是要造就一个新的大家庭,造就一个证明阶级友爱可以战胜民族意识的无产阶级的苏维埃国家。
关于苏联在文化方面对少数民族的控制,笔者在《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46)》一文中,就苏联官方以行政命令方式在少数民族地区强行推广俄语已有阐述。这里说一个具体事例:
1978年4月14日,在格吉亚首都第比利斯的大街上发生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游行。约有五千多名大学师生在校园聚会后浩浩荡荡向格鲁吉亚政府大厦走去。他们的目的是抗议格鲁吉亚共和国的新宪法取消了格鲁吉亚语的国语地位。这种行为大大激怒了民众。年青人的情绪尤为激动。《纽约时报》当时报道: “由于一位主管安全的将军的出面,才避免了流血事件的发生。当他意识到形势的严峻后,就建议在语言问题上作出让步以求大全”。第二天,这条不得人心的条款就得到了修正。很快,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共和国的宪法草案中也作出类似的改动。
三年后的同一天,即1981年4月14日,持续了几个月的格鲁吉亚学生骚乱达到了高峰。许多年轻人试图在格鲁吉亚的旧都姆茨赫塔集会,为他们民族进行祈祷。当地克格勃和内务部队得知这一计划后,封锁了通向该城市的道路,甚至不许人通行,禁止火车停靠该市火车站。尽管如此,还是大约有三百名示威者成功地到达了姆茨赫塔古老的斯维提特斯克科维里教堂。他们聆听完古老的格鲁吉亚赞美诗的录音后,便跪下来共同吟诵主祷文,为格鲁吉亚祈祷。与此同时,在第比利斯,一队民兵和克格勃人员包围了这个城市的大教堂,不允许任何人进入。随后,一百多名学生联名给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谢瓦尔德纳泽写了一封信,抗议当局的这种行径。
卷入格鲁吉亚骚动的不仅只有学生。在1976年召开的格鲁吉亚作家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作家贾帕里泽严厉地批评了格鲁吉亚的教育部长,指出今后诸如历史和地理课程也改用俄语教学的话,那么所有的教科书都是俄文版,学术论文也得释成俄文了。贾帕里泽的发言获得了长达15分钟的掌声。与会者拒绝让部长作出回答。谢瓦尔德纳泽发言力图减轻人们对俄罗斯化的不满,但他的话被愤怒的吼声所打断。
这些事件表明,语言、文化、宗教和民族性与苏联少数民族人们的思想有着明显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任何企业割裂这种联系的企图都不可能得逞。
美国斯坦福大学高级研究员邓洛普对此提出这样的见解:
也许有人会问,苏联政府为什么要自找麻烦,企图去使这么一个古老而且民族意识这么强的民族比如格鲁吉亚俄罗斯化呢?这个解释要追溯到1917年以来苏联运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从一开始,苏联领导人就把苏维埃国家看成是一个统一体,其根本方针是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不允许有民族差异和民族理想存在。尽管在策略上存在着许多曲折,但是从实行新经济政策时起,苏联领导人从未放弃最短命的“各民族”的概念。赫鲁晓夫主持召开的苏共二十二大会议上,甚至提出了激进的口号“融合”——暗示苏维埃各族人民的生物均化。赫鲁晓夫后继者的态度较为谨慎,使用了较为温和的措词如(各民族人民的)大团结,等等。尽管策略上有此波动,但勃列日涅夫政府对各民族的兴衰亦未真正关心过。埃莱娜.唐科斯曾说,苏联领导人中充分意识到各民族的持久和倔强特性的是斯大林,他的工具之一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斯大林的高压统治(必要时还包括对整个民族的灭绝),与赫鲁晓夫提出各民族未来“融合”的天真信念是相辅相成的。
如果有人接受这个前提,即民族是昙花一现的实体,那就是说他们的交流工具——语言也一样不会长久。植根于一种包容关于人和社会全部真谛的意识形态之中的统一国家,需要一种惟一的混合语言来保证思想控制和内部安全,以普遍地提高行政效率。通过一个国家的共同语言,公民们就会被惟一的意识形态马列主义所塑造和改造。有评论家指出,俄语由于被利用来达到这么一个目的而使语言本身也付出了可观的代价。一评论者说:“俄文属于俄罗斯民族,两者一脉相承,但它也是 ′列宁的语言’ 。” 立陶宛诗人温克洛瓦则透彻地阐述了这个问题:“俄文已日益不被看作是俄文了,而是‘苏联的’,并且很多俄罗斯人也这样认为。事实上,俄语与官方意识形态关系甚为密切,其程度远远超过它与苏联其他非俄罗斯语言的关系”。作为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语言,俄语经受了“第二符号体系的反作用及破坏性的影响。”
综上所述人们可以知道,语言在苏联既是人们交流的工具,又是政府控制民众的工具。
说一说列宁在民族问题上的失误。
列宁把民族问题的最终解决放在了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上,认为无产阶级的苏维埃政权是超民族的、完全摆脱了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政权,因而是完全能够全面地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政权。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列宁把迅速建立统一的各民族布尔什维克政权看作是各民族走向团结和融合的必然道路。
这只是一种想当然的美好愿景。历史进程已证明,即使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也不能完全彻底地解决民族问题。一方面是因为民族问题是一个比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更长期、更复杂的问题,而苏共建立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又始终处于民族矛盾的斗争当中;另一方面苏联各民族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不同,因而民族发展的客观条件也差距甚大,根本无法达到用统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水平要求他们。由于上述原因,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各民族的“天堂”,苏维埃政权就采取各种手段,甚至是损害各民族的利益的手段来达到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实现民族“融合”的目的。典型的事例就是俄罗斯布尔什维克党对其他民族布尔什维克党的强制态度,在格鲁吉亚问题上充分暴露出来。此外,苏俄红军1920年对波兰的进军,就是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号召下,掩盖了一种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行动。
列宁的民族理论对后来苏联的民族政策产生了重大的负面影响,主要在于: 一是始终是以建立统一的集权制的大国为目标,为引起资本主义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而极力“输出革命”。二是在建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以后,把各民族改造成统一的“苏维埃民族”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必然结果,因而采取人为的强制措施加以促进。
十月革命前,列宁本来是反对联邦制的。但是当俄国布尔什维克党面临其他民族组建自己的政党并快步走向独立时,“俄罗斯母亲”情结同样对布尔什维克党起了作用。如果当时布尔什维克党真的能够展示出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20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也许会在一个全新的历史层次上进行。可事实却不是这样。所以,必须承认列宁领导的俄国布尔什维主义运动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层次上具有历史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对于苏共来说是与生俱来因而是不可克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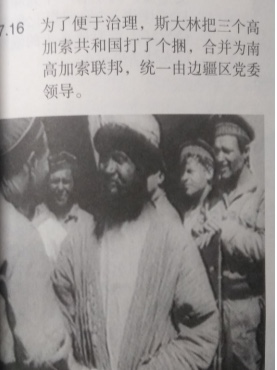
(未完待续)
荀路 2022年9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