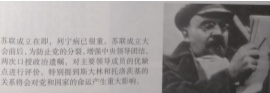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94)
赤色帝国覆亡之谜(48)
格鲁吉亚事件还没有完结。
列宁在1923年1月24日的《真理报》上没有看到自己写的关于工农检查院的文章后,要求秘书福季耶娃向捷尔任斯基或斯大林索要格鲁吉亚事件调查委员会的材料。他说,格鲁吉亚事件使他“感到很难受”。
1月25日,列宁问福季耶娃是否从捷尔任斯基那里得到了材料。到27日还没有收到材料,于是福季耶娃就给斯大林发去了一封信。斯大林29日回答说,没有政治局的决定他不能提供材料。福季耶娃证实,列宁当天了解到这个情况后说,他“要为取得材料而斗争”。
2月1日,政治局批准给了列宁所需要的材料,列宁马上委托他的秘书班子着手研究,要他们提出一个报告供他在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用。列宁作了如下指示: “一、为什么指控格鲁吉亚CP原中央委员会犯倾向主义。二、给它什么罪名,如破坏党的纪律。三、为什么指控外高加索边区党委压制格鲁吉亚CP中央委员会。四、肉体上的压制办法(‘肉刑’)。五、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不在时和在时中央的路线。六、委员会的态度。它是否只审查对格鲁吉亚CP中央的指控,还是也审查对外高加索边区党委的指控?它是否审查了肉刑事件?七、现状(选举运动、孟什维克派、压制、民族纠纷)。” 这实际上就是一个详细的调查提纲。这里,列宁特别提出了列宁在时和列宁不在时俄共中央的路线问题。
2月3日,列宁得知政治局已批准捷尔任斯基委员会的结论,他指示秘书在三星期内写出调查报告。此后他多次询问工作进展情况,由于估计到很可能还需要到格鲁吉亚去进行补充调查,他指示务必抓紧进行,在党的十二大以前作出结论。在进一步了解情况之后,2月14日,列宁指示福尔耶娃向俄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索尔茨示意,他(列宁)“站在被欺侮者一边。让每个被欺侮者都知道,他站在他们一边。三点: 一、不能打架。二、需要让步。三、不能把大国同小国相提并论。斯大林是否知道?为什么他没有反应?‘倾向分子’和‘沙文主义和孟什维克主义倾向’这一称呼证明,这种倾向本身就在大国主义者身上。” 这表明列宁对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不满意。
3月3日,列宁收到了福季耶娃收集到的材料的报告和一件附件。附件中说,卡巴希泽(他曾被奥尔忠尼启则打过一记耳光)的声明“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李可夫的一封信。信中说冲突是私人性质的。附件中还有一些文件,其中报告了中央委员会在这个问题上的意向,还有福季耶娃与季诺维也夫交谈的记录。一些中央委员对情况作了如下评论:
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信口雌黄,可是斯大林不但不制止他,反而支持他。谢尔戈有百分之二十的过错。
如果不是有中央委员会的威信,那么马哈拉泽就会在党内(格共中央)拥有多数。(与斯大林的第三次)妥协正在酝酿之中。不同意奥尔忠尼启则路线的有: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布哈林、加米涅夫(态度不坚定)。妥协办法是,让一部分倾向分子回来,季诺维也夫和奥尔忠尼启则必须留下来,斯大林可以被派往土库曼斯坦一年。
看过这些材料之后,列宁3月5日向托洛茨基发去如下内容的一封信:
绝密。亲收。
尊敬的托洛茨基同志:
我请您务必在党中央为格鲁吉亚事件进行辩护。此事现在正由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进行‘调查’,而我不能指望他们会不偏不倚。甚至会完全相反。如果您由于某种原因不同意,那就请把全部案卷退还给我。我将认为这是您表示不同意。
致最崇高的、同志的敬礼!
列宁
但托洛茨基并没有替列宁为格鲁吉亚事件辩护。托洛茨基推说他因生病,不能承担列宁的委托。托洛茨基同斯大林个人之间存在着龃龉,但他没有利用这一机会,这使后来研究苏联历史的学者大惑不解。
3月6日,列宁给姆季瓦尼、马哈拉泽等人去信对他们表示支持。列宁在信中说: “我全心关注着你们的事。对奥尔忠尼启则的粗暴、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的纵容姑息感到愤慨。我正为你们准备信件和发言稿。”
这是列宁所写的最后一封信,这一天列宁病情恶化,从此未能恢复健康继续工作,因此他对格鲁吉亚事件的直接干预也就到此为止。
但是事情并没有就此了结。斯大林很快从加米涅夫那儿得知了列宁给姆季瓦尼信中的内容,3月7日他给奥尔忠尼启则写信说:
亲爱的谢尔戈!我从加米涅夫那儿得知,伊里奇给马哈拉泽等同志写了一封短信,表示他同情倾向分子并责骂了你、捷尔任斯基同志和我。看来目的是要为倾向分子而压制格鲁吉亚CP代表大会的意志。不用说,倾向分子收到这封信后会尽量利用它来反对外高加索区委,特别是反对你和米高扬同志。我建议:一、外高加索区委不要给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多数人的意志施加任何压力,不管怎么样,让这种意志最后得以充分表现;二、争取妥协,但这种妥协应以在其贯彻时不必对格鲁吉亚的多数负责干部进行压服为限,即必须是自然而然的自愿的妥协。
俄共中央通过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获悉列宁给姆季瓦尼等人的信件后,决定向格鲁吉亚派出新的委员会重新调查。委员会由加米涅夫和古比雪夫组成,他们当即动身前往第比利斯。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消除分歧和争端,恢复格鲁吉亚党内的统一。因此,他们采取的主要办法是进行内部协商以达成协议。3月14日,以奥尔忠尼启则等人为一方,姆季瓦尼等人为另一方,在加米涅夫和古比雪夫参加下签署了《关于格鲁吉亚共产党(布)当前首要任务的提纲》。提纲肯定了外高加索联邦的必要性,同时又指出在实践上联邦形式应当灵活,不应破坏各联邦共和国内无需联合的那些经济和管理部门的独立性,强调不要使联合机构变成推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工具,应进行系统的斗争以反对这样做的任何企图。此外,还对格鲁吉亚党政领导成员的人选达成了协议。
但是委员会的工作过于仓促,因为委员会到达后不久就传来列宁病重的消息,所以他们急于返回莫斯科。在签订协议后的14日当晚,加米涅夫等人即离去。
托洛茨基在民族问题上的观点同列宁相近。3月7日列宁的几位秘书访问了托洛茨基,看来就是这一天福季耶娃把列宁的《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一文交给了托洛茨基。当时托洛茨基抄了一份供以后写文章之用,这时大概只有他和加米涅夫两人看到列宁的这篇文章。应该说,他们是最清楚列宁在民族问题上的想法的政治局委员。3月20日,托洛茨基在《真理报》上发表了《关于党的一些想法》一文的第二部分《民族问题和青年党员的教育》。他认为,小民族中间的民族主义是“防御性的民族主义”。 “小民族中共产党人的民族主义倾向乃是在一般国家机关,甚至在执政党的一些角落里的尚未完全消除的大国沙文主义罪过的症状”。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应当“具有耐心宣传的性质,不是无视民族的要求,而是关怀地满足这些要求”。他还指出,“在小民族或最落后的民族里,最革命的分子,其中包括无产阶级分子往往对民族问题不给予足够的重视”;而在我们这里有些老同志也对民族问题置之不理,仅仅把它看作是一种“暂时的 ‘让步’ ”。
3月26日,政治局会议通过决议,将姆季瓦尼等格鲁吉亚领导人说成是“热衷于在党内制造紧张关系,从而造成格鲁吉亚共产党内的派别斗争气氛和难以克服的有碍和平的障碍”,建议将他们调任别的工作。托洛茨基在会上提出三条建议: 一、将奥尔忠尼启则从外高加索边区召回;二、认为外高加索联邦是一种歪曲苏维埃联邦思想的过度集中制;三、认为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处于少数的同志并不是在民族问题上偏离党的路线的一种倾向,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具有防卫性质——是为了抵制奥尔忠尼启则的错误政策。但是会议以六比一否决了托洛茨基的建议。加米涅夫的“非原则性斗争”观点也没有得到政治局明显的支持。3月31日,中央全会对他提出并经政治局同意的决议案作了重大修改,同时决定召回姆季瓦尼。这些事实表明,即使托洛茨基站出来替列宁为格鲁吉亚事件进行辩护,也已经无济于事了。
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是在1923年4月17日开幕的。开幕的前一天福季耶娃把列宁的《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的信件送交政治局。18日,大会主席团作出《关于列宁同志有关民族问题,包括格鲁吉亚问题的信札》的决定,决定在代表团领导人会议上宣读列宁的这些信札以及与之有关的全部材料。然后由主席团委员向代表大会各代表团分别宣读这些材料。与此同时,把中央全会关于格鲁吉亚问题的决定通知代表团领导人和各代表团。上述信札和材料不在民族问题委员会上宣读。根据这一决定,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信没有向全体代表传达,甚至也不向民族问题委员会传达!而代表高加索参加“代表团领导人会议”的是斯大林、奥尔忠尼启则、基洛夫以及后补的卢卡申,没有一个“倾向分子”!因此,在大会上姆季瓦尼等人一再要求公布这封信,都遭到了拒绝。
这样,在俄共(布)党的代表大会上开创了一个先例: 只有享有特权的党内高层才能了解列宁的文件,而有关信息不让普通党员知道。而且,就连党的高层人物也没有讨论列宁的建议。
民族问题在这次大会上占相当分量,不仅在进入民族问题议程时有激烈的争论,而且在讨论中央工作总结报告时就有不少人谈到民族问题特别是格鲁吉亚问题。但是从报告到讨论一直到决议,贯彻始终的主导思想是反对所谓的地方民族主义。虽然口头上也说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是主要危险,但没有具体的针对性,而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则是具体的,实际上成了头等任务。格鲁吉亚的“被欺侮者”没有得到保护,而是处于挨批判、受指责的地位。在大会上发言的斯大林、奥尔忠尼启则等人对外高加索区委的错误不置一词,至于列宁对他们本人的批评更是讳莫如深。
由此可见,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盘根错节,根深蒂固,即使列宁亲自出面干预仍不能解决问题,这一情况不能不影响到苏联以后几十年的民族政策,给苏联最终解体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唐科斯在《分崩离析的帝国》一书中对斯大林在民族政策上恢复“老大哥”的权利,建立新的帝制阐述如下:
在苏联,(卫国)战争在精神上带来的变化究竟有多大以及斯大林从中吸取了多少教训,这从战争胜利以后的局势中便可以看出来。在这个极端民族主义的国家,斯大林完全拖弃了战前的平等主义,他把民族情感等级化,把俄罗斯民族及其传统和文化放在首位。战争给他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借口。
德国军队刚从那些表现出民族自治倾向的领土上撤走,斯大林就大张挞伐。1943年10月到1944年6月期间,有六个小民族被指控为叛逆,被赶出他们的故乡并被放逐到了中亚或西伯利亚。这样,他们就与1941年被流放的日耳曼人会合在一起了。至少有一百万人(有407690车臣人,92074印古什人,75737卡拉恰伊人,42666巴尔卡尔人,134271卡尔梅克人,20万以上的克里米亚鞑靼人,38万伏尔加日耳曼人)被指控为犯了罪,并且所属整个民族都被指控为犯了罪。1946年,按照放逐的做法,将取消车臣族、印古什族和鞑靼族的领土。这样,在十年中,这些部族没有任何合法的存在权利。
斯大林这样打击整个民族而不是打击某些个人,无疑是要杀一儆百。但他的主要意图是要在苏维埃的生活中把民族分成不同的等级。有不好的民族,也有模范的民族。在所有的各民族中,最模范的是俄罗斯民族。斯大林在1945年5月24日庆祝战争胜利时的讲话含义是清楚的。当时他向俄罗斯人民致敬,而没有向苏联人民致敬。他说俄罗斯人民是“苏联的起领导作用的人民”,“因为他们在这次战争中,证明自己真不愧为公认的我们苏联一切民族中的领导力量”。他们突出的特点是“具有明确的智慧,坚毅的性格和耐心”。同在战争中表现出软弱性的其他民族(斯大林说,“如果我真想实行惩罚的话,我就要放逐整个乌克兰民族”)相比,俄罗斯族已表明它应该赢得的地位: 第一位。正式维持着的平等主义就这样消失了,代之而来的是以一个“老大哥”为核心而组成的民族共同体。这个“老大哥”就是作为全体的负责者和向导的俄罗斯民族。
从现在可以清楚地看过去。在1917年进行了革命的俄罗斯之所以能发动革命,是因为它的整个过去都注定它要充当这个先驱者的角色。从9世纪的基辅罗斯时代起,它就与加洛林王朝一样发达,它对西欧的影响是不容抹杀的。在19世纪,它就已经不是一个反动的堡垒(这里,斯大林改变了恩格斯的观点),而是在向革命前进了。从此,对于被征服的民族来说,过去先后被说成是“绝对的坏事”、“相对的坏事”、“最小的坏事”的俄罗斯统治就成了“绝对的好事”了。阿塞拜疆CP领导人巴吉罗夫就明确地表达过这种观点。他在1952年这样写道: “绝不应当低估沙皇殖民政策的反动性,但我们也不应当忘记……被俄罗斯兼并,这对于那些被兼并的民族来说是唯一的出路,而且,这种被兼并对它们未来的命运只有好的影响。”
自从(被俄罗斯)征服成了一件绝对的好事之后,以往与征服作过斗争的那些人就再也没有光荣的称号了。所有民族英雄、抵抗殖民化的首领都被打入了历史的地狱。尽管民族中坚分子对他们的英雄人物仍怀有忠诚的热爱,但他们的行为都被斥为封建愚昧主义的行为。至于各非俄罗斯民族的历史,则只能保留那些使它们与俄罗斯接近的东西。它们既然已被剥夺了自己的历史,也就只能从俄罗斯民族的身上来认识自己的过去,就像巴吉罗夫所说的那样: “联合、巩固和引导我国各民族的领导力量是我们的老大哥,伟大的俄罗斯民族……由于它的美德,它值得其他所有民族信任、尊敬和热爱。”
1918年,由于俄罗斯族在人数上的优势,由于它的中心地位,由于它比周围各民族先进,苏维埃联盟内出现了事实上的不平等。到了战后,人们用古代史和近代史来为这种不平等辩护,并把它树为民族关系的基本准则。这个联盟就像过去的帝国一样,以一个主导民族为中心集合了众多的民族。
在使俄罗斯族的突出作用合法化的同时,又在文化上实行同化。各民族文化都遭到了批判,因为它们分裂人们的思想意识而不是使它们互相接近,同时也因为斯大林认为它们是反动历史的象征。一切民族文化的不朽珍品——史诗、民间诗歌等——都遭到了无情的攻击并被禁止。民族文学艺术都被指控为传播过时的语言和观念的东西。民族语言必须用来描写社会主义现实的世界——拖拉机和挤奶工的世界,任何时候也不能描写个别特殊的传统。强迫各民族改变文化,就是要无休止地移植和重复某个单一的文化模式,而其他民族形式只能体现在词汇上。
当各民族文化被这样推向极端、仅剩下一堆词汇的时候,俄罗斯文化却蓬勃发展起来并取代了那些受到批判的文化。与一些民族史诗的命运相反,俄罗斯文化名著却被捧为全人类的文化遗产。非俄罗斯民族必须接受这份遗产,并以此作为指导它们将来创作的经典。
1952年,苏联各民族不得不转向俄罗斯文化,因为除此之外已没有别的选择。对少数民族漠不关心的沙皇帝国从未试图对它的臣民进行如此系统的俄罗斯化,也从来没有明确的和涉及到其全部疆土的帝国理论。而1952年的苏维埃联盟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帝国。在这个帝国,如同以往的殖民主义帝国一样,俄罗斯民族的主导地位被说成是理所当然的,理由是这个民族比其他民族文明并能领导其他民族走向进步。“各民族的大监狱”不复存在了。但是,联盟却是一个完全不平等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内,“老大哥”统治着、并试图同化其他民族。对于在战争年代里突然兴起的民族运动,斯大林的回答是强加给各民族一个粗暴的解决办法: 迅速俄罗斯化。
从1930年代起,苏联领导人和史学界不仅不批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反而歪曲沙皇政府征服少数民族的历史,继承沙俄帝国的意识。1934年7月,斯大林在评论恩格斯的《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一文时为沙俄帝国对外侵略扩张政策辩护,认为恩格斯当时写作时“过于兴奋而忘记了最基本的他非常清楚的事实”,“片面地夸大了沙皇政府对外政策的扩张性”。1952年10月,苏共十九大总结报告公然认为,二战中苏联用武力收复西乌克兰、西白俄罗斯,强迫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摩尔多瓦归并苏联,收复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这样的边界才符合苏联历史发展的实际。这就是说,凡是历史上沙俄征服过的领土均应归入苏联版图。在斯大林观点的影响下,苏联史学界认为,18世纪末沙俄征服白俄罗斯、立陶宛、拉脱维亚等民族,是把这些民族从波兰的民族和宗教压迫下解放出来,促进了他们的经济和文化发展,“是有很大历史进步意义的,加速了同俄罗斯的接近”。19世纪沙俄征服中亚各民族带来了“进步和文明”;1801年格鲁吉亚等民族归属于俄国,是使他们“从伊朗和土耳其的奴役下获得解放”。1954年12月1日《真理报》发表纪念乌克兰与俄罗斯合并三百周年的宣传提纲认为,沙皇政府在乌克兰、白俄罗斯等民族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历史进步作用”。
上述情况表明,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是沙俄帝国对外侵略扩张,对少数民族实行殖民统治的历史产物,而红色帝国继承了沙俄帝国的意识并竭力维护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传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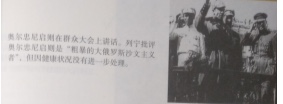
(未完待续)
荀路 2022年10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