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93)
赤色帝国覆亡之谜(47)
说了斯大林民族理论形成的历史原因,再说斯大林民族理论形成的社会原因。主要是:
首先,它是一种由于专制的异民族统治导致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内部极端的、尖锐的两极分化,以及由此造成的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之间、压迫阶级与被压迫阶级之间的仇恨和斗争。这种社会矛盾对于一个处在沙皇专制殖民统治之下的格鲁吉亚革命者来说,无疑埋下了对民族压迫和贫富悬殊强烈憎恨的种子。几百年来,沙皇统治异民族的一个主要手段就是采取分化的办法,即给予那个民族的上层统治集团以特殊的待遇,培养他们和俄罗斯贵族一样的爱好、一样的政治倾向,甚至一样的沙文主义精神。这就使一个民族内部阶级分化加剧,阶级对立尖锐。所以,十月革命前俄国的一个特殊国情是所有民族的劳动阶级能够联合起来,共同反对沙皇专制制度。这种由阶级压迫导致的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各民族劳动大众之间产生的凝聚力,是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能够成功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原因。所以,在斯大林的民族思想形成过程中,他最反对各民族的分裂、分治或者独立,坚决主张由党把各民族的革命运动统一起来。斯大林说: “我们本来需要一个统一的灵活的集中的党,这个党的中央委员会能在瞬息间发动全俄工人,并领导他们向专制制度和资产阶级作坚决的冲击。可是有人却硬塞给我们一个畸形的、分散成各个政党的‘‘联邦式的联盟’!他们给我们的不是锋利的武器,而是生锈的武器。” 因此,“在俄国活动的社会民主党是把自己称为俄国(而不是俄罗斯)社会民主党的。显然,它是想以此向我们表明,它不仅要把俄罗斯无产者集合在自己的旗帜下,而且要把俄国一切民族的无产者集合在自己的旗帜下”。所以,“所谓‘民族利益’和‘民族要求’,就其本身来说,并没有特殊的价值;这些‘利益’和‘要求’究竟有多少值得注意,是要看它们把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和阶级发展向前推进多少或能够向前推进多少而定的”。
其次,它是一种由于长时间内各民族的碰撞而造成整个社会对民族差别和民族矛盾麻木、漠然的倾向和态度。这种倾向和态度使苏俄和苏联领导人对少数民族的要求和他们之间出现的矛盾重视不够、处理不当。俄国的历史可以说就是一部民族征服的历史,所以列宁把沙皇统治下的俄国称作“各民族的监狱”,而生活在这个“监狱”里的不同民族对民族差别、民族歧视、民族兼并对整个社会产生的震荡习以为常。斯大林十分清楚存在于俄国社会生活中的这一特点,因此,在分析民族问题时,他对任何可能出现或造成俄国革命力量分裂或削弱的民族主义“要求”都给予抨击并在实践中加以拒绝。但这埋下了忽视少数民族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处理民族矛盾时简单粗暴的隐患。斯大林对俄国民族问题的看法归结到一点,就是他认为俄国必须是一个整体。因此,他坚决反对任何其他意义上的所谓“民族独立”,只有一种,即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的“民族解放”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政治信仰和民族心理因素对斯大林的民族理论的形成也有很大的影响。马克思乐观地认为: “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 “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 这种把解决民族压迫和民族矛盾的宝押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上的设想,具体落实到一个国家特别是像俄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民族矛盾尖锐的国家,却面临着极其复杂的窘境。而在实践中,执政的布尔什维克党却抱有教条主义的幻想。斯大林就过高地估计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对民族矛盾的自然化解作用,把各民族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信仰作为彻底割除民族保守意识的有力武器,因而在处理民族发展过程与建设社会主义国家过程的矛盾时出现简单化甚至粗暴的倾向。
1913年2月,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一文中,在谈到民族要求和党的组织问题时认为: “少数民族感到不满的不是没有民族联盟,而是没有使用本民族语言的权利。让他们使用本民族语言,这种不满就会自行消失了。少数民族感到不满的不是没有勉强凑成的联盟,而是他们没有本民族的学校。给他们这种学校,这种不满就失去任何根据了。少数民族感到不满的不是没有民族联盟,而是没有信仰(信教)、迁徙等等的自由。给他们这种自由,他们就不再会不满了。” 如此看来,斯大林是知道少数民族的意愿和要求的,而这些要求正是布尔什维克所不愿和不能给予的。当时在反对民族联盟问题上斯大林和列宁的态度是一致的,就是以统一的党组织和俄国无产阶级统一的革命行动来建立苏维埃政权,在此之下以民族“区域自治”来应付少数民族发起的权利要求。斯大林认为: “区域自治不是把人们按民族划分的,不是巩固民族壁垒的,相反,是打破这种壁垒,把居民统一起来,以便为实现另一种划分即按阶级划分开辟道路的。” 虽然列宁后来根据十月革命前后的具体情况多少改变了这种观点,但在斯大林的民族理论和实践中,这一思路是贯彻始终的。这种强硬僵化的政治立场在后来成为苏联当局压制少数民族正当要求、甚至干涉他国内政的大国沙文主义的口实。
应该说,斯大林对大俄罗斯主义和民族压迫有更深的体会,因为他本人出身于一个穷苦的格鲁吉亚人家庭,而格鲁吉亚在沙皇统治之前不仅已形成独立的民族国家,而且格鲁吉亚人有着悠久的历史和顽强的民族性格。斯大林称自己是“科巴”(格鲁吉亚劫富济贫的罗宾汉),表示了他为祖国解放奋斗的决心。但斯大林从参加布尔什维克革命的那一天起,就不是一个格鲁吉亚民族主义者,他是以国际主义精神和无产阶级革命利益原则来衡量民族归属和民族意识的。作为一个布尔什维克党的少数民族出身的领导人,他一方面必须以无产阶级利益来打击各种民族利己主义,另一方面又必须远离少数民族随时出现的狭隘民族主义。要使俄罗斯人不怀疑曾是被压迫民族的少数民族没有民族分离或复仇意识,又要使少数民族不怀疑俄罗斯人是平等、真诚地关怀和帮助他们发展,这就使斯大林作为一个格鲁吉亚人在民族心理上处于矛盾状态。
俄罗斯人作为苏联的主要民族,它在苏联政治经济中的主导和决定性作用是毫无疑义的,因而,俄罗斯人的意志势必发挥主导作用。所以,斯大林必须“矫枉过正”地显示自己的“俄罗斯化”,以取得俄罗斯人的信任和支持,同时,他的“非俄罗斯”身份使他的“俄罗斯化”政策具有“纯粹”的无产阶级性质和相当的说服力。所以,列宁曾批评斯大林的“俄罗斯化了的异族人总是在表现真正俄罗斯人的情绪方面做得过火”。
列宁在世时,斯大林在民族问题上与列宁的分歧一度公开化和激烈化,具体表现在格鲁吉亚加入联盟的事件上。
在加入苏联的问题上,格鲁吉亚共和国党中央一开始就坚决反对斯大林的民族”自治化”计划。他们认为,“各独立共和国以自治形式进行联合为时过早”。1922年10月,俄共(布)中央全会通过列宁修改后的成立联盟的决议,其中规定: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三国通过外高加索联邦而不是直接加入即将成立的苏联。这条规定遭到以姆季瓦尼为首的格鲁吉亚CP中央的强烈反对。他们要求同其他共和国一样直接加入苏联。但是,以奥尔忠尼启则为首的俄共(布)外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对这一要求采取高压政策。
10月20日,外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召开全会,奥尔忠尼启则在会上斥责“格鲁吉亚共产党的上层是沙文主义败类,应当立即抛弃”。全会认为格鲁吉亚党中央领导人奥库查尼、钦查泽和马哈拉泽违反党纪,给他们以党内警告处分,解除奥库查尼的格共中央书记和主席团委员职务。
在这种情况下钦查泽、卡夫塔拉泽、马哈拉泽于10月21日凌晨给俄共(布)中央打电话上告。接电话的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叶努基泽,他作了电话记录,内容如下:
“格鲁吉亚这里走投无路的局势白迫使我们来打扰您。请把下述一切转告列宁同志,我们相信,他和您的绝对权威决定一定能结束现在的灾难性混乱和纷争。奥尔忠尼启则极端刚愎自用……开始摧毁格鲁吉亚共产党(布)中央了。奥库查尼被解职,我们已无法承担责任,明天我们将在中央全会上声明这一点。总之,格鲁吉亚的苏维埃政权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处于危险状态。这一切全是奥尔忠尼启则造成的……” 接着是对奥尔忠尼启则的谩骂。
这个电话记录当天送到列宁和斯大林那里。列宁于当天深夜给钦查泽等人发去电报。列宁这时显然认为由于十月全会改正了“自治化”方案的错误,问题业已解决,因此他对钦查泽在电话中的不礼貌口气表示惊奇,谴责对奥尔忠尼启则的谩骂,要求按照组织手续把冲突“以恰当的、有礼貌的口气提交俄共中央书记处解决”。
10月22日,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通过了格共中央主席团的建议,中央委员会提出辞职。辞职的原因是: 一、外高加索边疆区党委向中央大量上报关于格鲁吉亚党组织的“不正确情报”,造成“中央对地方同志的不信任”。二、不断给格鲁吉亚地方组织发布各种指令,造成了一种不允许地方进行富有成效的工作的局面。三、格鲁吉亚共产党主张直接加入苏联,这就成了一种“罪行”,被斥之为“沙文主义者”、“孟什维克”等等。四、边疆区党委越过格共中央直接领导格鲁吉亚的工会、第比利斯市委等地方组织,造成一种格共中央无法进行工作的局面。因此,它不得不提出辞职。
就在这一天,斯大林给奥尔忠尼启则打电报说: “我们打算结束格鲁吉亚的争吵并狠狠惩罚一下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会。依我看,应当采取一条坚决的路线,把各种民族主义残余统统从中央委员会清除出去。收到列宁的电报了吗?他对格鲁吉亚民族主义分子感到愤怒和极端不满。”
外高加索边疆区党委会和俄共中央接受了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的辞职,成立了以罗明纳泽为首的新的格共中央委员会。接着又从政府部门撤换了大批干部,“民族主义倾向分子”马哈拉泽被撤去格鲁吉亚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职务,卡夫塔拉泽被撤去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钦查泽被撤去肃反委员会主席职务,等等。
由于格鲁吉亚的一批原领导人不断地向俄共中央申诉,俄共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一个委员会去第比利斯调处。11月24日,书记处任命了由捷尔任斯基为主席的委员会,表决时列宁弃权。25日第二次表决时,列宁仍然弃权。
捷尔任斯基委员会在格鲁吉亚进行了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外高加索边疆区党委会和奥尔忠尼启则的路线和工作完全符合俄共中央的指令,是完全正确的,而辞职的格共中央的立场则是根本错误的。委员会谴责姆季瓦尼集团的“民族主义”路线。这里,委员会的工作显然带有片面性,偏听偏信,而没有做全面调查。另外,委员会对奥尔忠尼启则动手打人事件也没有进行调查。
奥尼忠尼启则打人事件经过大致如下: 1922年秋,俄共(布)政治局委员李可夫路过第比利斯,住在奥尔忠尼启则家里。有一天,李可夫的老朋友卡巴希泽来访问李可夫,在谈话中争执起来。开始奥尔忠尼启则没有参予,但是后来卡巴希泽指责奥氏,说他把一匹马据为己有,于是两人发生对骂,期间奥氏动手打了卡巴希泽一个耳光。据米高扬回忆说,这匹马是当地山民送给奥氏的,奥氏按照高加索风俗收下了这份礼物。但他把这匹马上交给革命军事委员会,只在阅兵时才骑一骑。就马匹一事而论,奥尔忠尼启则并无错,但是他在争执中动手打人却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12月12日列宁从疗养的哥尔克庄园回到莫斯科,最后一次在克里姆林宫工作,晚上接见了刚从格鲁吉亚回来的捷尔任斯基。捷尔任斯基向列宁汇报了调查情况,其中谈到奥尔忠尼启则打人事件。关于这次谈话,列宁后来这样说: “我害病前夕,捷尔任斯基曾向我谈到过委员会的工作和这一‘事件’,这对我有严重影响。” 13日凌晨列宁两次发病,16日夜出现中风。列宁这次发病多少是同“格鲁吉亚事件”有关的。他对捷尔任斯基委员会的工作不满意,认为它在调查时偏袒一方,缺乏应有的公正。在病情略有好转时,列宁在12月30日、31日口授了《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的信件。
列宁在信中一开始就内疚地说:“我觉得很对不起俄国工人,因为我没有十分坚决十分果断地过问有名的自治化问题,其正式的说法似应叫作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问题。” 列宁遗憾地表示,上述问题因其患病而“完全绕过了我”。列宁对奥尔忠尼启则动手打人十分气愤,并表示“莫大的忧虑”。他说: “如果事情发展到奥尔忠尼启则竟会动手打人——这是捷尔任斯基同志告诉我的,那么可想而知,我们已经掉到什么样的泥潭里去了。可见,整个这个‘自治化’的想法是根本不对的,是根本不合时宜的。”
列宁指出: “在这种条件下,很自然,我们用来替自己辩护的‘退出联盟的自由’只是一纸空文,它不能够保护俄国境内的异族人,使他们不受典型的俄罗斯官僚这样的真正俄罗斯人,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实质上是恶棍和暴徒的侵害。毫无疑问,在苏维埃的和苏维埃化了的工人中,会有很少一部分人沉没在这个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垃圾的大海中,就像苍蝇沉没在牛奶中一样。”
列宁接着说: “我想,斯大林的急躁和喜欢采行政措施以及他对有名的‘社会民族主义’的愤恨,在这件事情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愤恨通常在政治上总是起极坏的作用。” 列宁批评捷尔任斯基处理问题不公,他说: “我还担心,去高加索调查这些‘社会民族主义分子’ ‘罪行’案件的捷尔任斯基同志,在这件事情上也只是突出表现了他的真正俄罗斯人的情绪(大家知道,俄罗斯化的异族人在表现真正俄罗斯人的情绪方面总是做得过火),他的整个委员会是否不偏不倚,这在奥尔忠尼启则‘动手打人’这件事上得到了充分说明。我想,这种俄罗斯式的动手打人行为是不能用受到任何挑衅甚至侮辱作辩解的,而捷尔任斯基同志无法补救的过错就在于他对这种动手打人的行为采取了轻率的态度。” 列宁最后指出:
“奥尔忠尼启则对于高加索的其余所有公民来说就是权力。奥尔忠尼启则无权发怒,尽管他和捷尔任斯基借口说是被别人激怒的。相反,奥尔忠尼启则必须克制自己,而任何一个普通公民,尤其是一个被指控犯了‘政治’罪的普通公民倒不是非克制自己不可的。要知道,从实质上说,社会民族主义分子就是被指控犯了政治罪的公民,而且从这种指控的全部情况来看,也只能这样认定。”
列宁强调说: “抽象地提民族主义问题是极不恰当的,必须把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大民族的民族主义和小民族的民族主义区别开来。” 在列宁看来,大民族、压迫民族总是有过错的。所以,列宁主张对少数民族要“多让步一些,多温和一些”,必须“采取非常谨慎、非常客气和让步的态度”。“用自己对待异族人的态度或让步来抵偿‘大国’民族的政府在过去历史上给他们带来的那种不信任、那种猜疑、那种侮辱”。 “在这种情况下,在对少数民族让步和宽容这方面做得过些比做得不够要好。”
列宁在信中建议: “需要处分奥尔忠尼启则以儆效尤”, “并要补充调查或重新调查捷尔任斯基的委员会的全部材料,以便纠正其中无疑存在的大量不正确的地方和不公正的判断。当然,应当使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对这一真正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运动负政治上的责任”。
可是,列宁的这封信当时没有送交俄共中央,而是收存在列宁的秘书福季耶娃那里。福季耶娃在1923年3月16日曾写便条给政治局委员加米涅夫,说列宁告诉她,民族问题“一直使他极为忧虑,他准备在党的会议上谈这个问题。在他这次发病前不久,他告诉我,他将要发表这篇文章,但是要再过一些时候才发表。以后他就病了,没有给我最后的指示。列宁认为这篇文章是有指导意义的,并且非常重要。按照他的指示,曾把这篇文章抄送托洛茨基同志。由于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一致,列宁委托托洛茨基在党的会议上为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辩护。”
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局于1923年1月25日听取了捷尔任斯基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后批准了这个报告和建议,同意撤换格鲁吉亚党政领导,认为这是“高加索的局势和格鲁吉亚党内斗争进程造成的”;同时,批准中央组织局1922年12月21日关于把姆季瓦尼、钦查泽、卡夫塔拉泽和马哈拉泽调离格鲁吉亚工作的决定。
接着,政治局于2月初批准下发了关于格鲁吉亚事件的党内通告信,申述促使政治局就捷尔任斯基委员会的报告作出的决定的理由。信中说: “俄共中央要么应当撤销外高加索区委和新的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再度同外高加索党组织和格共(布)中的多数发生冲突,要么按照格鲁吉亚和外高加索多数党员的愿望撤回四名倾向分子”,所以“继续支持姆季瓦尼同志已经是不可能和不允许了”,撤换是“惟一可能的出路”。
这时,重病中的列宁已大权旁落,对此已无可奈何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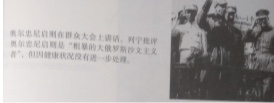
(未完待续)
荀路 2022年10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