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海子发表的第一篇文字或是以“扎卡”为笔名翻译的小说
海子的原名叫查海生,但查海生在没有使用“海子”这个笔名前,曾给自己起过另外一个笔名——扎卡,此事恐怕鲜为人知。海子是一名杰出的诗人,生前创作了大量优秀的诗歌作品。但是,他除了写诗之外,其实也是一位外国文学的翻译者,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时候,他就十分热衷于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并以“扎卡”的笔名,翻译了德国作家海因利希·伯尔的短篇小说《音乐会上的咳声》,发表在当时北京大学西语系学生创办的油印文学刊物《缪斯》上,这也是笔者所能见到的海子生前唯一翻译的一篇小说作品。 2016年3月21日,我从诗人陈陟云那里看到他写海子的文章《八十年代的北大诗歌,我们生命之中的青春小站》,突然想到他给我寄来的几十张有关北京大学学生刊物的图片。陈陟云是海子北大法律系的同学,和海子因诗歌而结识,并成为了好朋友。对于和海子那段珍贵的友情,时隔三十多年后,陈陟云在接受我关于《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访谈录》的采访时说道:
1983年三四月间,我认识了79级的查海生,也就是后来的海子。当时,查海生正在编辑自己的一个诗歌小集子《小站》,我已任文学社理事长。社长郭巍对我说,79级有个小个子查海生,一直在研究黑格尔,诗歌写得很棒,与我应是同一类型的人,想介绍我们认识。一天晚上,郭巍带小查到28栋楼我宿舍见面,我们再一起到39栋楼他们的宿舍,几位同学正在用蜡纸刻写查海生的诗。小查比我还小一岁,有点腼腆,与我一样沉默寡言,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很快就成了最要好的朋友。从认识到他7月初毕业离校,我和小查之间的交往不到四个月,但这四个月里,我们几乎每隔一两天都要见一次面,一起谈论诗歌,或者一起参加诗歌活动。其间,经小查介绍,我还认识了79级中文系的骆一禾。骆是五四文学社的核心成员,诗写得好,诗歌理论也很棒。虽然与骆交往次数不多,但每次同他在一起,我在诗歌写作上都会受到启迪。后来骆一禾还叫上海子和我一起去找过他们辩论。五四文学社办了很多诗歌讲座和诗歌研讨会。海子的诗歌小册子《小站》出来之后,骆一禾还专门给他搞了个研讨会。应该是《小站》让骆一禾认识了海子,让他们结下了一直到生命终了的友谊。
由于这段时间,我专注于海子的研究,脑海中多是关于海子最新佚诗佚文的发现情况。出于“职业的敏感”,我当时的想法就是:看那些图片里有没有遗漏的海子的诗文。于是,我查看了陈陟云2013年3月给我发来的那些图片,在翻阅到北京大学西语系创办的《缪斯》时,我突然看到第47页上的一篇题目叫《音乐会上的咳声》的翻译小说,作者是德国的海因利希·伯尔,翻译者是扎卡。当看见扎卡两个字时,我第一时间给陈陟云发去了信息,请他帮助把这篇小说扫描或拍照下来。结合图片,我进行了反复研读,并推断这篇翻译小说的译者就是海子。谈起原因,我认为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关于海子的最初笔名叫“扎卡”这件事,在海子的朋友圈里,似乎是人所共知的事。海子在北大同校不同系的同学、后来在中国政法大学的同事及好友唐师曾在《海子忌日:再沾“扎卡”的光》中写道:“小查绰号‘扎卡’,是上北大时半大孩子起的外号,仅因为他姓查,查与扎同音。”又据海子的同事、好友、兄长吴霖在《再见了,小查》中描述:“就像我当时随意写下‘江南’作为自己的笔名一样,你的‘海子’笔名终于使大多数校园中人忘记了你的真名。就像你最初的笔名‘扎卡’一样。”另外,在《海子,一个远游的兄弟》中,吴霖又进一步阐述了海子第一个笔名“扎卡”的由来:“他先是给自己起了一个叫‘扎卡’的笔名,说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觉得这两个字很狠,有穿透力。没多久,他又给自己起了一个新笔名,叫‘海子’,这笔名并不是‘海之子’的意思,而是与‘扎卡’一样,是他极其向往雪域高原的一种观照。”
第二,海子翻译这篇小说的时间大约是在1982年10月,当时他正在北京大学法律系读大四。按照唐师曾文章中的描述,海子当时已经给自己起了“扎卡”这个笔名。因此,以“扎卡”署名发表翻译作品,正好在时间点上吻合。另外,海子在大学时期酷爱阅读外国文学作品,更喜欢歌德、海涅、荷尔德林、黑格尔、马克思等德国作家、诗人、哲学家的作品,曾经购买了大量德国作家的书籍,并且具有良好的外语功底,对翻译外国文学作品自然很感兴趣。因此,翻译这篇德国作家的小说,对于他来说并不是很困难的事。这在他后来翻译并发表在中国政法大学的油印诗集《青铜浮雕·狂欢节·我》中的《美国现代诗四首》中也可以看得出来。作为北京大学学生,海子将翻译小说投稿给学生刊物《缪斯》是一件很正常的事,而发表海子的作品,对于《缪斯》来说也是很自然的一件事。
在这期刊物题为《写在前面》的前言上,配发有编者的话,其中对海子翻译的这篇小说给予了简要的解析:“西德当代大作家伯尔的《音乐会上的咳声》则以揶揄的口吻,对民族的‘劣根性’进行了深刻的剖析。”通读海子翻译的这篇小说,给我的印象是:译文流畅,清新生动,有些段落精彩纷呈,有些句子诗意盎然,我从中感受到了海子最初的文学才华。
海子这篇翻译小说的发现,无疑是我在研究海子过程中一件意外的、可喜的事情。我甚至以为,从我目力所及的搜寻和整理来看,这篇翻译小说或许是海子自开始热爱诗歌(文学)写作以来发表的第一篇文学作品(翻译小说),是海子第一次使用“扎卡”的笔名发表文学作品(翻译小说)。海子的小说翻译不但是他个人文学(诗歌)生涯的重要事件,更是他后来走上诗坛的重要影响因素。于海子而言,这篇翻译小说的发表,是否对引领他最终走上诗歌创作道路,成为中国当代新诗史上的杰出诗人有所帮助,更加值得我们思考和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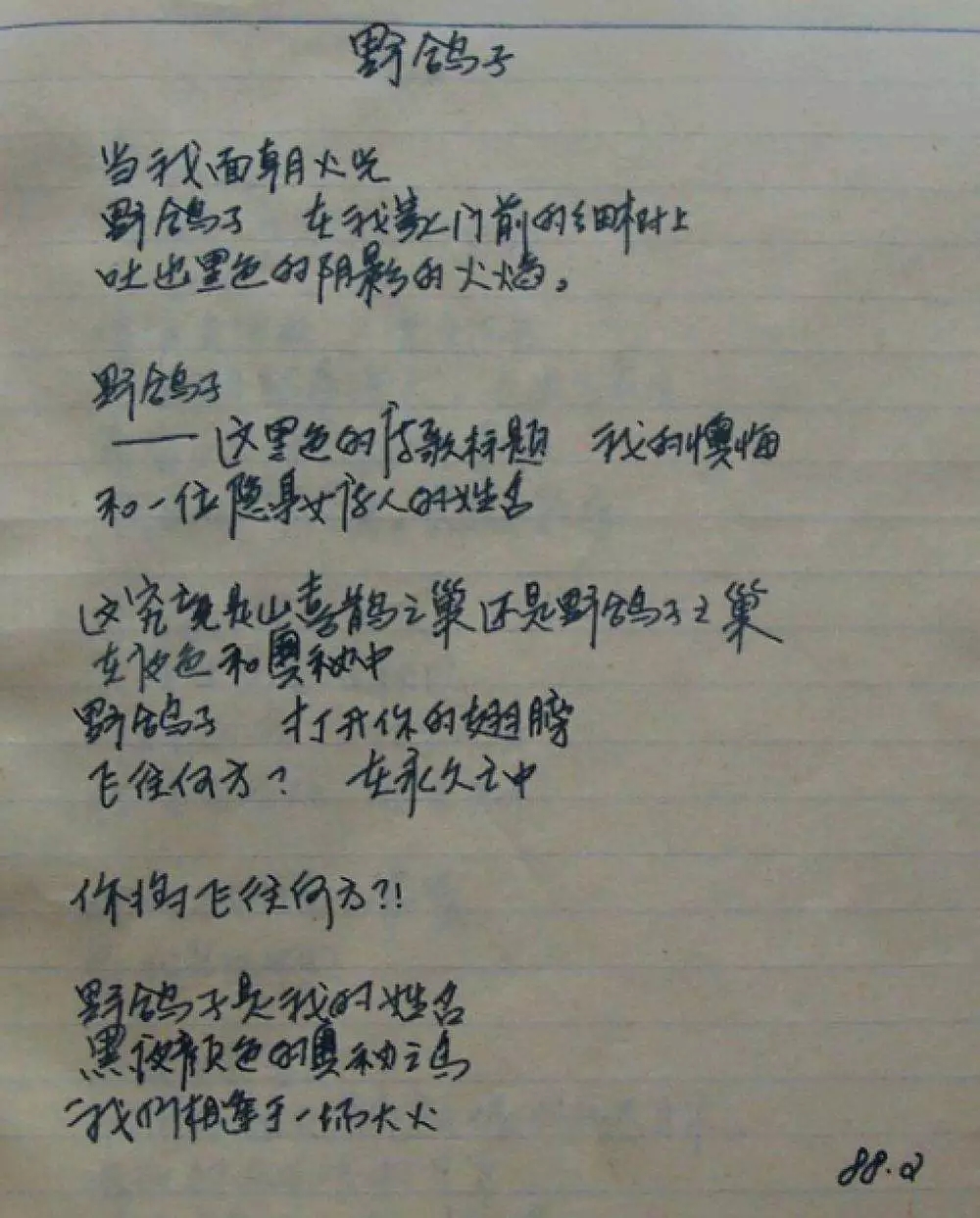
二、海子一篇“残缺不全”的诗歌评论佚文
在海子生前发表的作品及逝后遗留的手稿中,诗歌评论是极其罕见的。2018年8月12日,我偶然间看到一幅照片,一张油印刊物的页面上印着一行文字:故乡修道院的女儿墙——王淑敏的诗印象 海子。照片只有一页文字,文章虽然有头有尾,却缺少中间部分内容,从而导致了这篇诗歌评论不完整,给读者留下了阅读的缺憾。但在看到这行标题和文章内容的时候,我还是感到十分欣慰,对于一个长期挖掘整理海子佚诗佚文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发现一篇从未听说过的海子的诗歌评论更让人开心的。这篇诗歌评论题目叫《故乡修道院的女儿墙——王淑敏的诗印象》。照片里的文字是这样写的:
就在这个时候,在海身边。在这一种巨大有力的精神的东西旁边,你的呼吸急促,你的脉搏跳动过快。你的方块字解体后变得新鲜,重新使人痛苦不堪。就在这个时候,我读了你的诗……
转过身来,而我要对你们说的是,这里的问题不在于诗歌本身的复杂。而在于诗歌所面对的、所热爱的人心的复杂。这就是诗人们痛苦不堪,重新寻找语言和新的纯洁(新的情感新的道德),或者过早谢世的原因。诗人们的心,过于简单,正因为如此,它的语言变得格外复杂。除了情感和情感的衣服——语言,他是一个穷光蛋。“技巧是对一个人真诚的考验”。
活该他引颈歌唱,说些别人难懂或不懂的话,因为他过于幼稚过于执着,因为他对这个世界毫无准备,束手无策,除了写下消耗生命,枯萎自己的诗行。
其他的人也活得并不轻松。
……“父亲二十年来愁苦地喝酒,心乱如麻。”这种极其口语的东西一下就抓住了我的心。我知道,这是你的追求。语言和文学是互为养料的。口语的追求和谣曲的追求在中国新诗的现阶段已成为一股不小的潮流,因为你直接的爱和恨是保存在人群和他们时……”
这篇文章并不完整,很难窥见海子对王淑敏诗歌评论的整体内容,对于来源和最初刊发在什么地方,我也是一无所知。然而,面对这篇残缺不全的海子诗歌评论,我却不想半途而废,而是想继续寻找后半部分文章的内容。也许是与海子的这篇诗歌评论有缘吧,在时隔四个月之后,我不但找到了文章刊登的刊物名称,而且还找到了后半部分内容。
2019年1月13日,我收到了原中国政法大学诗社第三任社长王艳霞寄给我的十余本油印刊物《星尘》《潮声》《我们》。在翻阅那本由政法大学团委主办、1985年12月出版的《我们》改刊号第一期的时候,我发现这期刊物设立的“五色石”专栏上,赫然印着两行文字,第一行文字是:北戴河之旅(组诗)王淑敏。59页。第二行文字是:故乡修道院的女儿(此处遗漏了一个“墙”字)(评论)海子。67页。
看着这两行搜寻多日未果的文字,我再次兴奋起来。急忙翻开第67页,但这本刊物是一个残缺本,第36—71页之间是空白,也就是说海子这篇诗歌评论缺少了第67—70页共四个页码的内容,那也意味着海子的这篇诗歌评论,缺少了四个页码。除了偶然间在李青松处发现的第67页开篇之外,海子的这篇诗歌评论整整缺少了三个页码,据估计,大约是1500字。而残留在这期《我们》刊物上的文字只有三个页码。令人遗憾的是,在第72页上,由于纸面上不知被谁书写了十多个毛笔字,一些文字被墨迹遮掩,已经无法看清。幸好,第71页和第73页纸面是干净的,从而保证了后面内容的适当整理。我抄录如下(有个别文字因无法看清而难以整理,固以……代替):
雨中的依恋。我想,男人们是不会在新房里养些小鱼的。男人们头颅里尽是些灰尘和石块(故乡的元素)。这很有可能。它们能用来堆山、垒井、盖房、建立畜栏。在更少的时候,里面也可能蓄存了一汪清水或更多。
没有草丛、所有的天空就睡在里面。所有的爱情的月亮也就像你在另一个地方写下的“用一个夜晚走完了一个妇人的一生/回家去/回家去/家里有一面永远对我微笑的墙”这是一种温暖的孤独,这种孤独的念头是从哪儿开始,又要到何时才能结束呢?任何艺术的触发都开始于心的流浪。但流浪是要有归宿的。无论种子撇下没有、庄稼长出没有,你的痛苦仍旧在山脊梁的那边起伏。有一次,你跑去看了,那便是海。
对于任何一颗复杂的心,我都会感到莫名的恐怖。当钟声四溅的时候,你的情感就像那绳索结成的网,在你手中抖动,同时也像那网中的鱼。这绳索像是一面镜子,无论是渔夫还是鱼都在上面照见了相互酷似的灵魂。
感悟应该简单,像捕鱼一样。
而且,你知道不知道,那故乡的修道院里至今还长满了草。
在海边,浪头在心里翻滚。如果没有纯洁,也就没有了一切。脚下会突然出现一道裂缝。我对你说,有时候我也迫不得已像一只旧船泊在水上,并不比月亮结实。
同时,希望你一路顺风,在故乡修道院里凝成一团……
故乡修道院的女儿墙呀!
美国有一位农夫,名叫弗洛斯特,别看他是一个天主教徒,骨子里比谁都凄凉。他写了隔绝人群的墙,我们竖立的墙,由我们的手一块垒起的墙。这墙,或许要求别人和解,只是对……的一种苛求。
然而还有另一面墙。苦修的面壁的爱情的墙。修女张狂的心。让一切复杂的……者见鬼去吧,如果有可能的,我要做一位有痛苦的诗人。我愿意永远,活在纯朴之间,使你对生活恋恋不舍。
在《桥的悬念》里,这简朴的相亲相爱的幸福,所有漫长的心的距离缩短了,在一只胳膊搭成的桥上消失。
忧伤肃杀的秋雨已断。眼睛燃亮了那能打开爱情建筑物的钥匙。风扶着我的爱情前行。孤独的灯可能再也不会孤独了。最后,这满腔柔情第一次化为对故乡白色的时空和黑色的雪的热爱,从面向整个诗坛迈进的方向开放。这是一个东方民族光辉蒙临自身的时刻。儿子们从智慧与力、庙堂、遗址、废墟和经书中寻找源源之根,最初的水、土与水。奔跑的野鹿一样的情感和整体上重新诞生的体验。女儿们则从爱情消化这个民族的进程。女儿们温婉的提到故乡,月亮和月下散发出温暖的树的肉体。无论如何,故乡总是能使我们恢复元气和力量。
总之,为我这个古老的民族重新恢复情感本身的努力,反射到一切行进的诗篇中。情感是一种最严肃的东西。我们要使它纯洁、结实,而且简单。我们要把它放回我们的心中哪怕引起一场悲剧,新人就从这悲剧中诞生,果核中有一棵参天大树。为我的古老的民族重新建造一个不垮的活生生的内心,一个良心、一个心灵上的立足点,一个旅程的出发点和目的地,是诗人们共同的任务。无论你是面墙背海述说自己,还是回到人群,重新站立,疯疯癫癫。
我们的穿布裙子的回到故乡修道院的小女孩……愿你快活。
也愿你加倍的忧伤。”
海子这篇写于1985年10月的文章,是他生前为数不多的诗歌评论,同时也是一篇被《海子诗全集》漏收的佚文。尽管此文目前呈现的内容残缺不全,但从字里行间依然能看出海子独特的评论才华,海子熟练地运用散文笔法写作诗歌评论,使这篇诗歌评论具有了不一样的风格和文本魅力。
三、海子的一篇序言佚文
海子生前创作了大量的长诗、短诗以及极少的诗论、短篇小说等作品。其实,在海子留下的诗歌遗产中,还有一种体裁鲜为人知,那就是序言。作为八十年代诗歌历史的爱好者与研究者,特别是作为海子诗歌的研究者,我并未听说过海子给别人诗集写过序言。因此,当我亲眼见到海子为他一位诗友油印的诗集所撰写的序言时,也十分惊讶。
2016年1月14日,诗歌民刊收藏家世中人在微信上贴出三张图片,第一张图片是16开本的油印本《惠风的诗》,浅蓝色的封面上印着惠风的诗——《星尘》增刊、中国政法大学诗社、1985年5月的字样。第二张图片的文字内容是,夏日里长成的女性——惠风诗印象(代序)海子。第三张图片则是手写油印的诗集第一页《纸船集》的前言文字和打印的诗歌《我愿》的前半部分。
我敏感地意识到,这三张图片对于海子诗学研究者来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我联系到世中人,同他进行了详细的交流,两天后,我到单位查收世中人发来的有关诗集的图片,并收到了海子的序言和《惠风的诗》的封面、封底、自序以及第一首诗和它的前言。于是,我开始着手整理海子的序言,一边打字、一边校对,将这篇自序打印下来,并进行分析、判断、研究。后来,我又请世中人寄来了《惠风的诗》。
海子的这篇序言题目叫《夏日里长成的女性——惠风诗印象》,大约1000字,写于1985年5月。在这篇序言中,海子以他优美的文笔对惠风的诗歌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解读,通篇文字富有诗意,犹如一篇精彩的散文诗,令人读后赏心悦目。全文如下:
雨中的依恋。我想,男人们是不会在新房里养些小鱼的。男人们头颅里尽是些灰尘和石块(故乡的元素)。这很有可能。它们能用来堆山、垒井、盖房、建立畜栏。在更少的时候,里面也可能蓄存了一汪清水或更多。
没有草丛、所有的天空就睡在里面。所有的爱情的月亮也就像你在另一个地方写下的“用一个夜晚走完了一个妇人的一生/回家去/回家去/家里有一面永远对我微笑的墙”这是一种温暖的孤独,这种孤独的念头是从哪儿开始,又要到何时才能结束呢?任何艺术的触发都开始于心的流浪。但流浪是要有归宿的。无论种子撇下没有、庄稼长出没有,你的痛苦仍旧在山脊梁的那边起伏。有一次,你跑去看了,那便是海。
对于任何一颗复杂的心,我都会感到莫名的恐怖。当钟声四溅的时候,你的情感就像那绳索结成的网,在你手中抖动,同时也像那网中的鱼。这绳索像是一面镜子,无论是渔夫还是鱼都在上面照见了相互酷似的灵魂。
感悟应该简单,像捕鱼一样。
而且,你知道不知道,那故乡的修道院里至今还长满了草。
在海边,浪头在心里翻滚。如果没有纯洁,也就没有了一切。脚下会突然出现一道裂缝。我对你说,有时候我也迫不得已像一只旧船泊在水上,并不比月亮结实。
同时,希望你一路顺风,在故乡修道院里凝成一团……
故乡修道院的女儿墙呀!
美国有一位农夫,名叫弗洛斯特,别看他是一个天主教徒,骨子里比谁都凄凉。他写了隔绝人群的墙,我们竖立的墙,由我们的手一块垒起的墙。这墙,或许要求别人和解,只是对……的一种苛求。
然而还有另一面墙。苦修的面壁的爱情的墙。修女张狂的心。让一切复杂的……者见鬼去吧,如果有可能的,我要做一位有痛苦的诗人。我愿意永远,活在纯朴之间,使你对生活恋恋不舍。
在《桥的悬念》里,这简朴的相亲相爱的幸福,所有漫长的心的距离缩短了,在一只胳膊搭成的桥上消失。
忧伤肃杀的秋雨已断。眼睛燃亮了那能打开爱情建筑物的钥匙。风扶着我的爱情前行。孤独的灯可能再也不会孤独了。最后,这满腔柔情第一次化为对故乡白色的时空和黑色的雪的热爱,从面向整个诗坛迈进的方向开放。这是一个东方民族光辉蒙临自身的时刻。儿子们从智慧与力、庙堂、遗址、废墟和经书中寻找源源之根,最初的水、土与水。奔跑的野鹿一样的情感和整体上重新诞生的体验。女儿们则从爱情消化这个民族的进程。女儿们温婉的提到故乡,月亮和月下散发出温暖的树的肉体。无论如何,故乡总是能使我们恢复元气和力量。
总之,为我这个古老的民族重新恢复情感本身的努力,反射到一切行进的诗篇中。情感是一种最严肃的东西。我们要使它纯洁、结实,而且简单。我们要把它放回我们的心中哪怕引起一场悲剧,新人就从这悲剧中诞生,果核中有一棵参天大树。为我的古老的民族重新建造一个不垮的活生生的内心,一个良心、一个心灵上的立足点,一个旅程的出发点和目的地,是诗人们共同的任务。无论你是面墙背海述说自己,还是回到人群,重新站立,疯疯癫癫。
我们的穿布裙子的回到故乡修道院的小女孩……愿你快活。
也愿你加倍的忧伤。”
这或是海子短暂诗歌生涯中唯一一篇序言文章,《海子诗全集》中未曾收录,对于当下研究海子而言,这篇序言具有比较重要的诗学价值,为进一步研究海子的诗学历程提供了十分有意义的参考。
四、海子以“查海生”署名的两首佚诗
我们通常以为海子发表诗歌作品只是用笔名“海子”,并非用“查海生”,事实是,海子不但以真名“查海生”公开发表过诗歌,而且还不止一首。
2015年5月27日下午,我正在写作一篇史料文章《内蒙古〈诗选刊〉创办档案(1984—1987)》,当我翻阅手边的1985年第10期《诗选刊》的时候,在第58页的位置上,题目为《灯》的诗歌突然跳入我眼帘,作者是查海生。在此之前,我从未听人说过海子以真名“查海生”署名公开发表过诗作,因而有些激动,也有些将信将疑,为了确认这首诗歌是不是海子原作,或者是否是重名作者的作品,我字斟句酌地阅读起这首诗:
外面的灯是蓝的
屋里的灯是黄的
外面的灯孤独的
举起一只手:
我不是坏人
我的周围应该
坐满邻居
一支蜡烛灯亮了
但不敢高声答应
因为有人说过
她的光明
无非是因为流泪的爱情
外面的灯是蓝的
屋里的灯是黄的”
仔细读过之后,从诗歌风格、句式、语言等方面进行分析,可以推断这首题目为《灯》的短诗确实具备海子诗歌的特点,或许是海子第一次使用真名“查海生”署名发表的诗歌作品。诗歌《灯》连同另一首《坐在门坎上》,最初发表在《滇池》1985年第6期,海子以真名“查海生”署名,是两首迄今为止不曾被各种版本的海子诗集所收录的佚诗。在发现这两首诗作的那刻,我也曾怀疑这两首诗是否为海子的佚诗。当时,由于手头没有西川选编的《海子诗全集》一书,为了解决疑问,我从其他渠道仔细搜索到《海子诗全集》的目录。结果,在目录上发现了一首海子的诗歌《灯》,我便信以为真地认为这首《灯》,就是我在《滇池》上看见的那首《灯》,连带另外一首《坐在门坎上》也误以为是夹杂在《海子诗全集》中的某一页里。就这样,我和海子的两首佚诗轻而易举地擦肩而过。
大约一个星期后,我头脑里再次浮现出确认那两首诗作究竟是不是海子佚诗的想法。在翻遍了《海子诗全集》之后,我确认了海子以真名“查海生”署名的两首诗作《灯》和《坐在门坎上》真是被所有版本海子诗集遗漏的佚诗!而《海子诗全集》里的《灯》与发表在《滇池》上的《灯》是两首不同的诗。
海子佚诗《灯》是海子诗歌中较好的诗作,与那首收入《海子诗全集》的《灯》相比,我能感受到这首诗更精致、更凝练、更隽永。而在《滇池》1985年第6期上和《灯》同时发表的另外一首诗歌《坐在门坎上》,语言朴素、节奏感强,植根大地与自然,很好地体现出了海子的诗歌精神。
坐在民歌的门坎上
自然想起
犁地
我们戴上爱情的草帽
音调的细绳子
在脖子上弄得痒痒的
太阳也不说什么
把影子踩到地里
坐在诗经的门坎上
昨天夜晚
我已度过关中小河
手握一把古代的野菜
风摆柳枝
风折柳枝
那些采薇的人们
睡在月亮的膝盖上”
如今,这两首海子的佚诗能够再次被发现,对于热爱海子诗歌的人们来说,是一种好事,亦是一种幸事。
注:为保持佚作原貌,编者未对其进行修改。
来源:《诗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