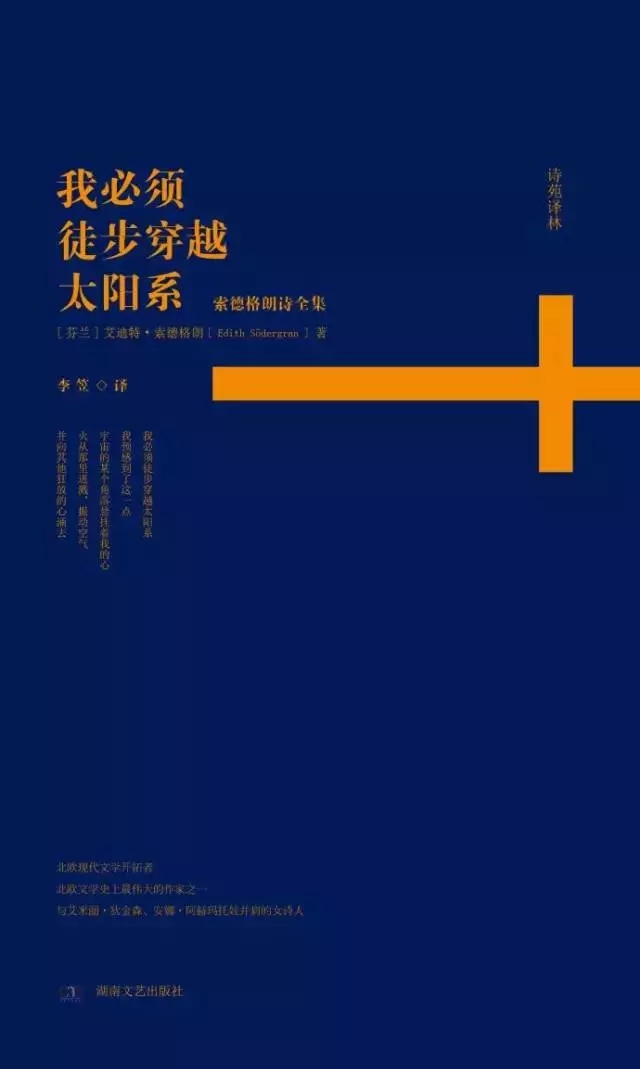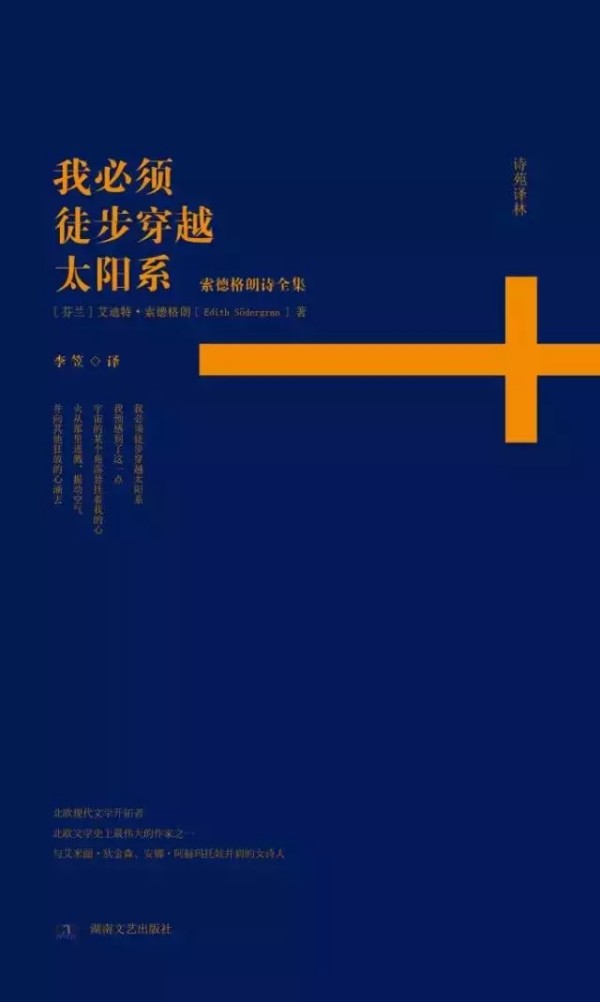1923年6月24日,仲夏节那天,身患肺结核的芬兰女诗人艾迪特·索德格朗病逝,年仅31岁。一位在她临终前不久探望她的诗友写道:“她的眼睛又灰又大,就像幽暗水面上的月光。她在微笑。”
索德格朗终生未婚,没有后代。她留下二百六十多首诗,内容大都围绕生命,爱情,死亡以及对上帝的冥想。这些诗短小深刻,形式自由,想象丰富,刻画了变幻不定的内心情绪。索德格朗生前出版的四本诗集,但遭到评论界的冷遇。她曾躺在病床上屈指数着自己的敌人,并在《风信子》一诗中写道:
我昂着头。我有我的秘密。谁主宰我?
我是折不断的,一棵不死的风信子。
我是一朵摇着粉色铃铛的春花,
它带着土地欢乐的歌声升起:
为了卓绝,安然地活着,没有对手⋯⋯
索德格朗对自己诗歌价值所具有的信念,最后被时间证明是对的。今天,她被誉为北欧现代文学的开拓者,她的诗歌在芬兰和瑞典家喻户晓。它们被传诵,被谱成曲子,被收入各种北欧诗歌选本,并对一代又一代的北欧年轻诗人产生着影响。芬兰专门成立了索德格朗研究会。索德格朗的名字常常和世界一流的诗人艾米莉·狄金森,安娜·阿赫玛托娃等人相提并论。
二
1892年,艾迪特·索德格朗(Edith Sodergran)出生在俄国彼得堡一个机械师家里。父母都是讲瑞典语的芬兰人。她出生不满三个月,全家撤回到芬兰一个叫莱乌拉的村庄。索德格朗在那里度过了自己孤郁的童年。而那里的白桦树,花楸树,花园,森林和湖泊则成了她后来诗歌中的主要意象。1902年至1908年,她在彼得堡一家德国人办的教堂学校念书,阅读了大量欧洲大陆作家的作品,并开始用德语写诗。十五岁那年,索德格朗正式用自己的母语瑞典语创作诗歌。索德格朗的母亲,一个聪慧能干的女人,也是女儿女权主义思想的启蒙者,她热心支持着女儿成为诗人的梦想。
1907年,索德格朗的父亲死于肺结核病。两年后,她也得了这一不治之症。那时她十六岁。疾病使年轻的索德格朗早熟,使她的创作欲如火山一样爆发,与此同时,死亡的阴影悄悄潜入她的诗中。
1911年,瑟德格兰和母亲一起到瑞士的一家疗养院疗养。在这期间,她接触了欧洲大陆的文学思潮,扩大了自己的文学视野。她在那里她爱上了照料她的路德维希·冯·穆拉特医生,一个有妇之夫的中年男人。1917年,冯·穆拉特去世,索尔格朗写下了回忆在瑞士时的两首诗:《断章》,《森林里的树》。
1914年春,索德格朗怀着成为诗人的抱负,在尚未康复的情况下,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莱乌拉。不久,她和一个离了婚的男人结婚。婚姻的不幸给地带来巨大痛苦,并在她心灵上留下了创伤:
《我们女人》
我们女人,我们如此接近这褐色的土地
我们问布谷鸟它对春天期待什么。
我们展开双臂拥抱光秃的松树,
我们在夕阳中探究预兆和出路。
我曾爱过一个男人,他什么都不信⋯⋯
他两眼空空,在一个寒冷的日子走来,
他在一个沉重的日子离去,面带遗忘。
如果我的孩子死了,那是他的……
1916年,索德格朗发表了自己的第一本诗集《诗》。《诗》收录了63首。这些具有浓烈法国象征主义和德国表现主义色彩的诗,语感新颖,题材宽广:诗人吟咏秋天,森林里的湖泊,傍晚的花园等等等等,在写景同时,坦诚大胆地抒发了自己胸臆。除山水诗外,《诗》还吟咏了“生命”,“地狱”,“美”“痛苦”——“它给予我的生命最高的收获:爱情,孤独和死亡的面孔”。《诗》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爱情诗。这些诗大多是诗人亲身经历的写照,写得直接,真挚。其中最有名的是《白天在变冷……》
你寻找花朵,
找到了果实;
你寻找泉水,
找到了大海;
你寻找女人,
找到了灵魂——
你失望了。
《白天在变冷⋯⋯》这首诗只有短短四节,然而却传神地刻画了亲密与距离之间冲突以及一个女新的强烈自我意识,以及爱与恐惧,亲近与疏远,渴望与自由等现代女性的情感,清晰地表达了诗人的女权主义观点。索德格朗是第一个芬兰和瑞典诗人中谁清楚从女性意识说话时,她富有极强女性特色的语言,意象和形式使她成为现当代很多北欧女诗人的榜样。
《诗》的表达手法在北欧诗坛前所未有。但它却遭到了评论家们冷嘲和热讽。有一个批评家问《诗》的出版商是否想给瑞典语芬兰文学提供笑料。
尽管索德格朗的诗歌遭到读者和评论家的冷遇,但她遇上了一位发现了自己文学价值的人——20世纪芬兰最杰出的评论家之一女作家、女评论家黑格·奥尔森。黑格后来成了索德格朗的终生好友。索德格朗曾为黑格专程去看她写了一首题为《春天的秘密》的诗:
姐姐,你像一阵越过山谷的春风到来,
阴影里的紫罗兰弥散着温甜的满足。
我要把你带往森林最温馨的角落:
在那里互诉衷肠,述说怎样看见了上帝
三
从第一部诗集的发表,到第二部诗集的诞生这两年间,索德格朗的生活,感情和诗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冷遇和嘲笑深深刺伤了她,而不久爆发的十月革命和席卷诗人家乡的芬兰内战,使她陷入了贫因和饥俄。与此同时,她的病情开始恶化,死亡的威胁在逼近,然而,年轻的艾迪特并没有因此而屈服。她在尼采那里找到了精神支柱。1918至1920两年间,诗人发表了《九月的诗琴》,《玫瑰祭坛》和《未来的阴影》。这三部诗集充满了怒灼火焰和奇异的幻影。诗的语言比第一本诗集更加大胆,比喻和像征似乎完全来之下意识。诗人在《九月诗琴》序中写道:“我在某节奏下试着创作了一些具有反抗特点的诗歌,从而发现只有在绝对自由情况下,我才能够把握词语和意象,也就是说,牺牲韵律。我的诗可被视作粗旷的手绘图,至于内容的处理,我则让我的直觉服从在旁观望的智力的监督”
在这些具有强烈表现主义特点的诗中,心理感受把整个世界,甚至整个宇宙化作了精神世界,生命的意愿在藐视一切和突出凯旋的“我”上显得欣喜若狂。诗人要“打开天空的大门”,把“人眼看不到的美”馈赠给众生。在《存在便是胜利》中,她向世界喊出了“呼吸就是胜利,活着就是胜利,存在就是胜利”的声音。她把自己看作是太阳的女儿,站立在太阳上,“除了太阳,一无所知”;她是一个无拘无束的自由的未来人,一个创造者:
⋯⋯
我们这些轻狂,强大的陌生人
我们骑着松解的马鞍摇晃而来。
风会带我们向前吗?
我们的声音像一阵嘲笑从远方,从远方飘来⋯⋯
在题为《首先我要攀登钦博拉索山》一诗,诗人以乐观积极的口吻再次体现了尼采的权力意志和超人学说:
首先我要攀登自己国家的
钦博拉索山
站在那里,头戴桂冠
一望无垠。
然后攀登名望的山顶
世界金黄的麦田将对我微笑
幸福地站在那里
被玫瑰色风景簇拥。
最后我将攀登不可攀登的
权力的山顶,
星星将温和地微笑
为万物祝福。
诗人,一个孤独的病者,一个生活的局外人,把尼采视作自己的精神之父,她《在尼采的墓前》袒露道:
……
奇异的父亲!
你的孩子不会背弃你,
他们迈着神的脚步穿越大地
……
在尼采的影响下,索德格朗中后期的诗很多都以先知,女王,圣徒,神,上帝的口吻来表达自己的愿望,观点和感受。这也是她诗歌与其他现代主义诗人的最不同的地方,也是吸引读者的魅力所在:
我们都是无家可归的漂泊者
都是兄弟姐妹。
我们背着包裹,衣衫褴褛,
与我们相比,权贵们又拥有什么?
黄金不能衡量的财富
随清风向我们涌来。
我们越是高贵,
我们就越明白我们是兄妹。
我们只有付出自己的心灵
才能赢得自己的同类。
假如我拥有一座大花园
我会邀请我所有的兄妹。
他们每人都会从我这里一份贵重的礼物。
没有祖国,我们会变成一个民族。
我们将在花园四周修筑篱笆
隔绝来自世界的喧嚣。
我们恬静的花园
会给人类带来一种新型的生活。
这首《大花园》被认为是她最美的诗歌之一,写于1920年4月,当时她得了流感,家中十分缺钱,不得不把一些用旧的衣服卖掉换钱。但索德格朗认为读者和评论家不应该把诗中我和生活中的我混为一谈——她在给黑格的信中反复提到这一点。她很少记述自己那令人绝望的贫困生活,她认为生命是残酷的,生命继续,她就要继续。
索德格朗因此而创造了奇迹,让自己变成了超人,自己的上帝。她走了一条自己的路,用她偶像尼采的话说就是:“这世界只有一条路,这条路只有你能走。它通往哪儿?别问。走吧!”
她找到了自己,或生存的意义:创造了一种自己的生活,或身份。她由此而变成了无法逾越的表现主义诗歌代表:
《我必须徒步穿越太阳系》
在找到我红衣裙上第一根线头之前
我得徒步穿越
太阳系,
我预感到了这一点。
宇宙某个角落悬挂着我的心,
光从那里涌出,撼动空气,
涌向其他不羁的心。
这些诗凸显了一个强大的个性或灵魂,也展露了表现主义诗歌最典型的特点:让非理性的情感通过大胆的不相连贯的意象并列和自由的形式(有时甚至破坏传统语法,比如:站在那里,头戴桂冠/一望无银(谁一望无垠?山还是我?)创造了奇特的幻景:
美是每一片奢侈,每一朵火焰,每一次充溢,每一个巨大的贫困;
美是对夏天的忠贞,对秋天的裸露;
美是鹦鹉的羽衣或预示风暴的落日;
美是清晰的特征,独特的音调:这就是我。
……
对于索德格朗这样一个神经敏感,身怀疾病的人,只有这种充满酒神精神的惠特曼式的语句以及赤露呈现思想和情绪的表现主义诗歌才能满足她的要求:“我的诗歌不是描写而是表现内心情绪”(给黑格的信),而目的则在于:激活沉睡的激情,揭示事物内在的实质。
诗人把目光转向心醉神迷而不可触及的高邈境界。她写星星,写太阳,写星球,并俯瞰整个宇宙。以此超越平庸痛苦的世俗生活。在诗集《未来的阴影》中,索德格朗的渴求已经触及到了天宇,她的生命和创作已进入最后一个阶段。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生活越加穷困,肺结核病使她常常大口大口地吐血。她开始转向沉思,奉信给人类带来福音的基督教。《来来的阴影》发表后的两年,她沉默了。但她仍在用笔与死神搏斗着。这一时期写的诗收集在她死后的第二年(1925年)出版的《不存在的国家》。这些诗一反过去对力和美的迫求,节奏柔和,语言朴实,充满了平静,温和与安详。她从染着太阳金色的阿尔卑斯山峰,高天汹涌的星星转向自己童年的树,并从树那里得到了自己生命的秘密:
我童年的树高高地站在草丛中
摇着头:请问结果怎样?
……
而今我们要告诉你生命的秘密:
打开所有奥秘的钥匙放在长着覆盆子的草坡上。
透过诗中的平静,我们看到这些在敞开着的死国门前写下的诗的背后,有着一场何等超人的搏斗。这位贫困潦倒,病入膏盲的女诗人终于在偏僻的荣乌拉安然地接受了死亡,并由此超脱了自己的命运:
我们应该像珍惜沙漠开花的瞬息那样
去爱被病魔纠缠的漫长岁月
和闪烁希望的短暂时光。

伊迪特·伊蕾内·索德格朗(1892-1923),芬兰著名的瑞典语女诗人。16岁时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疗养期间濒死和失恋的经历为她后来的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代表诗作有《诗》(1916)、《九月的竖琴》(1918)、《玫瑰祭坛》(1919)、《未来的阴影》(1920)等。1923年,诗人死于肺结核和营养不良,年仅31岁。她是北欧文学史上最早的现代主义作家之一,深受法国象征主义、德国表现主义、俄国未来主义的影响。她在世时没有获得读者和文学界的认可,但是后来人们发现了她的作品的文学价值,被认为是北欧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
诗人李笠,翻译家。1961年生于上海,1979年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瑞典语系。1988年移居瑞典,在斯德哥尔摩大学专修瑞典文学。出版有《水中的目光》(1989)、《栖居地是你》(1999)、《原》(2007)等6本瑞典文诗集,并荣获2008年“瑞典日报文学奖”和首届“马丁松时钟王国奖”等诗歌奖项。翻译包括索德格朗诗选《玫瑰与阴影》,瑞典当代诗选《冰雪的声音》以及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全集》等北欧诗歌,此外还翻译了《西川诗选》、《麦城诗选》等中国诗人的作品。兼事摄影,出过《西蒙和维拉》(2011)、《诗摄影》(2014)等摄影集,还有五部诗电影曾在瑞典电视台播出。
来源:诗歌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