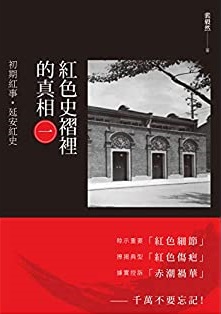 《红色史褶里的真相》第一辑: 初期红事(3)
《红色史褶里的真相》第一辑: 初期红事(3)
五四工读互助运动之兴亡
1919年底~1920年春,五四新文化运动进入高潮,京沪等城一度出现「工读互助」运动。从思想酝酿到正式筹款成立,前后近半年。打头的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一组,仅仅维持两个多月便告解体。1920年上半年,该运动在全国各大城市相继熄火。这一原本很有意蕴的「共产」预演,不仅当时未能引起知识界警觉,近百年来亦未得史学界开掘总结,未能对乌托邦的社会改造方案拉响警报。如今回首这一运动,可看出「大锅饭」之所以烧不起来的一系列深层次原因。
运动初兴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勤工俭学风行全国,一些无力远赴法国的贫家学子,或不愿去国的中产子弟,仿习欧美,在京沪津宁汉穗等城办起「工读互助团」,浙江、湖南平江等地亦有回应。1919年12月4日,少年中国学会执行部主任王光祈,在北京《晨报》发表〈城市中的新生活〉,提出组建工读互助团。「不到二、三日便有数十位同志来信愿从事此种生活;一星期后,外省亦有许多同志来信讨论此事。」[1]
王光祈(1892~1936),川籍学子,1912年毕业于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堂,1914年赴京,入中国大学攻读法律,兼职清史馆,先后担任《四川群报》驻京记者、《京华日报》编辑。1918年与李大钊、曾琦等七人发起「少年中国」学会(成员最多、影响最大的五四社团,即后青年党之基础),1919年7月1日成立大会,王光祈被推执行部主任。「少年中国」学会社员108人,知名者毛泽东、邓中夏、左舜生、张闻天、恽代英、高君宇、李达、缪伯英、蔡和森、赵世炎、许德珩等。
王光祈发愿宏大,工读互助团有明确理论:「人类分为三个阶级——知识阶级、劳动阶级、资产阶级。理想的无阶级社会该是知识阶级同时便是劳动阶级,劳动阶级同时便是资产阶级。」而达到这一胜境的途径只有:知识阶级中有觉悟的青年到农村与工厂去,将知识传授给劳动阶级,有创造力的华侨应兴实业办教育。如此这般,可消弭阶级。1919年底,王光祈发表〈城市中的新生活〉,建议组织「男女生活互助社」,帮助青年脱离顽固的家庭压迫。[2]
该团旨在帮助青年半工半读,维持生活与学业,成功离开「旧家庭」,达到教育与从业相结合——「人人作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王光祈的宣言是「平和的经济革命」,一种「城市中的新生活」;每天做工六小时,读书三小时,其余时间娱乐及自修。[3]上海工助团也为挣扎于底层的青年寻找出路:「替一般埋没于旧社会恶制度底下的青年,另造一种新组织新生活。」[4]
1919年底,王光祈奔走一月,得到李大钊、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周作人、张申府、高一涵、陶孟和、罗家伦等16位社会名流赞助,募款一千,在京创建第一个工读互助团。该团主要规定为四:一、团员每天须做工四小时;二、团员衣食住宿,均由团体供给;三、团员所需教育费、医药费、书籍费,由团体供给,书籍报刊为团体公用;四、工作所得收入归团体公有。
1919年12月,毛泽东在长沙撰文拥护「新村运动」——
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新学校中学生之各个,为创造新家庭之各员。新学校之学生渐多,新家庭之创造渐多。合若干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敬老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医院、公园、博物馆、自治区。[5]
青年毛泽东对新村运动的这番描绘,被认为是毛泽东1958年发起公社化运动的思想先导。
1920年3月,湘籍学子彭潢、毛泽东在上海发起上海工读互助团,在《申报》刊载〈上海工读互助团募捐启〉。上海团的章程略有差别:一、团员每天作工六小时,若生活费尚不足支持,由团员公议增加作工钟点;二、共有四项工作:平民饭店、洗衣店、石印、贩卖商品及书报,所得均归团体;三、会计等事务员每月选举一次;四、凡怠工并经三次集体劝告无改进者,即请其出团。[6]
运动初兴,震动全国,各地来函数百封,报名者犹如过江之鲫。好奇、冲动、喜好尝试……乃青年普遍特点。运动发起人(主要为王光祈)对入选「团员」有一番相当审慎的选择。[7]北京工读互助团成立后,沪津宁汉穗及长沙、杭州、扬州等城也陆续成立各种名称的工读互助团。1920年5月,北京大学校刊上有人呼吁将此运动推广到中学生。[8]
然仅仅半年,声势浩大的工读互助运动便无声无息消亡了。1920年,王光祈赴德留学。陈独秀、李大钊、恽代英、毛泽东、施存统……纷纷热衷建立共产主义小组。
思潮来源
克鲁特泡特金的互助理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和人道主义,乃工读互助运动的思想滥觞。这一思潮希望通过协作互助、平等劳动改变现实,进而对社会实现和平的渐进式改造,建立一种全新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协力与自由、互助与独立的社会组织——「新村」。
中国工读互助团运动的直接源头为日本的「新村运动」。1918年12月,日本著名作家武者小路实笃(1885~1976),在他主办的《新村》杂志上发表一首诗,对中国有人认同他的新村主义表示狂喜。是年,武者小路实笃在日本九州开展新村实践活动,周作人极为关注,1919年7月赴日实地参观,将其引入中国,促成新村主义于五四前后在中国风行一时。
1918~1919年,周作人撰写多篇文章介绍新村主义,如〈日本的新村〉、〈新村的理想与实际〉等。
主张泛劳动,提倡协力的共同生活。一方面尽了对于人类的义务,一方面也尽了各人对于各人自己的义务;赞美协力,又赞美个性;发展共同的精神,又发展自由的精神。实在是一种切实可行的理想,中正普遍的人生的福音。[9]
周作人对新村的热情并非一时之兴。一战后,时局动荡、社会迷茫、思潮丛生,周作人担忧暴力变革将带来乱象,但又希望能找寻到解决时弊的新式改造道路。新村主义构建的个人与集体、独立与互助、脑力与体力、物质与精神、肉与灵的融合模式,周作人认为「顺了必然的潮流」、又可避免「将来的革命」,恰好契合他的需求。1920年2月,周作人在《新青年》登载启事:
凡有关于新村的各种事务,均请直接通信接洽。又如有欲往日本实地考察村中情形者,本支部极愿介绍,并代办旅行的手续。
「支部」,即新村中国支部,所在地即周氏兄弟居住的北京八道湾胡同十一号。
1920年,在周作人介绍下,北大学生游日团、北京高师工学会成员,访日期间参观新村东京支部,极大鼓励了日本新村运动者。1920年,留日生王拱璧(1886~1976)在河南老家(西华县孝武营)建立「青年村」,开展新村运动。王光祈的北京工读互助团,即分娩于这一时代氛围之下,也可以说日本新村运动在中国的「着床」。
「团员」施存统认为「工读互助」乃推动社会改革途径:
对于工读互助团抱有莫大底希望,希望将来底社会都变成工读互助团!就是成为一个工读互助的社会。
终极目标是改造社会,实现世界革命。首先在「团」里实行:一、脱离家庭;二、脱离婚姻;三、脱离学校;四、绝对共产;五、男女共同生活;六、暂时重工轻读。胡适称这些宗旨为「武断地解决问题」。[10]
北京团
北京工读团成立后分四小组。第一组北京大学附近,骑河楼斗鸡坑七号;第二组北京专门工业学校、高等法文专修馆、北京师范学校附近,西城翠花街狗尾巴胡同五号;第三组女高师附近东城北河沿,团员全是妇女,称「女子工读互助团」;第四组在景山街东松公府夹道八号。[11]
1919年秋,浙江第一师范二年级生施存统撰文〈非孝〉,提出打倒「不合理的孝和行不通的孝」,引发轩然大波。受到打压的施存统与三名同学从杭州赶赴北京,加入工读互助团。
第一组成员施存统理解的工读互助运动:
工是劳力,读是劳心,互助是进化。工读互助,是人的生活;工读互助团,是做人的团体。我们以为要做人,就要入工读互助团。……一边劳力,一边劳心;终生工作,终生读书……
施存统反复强调,这是个「终身以之」的团体,「我即是团、团即是我」(无限将来都从这两句话里表见);「团的利害,就是个人的利害」。玄庐的赞美诗:
1920年前/额汗眼泪化余钱/1920年后/富贵功名不如狗……工即是学,学即是工。[12]
富家子俞秀松(父亲秀才)离家出走,抵达北京后,即入第一组,1920年3月4日致函父母:
我来的目的是:实验我底思想生活,想传播到全人类,使他们共同来享受这甘美、快乐、博爱、互助、自由……的新生活,才算完事![13]
与家庭决裂的快感,个体理想的书写,工读互助团员们青春热情,气血贲张,满怀激情地投入陌生清新的生活。第一组的团员洗衣服、制作信纸信封,尽管「收入都很少」,他们还是夜以继日、不知疲倦。很快,第一组的「俭洁食堂」也开张了,他们骄傲地贴上对联:「宁流额上汗,毋染手中血」。
第一组十三名青年的集体生活,起初异常融洽,相互视为同志,每周至少开会一次,讨论工读互助运动的未来。傅彬然回忆:
曾经把团员的衣服都集中起来,分类放置。只要谁爱穿,谁都可以自由捡来穿。这是我们对所憧憬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美好理想的尝试……
他们告诫自己:献身、实践、改良、创造,要成为这个「万恶社会的保险团体」,成为未来「少年中国的模范团体」。他们告别过去,兢兢业业充当起伙计、跑堂、业余教师、手工匠人乃至洗衣工、洗碗工,忘记自己曾是少爷、洋学生、中产子弟。
他们经过三番五次讨论,拟定宏大计划与具体步骤——
第一步巩固团体底基础……第二步扩张我们底团体,实行主义的宣传。第三步联络各处的同志,结成一个大团体,实行世界革命。[14]
第二组的内容有五:平民消费公社、平民实习学校、平民洗衣局、平民工厂(小型作坊式)、食堂。1920年2月15日在《晨报》上宣布:
精神方面非常团结,财产物饰之类均不分彼此,团内亦无繁琐规则,行动以不碍良心及人格为准绳,此皆可为吾人效法也。[15]
当时各地生活费、学费差异较大。广州大学生一年需要八九百元,上海四五百元,北京二三百元。专科生毕业修学四年,大学本科毕业六年,以最低的北京计算,也要1500~2000元。[16]中学生每年学费亦在六七十元。[17]北京组织「工读互助团」成本最低,按说成功概率甚高。「工读互助团」最初预算每人每月10元:房租1.5元、伙食3元、学费2元、衣服1元、书籍1元、医药费1.5元。后北大特准免费旁听、图书馆亦对团员免费开放,每月人均七元即可。[18]
共产分歧
许多参与工读互助运动的青年,纯粹凑热闹。以第一组为例。1920年1月20日,《新青年》刊载十五位成员名单,章铁民、张树荣、吴名世、(何)孟雄、焕业、施存统、(俞)秀松、党家斌、俞鸿、周方、彬然、百棣、张伯根、仰煦、周昌炽。仅仅两天,《晨报》又一则新闻,「家斌、周方二人,现已出团,故不列入……」
第二组团员十一人:王恕、郭会楷、张衡沛、张纯、刘晦、刘豪、罗汉、李实、匡侩、欧逊、訾久。[19]
1920年2月4日,第四组租定东城松公夹府道八号,先成立消费社随即筹备织袜厂,不日即可开工,并蒙蔡元培允许入北大旁听。这一组团员原十人,[20]因一人赴法,是为九人:张俊杰、赖庆祝、杜大学、李深荫、赵鸿恩、张遂能、刘鑫、蒲照魂、吴时英。[21]
矛盾很快来临,频频引发冲突。《工读互助团简章》明文规定「收入归公」,团员最初对此并无分歧。但组团之后,一些成员不时收到家里汇款,这部分收入该不该归公?要他们缴公,这几人不太愿意。但不归公,工读互助意义何在?几名团员兜有余资,大部分团员节衣缩食,口袋空空,贫富不均,有失平衡,「互助团」如何维持下去?几笔家长汇款,引发小组关于「共产」的争论。
争论结果:一、大部分成员决议共产,认为家中汇款应缴公;二、五位主张不合者要求退团。五人退团前夕,「团体非常紧张,差不多要破裂的样子」。王光祈非常着急,「跑到我们团里来,向我们几个主张激烈点的人疏通……主张不要太趋极端。」[22] 施存统等人认为,「共产」关乎工读互助理想之根本,万难迁就。
脱离家庭
「共产」风波后,接踵而至的是「脱离家庭」。
坚持不散的工读互助团成员认为:为什么会发生「共产」之争?根子在于老朽腐烂的旧家庭制度,不脱离旧家庭,团体将时刻笼罩在它的阴影下。不破坏旧家庭制度,美好的工读互助社会就难于产生。施存统认定:「家庭制度是万恶之源,非打破不可,脱离是打破之先声。」由此引发一场旷日持久、「极伤感情」的争论。争论尚未结束,又一人退团。全体决议脱离家庭后,又两人退团。
八名成员退团前后,另有六名青年先后加入第一组。这样,第一组仍有十名成员,观点上「全体一致」。第一组中有后来声名赫赫的中共党员施存统、俞秀松、何孟雄、缪伯英(何孟雄妻)。
接着讨论婚约,认为「离婚的离婚,解约的解约」;讨论学校问题,「凡是从前在学校里的都退出来改为旁听生」;男女共同生活问题,女团员缪伯英的态度比大多数男青年还要激进。施存统回忆:
这几个问题解决之后,精神上很有几天愉快。我们那时以为我们底无政府、无强权、无法律、无宗教、无家庭、无婚姻的理想社会,在团里总算实现一部分了,所以精神上非常快乐。[23]
经济危机
一两个月后,经济问题成为工读互助团的普遍危机。施存统留下了一份饶有意味的账单,折射出工读互助团的必然命运。
第一组「勤工」营生为五:放电影、洗衣报、印信封、办食堂、英算专修馆。电影股四人,1月20日领取130元开办费,在各大高校轮流放映。这份营生颇让团员兴奋。电影符合青年性情,而且很轻松,「不过只管收票卖票的事情」。最初生意兴隆,「在女子高等师范演了三次,承他们同学的好意,高兴来看,每次卖了二百左右张票。」此后,生意时好时坏。寒假前夕,「一连好几天生意冷落」。一个多月后结帐,除收回130元成本,盈余仅30元。这还主要靠女高师的连映三场,靠女生捧场。此后,生意清冷,连连赔本,于是匆促开会,议定电影股解散。
接着被停掉的是印刷业务。分信纸信封两种,「做的人一个二个不一定」,利润微薄,不时滞销;一个多月「大概赚三元」、还不够饭钱,只得「办理结束」。
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洗衣股。洗衣股投资40元,四个人,每天作工五小时,最初只能洗自己的衣服,三四天收了「还不到二十件衣服」。无奈,施存统只好去找学生宿舍的斋夫(门房),让斋夫们帮忙代收。斋夫帮洗衣局收衣服,每件得2%报酬,工读团加至3%,「我们以为这样一定可以有衣服洗了,那知仍旧不然!」斋夫转身以工读团的3%向洗衣局要价,「他一定向洗衣局要求百分之四或百分之五!」施存统去斋夫房收衣服,竟和洗衣局收衣的狭路相逢,既难过又郁闷。洗衣股办了两周,收入仅七十几枚铜子,而且,「夺平民的生计,究非我们底本心。平民是我们很亲爱的朋友,断无损害亲爱的朋友底道理。」工读团的住地也不适合洗衣,没有晾晒场所。七七八八一来,洗衣股「理所当然」地停办歇业。
更大的危机是食堂股也办不下去了。食堂在北大沙滩附近,以北大师生为主要客源。一开始,三间房、五张桌的「俭洁」食堂生意兴隆。两个多月后,扩大规模「另租两间房子,增添五张桌子」。可增添桌子后,「生意既不发达,开销又比以前大」。十几天后,食堂工作的八个人,「连这八个人底饭都没得吃!」「平均每天十二个团员在食堂里吃饭,都要拿出大洋一元五角。」即每天亏垫1.5元。
施存统:「食堂无异是我们底根据地」,「差不多我们这回失败,形式上都是它的缘故。」[24]直到此时,施存统还没有发现食堂失败的真正原因。食堂大部分收入来自学生的「包饭」,进店顾客很少,扩大店堂规模,徒增开支,无助生意。王光祈很诧异:
据一月以前我在北京的观察,食堂营业万无折本之理,此次亏折,实出意外。[25]
五种营生中最赚钱的竟是仅两名团员的英算专修馆,每月二三十名学生,收入四五十元。但两名从业团员的感受:「究非我们所愿做的工作呵!」
第二组的「平民消费公社」,以非赢利为宗旨:「欲使一般平民之正当消费不受贪鄙无厌之资本家所垄断」,绝不售卖妨碍健康的烟酒药物,凡消费两元以上者可电话通知,送货上门。饶是如此,仍无法扩大营业。
无奈散伙
1920年3月23日,因无法维持生活,「团体已不能一日存在!……万难支持」,工读互助团第一组解散了。施存统:
这个时候,差不多大家都对于这个团体都没有十分感情,除出一二人以外,都不愿去维持它。三月二十三日开一个会,议决各人自由另找工作。工读互助团底主张,从根本上推翻![26]
不到三月的工读互助团宣告失败,3月26日俞秀松回沪。[27]
第一组的解散,再次震动全国。4月1日,《新青年》第七卷第五期,王光祈、陈独秀分别发表文章,探讨第一组失败根源。在〈为什么不能实行工读互助主义?〉的标题下,王光祈的副标题——是人的问题,不是经济的问题。
王光祈列举了种种问题,人浮于事、浪费较多、经营不善、感情不洽、「互相怀疑」、精神涣散、一些人「不肯努力作工」、一些人不了解工读互助团「深厚远大的意思」……他反思自己的责任:虽经审慎挑选,但知行合一的团员「实不多见」、「今日演出此种现象,完全是我当日急于组织成功的罪恶!」[28]
1920年5月正式成立的上海团,主要团员彭潢、毛泽东、罗亦农、袁达实、张文亮等,租居上海民厚里几间房,共同做工共同读书、有饭同吃有衣同穿。6月,彭潢、毛泽东回长沙,该团终止。[29]
易群先事件
最令施存统耿耿于怀的,乃是他一语未及便令第一组「感情大坏」的易群先事件。易群先乃国会议员易夔龙之女,反对父亲安排婚姻,出走北京参加工读互助团。她漂亮、活泼、大胆,「差不多每个团员都喜欢她」。一天,易群先告诉施存统,她与何孟雄自由恋爱了。这句话引起轩然大波。
施存统后来说,他对此「又惊又喜」。几天后,几名团员连夜开会,以妒怒交加的态度逼迫何孟雄承认错误。这对情侣不服,易群先避走天津。几名团员决议驱逐何孟雄、施存统、陈公培。
王光祈认为这是「人的问题」的明证。1920年3月28日,陈独秀也撰文认为是「人的问题」,他转引第一组一位成员来信:
北京第一组的失败,千万不要使旁的工读互助团说什么办不得;老实说,实在是人的问题,只可说第一组的人失败了,并不是工读互助团不能办。[30]
分析败因
从表面看,原因很简单:依靠募捐发起,失去财力散伙,工读互助团无法依靠自身运作维持,失去经济支撑,只能解散。但深层次的原因却在于麻烦的以共产为核心的价值观。理想化的设计势必碰撞多棱面的人性,「共产」未能通过实践检验。但绝大多数运动参与者、赞助者归败因于人事。王光祈总结:
这次失败,就是不善经营、不善计算、不善办理,别无他故。所以我认为不是经济问题,而是人的问题。[31]
检讨局限于团员个人的主观因素,未能透过现象看本质,挖掘出「共产」设计这一核心败因。
工读互助团发起不久,胡适就持怀疑态度。一次演讲中,胡适批评工读互助运动「名实不符」。他说,十七名发起人中——
有几个人的目的并不注重工读,他们的眼光射在「新生活」和「新组织」上。因此只做了一个「工」的计划,不曾做「读」的计划……
胡适的批评对象是王光祈、陈独秀。胡适认为,这是计划的「根本大错」。因为「工作的时间太多……没有做学问的机会」,工读变成「挨役」、「只有做工的苦趣,没有工读的乐趣」;「但他们对于家庭、婚姻、男女、财产等等绝大问题,都早已有了武断的解决,都早已定为成文的戒约了」。
胡适说美国至少有几万人过着工读生活,极平常极现实:
工读主义只不过是靠自己的工作去换一点教育经费,是一件极平常的事……算不得什么「了不得」的新生活
用不着挂什么金字招牌……如不能使团员有自修求学的工夫,那么,叫他泛劳动主义也罢,叫他新组织也罢,请不要乱挂「工读主义」的招牌。
胡适还分析:
米可以合买,房可以合租,厨子可以合雇。但共产尽可以不必。为什么呢?因为我也许愿意用我自己挣来的钱去买一部鲍生葵的美学史,但是你们诸位也许多用不着这部,我还是买呢?还是不买呢?最好是许团员私有财产。[32]
王光祈、陈独秀、胡适等还在工读互助团范围内探讨败因。施存统则认为败在「感情不洽」,俞秀松再添三因:「工作不尽力、不肯协力商量办法、消费的办法」。[33]陈独秀认为失败在于:「我相信他们这回失败,完全是因为缺乏坚强的意志、劳动习惯和生产技能三件事;这都是人的问题,不是组织的问题。」[34]
但戴季陶、施存统则认为工读互助团的失败乃是社会黑暗,无法容忍青年的改良式尝试,将社会改革推向更宏大的范围。1920年4月1日,这位深研马克思主义、翻译《资本论解说》的国民党理论人物,于《新青年》发表〈工读互助团与资本家的生产制〉,以「剩余价值」为基础解析工读互助团的败因。
戴季陶认为工读互助团的失败根源在于财产私有制、资本家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压迫着大多数人群,工读互助团成员生活困难;作工时间不断增加,四小时到六小时、八小时,乃至十小时,只「工」难「读」;不仅不能以「工读互助」作为改造社会的方式,也不能达到「半工半读」之目的。戴季陶还认为在现实中,「独善其身、独善其家、独善其国,都是不可能的事情」。戴季陶号召有志青年「投向资本家生产制下的工厂去!」因为——
时间问题、工银问题、幼年保护问题、妇女保护问题、社会的保险、劳动者住宅、教育、娱乐、慰安,这些问题的各个解决,都是只有靠劳动者的团结与奋斗才可以解决得来的。[35]
即只有依靠工运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中共仇为国民党「极右」的戴季陶,左得如此可爱呢!
22岁的施存统发表了万字〈「工读互助团」底实验和教训〉,施存统的这篇文章后被反复转载、不断引用。施存统认为「散伙」的直接原因是「群先离团、外面攻击、适之演说,于是感情大坏、精神愈散,团体已不能一日存在。」和戴季陶一样,施存统将失败归因于社会——
现社会的组织是资本主义的组织,一般平民都做资本家的奴隶;
凡是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底下……都要直接间接受经济的压迫。
施存统甚至说赚了一些钱的电影股,承蒙「女师」姑娘们的好意,但「她们的钱是哪里来的?」英算专修馆学生大多是富家子弟,还不是替资本家作工!不管愿意不愿意,承认不承认,活在这个社会、这种秩序里,都参与乃至赞助着资本主义的运转!
他的归结是:
我们并不因此怀疑共产主义。我们因此更信共产主义。……我们最敬爱的朋友,不要因为我们一时的失败,就去怀疑神圣的主义!
我们如果有能力把资本家所掠夺去的资本收得回来,那才不至于受经济的压迫。
从这一次的工读互助团的试验,我们可以得着二个很大的教训……(一)要改造社会,须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枝枝叶叶地一部分的改造是不中用的。(二)社会没有根本改造以前,不能试验新生活。不论工读互助团和新村。
如果要免除这些试验新生活的障碍……惟有合全人类同起革命之一法![36]
施存统致函马哲民:
要拿工读互助团为改造社会的手段,是不可能的。要想在社会未改造以前试验新生活,是不可能的。要想用和平的渐进的方法来改造社会的一部分,也是一样的不可能的。……改造社会要用急进的激烈的方法,钻进社会里去,从根本上谋全体之改造。[37]
俞秀松回沪后宣称:
我此后不想做个学问家(这是我本来的志愿),情愿做个「举世唾骂的革命家」。
俞秀松在陈独秀的安排下,先入《星期评论》杂志,一周后,为「打破知识阶级的观念」,改名换服到虹口厚生铁厂,一面做工一面教学,宣传赤色思想,走与劳动人民相结合的道路。[38]
「点滴」的失败,提炼出必须全面推进社会改革。社会改造当然得从点滴开始,明明应寻找「点滴」失败的客观原因,挖掘不符合人性人情的悖谬,先找找自身问题,反而「枪口对外」,责怪社会不配合自己,倒过来从社会客观方面寻因。逻辑能力如此谬弱,思维层次如此低下,当然说明五四一代学人的不成熟,也是二十世纪中国的大不幸。
仅须摘选一段五四言论,便可窥知当年左士思想层次之低、立论之偏:
现在中国的社会,是受教育的人不能做工,做工的人不能受教育。受教育的人不能做工,所以教育几成一种造就流氓的东西;做工的不受教育,所以职业几成一种造就奴隶的东西。[39]
指教育「造就流氓」,指做工「造就奴隶」,如此歪斜偏激的视点,能够走向正确么?能够得到正确结论么?
罗亦农等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沪滨工读互助团的解散宣言〉:在有阶级的社会里,搞「新村」是改良主义的幻想,如不推翻剥削阶级的制度,永远达不到世界大同的境界。1920年8月22日,陈独秀约集俞秀松、叶天底、袁振英、金家凤等八人在上海霞飞路渔阳里六号发起社会主义青年团。[40]
一场小范围的共产尝试失败,竟成为必须进行更大范围红色革命的论据,如此不成逻辑的「逻辑」,极左思潮就这样从思想文化渐渐放射发酵,从形而上走向形而下,推耸赤潮涌动掀腾。
历史证明胡适是正确的,工读互助运动的失败,实乃「宗旨」之误。「互助」固然不错,也可行,然「共产」违悖人性人情,现实尚不具备均产的可能性。人心趋利,公产势必形成「短板效应」——向最低凹处看齐,压抑各种积极性。人性本私,大多数社会成员不可能「高尚奉献」、不愿因「共产」而失去种种自由。同时,个人素质、能力不均等个体差异亦不可能支援终端的「共产」。更重要的是人类社会已找寻到一条更高明更合理的发展通道,既产生效率又兼顾公平:通过累进税制、遗产税、慈善义捐,既鼓励强者积极创造财富,又兼顾弱者分享社会发展均值。
共产制只是一种原始幼稚的设计方案,既肤浅又无实际操作的客观可能性,还大幅降低生产效率,连带着破坏原本相对和谐的人际关系。这么一点点认识,这么一小步,中国思想界竟走了近百年,相当一部分左士至今尚未走出来哩。
尾声
1920年12月,周作人不得不失望承认「新村不易普及」。1921年后,周作人与日本《新村》的联络日渐减少。1924年,《新村》杂志虽仍列入北京支部,但周作人已心灰意冷,表示新村主义不过是个「蔷薇色的梦」。施存统勤工俭学去了法国。王拱璧河南家乡的青年村,坚持六年后于1926年宣告失败。
1925年夏,少年中国学会在南京举行年会,已分裂成国家主义与共产主义两派。与会者方东美记述:
双方争到激烈,拳不停挥,口沫四溅,各以杀头相威胁。当时若手枪在手,恐已血流成河矣。[41]
临分手,邓中夏对左舜生说:「我们以后疆场上相见吧。」南京年会成为少年中国学会的「葬礼」。工读互助团不少成员加入中共,施存统还是PY(共青团)创建人、中共旅法支部创始人之一。少年中国学会大部分成员都选择了中间道路,也有一些人成为中共要角——毛泽东、赵世炎、张闻天、恽代英。王光祈则坚持努力促进各项社会事业,希望国民精神与物质上都得到满足,最后走上音乐救国的道路。[42]
五四运动前后,北大出现三份大型学生刊物,分别代表左中右三派。左翼《新潮》、右翼《国故》、中派《国民》。「这些刊物都是由学生自己写稿、自己编辑、自己筹款印刷、自己发行,面向全国,影响全国。」[43]三份刊物标志性地代表一代青年的思想分裂,理想目标不一、图纸红白各异、标准差异太大,思想很快演变为行动,文斗最终转化为武斗,国共分裂实为「历史必然」。
1927年武汉「七·一五」,时任武汉中央军政学校政治部主任的施存统,在武汉各报发表〈悲痛中的自白〉,声明脱「共」入「国」,教书、翻译为生,1945年参与组建「中国民主建国会」,1949年后一度出任中共政府劳动部副部长。
1920年4月1日,王光祈以上海《申报》、《时事新报》及北京《晨报》特约通讯员身分远赴德国,开始研究经济学,1922年改学音乐,考入柏林大学音乐系,1934年获波恩大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中国古典戏剧〉。1936年1月12日,王光祈突发脑溢血骤逝波恩。南京追悼会上,徐悲鸿画像,蔡元培致悼词。1938年,骨灰辗转回到成都。1941年冬,李劼人葬王光祈骨灰于成都东郊沙河堡菱角堰侧。1983年10月,王光祈墓碑迁入四川音乐学院,建立碑亭。[44]
(与2011级硕士生厉彦美合作)
2013-1~3 于沪·三湘
[1] 王光祈:〈工读互助团〉,《少年中国》(北京)第1卷第7期(1920-1-15),页42。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2册,1985年6月编印,页116~123。亦可参见《五四时期的社团》(二)
[2] 郑学稼:《中共兴亡史》,中华杂志出版社,页490。转引自王章陵:〈匪区学校工读制度之研究〉,《匪情月报》(台北)第14卷第1期(1971-2-28),页63。
[3] 王光祈:〈工读互助团〉,《少年中国》(北京)第1卷第7期(1920-1-15),页42。
[4]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出版1995年3月第2版,页678。
[5] 毛泽东:〈学生之工作〉,《湖南教育月刊》第1卷第2号(1919-12)。
[6] 〈上海工读互助团募捐启〉,原《申报》(上海)1920-3-7。参见《毛泽东早期文稿》,页676~678。一说原《星期评论》第40期(1920-3-7),选自《五四时期的社团》(二),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2册,1985年6月编印,页124。
[7] 王光祈:〈为什么不能实行工读互助主义〉,《新青年》(北京)第7卷第5号(1920-4-1),页14。
[8] 郑年:〈提倡「工读互助」在中学里面实行的办法〉,《北京大学日刊》1920-5-6。参见《北京大学日刊》(第五册),人民出版社(北京)1981年(影印本)。
[9] 周作人:〈日本的新村〉,《新青年》(北京)第6卷第3号,页266~278。
[10] 存统:〈「工读互助团」底实验和教训〉,《星期评论》(上海)劳动纪念号,1920年4月,页1。
[11] 〈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二组之进行〉,《晨报》(北京)第415号,1920-2-15。
[12] 玄庐:〈工读互助团〉,《星期评论》(上海)1920-2-8,页4。
[13] 俞秀松:〈寄给家人照片后面的附言〉(1920-3-4,北京),《红旗飘飘》第31集,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1990年,页233。
[14] 存统:〈「工读互助团」底实验和教训〉,《星期评论》劳动纪念号(上海),1920年4月,页1。
[15] 〈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二组之进行〉,《晨报》(北京)1920-2-15。
[16] 陈东原:〈顾孟余氏工读互助论〉,《晨报》(北京)1922-11-27。
[17] 郑年:〈提倡「工读互助」在中学里面实行的办法〉,《北京大学日刊》1920-5-6。
[18] 王光祈:〈为什么不能实行工读互助主义〉:《新青年》(北京)第7卷第5号(1920-4-1),页14。
[19]〈北京工读团消息〉,《新青年》(北京)第7卷第3号,1920-2-1。
[20] 〈工读互助团将设第四组〉,《晨报》(北京)第394号,1920-1-24。
[21] 〈工读互助团第四组报告书〉,《晨报》(北京)第418号,1920-2-18。
[22] 存统:〈「工读互助团」底实验和教训〉,《星期评论》(上海)劳动纪念号,1920年4月,页3。
[23] 存统:〈「工读互助团」底实验和教训〉,《星期评论》(上海)劳动纪念号,1920年4月,页3。
[24] 存统:〈「工读互助团」底实验和教训〉,《星期评论》(上海)劳动纪念号,1920年4月,页1~3。
[25] 王光祈:〈为什么不能实行工读互助主义〉:《新青年》(北京)第7卷第5号,1920-4-1,页15。
[26] 存统:〈「工读互助团」底实验和教训〉,《星期评论》(上海)劳动纪念号,1920年4月,页3。
[27] 俞秀松:〈给骆致襄〉(1920-4-4),《红旗飘飘》第31集, 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1990年,页236~237。
[28] 王光祈:〈为什么不能实行工读互助主义?〉。原《新青年》(北京)第7卷第5期(1920-4-1)。选入《五四时期的社团》(二)。参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2册,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1985年6月编印,页127~128。
[29]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3月第2版,页678。
[30] 独秀:〈工读互助团失败底原因在那里?〉,《新青年》(北京)第7卷第5号,1920-4-1,附录〈工读互助问题〉,页17。
[31] 王光祈:〈为什么不能实行工读互助主义〉,《新青年》(北京)第七卷第五号(1920-4-1),页15。
[32] 胡适:〈工读主义试行的观察〉,《新青年》(北京)第七卷第五号(1920-4-1)。参见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页559~563。
[33] 存统:〈「工读互助团」底实验和教训〉,《星期评论》(上海)劳动纪念号,1920年4月,页4。
[34] 独秀:〈工读互助团失败底原因在那里?〉,《新青年》(北京)第7卷第5号,1920-4-1,附录〈工读互助问题〉,页16。
[35] 季陶:〈工读互助与资本家的生产制〉,《新青年》(北京)第7卷第5号,1920-4-1,附录〈工读互助问题〉,页8~11。
[36] 存统:〈「工读互助团」底实验和教训〉,《星期评论》(上海)劳动纪念号,1920年4月,页1~4。
[37] 〈存统复哲民〉,《民国日报》(上海)1920-4-11,「觉悟」副刊。
[38] 俞秀松:〈给骆致襄〉(1920-4-4),《红旗飘飘》第31集, 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1990年,页234~237。
[39] 〈介绍上海工读互助团·上海工读互助团募捐启事〉,《星期评论》(上海)1920-3-7。
[40] 李文宜:〈亦农,怀念你闪光的26个春秋〉;邵水荣等:〈不愿跪着生,宁愿站着死的叶天底〉;《红旗飘飘》第31集,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1990年,页133、123。
[41] 周宝三编:《左舜生先生纪念册》,台湾文海出版社(台北)1981年,页45。
[42] 任鲁萍:〈少年中国学会的分化及其历史启示〉,《中共党史研究》(北京)1992年第4期,页18。
[43]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三联书店(北京)1989年第2版,页333。
[44] 张阳普:〈毛泽东惦记中的王光祈〉,《党史文苑》(南昌)2008年第23期,页37。
原载:《世纪》(上海)2014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