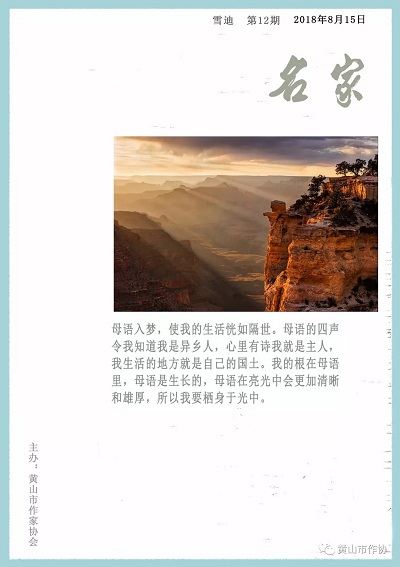
雪女:你是1990年应美国布朗大学邀请,任驻校作家与访问学者。这之后就留在此校工作的吗?
雪迪:我是在1989年9月收到美国布朗大学英语系的邀请,请我为该系的驻校作家、访问学者。当时用了3个月才拿到护照,不得不辞退工作;仅用了3 天就拿到了签证。布朗大学有东亚系,有一个很强的中国语言系,本以为我会被安置在那里;但大学的写作项目中心是在英语系,这个中心在美国非常有名,因为它的教学自由和高质量而享誉全美,郑敏女士是在这个中心毕业的。我被安置在大学英语系的写作项目中心,英语系是布朗大学最大的系之一。在任驻校作家、访问学者期间,我要每周四去写作项目中心参加学生们的茶话会,那时学生会讨论写作与文学,专题讨论或随意讨论。我要和学生们在一起,使他/她们了解中国文化。还有就是举办诗歌朗诵会,旅行,创作自己的作品。我在美国持续的获得了不同的有资助的奖项,这样在英语系和写作项目中心就继续了3年6个月。
3年半后,经济来源没了,我开始在英语系和写作项目中心的办公室打工,半天的工作,主要是发送邮件、做复印、递送重要文件。夏天和冬天学生放假,我就不用上班,我回国,旅游,去写作基地搞创作,系里会把位置给我保存下来。收入不多,但有固定的创作时间,可以回国,这样就是好几年。我不喜欢教学,觉得美国的学生难教,要讨好他/她们,加上当时的英文水平也不够教学和批改英文作业。当时那样的状态,我挺满意。我去了很多写作基地,写了好几本诗集,出了好几本英文诗集,生活也马马虎虎的过下来了,挺好。
一直到10年前,过不下去了,没钱了,大学的媒体技术服务部刚好有一个名额,我去应征,被录取了。这个工作是负责大学的文化活动和讲演的音像安排,还有教室的仪器使用。我中学时数理化很好,脑子的逻辑思维不错,加上喜欢鼓捣音响,结果没费什么劲儿就通过了面试。我当时都不知道在美国一流大学工作所享有的可观的福利。我记得我获取上班通知的时候是在佛芒特的写作基地,我正在写一本新诗集,通知告诉我2 个星期后上班,我心里好难受。我不得不提前离开写作基地,回到布朗大学,开始了我的分裂的生活。
雪女:八十年代初在国内就开始写诗,现在国外仍然笔耕不辍,中间有停过吗?不同的生活背景和地理环境,对你的诗歌写作有影响吗?
雪迪:80年代初开始写作,第一本油印诗集是《断壁》,看书名就知道诗集的内容。1988年漓江出版社出版《梦呓》,1989年工人出版社出版《颤栗》,这些诗集出版后就卖光了。1990年到了美国,头3年因为连续获奖所以有薪水,专注写诗和学英文。出版了英文诗集《火焰》《情景》《心灵-土地》《宽恕》。3年后开始在布朗大学的英语系、写作项目中心、东亚系、现代文化和媒体中心等部门打工,也在外面的餐馆洗碗、街头卖地毯、照顾残疾人、做园艺工、帮人遛狗、冬天铲雪、看大门等工作挣钱。那时的生活挺辛苦,存款不多就慌得很。写作一直在继续,陆续出版了英文和双语的诗集《地带》、《普通的一天》《另一种温情》《碎镜里的猫眼》《音湖》。在台湾出版了《徒步旅行者:1986-2004》和《家信:雪迪诗选》。在这期间还去了10多个美国的写作基地,其中包括LANNA FOUNDATION 在MARFA的写作基地、YADO、MACDOWELL、美国落基山脉国家公园。
生活环境不同了,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除去直接的经济压力,消解了思想上的压迫。对抗消失,你面对的现在就是你自己。我的写作开始转入内心,以往对外的爆发转变成内心的思考,情绪转化成凝视。诗歌显得安静了,有了更多的回声而不是轰鸣。技巧细腻,用字用词更简洁、准确、凝练。因为你要把以前用很多行表达的现在只用几行表达,你要创造和保留空间,在行与行之间设置空间,那些空间里有更多的事物在回旋;就像你在异国的生活,更多辛苦和喜悦在无法言喻之中。你无话不说的时候过去了,现在你要学会在寂静中言说。空旷是如此坚实、如此浑厚,你要用最精确的词,最少的行数来呈现这个空旷。除去精炼,空旷无法存在;除去准确,寂静不会莅临。
我还用大量的时间思考和实验将现代写作和古典诗歌联系起来。在很多国家公园的写作基地,我独处自然之中,用最原始的方式生活。我看到北极光,听到狼嚎,夜晚在海涛声中入睡。我有了机会体验古人离群索居的生活方式,面对天地独自冥思,和心魄在一起。那样的诗是通气的。通冷暖之气,通动植物之气,通天地之气。那时,你可以和古人连接,看到照耀古人的星光,听到古人旅行的马蹄声,酒倒入大碗里的声音,看见你在诗歌的光团里。
大量的时间也用在翻译诗歌上,和我的诗歌的译者们对话、商讨,看到一本诗集最终完成,以另一种语言面世,内心感激和欣喜。
27年,逗留在异国几十载,独自生活,独自体验,独自面对日常的琐碎和难过,独自体会生命的徜徉和跨越。在异国的孤独中,和诗歌在一起,眺望远方的家,辛苦和感恩地活着。
雪女:我所知道的50年代出生的诗人,在写作上只有少数几个突破了困境,站到了当代诗歌第一线,你应该算一个。有些诗人写不出诗歌,改写随笔小说了。有些诗人虽然还在写,但也是后劲儿不足,难出佳作。请谈谈你一路克服了哪些障碍,从而保持了现在良好的创作状态。
雪迪:需要一年,才能在心理上调整过来,如果你接受事实,执意在新地方生存。在一年之中思乡的痛苦,语言障碍带来的失落感和自卑,对新环境的本能的拒斥,在新文化中的迷失和已熟知的自我的消失因而产生的恐惧,这些都是无形但巨大的,紧紧地裹着你,压迫你,使你发疯。如果你还要因为生计而忙碌和忧虑,那就是雪上加霜了。我很幸运,在最初的3年有奖金资助,因此可以全力以赴的学英语,把握内心的变化。接受事实并有一个明快的计划,会使生活轻松一些,心智免于扭曲。用母语写作缓解了在异乡生活的苦痛,不仅仅是帮你挥发心绪的纠结,也使你在用熟悉的文字沟通内心时感到安慰和快意。
孤独是无穷无尽的,在清晨的洗脸水、中午的汤和夜晚的酒盏里。没有人和你用母语谈论诗歌,没有人告诉你2个意象之间的生命的窘迫和失落,一首诗完成时生存的欣喜和哀伤。你必须有一个目标,你必须相信自己,没有怀疑的余地;唯有这样,你不会垮下去。孤独是美妙的,它使你清晰地看见自己,听见你体内流动的声音,当你和人群一起,这些宝贵的都会消失。我从小被父母遗弃,在7 岁时就开始对抗孤独和恐惧,我习惯了孤独,熟知恐惧。诗歌一直在我的生命的里面照耀,时而明亮,时而微弱。在异国的生存使诗歌的声音更清晰、尖锐,它在孤独中的回声更长久。
我就这样在异国活着,目标明确。我知道我不放弃生活,诗歌就不会离开我。对写作技巧的研习使我欣然,能把一首诗写的越来越短,内涵却愈加丰富,这样的结果使我满足,领会生命的意义。对于我来说,已经不是在异国坚持下去的问题了,是我在看着我自己能走多远,保持心灵的纯正和喜悦,命里有光,诗歌相伴相随。活着,爱着,努力着,从艰难困顿中走出;老了,但心是这样的年轻。
雪女:读你的诗,就像看冷色调的油画,冷静、忧伤、细腻、尖锐、深情等构成了你诗歌的主要特征。它既来自心灵深处,又有陌生化的语境,呈现出迷人的气息和创痛的力量。这是否是你在诗歌写作中所追求的审美效果?
雪迪:感谢你对我的诗的评价。忧伤来自我的被毁了的童年,加上国家的动荡,民生的艰难。在异国的生存和从不同的角度领会文化和进入诗歌,使我的抒写也许和国内同仁不同。生命的过程与众不同,这会给诗涂上异样的色彩。我画过油画,酷爱音乐,和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学过美声唱法;12 岁时进入少年体校打乒乓球,到美国后曾连续10年是我所在州的乒乓球俱乐部的冠军;我兴趣广泛,但凝聚于诗,持之以恒的研习写作技巧,并有机会在自然中独处,与动物为伍,这些经历提供了经验诗歌写作的不同的途径。如果你有惨厉的童年,但你没垮掉;如果你经历了国家的动荡,你幸存但没有扭曲,你仍旧爱;如果你漂泊异国,但家园由始至终都在你的心里,你说梦话时仍是中文;如果你历经磨难,但奉献的都带着光亮;如果,你仍旧写诗,你一定会打动热爱生活的人。
把你自己准确的表现出来,要说的与众不同,要坚忍,亮光在你的脑海里。
雪女:在你的诗歌中,我读出了乡愁。这种乡愁在去国离乡的作家诗人中尤其浓郁。你至今坚持用母语写作,是否也是表达乡愁的一种方式?
雪迪:我33 岁离开中国,至今已是二十七载。刚到美国,一句英文也不会。我不倦的学习英文,也感谢我的美国女友,二十多年相伴相爱,也使我的英文长进。用母语写作不是因为乡愁,而是为了表述的准确。写出诗句,就是母语,因为是母语和心相连,母语在气息之中。母语清晰、细腻、落在扎实的地方,诗歌也是如此。二十七载,母语与我同在,同甘共苦,使我强壮,使我细致,使我在风雨之中稳稳的站着。
母语入梦,使我的生活恍如隔世。母语的四声令我知道我是异乡人,心里有诗我就是主人,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自己的国土。我的根在母语里,母语是生长的,母语在亮光中会更加清晰和雄厚,所以我要栖身于光中。
你会看到一个异国的跋涉者,鞋上沾满泥泞,但脸是干净的。母语是他的粮食,他告诉你他的事情,他写诗。他的一生充满乡愁。
摘选于《心里有诗,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自己的国土》,采访录第3, 7, 12, 13, 15节。
雪迪,出版诗集《梦呓》《颤栗》《徒步旅行者》《家信》,著有诗歌评论集《骰子滚动:中国大陆当代诗歌分析与批评》;出版英文和中英文双语诗集9本。作品被译成英、德、法、日本、荷兰、西班牙、意大利文等。
雪女,本名胥永珍。诗人、作家、摄影师。六十年代生于山东,现居深圳。诗歌、 散文、评论等作品散见各报刊及网络平台,被选入多种选本。出版散文集《云窗纪事》、诗集《无尽的长眠有如忍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