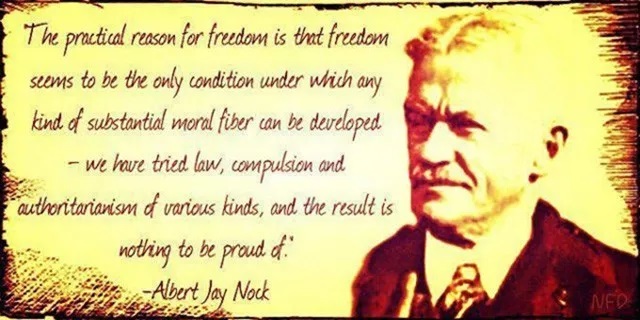© 诺克/文
© 彭芬/译
本文选自艾尔伯特·杰伊·诺克(Albert Jay Nock)著:《我们的敌人:国家》一书的第二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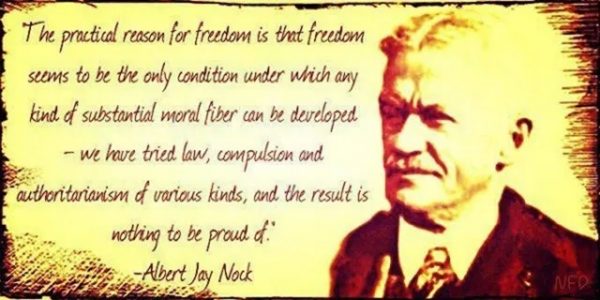
诺克(Albert Jay Nock,1870~1945)
1.政府与“政府”
回溯文明的历程,能发现存在两种根本不同的政治组织。它们的不同不是量上的,而是质上的。这种分并不是为了将两种组织分出原始与文明的高低等级;虽然它们常常被如此误解,却谬之千里。同样,两种组织也不能被分类为同一属的不同种,都划归为政府这一属之下。这是最近的通常做法,即,造成了严重的混淆和误会。
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很好地印证了这种错误及其影响。在其名为《常识》(Common Sense)的小册子的开头,潘恩区分了社会与政府。他指出,任何形态的社会都是良性的,然而,“政府,其最好的形态都仅仅是必要的恶而已;其最差的形态则是无可容忍的”。在另一处,他称政府为“因人无法用道德治理世界而生的一种必要的组织类型”。然后,他分析了政府是如何以及为何发源的。他认为,政府起源于社会的共识和共同协议之上,“政府创设的目的”,他说,是“自由与安全”。目的论的解释路径认为,政府实现社会的共同需求,首先是自由,其次是安全。除此之外它不作为,它不对个体采取任何积极的干预,而仅仅是消极性的保护。由此可见,潘恩眼中的政府法典应该如小说中包索尔王(King Pausole)所做的那样,仅仅为其臣民制定两条法律:第一条,不要伤害人;第二条,行己所欲的。政府的全部职能仅仅是消极地守护这一法典得到遵循。
至此,潘恩的理论貌似简洁而可靠。然而,他在接下来对英国政治系统的抨击却显得逻辑不融贯。当然,对此不必苛责,因为,他写作的是小册子,这种文本需要采用取悦大众的逻辑论辩,而且众所周知他在这点上做得很成功。然而这掩盖不了,当他评论英国政治体系时,所谈论的政治组织与其曾描述的政府根本不同;在起源、目的、主要功能以及所反映的利益秩序上都不同。这个政治组织不起源于社会的共识和协议,而是起源于征服与征用。它的目的,远非实现“自由与安全”,其图谋绝不在此。它图谋的主要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持续性的经济掠夺,它对自由与安全的致力必须服从于这一首要目的;而且,事实上,它很少为这两点努力。它的首要功能和运作并非潘恩所说的对个人纯粹消极性的干预,而是无数的、极为繁重的积极干预,都是为了确保社会分化为一个有产的、剥夺性的阶级与一个无产的、经济依赖性的阶级的样态。它所反映的利益秩序并非社会性的,而是彻底反社会的;其权力行使者,参照普通伦理标准,甚至仅以适用于任何个人的法律标准来衡量,都与职业化犯罪阶层无异。
显然,我们需要分析两种不同的政治组织;同样明显的,仅分析他们的起源,就不可能得出其中一个仅仅是另一个的变态形态的结论。因此,如果我们以政府的通用定义来套用这两种类型时,就会面临逻辑上的困难;这是大多数论述这一主题的作者们多多少少有所觉察的困难,然而,在最近50年之前,没人设法解决它。
比如,杰斐逊先生曾谈到,他早期曾与印第安游猎部落有大量交往,发现他们拥有高度组织化的、优良的社会秩序,但是却没有政府。论及此,他曾向麦迪逊写道:“这种状态难道不是最佳的吗?这是我犹疑的一个问题。”但是,他怀疑,这种状态“不适用于大型人口社会”。斯库克拉夫特(Schoolcraft)观察到,齐佩瓦族(Chippewas)没有“常任”政府,却拥有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秩序。斯宾塞在谈到贝川那族(Bechuanas)、阿劳坎族(Araucanians)、霍屯督族(Koranna Hottentots)时,曾说,他们没有“确定”的政府。帕克曼(Parkman)在其著作《庞蒂亚克的阴谋》(The Conspiracy of Pontiac)的序言中提到了同样的现象,而且明确表示了对这一明显的反常现象感到的迷惑。
潘恩的政府理论与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提出的可谓异曲同工。《宣言》中明确宣称的自然权利原则暗含在《常识》里,潘恩认为的“建立政府的目标”与《宣言》如出一辙,也即,“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而且,潘恩也认为政府“起源于被统治者同意授予的正当权力”。现在,我们无论是采用潘恩的还是《宣言》的理论,都充分显示弗吉尼亚的印第安人是有政府的;依据杰斐逊自己的观察他们拥有政府。他们的政治组织,虽然简单,却完全实现了目的。他们的法典机构足够保障个体的自由与安全,充分地应对在那个社会形态中个体可能遭遇的任何违法行为,如欺诈、偷窃、攻击、通奸和谋杀。帕克曼、斯库克拉夫特和斯宾塞所提到的各部族也是如此。可以确定地说,如果《宣言》所宣称的无误,则,这些部族当然拥有政府;而且这些作家都表明,其政府充分实现了自身的目的。
因此,当杰斐逊说他认识的印第安人“没有政府”时,应该指的是他们不拥有一个他所认为的那种政府;当斯库克拉夫特和斯宾塞说“常任的”和“确定的”政府时,这两个定语也应该这样理解。然而,这种“没有政府”的政府存在于历史长河中,也存在于现在,完美地实现了潘恩和《宣言》宣称的政府形态;虽然我们中大多数人鲜有机会见到,但它们绝不应该被贬低为低等的制度模式,因为,制度的简单并不必然意味着落后或低劣;我们已经充分认识到,在某些本质性层面,这种政府形态下的人,相对而言,反而更显示出其文明的程度。杰斐逊先生自己对这点的描述值得注意,还有帕克曼的记载。虽然《宣言》以书面的形式辩护了这种政府形态,但是,它与一直占据历史主流、今天仍然主导世界的那种政府形态根本迥异,所以,为了廓清两种形态,必须对其不仅在名称上,而且在本质上加以区分。它们的原理根本不同,因此,若要稳固自身的话,严格地将其加以区分恐怕是现在各文明体最重要的使命。从而,称呼其中一种形式为“政府”,另一种仅仅称为“国家”,既非武断,也非咬文嚼字。
2.国家的起源
亚里士多德因为混淆了国家与“政府”的概念,认为国家起源于家庭自然的集结。其他希腊哲学家们的研究也未摆脱此种混淆,某种意义上启发了卢梭从社会本质和个人本性中寻找国家的根源;而持相反立场的流派则认为个体本性上是反社会的,某种意义上开启了霍布斯所创造的以之为抗衡个人的反社会倾向的强制性设计的国家理论。另一种蕴含于亚当·斯密的学说中的理念认为,国家起源于一部分具有卓越的经济德行——勤奋、审慎和节俭——的个体之间的联合。理性主义的哲学家,采取不同形式将康德的先验论运用于其中,得到了不同的结论;还有一两种其他理论,相对于前述学说不那么合理。
这些学说的根本问题并不在于他们是推断式的,而是在于他们对推断依据的观察不够全面。他们忽略了这一主题呈现的恒定的标志性特征,这种情况就如直到最近,关于疟疾起源的种种理论都忽视了其恒定的传播载体——蚊子,或者如关于黑死病的学说忽略了寄生在老鼠身上这一不变的特征。将历史的方法用于国家问题的研究仅仅始于半个世纪前。此种方法通过回溯国家现象的历史,直至有文字记载的国家最初出现时的形态,观察其中一以贯之的标志性特征,据之进行推理。早期作家中青睐这种方法的不在少数,最早可追溯到斯特拉波(Strabo),所以令人疑惑为什么历史学方法的系统运用被长久忽视了。但是在所有这些例子中,正如疟疾和伤寒症的研究所显示的,一旦确定了显著特征,人们就禁不住感叹为什么长久忽视它。也许在国家这一问题上,能给予的最合理的解释是,需要时代精神的相应演变,而那需要假以时日。
历史鲜明地显示出,国家往往起源于征服与征用。历史上所知的最早的国家无不以此种方式起源。反过来说,历史证实,源国家无疑从未有其他起源。而且,国家唯一的恒常的特质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这个意义上,任何历史中的国家都是阶级国家。奥本海默曾参照其起源将国家定义为一种“征服集团强加给被征服集团的、为了征服集团系统地统治被征服集团、保护其自身免于内部的暴乱与外部的侵略的”制度,“此种征服的目的在且仅仅在于征服的集团的经济掠夺”。
美国政治家约翰·杰伊(John Jay)完成了一件“伟大”的壮举,即,以一句话精炼概括了整个征服学说,他说“总体而言,不论能否从中获利,国家都会发动战争”。可观的经济积累或者大量的自然资源都是征服的动力。原始的手法是劫掠觊觎的财产,完全瓜分之,消灭其所有者或者驱逐他们使其再难染指。然而,很早,征服者们就观察到,一般而言,将财产所有者变为依附者、使用其劳动力创造财富才是获得更为丰厚利润的方式,因而,原始手法发生改变。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后一种手法不可行或者无利可图时,原始的手法常常死灰复燃。比如,西班牙人在南美的手法,或者我们对付印第安人的方式。但是,这种情况不常见;改进后的手法从起初到现在一直在被使用,因而对它的启用往往标志着国家的起源。以兰克(Ranke)记载的希克索斯(Hyksos)这一以劫掠为业的游牧民族的手法为例,该民族于公元前2000年在埃及建立了他们的王朝,龚普洛维奇(Gumplowicz)评论道,兰克的观察精练地总结了人类的政治史。
事实上,改进后的手法横行天下。“任何地方我们都会见到一群武装的暴徒侵略一群更为和平的人,征服他们后,建立国家,自己成为贵族。在美索不达米亚,侵略一波又一波,国家一个继一个,巴比伦人、阿摩利人、亚述人、阿拉伯人、米堤亚人、波斯人、马其顿人、帕提亚人、蒙古人、塞尔德沙克人、鞑靼人、突厥人轮番上场;在尼罗河谷,希克索斯王朝、努比亚人、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阿拉伯人、突厥人相竞出现;在希腊,多立克城邦是典型案例;在意大利,罗马人、东哥特人、伦巴底人、法兰克人、日耳曼人都曾称雄;在西班牙,迦太基人、西哥特人、阿拉伯人相继登台;在高卢,罗马人、法兰克人、勃第人、诺曼人相继称雄;在英国,撒克逊人、诺曼人轮番登台”。无论何处,我们都会发现政治组织的起源大致相同,也体现了相同的目的,即,征服集团对被征服集团的经济掠夺。
这条定律适用于任何地方,仅有一种显著例外。何处经济剥夺因为某种原因不可行或者无利可图时,国家便不会产生;“政府”可能存在,但,国家绝不可能。比如,美国游猎部落从未曾形成国家,因为无法使猎人产生经济依赖,令他为他人狩猎,这样的组织令观察者困感。征服和剥夺当然可行,但是无利可图,因为剥夺能为征服者增添的财富很少;最大获利不过某种形式的封地带来的满足感。因为类似的原因早期的农民从未形成国家。邻人的经济收益太过微少也易腐败,挑不起他们的兴趣;尤其四周未被占用的土地应有尽有,对邻人的奴役也不可行,除非牵涉治安问题。
至此,潘恩和《独立宣言》领会到的,称为“政府”的制度与称为国家的制度间差别何等大已经显而易见了。“政府”的起源可以合理推断为与潘恩或亚里士多德、霍布斯、卢梭等认为的那样一致;然而,国家却不仅从未、也绝不可能如此起源。“政府”的本质与目的,正如帕克曼、斯库克拉夫特和斯宾塞证明的,是社会性的。基于自然权利理念,“政府”通过严格的消极性干预保障个人的自然权利,令正义实现的成本小、效率高;此外再不作为。然而国家的起源和首要宗旨,完全是反社会的。它的基础并不是自然权利理念,而是个人除了国家有条件地赐予的以外再无权利的理念。国家往往令正义的获得代价昂贵,难于实现,而且,它自身只要能有利可图就会凌驾于正义与普遍的道德观念之上。所以,远非培育社会权力健康发展,国家正如麦迪逊所说,始终会化任何权力变为汲取社会权力填己之欲壑的机会。正如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看到的,甚至不能说国家显示了任何制止犯罪的意图,它仅仅是护卫自己对犯罪的垄断权而已。比如,在德国和俄国,我们可以看到,其国家一方面敏捷地抵制私人对其垄断权的入侵,与此同时,极其残忍地实施此种垄断。无论何处的国家,无论观察国家的任何阶段的历史,人们都无法找到其创立者、管理者与受益者的行为与职业犯罪阶层有任何区别。
3.国家的本质
以上就是国家这一制度的身世,现在它正在四处大张旗鼓地将社会权力转化为国家权力。回顾其身世对解释现代国家呈现的大部分(若非全部)明显扭曲的行为大有裨益。例如,它可以帮助解释这一公开的、臭名昭著的现象,国家在为任何增益社会的目标努力时往往进展缓慢且十分勉强,但若是为增益自身的目标行动却迅速且富有效率;它也绝不曾主动服务于社会的目标,仅仅是在面临巨大压力之时才会有所妥协,但对任何反社会的目标却主动积极。
19世纪的英国人怀着可理解的焦虑指出了上述现象,当他们目睹自己的国家将社会权力迅速吸干时。其中一位就是赫伯特·斯宾塞,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后来集结成集,命名为《人与国家之争》(The Man versus the State)。以美国现在的公共事务的状况,不得不惊讶,美国竟然没有任何政论家能学习,哪怕仅仅以美国历史上的案例替换斯宾塞从英国历史中选取的来复制此书的写法。若能如此,必将会写成现时代所能达到的最中肯、最有用的著作之一。
这些论文从多个角度审视了英国现阶段国家权力的扩张。在一篇名为《过度立法》(Over-legislation)的论文中,斯宾塞评析了在我们的经验中司空见惯的事实,即,当国家权力致力于社会目标时,行动天然“缓慢、愚钝、华而不实、不灵活、腐败的,还败事有余”。他对所列举的国家权力的每条罪状都用了数段加以分析,构成一个完备的证据链。证据陈述完,分析也完结,因为这些证据胜于任何言语。他进一步指出,国家甚至不能有效地完成对社会负有的所谓的“无可推诿的责任”,因为它未能有效裁决和维护个人的基本权利。鉴于这样的事实(对于我们也是屡见不鲜),斯宾塞不觉得有理由期望国家权力能更有效地达成次级社会目标。“简而言之,仅当我们证实了它能有效地裁决和护卫权利,而不是总发现它奸诈、残酷、令人唯恐避之不及,才能希望从它手中得点其他利益。”
然而,他评论道,社会沉溺于这一匪夷所思的荒唐希望中不可自拔,即使每天都证明这希望多么虚妄。他指出这样的悖论司空见惯于报端。斯宾塞信手拈来一个例子:你可能经常看到这样的社论,“曝光国家部门的腐败、玩忽职守或失职”,目光挪到下一栏,你却完全可能看到作者建议国家加强监督。……因此,国家日复一日累积失败的记录,人们却每日重新升腾起这一信念。只要提出议案或者设立官员来管理,就一定能达成任何目的。再没有比这更说明人类信念的顽固了。
无须赘言,斯宾塞对国家的反社会行为的分析是十分有力的,但是我们现在看看,历史学方法能怎样为之如虎添翼;斯宾塞写作时并未用到这一方法。审视这些发现,很明显,斯宾塞所揭露的行为是历史一贯的。当18世纪定居城镇的商人阶层取代了持有土地的贵族阶层掌控国家机器时,并未改变国家的本质;他们只是将国家机器调整得适合他们的特殊利益,并且无限地加强它。商业国家仍然是反社会的制度,赤裸裸的阶级国家,与贵族统治的国家无异;它的目标与功能未变,仅仅是根据其所服务的新利益秩序适当调整而已。因此,它公然损害社会目的的行径(正如斯宾塞控告它的),仅仅是据本能行事而已。
斯宾塞并未进一步阐述所谓对国家行为的“人类顽梗的信念”,而是止步于对基佐(Guizot)的格言的点评,比如“对政治机器的最高权力的信念”不过是个“庸俗的幻想”。而这一信念主要是源于国家在四世纪或者更直接说是在“君权神授”(jure divino)论衰落后殷勤地为自己建立起来的光辉形象。我们在此无须全面分析国家树立自己形象的各种手法,因为,其中大部分手法及其实施方式我们都熟稔于心。然而,有一种是共和国特有的手法。共和主义引导公民个体相信国家是他自己的产物,国家的行为就是他的行为,国家的意志就是他的意志的表达,国家荣即他荣。共和国无所不用其极地灌输这种信念,因为发现这是提升其权威的最有效的手法。林肯的名言“民有、民治、民享”恐怕是共和国形象营销中最得力的案例。
所以,个体所意识到的自身的重要性驱使他强烈厌恶任何称国家天然反社会的观点。他以父母般的胸怀对待国家的失败与过失,对自家“孩子”适用特殊的伦理标准。更有甚者,他常常期待国家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不断改善。即使承认国家实践社会目标的方式粗笨、浪费甚至不道德,即使正如斯宾塞所列举的官员承认,国家所在之处必有邪恶,但个体仍然质疑:随着经验和责任感的增加,国家不会改进。
其实,这样的观念已经符合集体主义的基本假定了:让国家征用所有社会权力吧,那样,它的利益将与社会的利益变得一致。即使国家根子上是反社会的,它在历史中展现出始终如一的反社会本质,还是让它耗竭社会的权力吧,它的本性会改变的;它会与社会融为一体的,将成为社会有效的、无私的机体。总而言之,历史中国家将消亡,仅存“政府”。多诱人的学说!然而,将之付诸实践的冲动几年前造就了“俄国实验”,这场“实验”令那些完全被国家所俘获的“高贵的灵魂”着迷。然而,仔细审视国家的行为就能证明这貌似诱人的学说在入门经济学的铁律面前不堪一击,这条铁律说,人总是追求以最小成本满足自己的需求。接下来我们对此加以仔细分析。
4.国家的功能
人满足自己需求有且只有两种方法或者途径。一种是财富的生产与交换,即,经济的手段。“还有一种则是无回报地征用他人劳动创造的财富的方式,即,政治的手段。政治手段的习用手法是采取征服、剥夺、征用以及建立奴隶经济的方式。征服者将征服的土地分配给既得利益者,这些人就通过剥削被奴役的居民的劳动来满足自己的需求。无论何处所见的封建国家和商业国家,都成功地继承与发展了原初国家传承下来的剥削的本质、目的与手法;他们实质上是对原初国家的扬弃。
所以,国家,无论是原初的、封建的还是商业的,只不过是运用政治手段的组织。既然人从来都趋向于以最小成本满足自身需求,他当然会尽所能采取政治手段,甚至以之为唯一手段,如果可能的话;实在不行,再与经济手段兼而使用。现阶段,他会求助于国家的现代剥削手法,即关税、特许权、租金垄断等。因此,只要运用政治手段的组织可行,即,只要存在权力高度集中的、官僚制的国家作为经济利益的分配者、剥削的主宰者,人青睐政治手段的本能便会展露。无产阶级国家将重蹈商业国家的覆辙,不过只是改变剥削的具体形式而已,所谓集体主义的国家将会本质上与此前的国家完全不一样的假设毫无历史根据;正如我们已经开始看到的,“俄国实验”实质上在前一个国家的废墟之上建成了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官僚化的国家,完整而充分地接手了整套剥削机器。因此,参照以上提到的入门经济学原理,期望集体主义将根本改变国家的实质完全是个幻想。
因而,历史学方法所得到的发现充分支持了斯宾塞提出的为了防止国家侵害社会权力的许多实用策略。当斯宾塞断言“国家机构中腐败难以避免”时,历史学方法追根溯源,揭示为什么这种趋势难以避免,即,宿命如何注定(vilescit origine tali)。弗洛伊德曾评论国家伦理与个体伦理之间的巨大差异,他对这一点的观察非常深刻且透彻,运用历史学方法则立刻能解释为什么此种差异毫不令人意外。当奥特加·伊·加塞特说“国家主义不过是暴力与抢夺被树立为标准时采取的高等的形态而已”时,历史学方法令我们洞察到,他的定义可以从国家的普遍本质中演绎得到。
然而,历史学方法确立了这一重要的事实,即,正如脊髓痨症或寄生虫病一般,国家吸干社会权力的疾病的演变如果突破了某个点则再也无法控制。历史上还未有案例显示,一旦突破这个点,社会权力的枯萎不会以其完全和永久的崩塌告终。在部分案例中,崩塌的过程缓慢且痛苦。罗马在2世纪末就已经显示出灭亡的征兆,却苟延残喘到安东尼之后。相反,雅典则迅速消亡。有些政府认为欧洲即使未达到,也已经濒临此临界点。但是,当下这些猜想并无多少助益。也许美国已经达到了此临界点,也许没有,这无从确定,因为这些观点似乎都有道理。然而,我们可以确定两条:第一,美国向此临界点演变的速率在惊人地提升;第二,美国人没有表现出任何想要阻止这种趋势的意愿,甚至学术界对这种加速度演化预示的危险没有任何焦虑。
译者秦传安 2019-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