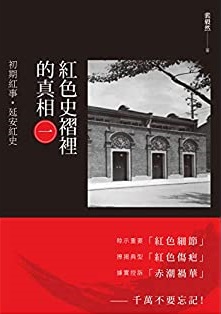 《红色史褶里的真相》第一辑: 初期红事(17)
《红色史褶里的真相》第一辑: 初期红事(17)
白区地下党生活
北伐以前,中共组织一直处于地下秘密状态,党员也是零星个别,绝大多数为知识分子。发展工农党员,一般通过亲串亲、邻串邻介绍,支部大会通过就可以了。入党宣誓时,不少地方要喝鸡血酒,誓词如下:
遵守纪律、严守秘密;努力革命,服从命令;打破宗族,不分姓氏;牺牲个人,不害同志;生死共存,永不叛党;如有变心,刀斩弹穿。
大革命起来后,中共走向公开与半公开,各级组织分设组织、宣传部门,发展党员要填写申请书,由党员介绍、支部通过,并经区委(省委)审查,才能举行宣誓仪式。[1]
「四·一二」后,中共暴动「闹赤」,各地建立「赤区」,赤区以下称白区,学员潜伏于危险的「地下」,与监狱、刑场相邻。第二次国共合作后,党内流传两句话:「二万五千里,三千六百日」。二万五千里指长征,概括赤区武装斗争;三千六百日,指白区地下活动十年,包括监狱刑场。[2]
南昌暴动后,一大代表包惠僧因病无法随部队行动,周恩来嘱其在南昌潜伏,如赶不上队伍即到武昌去找组织,并为包写了介绍信。包惠僧在南昌一表亲家住了月余,化装逃出南昌,从九江搭船回湖北老家黄冈,因白色恐怖,在乡下也住不下去,遂到武昌,没找到组织,携妻再逃至江苏高邮岳家避难,两个多月后,风声不好,走避上海,见了李达、施存统、马哲民等人,「上海的情况很混乱,我遂和这些人一起走了失败主义的道路,消极脱党。」[3]包惠僧这一段〈自述〉,寥寥数语,构勒出大革命失败后全国紧张的白色恐怖。
一、经济状况
1927年6月1日,政治局修改党章,规定党费缴纳:月收入不满20元减免党费,20元以上起征;30元以内月缴党费二角;60元以下一元;80元以下3%;80元以上特别征收;失业工人或在狱者免缴。[4]
1927年10月27日,陕西省委发出征收党费的第十号通告,要求党员都应按时缴纳党费,规定不同缴纳数额与月薪20元以上的累进「特别捐」,严令「党费于每月十号前一律收齐」,无故拖延超过三日,视情节给予警告直至留党察看;迟过五天仍抗拒不缴者,呈上级予以开除。此时全陕甘党员不过1681人(1/3为农民),要求1928年1月发展党员达到5430名。[5]党员人数有限,所缴党费甚微,不可能支撑全党庞大活动。
也有较富裕的总支。1925年广州中山大学总支的经费就十分宽裕,许多党员每月留下生活费,其余全交党费。总支全职党员,每月可领生活费40元。供职国民党机关的共产党员月薪甚高,收入远远超过40元。恽代英仅国民党中委一职,每月就有240元,他每月留80元生活费,其余均缴了党费。国民党议员林伯渠、李锡九,每月缴党费80元。教授党员章伯钧,也每月缴党费80元。因此,中大总支很阔,不但职业党员养得好好的,出版刊物或开展活动,根本不用向区委(省委)要经费。[6]
1927年10月,党在上海收容南昌暴动散失的归队者,一时没分配工作的,每人每天二角生活费,首次发放最多只给二元。[7]同月,湖南省委环境越来越恶劣,生活也越来越艰苦,省委候委兼妇女部长刘英(1905~2002):
由于党的活动经费太少,我们几乎领不到生活费,饱一顿、饿一顿成了常事,可是大家都毫无怨言。[8]
职业革命家众多,大大超过非职业化党员,根本无法用党员缴纳的党费维持这么一大坨职业革命家的生计。当时中青年党员流行「以身许党」——领取党的生活费,全力从事党的工作,断绝一切社会关系以至家庭关系,才是「职业革命家」。大多数党员都等着领取生活费,怎么还有钱缴纳党费?为此,1928年后,中组部长周恩来提出白区干部的「三化」——秘密机关社会化、党员职业化、身分合法化。[9]
1931年4月,广西红七军东调部队干部王震(1908~1993),负伤来沪,地位不高,尽管携妻带子,生活费也仅每天二元,住旅馆及伙食都包括在内,度日艰难。红七军师长龚楚(1901~1995),因是高干,左腿重伤,每天生活费三元,另加电疗费二元。龚妻前来照料,还要帮助红七军其他在沪疗伤干部,「在极其节省的情形下,尚可维持。」但也仅仅维持,无力添衣购物。贴光个人存款后,龚楚打报告要求增加生活费,始终未得同意。这位后来的「红军第一叛将」,晚年仍抱怨:
迫不得已将电疗的次数减少,以维持日常必需开支。有时我想起我在广西工作时,为党筹措了五万元港币,毫无保留地贡献给党为活动经费,另外支持香港日报亦用过一万多元。我抛弃家庭温暖,为革命流血,现在必需的医疗费和生活费都无法维持,未免太刻薄。
1931年8月,龚楚奉命转道香港进入江西苏区,其妻掩护陪送赴港。聂荣臻交给他一笔交通费:
你是党的重要干部,曾经为革命付出重大牺牲,所以应该买一张西餐房的船票,以免被发现;嫂子对革命没有贡献,只能住三等舱,以免浪费。给你的钱便是依照这个原则预算的。
龚楚再发牢骚:
我听了很不高兴,觉得他们太不近情理,太不体谅为革命牺牲者的心情。
其时负重伤的红军高干,每月十元营养补贴。[10]
1928年,中央委员生活费27元/月。1929年秋~1930年初,后为托派骨干的王凡西(1907~2002)任中组部干事,周恩来助手,其回忆录:
党费收入太微,而革命职业家的维持费又太大,巨大的不敷之数,从来靠联共党的帮助。当我在党内工作时,党的主要支出,据说是靠列宁格勒党员的全部党费。……当时,中央工作人员的生活费每月25元,区委会的同志为19元。这个数目约等于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资。如有特殊需要,如疾病之类,或有家属而「住机关」者,则有额外补贴。这点生活费当然不宽裕,但足够维持。[11]
1928年5月7日,苏兆征、向忠发致信共产国际执委会求援:
深信正是由于缺乏必要的经费,近半年来党的工作受到了很大损失。……最近有几个同志被逮捕,法国人拒绝把他们移交中国当局。我们认为,如果有必要的资金的话,党组织就可以把他们解救出来。中国共产党在目前时期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物质援助。党希望共产国际能像它过去在物质方面援助国民党那样来援助它。期待你们尽快就此问题作出答覆。[12]
创造社的李初梨(1900~1994),1928年入党,1929年11月任上海闸北区委宣传部长,半年后调任江苏省委宣传部秘书——
党组织(按:基层)是不给津贴的,到了区委每月给五元钱,根本不够用,只好住亭子间、灶披间,穿得也破破烂烂的。到省委工作后,每月发18元钱,办公室一般伪装成商号。当时,中央机关一般虽独门房子。我们到省委开会大多穿长衫。[13]
王明集团就是利用生活费控制上海党组织。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他们对何孟雄等「持不同意见」的上海基层组织就采取这一招。刘晓(1908~1988)时任江苏省委秘书长:
我曾奉命到沪西区委去谈判,要区委的同志不要反对省委,否则就不发给生活费。这些同志当时没有公开职业,没有任何收入,为生活所迫,他们不得不服从省委,从而使王明控制了上海的党组织。[14]
1930年4月,汉口党组织派曾三(1906~1990)赴沪学习无线电收发报,但组织太穷,只给路费15元。曾三已在小旅馆待命很久,积欠十几元房租、饭钱,十五元全交出都不够。曾三只好当了蚊帐,得2.8元,再向两位穷同乡挤借十元,才结了旅馆的账,所剩不够买船票,通过水手帮助,用「看黄鱼」的办法上船。抵达上海,身上只有一角多钱。到饭店一看,每天房租2.97元——
我怎能住得起!只好拿出一件夹袍子去当了四元钱,第二天就搬到一个小旅馆去了。又过了一天,李强(化名张振声)找到我,给了我五元钱……学习期间,组织上给我们每人每月七八元钱的生活费(房租不算在内),除了吃饭所剩不多,还要订一份报纸,买些生活必需品,因此生活过得比较艰苦。……长期都是每天买一把小白菜、一块豆腐,或者一块「日本」咸鱼充当副食。如果买二角钱肉,就一定要放在菜篮子上面,好让二房东看到我们也能吃到肉。有时生活费晚送一两天,就得当衣度日,从当衣铺出来,捏着刚刚当得的钱去吃阳春面和烧饼。[15]
1933年7月入团的绸厂青工邢子陶(1912~ ),旋任上海法南区团区委组织部长,10月江苏团省委巡视员,很快调任沪西团区委书记,领导一二十个团支部、百余名团员——
当时我们的生活是很艰苦的,每个月发九元钱,三元钱交房租、六元是生活费,每天只能吃点大饼的阳春面。要「改善生活」就得到黄包车夫们吃的饭店去,那里有鱼有肉,但都是搜罗大饭店里人们吃剩的残羹剩菜,买一碗很便宜。住的是亭子间,行李很简单,一张行军床、一只帆布箱、一张圆藤桌、一个洗脸盆。为了安全,还常搬家。[16]
1934年任团中央局宣传部长的黄药眠(1903~1987),每月领伙食费12元,零用交通费三元,添置衣服鞋袜要向组织再提申请。一次黄药眠买东西多用五毛钱,吃了组织批评,说他经济观念不正确,做了半天检讨。[17]
这一时期也在上海搞地下工作的谢觉哉(1884~1971):
每月生活多的给30元,少的给10元,即是说除房租外,每天至多花一元。那时黄金每两值洋112元。[18]
苏区形势稍发展,财政上有时可支援上海中央及各地党组织。曾志:
当时福建省委的活动经费主要是由闽西特委和红军提供的,取之于地主豪绅的浮财。[19]
向忠发被捕后,供词中有关财务部分——
共党经济来源:
(甲) 俄共每月资助1.5万美金(折合中国五六万元),实际上国际的款是俄国共党供给的。最近经济的支配权操在周恩来手里,我不知其详。但是从前中央总行动委员会时,由我来支配经济,所以我知道的很详细。其分配如下:
- 江南局 五千五百元,后又加上一千元;
- 南方局 四千二百元;
- 长江局 六千元;
- 北方局 四千八百元;
- 满洲 一千二百元;
- 军部 九千元;
- 宣传 九百元(印刷费另外);
- 组织及招待 一千三百元;
- 红旗报 二千元(现由罗绮园负责)
(乙)赤区接济者:
在赤区中所没收或抢掠的财物,统统都换成现金,再由在芜湖开发金铺子的同志张人亚兑换成现洋及钞票,交来上海给中央。前后由我经手有两次:第一次,一九三○年六月由闽西运来七百两;第二次,一九三○年底,由赣西南运来两千零七两。由这两批款内提出八百元组织商业机关,派陈绍禹作老板,——现由廖成云负责交付,此外尚有许多大批现金由赤区运来,但都不是我经手的。
(丙)绑票或抢掠:
共党的经济有时因国际的关系一时中断,款子不能来,亦有的因赤区的接济没有到,因此就时常采用绑票和抢掠的方法,这种工作主要是由特务第三科红队负实干的。[20]
1930年代初,高岗在西安看到省委领导逛妓院,很惊讶,后来理解了——环境险恶,说不定哪天就掉脑袋,过一天算一天,及时行乐呵!1934年1月,高岗因奸污妇女受严厉处分,但他仍每到一处就找女人。中央红军抵陕,他见党内一些高干与自己「同好」,自然不但不收勒自羁,还有所发展。随着权位日高,部属投好,女人送怀,高岗从西北一直「玩」到东北再到北京,其妻李立群多次向周恩来哭诉丈夫「搞腐化」。[21]但「生活小节」并未影响高岗政治上一路走强,若非毛泽东权衡利弊弃高保刘,高岗差点取代刘少奇成为「接班人」。
杨之华在总结顾顺章叛变经验时,认为教训之一是没有预警其「生活腐化」:
党对于同志们日常生活上的检查很缺乏。例如对于顾顺章生活的腐化(吸鸦片甚至玩妓女)、打老婆等等的行为没有加以研究和注意,以致他借口特务工作的关系一日加一日的堕落,没有惹人的注意。然而从他的生活上可以知道,他的叛变不是偶然的。而我们对于他不好的倾向——叛变的预兆,没有加以及时的警惕。[22]
工人出身的总书记向忠发生活腐化,经常嫖妓,李立三、关向应怕他常去妓院出问题,便同意他花钱买下相好为妾。1931年6月下旬,向忠发被捕遭杀,就是为了舍不得这位妓妾,冒险回去看她。[23]
二、街碰与伪装
1927年4月13日(或14日),陈延年、李立三、聂荣臻自汉口抵沪,找到中宣部的郑超麟,要见罗亦农、赵世炎。原来汉口中央免了罗亦农的江浙区委书记之职,派陈延年来接替。三人汉口出发时,「四·一二」还未发生。从罗亦农家出来后,郑超麟陪李立三上街买棉被,更重要的是去配一副墨镜。[24]
党组织转入地下后,一旦失去组织联系,一些缺乏经济基础的党员,有时会很惨。寻找党的办法之一竟是满大街去「碰」。大街小巷不懈转悠,遇到同志就接上头,但若碰到叛徒或特务,那就被捕,接着有可能牺牲。明知危险性很大,仍然只能去「街碰」,因为别无他径。
1921年底入党的颜昌颐(1900~1929),南昌暴动前敌军委委员,二十四师党代表。潮汕失败后,颜昌颐率残部千余人参建海陆丰苏维埃。1928年8月,颜昌颐受伤,广东省委命他赴香港疗伤,到港后发现省委机关已搬走,生活陷于绝境,进了难民收容所。11月,颜昌颐搭船赴沪,伤势更为严重,但身无分文,处境甚窘,为寻组织,拖着病体踯躅街头,月余才邂逅相识的同志,接上关系,任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军委秘书,协助彭湃。[25] 1929年4月,因叛徒白鑫出卖,与彭湃、杨殷、邢士贞一起被捕,8月30日牺牲上海龙华。
女性找党又多一重困难。大革命时,开明女性大多剪去长辫,短发短辫。湖南白军流谚:「巴巴头,万万岁!瓢巴鸡婆遭枪毙。」巴巴头指旧妇脑后的发髻,「万万岁」是说留有旧式发髻的妇女长命百岁;「瓢巴鸡婆」指秃尾巴鸡,指剪了短发的女性,抓住要杀头。[26]
1930年1月,留苏归来的朱瑞(1905~1948)在上海街头遇到两位莫斯科中大同学,两人均已「消极」(按:不再参与革命活动)——
现漂流上海,以写文稿费度日。我们会见时已二、三日不食,饿得面蜡黄,仍在等他写作之《墨子问题研究》的稿费以解决食住问题。
朱瑞回国时在莫斯科领得六七百元路费,「为争取他(怕他们可能卖我),给了他们一些钱,结以感情。」[27]
1929年6月,国共合作期间送赴苏联的留俄生开始回国,国民政府刊布广告,以月薪200银洋召募他们向国府报到。谷正伦、谷正纲兄弟就是此时进入国民党。张如心等为追求马列主义,回沪后住棚户、当码头搬运工,甚至吃不上饭,过了一年艰苦生活,1930年才与党接上关系,1931年6月入党,8月参加红军。[28]
南昌暴动队伍南下,抵达潮汕地区后,汤坑失败,贺龙与刘伯承逃到香港,狼狈得很。下船前,他与贺龙约好,贺龙胖,扮主人;刘伯承稍瘦,扮仆人。上岸后找旅馆,茶房引他看房间,一间又暗又小的房间,刘伯承很生气,说这也不好那也不行。当他站在镜子前一看,脸又黑又瘦,一身破军装,胡子头发那么长,这才连忙说替主人来看房间,「差点就露出马脚……哈哈……」[29]
1931年,上海临时中央局交通主任陈刚,身材魁梧,灰色哔叽大衣,手提一只黑色大皮夹,一副阔绰绅士派头,可内衣十分破烂,同志笑讥:「金玉其外,败絮其中。」[30]
为了隐蔽,党组织要求地下党员在集体参加国民党、三青团时,不要顶抗,要顺大溜加入,调训也应参加,然后再向组织汇报。1940年5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秘密党员加入国民党问题的指示》,「凡服务于国民党军政教育机关之秘密共产党员遇强迫加入国民党时,『就即加入国民党,但事后必须呈报党组织追认。』」[31]党组织明确「这是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两面是两面了,但对思想纯洁的红色青年来说,参加「反动活动」时的心理矛盾相当难受。[32]
反应灵敏是白区干部的基本素质。1935年春,上海地下党大破坏,夏衍去找田汉,一脚踏上楼梯,房东家保姆拉了他一下衣角,夏衍立即会意,马上跑出去,才脱险。周扬夫妇闻讯当即离家避险,身上只有四角钱,借宿小旅馆楼梯间过夜,「彻夜的胡琴声和下流笑谑声,至今犹在耳际。」这一时期,青年苏灵扬的主要任务是「联络员」,包括将鲁迅先生从北四川路「内山书店」带至一家小咖啡店,与周扬会面,以及为刚出狱的邓洁送衣服等。
周扬要用相当时间「找钱」,他向章汉夫、夏衍、羊枣(杨潮)、谭林通、梅雨(梅益)等人借钱,借的最多的是周立波、沙汀。有时仅有一块钱,上烟纸店兑开,几人「瓜分」。史沫特莱支持过周扬50元。但由于有革命与爱情,「同志们来到我家,谈笑风生,从无倦意,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总是热气蒸腾。」两个口号论争停止后,周扬不再担任上海中央局文委书记兼文化总同盟书记,冷清下来,周扬、苏灵扬夫妇「却一点也不觉得轻松愉快」,他们向往「沸腾的生活」。
地下党员有时需要身分掩护,假亲戚、假夫妻便成了必须扮演的角色。影片《永不消逝的电波》李侠原型李白(1910~1949),湖南浏阳农民,1925年入团并转党,参加秋收起义,上过井冈山,参加长征,红五军团无线电队政委。1937年10月,李白由延安来沪建立电台,组织派23岁纺织女工裘慧英扮妻,以便租房。最初,裘慧英十分不习惯与陌生男人同居一屋,太尴尬了,要求回厂,李白用「大道理」压住她,最后两人由假成真,1940年正式成婚。[33]
1928年春,六大代表、无锡农运领袖严朴(1898~1949),回国后任淞浦特委常委,领导淞浦农运,组织奉贤县千余农民暴动;后在上海法南区从事黄包车夫工运,组织决定小脚女姜兆麟(1893~1971)以妻子名义入住「机关」。严朴扮成黄包车夫早出晚归,不出门时穿西装充大少爷。姜兆麟在机关内做会计兼秘书。一段时间后,假夫妻成了真夫妻。1929年秋,叛徒告密,严朴被捕40 多天,胞兄花500 大洋赎出,10月调任松江中心县委书记兼青浦县委书记。1930年,严朴出任浙南军委书记兼红十五军政委,参加进攻温州之役。1931年冬,严朴调中央机关担任掩护工作,后携妻进入中央苏区。严朴参加长征,姜兆麟因小脚无法随行。六天后,姜兆麟被捕,严刑审讯,始终伪装笋贩,八个月后获释,行乞返沪,与党失去联系。1949年后,重新入党,先后在松江人民医院、松江地委供给科、专区妇委工作。[34]
1941年夏,南方局安排女青年李冠华携电台隐蔽起来,以便日后必要时起用。南方局组织部秘书荣高棠将李冠华送到李莫止同志家。李家有老母、弟弟,没有妻子,李冠华便成了「老婆」。四十年后,荣高棠(1912~2006):「后来他们真的成了夫妻。……这也是组织上怎么安排就怎么办,没有二话的例子。」党员绝对服从组织,广东县委书记梁隆泰,南方局分配他当传达室门房,担任第一道门保卫,他欣然接受。
夫妻有可能是假的,组织纪律则是真的。即便假夫妻成了真爱人,不该知道的事坚决不问不谈。苏灵扬1938年才在延安入党,1934~37年还在党外,与周扬同床,但还不是「同志」, 许多党内活动周扬不能告诉她。[35]
恩来同志和邓大姐也是如此。总理联系的人,邓大姐不知道;邓大姐联系的人,总理也不具体知道。我们也是这样。那时,我们住在红岩办事处楼里,房间很小,大家住在一起,每天进出走一个门,吃饭、生活都在一起,熟极了。但是,他干的什么我们不问,不知道。现在,没有哪个人可以知道当时的全部情况。[36]
1935年春,中华全国总工会白区执行局机关在上海法租界建国路一带,执行局主任夏爵一与李维汉(罗迈)夫人及其女儿李茜住在一起,李妻扮夏爵一的「岳母」,李茜则为「小姨子」,组成一个家庭。三人均靠组织经费生活,生活费、书报费、交通费加起来,「每人不过十多块钱,日子仍算过得去」。[37]
抗战后期,白区工作有了较成熟的经验,提炼出一些易记易行的口诀。如对学运,要求学生党员「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对地下党员提出「三化」——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斗争策略「三有」——有理、有利、有节。
1939年夏,清华生荣高棠在川东特委工作,没有职业。罗清在重庆沙坪坝省女职校教英文,匀出初中课程,九十多元薪水分一半给荣高棠。1940年8月,荣调入重庆城里工作,需要在城里找职业,电力公司的张瑞芳帮他在业务科找了一份抄表员的差事。后为部级高干的荣高棠,抄了一年电表,毫无贵相。[38]
国民党机关里的党员,活动方式之一为画「鸡爪」 凑份子(各爪上写有款额),买零食或聚餐,边吃边摆龙门阵,不经意间说一些红色思想。重庆税务局文书、川东特委书记廖志高:
我就利用这样的机会给他们讲一些不太暴露的革命道理。给他们介绍一些比较进步的书籍。这样做不仅不会暴露,并且同他们的关系搞得很好。[39]
三、被捕与牺牲
「四·一二」时,上海吴淞大学川籍生何洛(?~1927)与妻子刘尊一(1904~1979)被捕。何洛参加上海工人三次武装暴动,民选上海市府委员兼局长;刘尊一为江浙区妇委书记。刘也是四川妹子,1923~26年就读北京大学政治系,由罗亦农介绍入党,与赵世炎二姊妹及其他七女生结拜「十姐妹」,相约终身不嫁。不过,此时已过半数背约。刘尊一是「十姊妹」中最漂亮的一位。此时,桂系接管上海特别市党部,白崇禧淞沪警备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潘宜之(1893~1945),受同事托请,从轻发落有孕在身的刘尊一,假释送医院疗治刑伤。有人向蒋介石告状:潘宜之包庇共党要犯,蒋下令将刘尊一转南京监禁。与何洛一同被杀的有从杭州逃来的中共党员宣中华(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委员)、安体诚(杭州法政专校教授)。[40]
1927年夏,孙传芳败退苏北后,取得张宗昌等军阀支持,从扬州渡江,攻占镇江,向南京推进。何应钦、白崇禧率北伐军第一、第七军迎敌,双方对峙于南京与镇江之间的龙潭,战况惨烈。潘宜之在上海率领东路军刚接收的两艘军舰楚同号、永安号,溯江而上,直抵龙潭江面,炮击孙部,使其腹背受敌,一败涂地。是役,潘宜之立了大功。潘没邀功讨赏,而是上南京再次将刘尊一保释出狱,送进医院,让刘生下前夫何洛的遗孤。刘尊一大受感动,决定嫁潘宜之。此后,刘尊一留英学习教育,终身从教。潘宜之乃同盟会员、孙中山侍从秘书、保定军校三期生(白崇禧同班同学),「四·一二」次日夜晚,周恩来在上海七宝镇被捕,潘念旧情,当即放了周。1940年,周恩来在重庆特函国府经济部次长潘宜之,以示谢意。[41]1945年9月9日,潘宜之愤于国府降格使用,服用烈性安眠药自杀于昆明,终年52岁,留下24字遗嘱:「穿上大衣,放进棺材,抬往后山,埋在地下,树立碑子,就此了事。」1950年后,刘尊一为西南师院教育系任教授。[42]
被捕是白区地下党员必须的「时刻准备着」,日常生活中悬系的最大心理阴影。一天,瞿秋白、杨之华夫妇在上海电车上,一人盯着瞿秋白,瞿吓得面如土色。[43]甚至「二进宫」、「三进宫」也是家常便饭。就是不搞「飞行集会」之类自杀式「大干」,按周恩来给顺直省委的「小干」指示:「要能在群众中注意日常生活的痛苦所在,鼓动起日常斗争的要求和情绪,以发展到行动。」[44]再隐蔽再掩护,「反侦察」能力再强,还是会留下痕迹。仍然相当危险。
大革命后,各省地下党人数锐减,「全国各地党组织几乎没有一省未经敌人破获。1928年3月初,湖北省委和武昌市委机关被完全破坏。」[45]不少省市党组织屡建屡毁。1929年5月,厦门党员人数总共45人,其中工人16名、士兵2名、知识分子23名,其它3名;男40人,女5人。[46]
1929年秋,张爱萍(1910~2003)在上海「二进宫」。第一次进提篮桥二十天,同时被捕的还有佘一梦及后为着名演员的王莹;第二次先入龙华警备司令部,再转苏州省法院审判,一月后因证据不足获释。此时,苏北南通、如皋、靖江、泰兴等农民暴动,成立红十四军,江苏省委从上海增调干部,支部大会上张爱萍报名,学生娃转为军人。1930年初秋,进军泰州的战斗中张爱萍打断左手,秘送上海日本医院疗伤,这段经历文革中被诬为红十四军的「王连举」(文革京剧《红灯记》中叛徒,开枪自伤左臂)。[47]
江西苏区发展之前,中央机关只能设置大城市。上海因其租界、地理、交通等条件,便于隐蔽,「七·一五」后,1927年9月中共中央从武汉秘密迁沪。便一直为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各苏区重要干部也均由上海派出,各地也一直向上海中央要干部。1927年2月,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创办《革命军日报》,居然南昌、武汉都找不到合适者,郭沫若建议向上海要「创造社小伙计」潘汉年(1906~1977)。[48]
上海被捕的地下党员最多,成仁成烈者最多,叛徒也出得最多,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生死大戏。1931年4月24日,顾顺章在汉口演出魔术被捕,乃是上海过来的叛徒尤崇新认出。1933年中央军委被破坏,陈赓被捕,乃顾顺章派特务巡回小菜场,发现陈赓之妻后盯梢而至。政治局委员、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书记罗登贤被捕,因秘书叛变告密。[49]
最有代表性的叛徒事件,除了大叛徒顾顺章(中委),还有中央军委秘书白鑫。1929年8月24日,上海新闸路经远里12号白鑫家,政治局委员、江苏省军委书记彭湃主持省军委会议,出席者有政治局候委、中央军事部长兼江苏省委军事部长杨殷、江苏省军委委员颜昌颐、江苏省军委委员邢士贞(负责兵运)、上海总工会纠察队副总指挥张际春等。开会时间已到,军委秘书白鑫(1904~1929)未到,不一会儿,白鑫来了,身后跟着工部局巡捕与国民党暗探。8月30日,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同案」四人,被上海警备司令熊式辉「正法」于龙华。惟张际春得存,因张际春为黄埔一期生,蒋介石有「不杀黄埔生」的规矩,特派国民党中组部秘书曾扩情赴沪,保下张际春,1932年初释放。[50]
说明一下,此张际春(1904~1933)非另一同姓同名张际春,两位都是黄埔一期生。这位黄埔一期生乃湖南醴陵人,1933年死于战斗,一说出狱后任国民党中央军校政训处中校政治教官,1933年4月病逝重庆。另一张际春(1900~1968),湘南宜章人,1924年入黄埔一期,先入团,1925年入党,参加两次东征,升任中校营长,中山舰事件被免职;后随朱德上井冈山,历任红四军秘书长、抗大政治部主任、中宣部副部长,1968年死于文革迫害。
白鑫,湖南常德人,黄埔四期生,旋入党,参加南昌暴动,一路升至团长,1929年随领导人赴沪,任江苏省军委秘书。此前,白鑫表弟在海陆丰叛逃,被彭湃下令处决,此为白鑫叛变心理原因之一。抵沪后,在国民党捕杀压力下,白鑫通过南京的哥哥(被服厂长),联系上国民党上海党部情报处长范争波,表示一念之差误入歧途。范争波要白鑫戴罪立功,特别希望白鑫设法捉捕彭湃。彭湃、杨殷等四人被杀后,白鑫躲进范公馆,深居简出,以防「红队」(红色恐怖队)复仇。1929年11月11日晚11时,霞飞路范公馆门前停着一辆黑色别克轿车,范争波等人簇拥白鑫走出,送白鑫上南京领赏并远赴法国。白鑫与范争波拱手作别,正要举步上车,拐角处突然飞来一辆黑色轿车,车门一开,跳下三人,三声清脆枪声,范争波还未明白过来,白鑫就已倒地,一命呜呼。范赶紧叫人动手,为时已晚,三名红队队员迅速跃上车,消失在夜幕中。
白鑫的叛徒级别跻身「十大叛徒」,其余九位为:陈公博、周佛海、向忠发、顾顺章、张国焘、丁默村、李士群、文强(毛泽东表弟)、胡均鹤(赵尚志妹夫)。所谓「十大叛徒」,乃民间根据「综合内容」排列,大致反映「排列前十」。
就是遭遇被捕,也有讲究。1939年中共南方局机关设有三道门,要求若遇国民党突然袭击,每道门可抵挡5~10分钟,以便二楼三楼烧文件。[51]
1928年秋,福建省委书记陈少微被捕,他刨挖墙洞逃出,省委常委李连生则在漳州被枪毙。1931年11月,郑超麟等托派骨干被捕半年多,提他出去照相,胸前挂上姓名牌牌。照规矩,照相之后三天就是枪毙。同牢难友都将家里送来的最好菜肴给他吃,他摘下眼镜托难友转交其妻作纪念。苦熬三天,平安无事。事后知道:原判死刑,恰好龙华警备司令换人,蒋介石嫡系熊式辉换了十九路军的戴戟,刀下留人,改判十五年徒刑。[52]中共党员韩子健被捕后被押贵州息烽集中营,利用哨兵夜间换岗越狱逃出,不敢走大路,行进于崇山峻岭,夜行昼宿,历尽艰辛,三十六天才到达湖北大别山根据地。[53]
1935年2月19日晚,上海中央局书记黄文杰因叛徒出卖被捕,搜走三千现金、二十多只金戒指、四十多对玉镯、九箱档及印鉴等。是日,被捕男女及家属共三四十人。这次大逮捕中,被捕的还有宣传部长朱镜我、组织部长何成湘、秘书处负责人张唯一,以及王凌波、杜国庠、罗晓红、田汉、阳翰笙、许涤新等,上海地下党被捕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共党史称「二·一九」事件。[54]
白区地下工作花絮甚多。郑林(1908~1987),山西永济县任阳村人,1934年入党,1935年5月被叛徒出卖被捕。是日,时任「中国民族武装自卫会」书记的郑林,受山西工委宣传部长李雪峰委托,将一封来信捻成比火柴棍大一点的纸卷,夹在食指与中指之间,上太原某宅接头。一进门,见一位中年妇女,刚打听寄信人,屋里便出来一男人:
快进来坐,那位朋友刚出去,马上就回来。你把信带来了吧?快给我。
郑林十分警觉,明明单线联系,他怎么会知道有信?郑林装着找错门牌往外走,密探上来一把拧住:「先生,我领你去找那位朋友。」此时已有围观者,郑林知道不能硬来,但必须销毁那封信,随机应变地:「先生,那就太麻烦你了。」密探不便当众搜身,一转身,郑林将纸条撕得粉碎,扔在人群杂乱的脚下。此后,郑林被囚山西陆军第一监狱,1937年5月释放。1949年后,郑林任太原副市长、山西省常务副省长、省政协主席。
1936年初,山西第一模范监狱——山西陆军监狱,灰色囚衣的政治犯,戴着脚镣,两人一间、四五人一间,也有二三十人一间,上下午各有一次可出来大便,后白天可在院内晒太阳,但规定亲属不准探监,不准接触刑事犯,且不准看什么书报。吃饭上厨房排队,发臭的小米,几片发酸的萝卜干,有一次竟从饭锅里捞出两只焖烂的老鼠。犯人们提出要吃一碗干净的饭,狱方回答:「犯人就是要吃陈仓米,陈仓米就是这样,谁不爱吃就不要吃。谁叫你们犯罪呀!」政治犯抗议绝食,要求狱方答应三项条件——改善伙食、去掉脚镣、阅读书报。坚持绝食五天,终获胜利。政治犯还在狱中办起拉丁化新文字板报《都来看》。监方看不懂,看守长文化程度很低,看不懂拉丁化文字,政治犯见他「狗看告示」,故意问他上面写了什么。看守长煞有介事:「这是英文,咱不认识。」还回头训斥刑事犯:「这是外国文,你们能看懂?都快走!」看看犯人都不走,只好在一片哄笑中尴尬退身。[55]
蹲监也有好处:一切免费。有人说:「房租不必付、电灯免费、饭是警备司令送吃的,小菜有济难会接济,肚子饿时,早晨和下午还可买大饼油条吃,虽然比外面买的要贵一些。」[56]
经济力量在监狱也「无坚不摧」。1932年北京草岚子监狱(军人反省院),关押着一批日后省部级高干的政治犯:薄一波、刘澜涛、杨献珍、殷鉴、安子文、李楚离、徐冰、刘格平、廖鲁言、冯基平、魏文伯、王其梅、徐子荣、王鹤峰……因禁止读带「马」、「观」书名的书籍,最初用旧小说封面「换装」弄进来,后被发现,狱方禁止一切书籍带入。薄一波每月私塞20元好处费给看守,请他们代为购书,解决了狱中的阅读。因了这20元,薄一波违反监规,看守会为他「运作」,不称送军法处隔离反省。监狱跳蚤臭虫特多,伙食又差,他们改编《打倒列强》歌词:
谷子窝头、谷子窝头,白菜汤、白菜汤,一人一片咸菜、一人一片咸菜,真不够,真不够![57]
白区干部被捕虽然十分「正常」,但到「审干抢救运动」、「肃反」及文革,要说清楚「怎么出来的」,就很麻烦了,因为必须得有「证明人」。可这种事儿,实在不好找证明人。因此,1942~44年的延安「抢救运动」,凡是曾经被捕的白区干部,都有「敌特」、「变节」嫌疑,甚至一个省的地下党都被划为「红旗党」。如川豫两省党组织就吃了大冤枉。川省工委书记邹风平(1905~1943)被逼自杀。河南省委秘书长危拱之(1905~1973,叶剑英妻),关押致精神失常。
杨述(1913~1980), 出身江苏淮安工商地主、韦君宜之夫;1934年入清华哲学系,1936年入党(母亲兄嫂皆党员,哥哥烈士),1937年肄业清华,1938年任重庆市委组织部长兼青委书记,1939年赴延,入马列学院,任职中央党校、新华社、解放日报;1948年任团中央宣传部长,后任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国青年》社长;文革后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学部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1939年「五·一」,杨述在重庆被捕,短短一天,却成为一生甩脱不掉的梦魇。
1939年「五·一」,川东特委青委书记杨述等在重庆夫子池召集数千人大会,国民党宪兵把场,须按组织集体入场。杨述因去沙坪坝联系一党位员,回来时想入会场,宪兵不让进,杨述坚持要进,与宪兵撕打起来,所带《新华日报》等红色材料掉落,宪兵立即将他抓起来。一说杨述正要走进队伍,一阵拥挤将腋下纸包挤落,他连忙拾起,将一张纸条塞进嘴里,特务确认他为共党。押往宪兵司令部途中,路经五月书店(川东特委书记廖志高居所),杨述高呼「共产党万岁!」廖即报告南方局。南方局领导人周恩来(一说董必武)向国民党交涉,说明杨述为「八路军渝办」工作人员。次日,杨述放回,因已暴露,不久送往延安。
1984年1月,廖志高——
这件事是清楚的,杨述同志没有自首、叛变问题。但以后,杨述同志为此不知被整了多少次,特别是延安抢救运动,康生有意诬陷好人,对杨述同志揪住不放,并多次残酷毒打。直到1943年我回到延安后,才给杨述同志澄清了这个问题。[58]
1998年,其妻韦君宜《思痛录》详述杨述文革之冤——六年隔离审查、六年奔走申诉,1978年11月等到结论——「维持原有结论」。
杨述为了这一句话,把自己的生命赔了进去。……他只为了要向党证明自己的纯洁、自己的忠心。为了希望党承认他这一点,得不到这一点,他就不能活。[59]
四、卖稿为生
报刊界向为左翼文士聚集之地,如「辛亥革命时期的《太平洋报》,几乎全部是南社中人。」[60]维新党、同盟会、国共两党高干亦多出文化界。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邹容、陈独秀、陈布雷、戴季陶、叶楚伧、陈公博、于右任、吴稚晖、叶楚伧、邵力子、乔冠华、杨刚、宦乡……文士易浪漫,容易不满现实,因此文学也总是革命的起点。
邵力子弃文从政前,编了十年《民国日报》「觉悟」副刊(1919年3月4日~1929年1月20日)。[61]创造社几乎「集体加入」中共,胡也频、蒋光慈、瞿秋白、丘东平、陆蠡、沈泽民、叶紫等文学青年,后均为着名中共党人。
但文士易穷酸。瞿秋白母亲因穷发急,吞红头火柴自尽。1925~27年前后,瞿秋白不仅每月要汇三十元赡养济南老父,还要维持两个弟弟的生活、学业。他每月领取党内生活费五十元,当然不够,主要靠替塔斯社写稿,「得到相当高的报酬」。彭述之在广州时生活艰苦。张国焘在上海也过得紧紧巴巴,借贷度日,搭伙中宣部,每月七八元伙食费,欠了三个月,由郑超麟垫付。[62]
1928年,托派留苏生陆续回国,他们中许多人在上海卖稿为生,托派活动经费亦靠此维持,尤其靠翻译稿酬。托派青年大多留过学,懂外文。他们依托上海的文化环境,趁时托势,形成一点小气候,宣扬托洛茨基主义。
以卖稿得来的稿费维持个人的生活和托派组织的经费,这是当时上海托派分子之所以能聚集较多,搞成一点小气候的政治背景和经济原因。没有这个条件,那些离开了文字手段难以谋生的人,很难较长时间聚集在一起,中国托派运动也就很难搞成那样的声势。
卖稿为生的托派文人有的也很穷,如没出过国的北大毕业生陈其昌,为报刊写国际政评,一家三口,妻子家庭妇女,有时帮佣,全家穷到「三月不知肉味」。但「他从不发一句怨言,不向人诉苦,也不轻易向人告贷,不影响对托派工作的热忱,以此赢得托派同志的尊敬。」[63]
下狱后的郑超麟等人,狱中继续译稿,并能很快出版或发表,「收入不少稿费,有的人还可以拿去养家。超麟译得多,译得快,他的稿费也多。」[64]1930年,托派王凡西被开除出党,生活无着,卧病在床,妻子又临近分娩,
惟一可以找点生活费的是卖稿子……于是口译了普列汉诺夫的《从唯心论到唯物论》,由妻子笔录,居然卖到120元(约等于五个月的党内生活费),如此才算度过了被党(中共)逐出后的第一个难关。
王凡西后来编译《俄国革命史》(插图本),稿酬三元/千字,共约三四十万字,稿费达千元。
我在1931年5月被捕以前,生活来源完全靠了此项稿费。不仅我一人如此,所有的反对派(按:托派)干部分子,只要是能够提得起笔的,均以译著社会科学文稿解决生活问题。不但各人自己的生活,甚至当时各小派(按:托派内部小派别)的经费,以及每派中从事组织工作的同志们的生活,也取给于那些卖文者的收入。[65]
无论横向比较还是纵向比较,其时稿费都不算低,也是那些「亭子间作家」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
当然,也有少数富余者。1928~34年,夏衍搞日文翻译,「译稿费大概是每千字二元,我每天译2000字,我就可以有每月120元的收入。这样,在文艺界的穷朋友中,我不自觉地成了『富户』。」[66]夏衍还有编剧顾问的「车马费」、电影剧本编剧费,月入至少200元,很阔呵。夏衍1924年入国民党(孙中山介绍)、1927年5月入共产党,但「我的生活靠稿费、版税,除了皖南事变后中央要我从桂林撤退到香港,组织上给我买了飞机票,以及1946年恩来同志要我去新加坡,组织上给了我一笔旅费之外,我一直是自力更生、卖文为生。」在红色职业革命者中,夏衍属于绝少数的自食其力者。
1950年代初评职级,人事干部问夏衍供给制每月领几斤小米,夏衍答从来不吃小米,更没领过,人事干部一脸惶惑。华东局、上海市委根据夏衍党龄、职务,评了个「兵团级」。书生从政的他「还是不懂得兵团级是怎样一个职位」。[67]
1928~35年,阳翰笙稿费加编剧费,月入200元。1935年春被捕,10月由柳亚子、蔡元培保释出狱,仍靠稿费与编辑《新民报》「新园地」副刊为生,月得百余元。1929年,鲁迅推荐柔石编辑《语丝》周刊。柔石小说《二月》、《旧时代之死》由鲁迅作序、校订出版,20%版税,月入80~100元。[68]当年文化界的整体收入不错,摆弄文学不仅可以成名成家,而且「回报颇丰」。
1932年陈白尘回江苏淮阴老家闹红,秋天被逮捕,次年解送镇江,判刑五年。1933~34年,他在狱中写下50多万字作品,取材多为控诉黑牢生活,两块大洋买通看守,稿件寄往狱外,陆续发表于左翼刊物。独幕剧《虞姬》发表于《文学》(1933年1卷3期),稿费50元,狱犯十分红眼,陈白尘惴惴不安,不得已用此款去买「外役」(牢内较自由的义务劳动),将钱花在狱中,别人也就不怎么眼红了。[69]
1934年9月,首任满洲省委书记邓洁(1902~1979),在大连蹲狱七年两个月后获释,因单独关押,出狱时连话都不会说了。他通过杭州艺专校长林风眠寻找党组织,林风眠派人陪同赴沪找到周扬。邓洁靠稿费维持生活,经常在饭摊上买碗菜饭或几只粽子解决问题。1936年春,两位初到上海参加革命的青年,对他说没有生活费,邓洁让两青年在路边等一等,二十分钟后回来,递给他们三块钱。两青年接过钱,发现他身上的旧夹大衣不见了。[70]
1934~1935年,上海地下党与中央失去联系,为筹措经费,做公债买卖,因消息不灵、缺乏经验,反亏蚀不少本钱,为偿清借贷,大家只得典当冬衣。1936年9月,上海临委书记邓洁在中山公园与冯雪峰接头,再次被捕,当时上海公园只有年票,无零售票,票上填有姓名、住址,但无照片。邓洁拿着孟心波的公园年票进去,被捕时吞吃月票,并一直熬到次日,估计外面同志已做好应变准备,才说出自己的住址。邓洁只说参加救亡,不承认参与其他活动,不久被保释。[71]
1934年11月初,萧军、萧红揣着朋友资助的40元搭船赴沪,租居亭子间(月租九元),兜里已不足十元。他们买了一袋面粉、一只炭炉、一些木炭、几副碗筷、盐醋,已买不起食油。每天白水煮面片,外加几个铜板的菠菜青菜。一天,张梅林来看他们,萧红留他吃饭,梅林甚感不忍,因为那袋面粉在渐渐瘪下去。为复写誊抄《八月的乡村》,萧军去当萧红的一件旧毛衣,押得七角,坐车就不能买纸,买纸就不能坐车。萧军还是走到北四川路内山书店,购回日产美浓复写纸,皮鞋不跟脚,脚后跟又红又肿。1935年3月1日,《文学》杂志刊出萧军第一篇小说《职业》,稿费38元,算是将二萧从窘迫中捞救上来。[72]
周扬(1908~1989)抗战前在上海:「那时候我的生活没有着落。我虽然是个职业革命家,但是在上海的生活我完全靠自己的稿费,党并没有给我钱。」[73] 周扬据称周瑜后裔,家道衰落,其妻吴淑媛(1908~1942)乃大户之女。周扬最初在沪搞革命,全靠岳家经援。1934年暑假,周扬爱上光华大学女生苏灵扬,与之同居,将发妻送回湖南益阳,断了岳家接济,经常上胡风处告贷,求借三五元菜金,「周扬经常来借钱,很少归还。」[74]1936年苏灵扬临盆,阵痛难忍,周扬身无分文,没法送医院,急得团团转。其女周密:
最后从郑振铎伯伯处借回20大洋,才使我免于落生在那间不满十平方米、整日不见亮光的亭子间里。有了我,您和妈妈的生活更加拮据了。不得不设法挣点稿费来糊口度日,列夫·托尔斯泰名著《安娜·卡列尼娜》的中译本,就是在那种境况下问世的。[75]
翻译《安娜·卡列尼娜》得酬800元,周扬经济状态才有所好转。[76]
亭子间作家
红色文士中也有依靠稿费坚持写作的「亭子间作家」。1935年3月中旬,陈白尘系狱两年半后出走苏州反省院,上海《文学》杂志主编傅东华答应每期用他两篇稿,以支持其生活——
这可大出我的意料:原本一篇稿子的稿费就可以维持我两个月的生活了。于是我便有了信心,做一名所谓的「亭子间作家」。[77]
住亭子间的左联文学青年,早餐三分钱,一碗豆浆、一个饭团包油条(加点白糖);中餐七分,小饭馆的米饭豆腐、猪肝菠菜汤;晚餐四~五分,喝粥,一碟小菜,每天不到二角,每月伙食费五~六元(合2003年150~180元人民币),最低生活水平的城市贫民。[78]
贾植芳(1916~2008):
没有住过上海亭子间,怎么可能成为艺术家?三十年代的时候,我和黄永玉都住在亭子间里,开荤的日子就是吃碗阳春面,上面漂着几滴猪油花。那会儿,唉,黄永玉穿的西装裤子上哪里去烫啊,还不就是折了一条线,压在枕头底下,睡觉的时候把它压一压。到关键的时刻,才舍得拿出来穿啊。……上海的亭子间,可了不起呐!出了多少人啊![79]
1933年,广东女师生草明(1913~2002)因「红」暴露身分,上了通缉黑名单,逃亡到上海,加入左联——
我们这些年轻的进步的文艺工作者都找不到职业,生活是很艰苦的,稿费也很低,仅够维持最低的生活。有时实在吃不上饭,鲁迅先生和左联的一些同志热情地从他们有限的生活费用中匀出一小部分来接济。我住在租界里房金最便宜的亭子间里埋头写作。[80]
彭家煌(1898~1933),1919年毕业于长沙省立一师,1925年入商务印书馆,帮助编辑《妇女杂志》、《教育杂志》、《民铎》等,月薪40元。1930年3月,加入「左联」,同时参加地下工作,任《红旗日报》助编及通讯员。1931年被捕。出狱后,到宁波教中学,一面教书一面搞宣传。[81]
「一二·九」后参加中共的李锐、范元甄,没有经济来源,衣食住行、婚嫁病残等都要家庭或亲友资助,尽管这些青年革命者看不起供养自己的「不革命者」。[82]
2014-8-10 上海
[1] 方志纯:《赣东北革命斗争的回忆》,《回忆闽浙皖赣的革命斗争》,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页89。
[2] 杨超:《在西南四省区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1982年10月26日),《四川党史研究资料》1983年第1期,页42。
[3] 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北京)1983年,页440。
[4]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192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1989年,页154~155。
[5] 赵赴:〈五大至六大期间陕西省党的组织状况(三)〉,《党的文献》(北京)1990年第4期,页94~95。
[6] 徐彬如:〈大革命时期我在广州的经历〉,载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党史研究资料》(北京)1983年第10期,页5。
[7] 李逸民:《李逸民回忆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58。
[8] 刘英:《刘英自述》,人民出版社(北京)2005年,页24。
[9] 璞玉霍:〈周恩来与党的白区工作策略方针〉,《党的文献》(北京)1991年第3期,页58~60。
[10] 龚楚:《龚楚将军回忆录》,明报出版社(香港)1978年初年,下卷,页335~338、506。
[11] 王凡西:《双山回忆录》,东方出版社(北京)2004年,页125~126。
[12] 〈苏兆征和向忠发向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1928-5-7),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831),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2002年,页445~446。
[13] 李初梨:〈六庙四中全会前后纪事〉,参见欧阳淞、曲青山主编:《红色往事》,济南出版社2012年,第一册·政治卷(上),页第116。
[14] 刘晓:〈党的六庙三、四中全会前后白区党内斗争的一些情况〉,参见欧阳淞、曲青山主编《红色往事》,济南出版社2012年,第一册·政治卷(上),页128。
[15] 曾三:〈我党无线电通讯事业的创建〉,参见欧阳淞、曲青山主编《红色往事》,济南出版社2012年,第六册·文化卷,页12~13。
[16] 邢子陶:〈内战时期我在上海做地下革命工作〉,《上海党史资料通讯》1989年第12期,页18~20。
[17] 黄药眠:《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页246。
[18] 《谢觉哉日记》,人民出版社(北京)1984年,下册,页934。
[19] 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页105。
[20] 原《转变》1933年(民国22年)10月号,页331~343。参见辽宁省党史学会、辽宁省高校党史教研会编印:《党史研究参考资料》1981年第15期转载,页23~24。
[21] 赵家梁、张晓霁:《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大风出版社(香港)2008年,页66。
[22] 杜宁(杨之华):〈叛徒顾顺章叛变的经过和教训〉,《党的文献》(北京)1991年第3期,页22。
[23] 郭德宏:〈关于顾顺章和向忠发——王明的回忆〉,《同舟共进》(广州)2012年第8期,页58。
[24] 《郑超麟回忆录》,东方出版社(北京)2004年,上卷,页238;下卷,页98~99。
[25] 〈颜昌颐小传〉,《上海党史资料通讯》1989年第11期,页26。
[26] 《刘英自述》,人民出版社(北京)2005年,页21~22。
[27] 朱瑞:〈我的历史与思想自传〉,《中共党史资料》第9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页238。
[28] 沈漪:〈怀念张如心同志〉;温济泽等编《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页188~189。
[29] 荒煤:〈在晋东南前线——刘伯承将军会见记〉,原《新华日报》(重庆)1940年9月30日,第四年。参见《刘伯承回忆录》,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页217。
[30] 何盛明整理:〈陈刚战斗在上海〉,《上海党史资料通讯》1989年第9期,页38~39。
[31] 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重庆出版社1986年,页93。
[32] 廖志高:〈抗日战争时期在南方局直接领导下重建、发展、巩固川东地下党的主要情况(1939年12月~1943年9月)〉,《四川党史研究资料》1984年第3期,页12。
[33] 周兆良编著:《永不消逝的电波——李白烈士的故事》,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上海)1996年,页79~80、170。
[34] 尹军:〈松江姜家姐妹革命花〉,《上海党史资料通讯》1989年第11期,页38~39。
[35] 苏灵扬:〈一个不是作家的「左联」盟员的回忆〉,《上海党史资料通讯》1987年第9期,页3~16。
[36] 《荣高棠同志的讲话》(1982-10-25),《四川党史研究资料》1983年第1期,页31~32。
[37] 夏爵一:〈三十年代我在上海进行的地下斗争〉,《上海党史资料通讯》1989年第6期,页14。
[38] 《荣高棠同志的讲话》(1982-10-25),《四川党史研究资料》1983年第1期,页288。
[39] 廖志高:〈抗日战争时期在南方局直接领导下重建、发展、巩固川东地下党的主要情况(1939年12月~1943年9月)〉,《四川党史研究资料》1984年第3期,页12。
[40] 《郑超麟回忆录》,东方出版社(北京)2004年,上卷,页302~303。
[41] 《历史漩涡中的蒋介石与周恩来》,中央党校出版社,第三章五节
[42] 刘亦实:《桂系将领潘宜之娶待决共产党员为妻》,《文史春秋》2002年第6期。
[43] 《郑超麟回忆录》,东方出版社(北京)2004年,下卷,页23。
[44] 周恩来:《在白色恐怖下如何健全党的组织工作》(1929-3-25),《周恩来选集》人民出版社(北京)1980年,上卷,页21。
[45] 璞玉霍:〈周恩来与党的白区工作策略方针〉,《党的文献》(北京)1991年第3期,页58。
[46] 〈中共福建省委给中央的报告——军事、党务与地方工作情况〉(1929年5月),《红四军入闽和古田会议文献资料》(续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页23。
[47] 张爱萍:〈抗日战争初期在上海组织苏浙敌后游击战争主要情况〉,《上海党史资料通讯》1989年第8期,页14~15。
[48] 何炎牛:〈从「小伙计」到担任「文委」书记的潘汉年〉,《上海党史资料通讯》1989年第8期,页24。
[49] 杜宁(杨之华):〈叛徒顾顺章叛变的经过和教训〉,《党的文献》(北京)1991年第3期,页22。
[50] 贺培真:〈关于彭湃等同志遇害经过的片断回忆〉,《党史研究资料》第二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页485~486。
[51] 〈荣高棠同志的讲话〉(1982-10-25),《四川党史研究资料》1983年第1期,页30。
[52] 《郑超麟回忆录》,东方出版社(北京)2004年,上卷,页310;下卷,页214。
[53] 李澄:〈纪念余硕卿(张露萍)烈士〉,《四川党史研究资料》1983年第9期,页20。
[54] 阿犁:〈忆张唯一同志〉,《上海党史资料通讯》1986年第2期,页17。
[55] 周宗奇:〈无畏的雄鹰——郑林在狱中的斗争〉,《党史文汇》(太原)1990年第3期,页12~13、16~17。
[56] 《郑超麟回忆录》,东方出版社(北京)2004年,上卷,页316。
[57] 芦焰:〈闪烁在敌人狱中的理想之光——记刘聚奎在「草岚子」〉,《党史文汇》(太原)1990年第5期,页44~45。
[58] 廖志高:〈抗日战争时期在南方局直接领导下重建、发展、巩固川东地下党的主要情况(1939年12月~1943年9月)〉,《四川党史研究资料》1984年第3期,页7。
参见冯兰瑞:《别有人间行路难》,时代国际出版社(香港)2005年,页384。
[59] 韦君宜:《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页133。
[60]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山西古籍出版社、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页453。
[61] 赵景深:《我与文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页125。
[62] 《郑超麟回忆录》,东方出版社(北京)2004年,下卷,页148、17~18。
[63] 唐宝林:《中国托派史》,东大图书公司(台湾)1994年,页133、178。
[64] 楼适夷:《玉尹残集·序》,《郑超麟回忆录》(下卷),东方出版社(北京)2004年,页699。
[65] 王凡西:《双山回忆录》,东方出版社(北京)2004年,页132~133、165。
[66] 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补本),三联书店(北京)2000年,页87~88。
[67] 夏衍:《懒寻旧梦录》,三联书店(北京)1985年,页610。
[68] 陈明远:《才·材·财》,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页160~161、158。
[69] 陈白尘:《对人世的告别》,三联书店(北京)1997年,页470。
[70] 陈光宇:〈邓洁同志在上海的二三事〉,《上海党史资料通讯》1986年第1期,页28。
[71] 何慧君:〈邓洁同志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片段〉,《上海党史资料通讯》1986年第1期,页30~32。
[72] 秋石:《两个倔强的灵魂》,作家出版社(北京)2000年,页81~83、118。
[73] 赵浩生:〈周扬笑谈历史功过〉,《七十年代》(香港)1978年9月号。参见朱鸿如编选《众说纷纭话延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页236。
[74] 陈明远:《文化人与钱》,百花文艺出版社(天津)2001年,页117。
[75] 周密:〈怀念爸爸〉,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页578。
[76] 陈明远:《文化人与钱》,百花文艺出版社(天津)2001年,页123。
[77] 陈白尘:《对人世的告别》,三联书店(北京)1997年,页480。
[78] 陈明远:《才·材·财》,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页157。
[79] 彭小莲:《他们的岁月》,天地图书公司(香港)2001年,页100。
[80] 草明:〈回顾与前瞻〉,《当我年轻的时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页79。
[81] 赵景深:《我与文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页268。
[82] 李南央编:《父母昨日书》,时代国际出版公司2005年,上册,页169。
原载:《同舟共进》(广州)2015年3月号
转载:《各界》(西安)2015年第5期
《文摘周报》(成都)2015-4-21
《新周报》(六安)2015-3-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