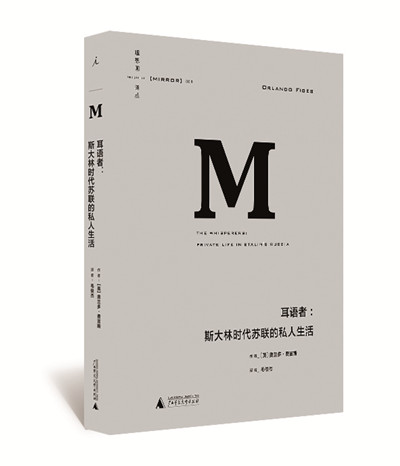在前苏联,当举报成为一个国家维持统治的常规手段,当告密成为一个公民获得表彰的便捷途径,当家庭和亲情濒临崩溃,文化和传统荡然无存······所有人都有可能是嫌疑犯或者秘密警察,人们只能被迫成为“耳语者”。
在前苏联,当举报成为一个国家维持统治的常规手段,当告密成为一个公民获得表彰的便捷途径,当家庭和亲情濒临崩溃,文化和传统荡然无存······所有人都有可能是嫌疑犯或者秘密警察,人们只能被迫成为“耳语者”。
斯大林时代(1924—1953)既是一个全面控制时代的开端,也是它的高潮时刻。经过改造的苏维埃人,既恐惧政治权力,又对它无比崇拜。他们几乎每个人都成了“耳语者”——或藏身于角落窃窃私语、互诉衷肠,或暗中迎合,成为向当局告密的举报人。许多关于苏联的历史著作都聚焦于恐怖的外在现象——古拉格、逮捕、判刑、囚禁甚至杀害,却几乎没有人关注普通的苏联人过着一种怎样的私人生活,他们的真实想法和感受是什么。
《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所关注的正是最为广泛的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和内在心灵,是第一部深入探索斯大林时期个人和家庭生活的口述历史著作。尽管在书中几乎每一页都能感受到斯大林的存在,但是《耳语者》并不讲述斯大林本人,讲的是,斯大林主义如何渗入普通人的思想和情感,如何影响他们的价值观和人际关系。本书也并不试图解说恐怖的起源,或描述古拉格的兴衰;只想解释警察国家如何在苏维埃社会扎根,让数百万普通百姓卷入恐怖制度,或是沉默旁观者,或为积极合作者。正如俄罗斯历史学家米哈伊尔·;格夫特所说,斯大林制度的真正力量和持久遗产,既不在于国家结构,也不在于领袖崇拜,而在于“潜入我们内心的斯大林主义”。
而对于这一切,我们绝不陌生。
作者奥兰多·费吉斯(OrlandoFiges,1959—),英国人,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博士,现为英国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历史学教授。他的一系列解读沙俄及苏联历史的著作——《耳语者》、《娜塔莎之舞》等,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是当今英语世界俄罗斯研究的一流大家。作品曾获沃尔夫森奖、NCR图书奖等,入围萨缪尔·约翰逊奖、达夫·库珀奖等,并已被翻译成20多种文字出版。
译者毛俊杰,1952年生于上海,1978年入复旦分校中文系,1981年后定居纽约,译作有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杰克·凯鲁亚克《吉拉德的幻象》等。
【精彩书摘】
1917年10月,叶丽萨维塔·德拉布金娜在布尔什维克总部的斯莫尔尼学院见到自己父亲时竟然都认不出他。上次见面时,她只有5岁,过后不久,父亲便潜入地下活动。12年后的今天,她已把他的模样忘得一干二净,只记得他的党内化名。叶丽萨维塔在斯莫尔尼学院任秘书,非常熟悉数十份法令上的签名—“谢尔盖·古谢夫”,他是负责首都秩序的彼得格勒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她沿斯莫尔尼学院无尽的拱形长廊匆匆走过,听到正在休息的士兵和赤卫队员发出嗤笑和口哨。这座贵妇学校营房一般的教室,已改为苏维埃新政府的临时办事处,她的工作就是分发法令。当她告诉其他秘书,这些签名属于她失散多年的父亲,她们都没将之当做一回事。从未有人建议,她应该与他重建联系。在这些圈子中,每一名布尔什维克的个人利益必须服从共同事业。党在为人类解放开展决定性的斗争,你如果仍在记挂私人生活,就会被视为“市侩”。
最后驱使叶丽萨维塔走向父亲的是饥饿。她在烟雾缭绕的地下室食堂刚刚吃完午餐,走进来一名身材矮小但肌肉健硕的英俊男子,身着军装,戴夹鼻眼镜,尾随一长列党的干部和赤卫队员,在中央长桌旁坐下。两名士兵向饿坏了的无产者们分发菜汤和粥。叶丽萨维塔仍然很饿,坐在角落的小桌旁,观察那名英俊男子一手以汤匙喝汤,另一手执铅笔在尾随者递上的文件上签字。
突然有人叫他“古谢夫同志”。
我意识到,这一定是我父亲了,想也没想就站起身来,朝拥挤的餐桌挤过去。
“古谢夫同志,我需要你。”他转过身来,显得很疲惫,因睡眠不足而双眼通红。
“我在听,同志!”
“古谢夫同志,我是你女儿,给我3卢布,我要吃一份午餐。”
也许,他已筋疲力尽,听到的只是我对3个卢布的索求。
“当然,同志。”古谢夫说,探手入口袋,掏出一张绿色的3卢布钞票。我接过钱,向他表示感谢,用它买了另一份午餐。
列宁很喜欢这一则故事,在1924年去世之前,经常叫其时已变得稔熟的叶丽萨维塔·德拉布金娜讲述此事。它在党内变成了一个传奇,生动表现了布尔什维克的个人牺牲,以及对革命事业的无私奉献。斯大林曾说:“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不应也不能拥有家庭,因为他必须将自己的一切献给党。”
执政的布尔什维克敦促普通党员以沙俄时的革命家为榜样,牺牲个人幸福,放弃自己家庭,为工人阶级服务。?他们提倡对“大公无私的革命家”的崇拜,构建全新的道德观,以一切献给党的单一原则取代所有的旧诫。在他们的乌托邦憧憬中,革命家是新人的原型—只为公众利益而活的“集体人格”—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将由这种新人组成。很多社会主义者把培育新人当做革命的根本目标。马克西姆·高尔基在1917年春天写道:“政治生活的新结构向我们要求全新的灵魂结构。”[5]
对布尔什维克来说,从根本上实现“集体人格”,需要“砸碎私人生活的甲壳”。列宁的妻子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认为,允许“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之间存有差别,迟早会导致对共产主义的背叛”。根据布尔什维克的说法,与政治领域截然分开的“私人生活”的理念是荒谬的,因为政治影响一切;所谓的“私人生活”,无不与政治有关。所以,私人领域仍应受到社会公众的监督和控制。布尔什维克将不受国家控制的私人空间视作孕育反革命分子的危险温床,认为必须予以揭露和铲除。
这次遭遇之后,叶丽萨维塔很少看到父亲,他们各自忙于自己的革命活动。1917年之后,叶丽萨维塔继续在斯维尔德洛夫办公室工作。在内战期间(1918—1920),她参加了红军,先是做医疗助理,后来成为机枪手,参与在西伯利亚、波罗的海、俄罗斯南部向西方列强支持的白军或反革命军队发起的进攻。她在抗击海军上将高尔察克白军的东线战役中,甚至在父亲指挥下投入战斗。其时,父亲在革命军事委员会担任高级职务,充当苏维埃军队的指挥中枢,该委员会以托洛茨基为首。叶丽萨维塔经常听父亲向战士发表演讲,但从没走近他。她后来说,自己认为布尔什维克不应“关注私人事务”。整个内战时期,他们只相遇两次。第一次是在1919年3月斯维尔德洛夫的葬礼上,第二次是同年稍晚在克里姆林宫的正式会议上。到了20年代,父亲和女儿都在莫斯科从事党的工作,见面更加频繁,甚至有一段时间住在一起,但仍然无法亲近。他们分开得太久,无法培养亲情。叶丽萨维塔回忆:“父亲从没对我说过他自己。我现在才意识到,等他去世后[1933年],别人讲起他,我才开始对他有所了解。”
内战不仅是对白军的军事斗争,还是对旧社会私人利益的革命斗争。为了应付白军,布尔什维克开发了第一套计划经济(战时共产主义),后来成为斯大林五年计划的原型。他们试图杜绝私人的贸易和财产(甚至计划以配给来取代金钱);向农民征集粮食来养活城市和军队;征召数百万劳动大军奔赴“经济战线”,包括伐木为薪、建筑道路、维修铁路;强制推行实验性的集体劳动,让人们住进工厂附属的宿舍和营房;向宗教开战,迫害神职人员和教徒,关闭数百座教堂;钳制所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异见者。在内战的“内部战线”上,布尔什维克发起反对“布尔乔亚”—前沙皇官员、地主、商人、富农、商贩和旧知识分子—的恐怖运动(红色恐怖),因为这些人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很容易使自己成为白军和其他“反革命”的潜在朋友。布尔什维克相信,如此凶猛地清洗社会,是通向共产主义乌托邦的捷径。
来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