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即使这样高贵的灵魂,也无法避免在极权统治下“自贱自辱”的命运。
“这次,你如果能单独来,会更好。”这是《布达佩斯往事》开篇的头一句话。这本书有一个长长的副标题:“冷战时期一个东欧家庭的秘密档案”。够了,单是这些,就已经足够吸引我去买下这本书,而它的原文标题则更显直白:“人民公敌”。一个多么熟悉的名词。但究竟谁是“人民公敌”?为什么档案管理员希望查阅档案的人“单独来”?在接下去的八小时里,我没有任何停顿地一字一句读完了这部纪实作品,仿佛在和作者一起,窥探着在那个“潘多拉盒子”里深藏了数十年的家族秘密。我得说,这是一次酣畅淋漓的阅读,尽管它涉及的题材,是如此地黑暗,如此地沉重。
监控:不是秘密的“秘密”
这部书的作者,是匈牙利裔美国作家、新闻人卡蒂·马顿。她生命里最初的六年时光,就是在匈牙利度过的。那时,她的父母分别为美联社与合众社工作的,作为匈牙利公民,他们也是这个共产主义国家里硕果仅存的外国通讯社通讯员。早在战后不久的1946年,用作者的话说,“父亲就开始出现在苏联的雷达屏幕上”,这也就意味着,他受到了当局的关注和监控。
这件事的起因是,当时统治匈牙利的盟国管制委员会的苏联主席,命令匈牙利当局解散包括童子军在内的青年组织,并且禁止反对苏联的政客担任公职。敏感的新闻人马顿先生立刻意识到,外国势力又开始干涉匈牙利内部事务了,而这还是自德国的占领终止之后从未有过的事情,于是他在第一时间发出了报道。也正是在那一年的9月,匈牙利秘密警察机构“国家安全局”刚刚组建完毕,马顿就这样“顺利成章”地上了这个新单位的名单,有关他和他家庭的秘密档案逐渐成形,正式开启了此后近二十年全面监控的历程。

秘密警察关于马顿夫妇监视和审讯记录的一部分
大约六十年之后,当马顿的生命即将走到终点时,新匈牙利的外交部长向这位始终忠诚于自己民族的声誉卓著的新闻人,颁发了匈牙利的最高文职奖。代为领奖的正是作者。当她从匈牙利外交部长的手中,接过秘密警察关于她父亲的一大袋材料时,不禁大为惊讶。而她的父亲,仍是一如既往地不愿意谈论过去,有生之年甚至从未打开过那个档案袋,也许是因为实在不堪回首。但正是这些材料,成为了作者探索那段隐秘家族史的起点,她开始频繁地返回匈牙利,细读档案,会见父母的老朋友或是老对手,揭开了一个又一个父母从未向她吐露过的秘密。
马顿夫妇出生于匈牙利的上层犹太家庭,两人都拥有博士学位,却常常因为自己的犹太出身而找不到工作,最后只能靠充任家庭教师谋生。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作者从小对自己的犹太身份一无所知,直到三十岁那年,在追踪一位瑞典外交官拯救犹太人的往事时,才偶然从别人口中获知了外祖父母的下落:他们双双死在了奥斯维辛。而这个家庭里的两位成年人,从来都不向孩子提及这场杀戮,外祖父母永远在家庭相册中缺席,当被孩子们追问时,马顿太太总是以泪流满面来作为回应,让人不忍再次提及。女儿曾经全然不知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二战期间,马顿先生曾经参加过小规模的地下抵抗运动,这对夫妇的婚姻,在1950面带中期曾经走到过崩溃的边缘……总之,在秘密警察的监控之下,一切的秘密、一切的家庭隐私,都早已不成其为隐私。

马顿夫妇在凡尔赛宫前,这是他们在1948年匈牙利当局停发护照前最后一次出国。
而另一方面,作为老牌记者和经验丰富的被监控者,马顿夫妇也完全对这种监控心知肚明。他们想出的对策是:在警察眼皮子底下,公开会见前来拜访他们的西方人士;每星期二,雷打不动开着漂亮惹眼的美国产白色敞篷车,去到美国公使馆参加记者招待会;定期带着孩子参加外国使团举办的聚会,并且永远是晚宴上唯一的匈牙利家庭。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显然是故意做给当局看,也是为了给将来注定要面临的审讯做准备。马顿太太在被捕之后,曾经为自己的行为辩解:“你们指控我从事间谍活动,可是你见过这样招摇过市的间谍吗?”太天真了!作为普通人,他们按照常理来做这样的自我保护,自然是没错了,可他们似乎忘了自己的对手是谁,或者说,也实在想不出更好办法来保护自己和孩子们,无奈之下只能用这种“自作聪明”的办法来获取一点心理安慰。
恐惧、告密与坚守
马顿夫妇可以算是极权统治之下难得的明白人。可是他们也许都不愿意承认,他们做出这样下意识的自我保护,恰恰是因为感到恐惧。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这部对后世影响巨大的著作中,早已指出过“恐怖”的实质。也是他,最早将“恐怖”认定为一种政治体制的标志。在孟德斯鸠看来,不论是共和制、君主制,还是独裁专制,在每一种政治组织形态背后,都有着与它相对应的不可或缺的精神因素或文化倾向,以保证维持这种体制。维护君主政治的是“荣誉”,维护共和政治的是“德行”,而维持专制独裁的,则是“恐怖”。用高压引出人民身体里的恐惧,靠这种永远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来换取被统治者的屈从,让他们自甘奴役,变得犬儒、冷漠,丧失与周围人之间活生生的联系。
更可怕的是,这种统治还胁迫民众充当告密者。在这本书里,作者就反复提到那些记载于档案之中的、围绕在马顿夫妇身边的告密者:从看门人到家庭教师,从朋友到亲人,几乎每一个身边的人,都成为了马顿夫妇身边的“潜伏者”。而让人更感荒谬的是,马顿夫妇对此并非毫无所知,为了自身的安全,他们甚至还不得不帮助告密者完成自己的对手给告密者布置的工作任务。比如,他们会为缺乏绘画天赋的保姆画下家里的平面图,让她拿给警察交差;每周在一起打桥牌的朋友告诉他们,自己需要定期写报告向国安人员汇报马顿夫妇的动向,安德烈·马顿就每月替他们草拟报告,自己“汇报”自己的一举一动,再由朋友用笔抄下送给警察存档。
那么,身处如此恶劣环境的马顿夫妇自身,究竟有着怎样的身份呢?难道他们就真的不曾出卖过自己身边的人?这也是作者在查阅档案时最害怕揭开的秘密:她怕有一天,从档案中发现,自己一直以来引以为傲的父母,同样是为人不齿的变节者或“线人”。她也终于理解了档案管理员的一番苦心:“你如果能单独来,会更好。”,因为这套记载着事无巨细生活内容的档案,很可能是一个 “潘多拉盒子”,一旦打开,就要冒永远打碎父母形象的巨大风险。
这并不是不可能的,想想看,从君特·格拉斯到米兰·昆德拉,盖世太保和克格勃的秘密档案,揭开了多少人所不知的龌龊往事。在20世纪规模庞大的档案库里,还隐藏着数量惊人的普通人背叛和告密的故事。当然,我们可以说,在几乎没有选择自由的政治高压下,这类行为是可以理解,最终也是应该得到谅解的。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对人的评价,毕竟是要以他自身的行为作基础的,某些切切实实存在的落井下石行为,难道就可以这样轻易地被原谅乃至遗忘了吗?
幸运的是,马顿父母的全部档案都可以证明,他们没有充当过告密者,即使是在被捕之后,官方档案也清晰地记载着,马顿夫妇没有在供述中牵扯到任何匈牙利同胞,对于那些享有外交豁免权、可以随时自由离境的各国外交官,他们写下的供述,也总是让国安人员找不到任何把柄。直到此时,长久以来折磨着作者的那种担心和忧虑,才总算是远离了她。在如此残酷、乃至可说是盛产恶棍的制度之下,能在如此艰难的境遇里,始终如一地坚守自己的底线,不做施害者的帮凶,不助纣为虐,委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马顿夫妇始终坚守的,不仅是自己的道德底线,还有对家人的爱。尤其是马顿的父亲,这位一生都不善于对孩子表达感情的老记者,在狱中是如此在乎自己妻子和孩子的安危。一名同监的告密者在报告中写道:“我了解他的本性。如果他仍在隐藏秘密,迫使他招供的唯一方式,就是威胁他的妻子甚至小孩。我确信,他的妻子,更甚者,他的小孩,如果大难当头,他会招出一切来拯救我们。”作者不无辛酸地写道:“多大的讽刺!他爱我们的最重要证据,竟来自一名秘密警察的告密者。”
而就在马顿夫妇的经历中,最让人感觉哭笑不得的是,他们曾经濒临破裂的婚姻,居然是被秘密警察的逮捕行动所拯救的。在马顿夫妇被捕之前的最后一个夏天,马顿太太发现自己的丈夫,跟英国大使馆一名官员的妻子有染,为了报复丈夫,她自己也开始接受来自一位朋友的追求。而1955年圣诞来临之前的那次秘密逮捕,以及随后而来的一段牢狱之灾,反倒是让他们更好地认识了彼此。伊洛娜在丈夫最艰难的时刻,竭尽全力争取西方支持,呼吁西方媒体向匈牙利当局施加压力,直到自己也因同样的罪名被捕,都始终没有失去过重获自由的信心。在狱中,她坚持向当局申请与丈夫会面,终于将外界的消息巧妙地传递给了对方。这一切,都给了一度企图自杀的安德烈以巨大的安慰和活下去的勇气。经此一劫,他们终于重新爱上了彼此,直到生命结束。
创伤,直到永远
在读这本书时,我总是忍不住为马顿夫妇的命运感到庆幸。诚然,他们的生命里,先后出现过可能危及性命的纳粹统治,以及匈牙利极权统治者的迫害,但不幸中之万幸,他们以自己的机智逃出了纳粹的魔掌;即使不幸在共产主义的匈牙利被捕,所幸其时赫鲁晓夫已经上台,尽管那个曾令全体匈牙利人胆战心惊的拉科西正在经历短暂的东山再起,但比之于斯大林时代,统治的残酷性毕竟已不可同日而语,这让这对夫妇得以免于死刑或长期刑罚的考验。
更有意思的是,从存放在档案中的秘密警察报告里可以看到,那个年代,政治嗅觉敏锐、永远善于骑墙的秘密警察们,正随时准备着抛弃他们服务的这个政权。因此在给上级的报告中,他们对怎样处置自己眼下监管的政治犯,总是持模棱两可的态度。而他们的上级,当然更不敢冒政治风险,监管人的这种态度,对改善了马顿夫妇的狱中处境,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直至后来先后被释放–而此时,距离匈牙利革命的爆发,只剩下两个月的时间了。马顿夫妇积极参与了这次革命,在第一时间向西方媒体报道了这桩关乎匈牙利民族命运的重大事件。这已经是这对夫妇第二次为西方世界瞩目了–第一次是在他们被捕时。随后,他们逮准了一个机会,终于得以前往维也纳工作,很快全家又移居到了美国,夫妇俩在那里度过了平静的后半生。
按理说,到此为止,他们与匈牙利秘密警察之间的故事就应该结束了。但根据档案记载,直到1967年,匈牙利当局派往美国的谍报人员,依然试图招募这对看起来仍有利用价值的夫妇,想要说服他们充当母国政府在美国的情报提供者。而与此同时,美国的反谍报机构联邦调查局也始终在关注他们,原因很简单:匈牙利政府情报人员在美的一举一动,始终处在美国政府的严密监控中。这对夫妇自身,也并不能让美国人彻底放心。事实证明,美国人的怀疑并非全无道理:这对夫妇当年之所以能够提前出狱,一半是当局基于形势的变化而做出的决定,一半则是因为这次出狱其实是附条件的,当局要求这对夫妇必须分别定期到“安全屋”或咖啡馆会见秘密警察,报告他们自己的行踪。

秘密警察用长镜头偷拍马顿先生
极权政治最残酷之处,恰在此处。无论以哪种标准来看,马顿夫妇都已经堪称勇者,他们的出身、教养和成年后的职业选择、政治倾向,也都表明了这对夫妇是极度自尊的人。但即使是这样高贵的灵魂,也终究无法避免在极权统治下“自贱自辱”的命运,更不要提马顿先生在狱中曾被迫承认自己的间谍罪名,重压之下曾数次想过要放弃生命。
这真实的一幕,令我禁不住想起,在前不久读过的一本涉及匈牙利历史的小说里,作者借一位作家之口说出的那句无比沉痛的自白:“一个人在自己当过奴隶的地方,永远都不可能自由。”可以想见,当马顿夫妇铁了心要离开前途未卜的匈牙利,甘愿作为新世界的政治难民,开始全新的生活之时,除了现实的考虑,在他们的心底,恐怕也曾有过类似的念头吧。所以,尽管孩子们每次从匈牙利返回美国,他们总不忘问问母国的人事变迁,但总是再也不愿返回那片伤心之地,即便它已重获自由。
而美国呢?且不说当年马顿先生服务的美联社,在他们被捕之前和出狱之后,曾几次拒绝帮助他们脱离随时可能危及生命的匈牙利政府的控制,也不说当年给马顿夫妇带来牢狱之灾的罪魁祸首,正是美国公使馆的一名内部人员–这位告密者在案发后,仅仅受到了遣返回国的处分。
单就马顿夫妇到达美国之后的经历而言,尽管马顿先生终其一生都以“美国新闻人”自许,但在这个他们热爱的国度生活了十多年之后,某种政治上的不信任、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眼神,依然是他在美联社外交记者的职业生涯中每天都可能遭遇的。除此以外,两人还都要面对来自联邦调查局特工的更为直接的盘问,直到他们分别向联邦探员作出如下保证:他们将始终忠于美国政府,一旦发现对方谍报人员试图招募他们,他们一定会将情况及时报告给联邦当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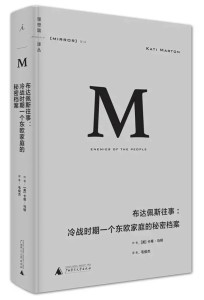
作为女儿,作为美国前助理国务卿的妻子,不知作者在看到父母曾作出过这样的保证时,内心作何感想。冷战是残酷的。马顿夫妇虽是享有国际声誉的新闻人,但说到底,仍不过是东西方对抗中那枚小得不能再小的棋子。不过,同样是利用或压迫,在不同制度下,依然有着方式和程度的不同,而对于曾亲身经历过极权统治下恐惧、屈辱、压抑和绝望的个体而言,那样的不同,或许就是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不同了。从这一点来说,苦难固然会给人的身心带来永远无法真正抚平的创伤,但也会让有幸熬过了这种苦难,或是至今仍在煎熬中的人们,都去期待一种更自由、更有尊严的生活,而不是那种许诺给人天堂,其实却需要人们付出全部的道德代价,却仅仅只能换来一片面包的生活。
来源:共识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