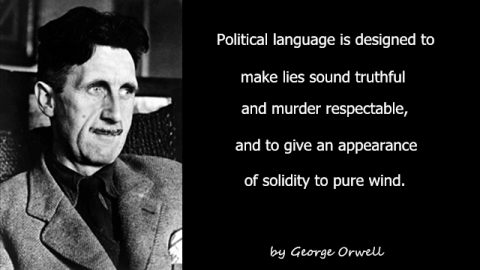西班牙内战是乔治·奥威尔生命与思想的转折点。
乔治·奥威尔以激进左派和国际志愿者的身份参加了这场战争。在前线,他的脖子中弹,所幸大难不死。奥威尔完全有资格颂扬这段“浪漫主义的战争时期”(何塞·狄亚斯语),然而他选择了一种截然相反的做法——尽力揭示这场战争背后最残暴、最黑暗的真相,因为真相才是最有力量的。他在回忆录《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中写道:“我个人在这场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无足轻重,战争只给我留下了最不愉快的回忆,可我还是不想与这场战争擦肩而过。……这场战争最终将被证明是一场骇人听闻的灾难,它所带来的远远超过一般意义上的屠杀和肉体上的痛苦。”他早已预见到“战后政府的发展趋势肯定是走上法西斯道路”,但他仍然坚称“整个经历让我更加相信人类的高尚品质”,也坚信“比起佛朗哥和希特勒的残暴而强大的法西斯专政,共和国政府还是值得我们去为之战斗的”。另一方面,他认为即使共和国政府取得了胜利,其代价也将是“西班牙重新回到令人窒息的独裁统治之中,以及西班牙的优秀儿女因此被投入监狱”。在阳光炽热的“解放区”,奥威尔发现了诸多他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形:“西班牙共产党绝对掌握了权力,内部秩序的控制权也移交给共产党的部长们,只要有一点点机会,他们都会打击竞争对手,没有人对此表示怀疑”,“消灭或者清除碰巧与你意见相左的人的观念成为天经地义的事情……‘斯大林主义者’控制着局面,因此每个‘托洛茨基主义者’自然都在劫难逃”。这一切,完全与他的理想相背离。
亲身经历了西班牙内战之后,奥威尔从一名左翼思想的服膺者蜕变为既反对法西斯主义、也反对共产主义的、“左右开弓”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这本被评为“二十世纪十本最佳非虚构类作品之一”的回忆录中,他无意攻击西班牙共产党以及为其提供援助的苏联当局,他所做的仅仅是用尽可能客观的笔墨描述出尽可能多的真相,当然他也承认“没有一个人能够将这场战争完全真实地描述出来”。其实,在西班牙左翼阵营的纷争中,奥威尔更倾向于共产党对战争的策略,但他仅仅因为偶然地被编入倾向托派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民兵队伍,他便成了无论怎样辨白也无济于事的“异类”。法西斯的子弹没有夺去他的生命,共产党的秘密警察却要将他置于死地。奥威尔本人侥幸逃出了西班牙,战友斯迈利却死无葬身之地,他用伤感的笔调写道:“我对斯迈利的死难以释怀。为了投身反法西斯的战斗,这个勇敢聪颖的大男孩,毅然放弃了自己在格拉斯大学的学业。在我看来,斯迈利在前线以无可挑剔的勇气和奋不顾身的精神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而那些人所做的,却是将他投入监狱,并让他像个无人关注的动物那样死去。”对于这样的一个政权,值得为之付出生命的代价吗?
在初次上前线时,奥威尔便发现了内战极其荒谬的一面。他虽然不曾有过军旅生涯,却在缅甸担任过英国皇家警察,多多少少知道一点军事常识。这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啊——“我们看起来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乌合之众。我们自由散漫,凝聚力还不如一群绵羊。……我们这群男子汉差不多有一半是孩子——我指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孩子,他们中最大的不过十六岁。”将这些没有接受过任何军事训练的孩子派上前线无疑是送死。那么,这支队伍使用的是些什么样的武器呢?奥威尔分配到了一支堪称古董的步枪:“这是一支德国长毛瑟枪,制造日期是一八九六年,已经四十多年了!外表锈迹斑斑,扳机很涩,从枪口往里看,枪膛也已锈蚀,完全没有继续使用的希望。”这种高度写实的黑色幽默堪与《二十一条军规》相媲美。经过由西班牙共产党方面控制的宣传机构的长期渲染,人人皆把法西斯分子想象成张牙舞爪的魔鬼。但是,奥威尔看到的第一个“真正”的法西斯主义者,却是一名从战场上逃往下来的可怜的孩子——“这是一个大约二十岁的高个子男孩,风吹得面色发暗,衣服破破烂烂,蜷缩在火堆旁,端起一盘炖肉,不顾一切地快速吃了下去。”奥威尔坦言,“他们”跟“我们”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无疑,奥威尔堪称二十世纪最优秀的战地记者。他长期为英国广播公司和《观察家报》工作,洞悉了“新闻”和“宣传”的区别。他热爱以报道真相为旨归的新闻事业,反对以政治斗争为目的的宣传工作。他无比厌恶那些大量使用谎言的宣传手段,即便其针对的是法西斯敌人。令奥威尔最为忧虑的一个现象是:在反对法西斯的过程中,反对者被法西斯同化了。比如,佛朗哥谎报军情,共和国也谎报军情;佛朗哥捏造政府军虐待俘虏的消息,共和国也捏造佛朗哥虐待俘虏的消息;佛朗哥说政府军是苏联的代理人,共和国则说佛朗哥是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的代理人。许多为共和国的媒体工作的人认为,为了战胜对方的谎言,自己这方不惜制造出更大的谎言来。这样便使得谎言成了权力赖以维持的支柱。此种做法,其实正中法西斯的下怀,因为这正是法西斯病毒得以迅速扩散的方式之一。
奥威尔不是政客,他拒绝使用权术和阴谋;奥威尔是记者、作家和知识分子,他以言说真相为天职。他深知,谎言可以取得一时的效果,但它将损害整个社会内在的信任程度;宣传可以暂时鼓舞人心,但当真相逐渐呈现出来时,崩溃的来临将更加迅速。因此,即便是“被动性的谎言”也是没有效果的和不能容忍的。奥威尔认为,策略不能压倒真相,他完全不认同左翼政权的宣传手腕,他直言不讳地指出:“谎言这场战争最阴暗的影响之一,就是让我认识到左翼新闻媒体在每一个方面都和右翼的一样弄虚作假、虚伪透顶。”他对那些高调鼓吹仇恨和暴力、自己却无比胆怯的宣传人员和文士充满轻蔑之情。那些人自己安全地呆在后方,却以英雄的姿态出现在媒体上。口头上的爱国者是最容易充当的,正如奥威尔所谴责的那样:“在所有的战争中都是如此,战士打仗,记者叫唤;除了短暂的宣传旅行外,自诩真正的爱国者从不在前线的战壕里停留。”
无节制地实行宣传煽动和制造谎言,已经从根本上动摇了共和国的正义性,也使得这场战争的性质变得更加复杂。它不再黑白分明,不再是纯洁的史诗。奥威尔痛苦地发现,失败的阴影正在共和国的军队和市民之中无可避免地蔓延,这并非因为佛朗哥的军队过于强大,乃是因为当局失去了来自民众的支持与信任,旷日持久的党派纷争又耗干了仅有的资源。许多勇敢的战士并没有如愿以偿地死在战场上,却死于自己“同志”的枪口之下。作为文字工作者,奥威尔指出,谣言也是可以杀人的,谣言一笔勾销了昔日面对“我们究竟为何而战”这个问题时候的斩钉截铁的答案。奥威尔用了一个非常形象的例子来阐明此观点:“看到一个十五六岁的西班牙男孩被用担架从前线抬下来,从包裹的毯子中露出惨白的脸,再想到伦敦和巴黎的那些圆滑世故的人正在写小册子证明这个男孩是一个伪装的法西斯分子,这实在令人感到不是滋味。战争的最恐怖的特征之一,就是煽动战争的那些宣传、叫嚣和仇恨,全都是出自从来不上前线作战的那些人之口。”这是一条屡试不爽的规律:越是高调的人越是可疑。
普里切特将乔治·奥威尔誉为“我们这一代的冷峻良知”。这一荣誉,奥威尔显然当之无愧,仅以西班牙内战为例,他就是诸多报道者中说出最多真相的人。如果将奥威尔与诗人奥登作一简单比较,更能看得清清楚楚:奥登也曾醉心于西班牙内战,写下了一首题为《一九三七年的西班牙》的诗歌,其中既有像“明天属于年轻的一代,诗人宛如炸弹般绽放”这样的田园牧歌般的句子,也有像“死亡的风险与日俱增,必要的谋杀化为默认的罪恶”这样的为杀戮开脱和辩解的句子。与大部分诗人一样,奥登是一名经常迷失在激情与想象之中的左派。为了达成某种“宏大叙事”,他们罔顾个人的生命价值与尊严,甚至不惜歪曲现实和窜改历史。奥威尔则以接近真相和捍卫自由为己任,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不能让他扭曲真相来迎合之。
奥登所张扬的“必要的谋杀”,触怒了奥威尔这位战争亲历者的心灵。对此,他愤怒地评论道:“值得注意的是‘必要的谋杀’。只有把谋杀纯粹当作一个字眼,才会写出这样的东西。因为本人亲眼见过许多惨遭谋杀的尸体——他们不是死在战场上,而是惨遭谋杀。所以我对谋杀多少有些概念——恐怖、仇恨、亲人的哀嚎、解剖验尸、鲜血淋漓、恶臭熏天。依本人看来,谋杀实在很要不得,相信许多人也有同感。希特勒和斯大林认为谋杀有其必要,但他们不会大声张扬,更不会用谋杀这个词汇,而是用‘清算’、‘净化’或其他听起来不那么刺耳的字眼。除非长久待在杀人如麻的地方,否则你难以苟同奥登的败德思想。许多左翼思想都是出自那些喜欢玩火、却又不知道火烫的家伙。”为了回应这段批评,奥登赶紧将“必要的谋杀”改成了“谋杀的事实”。有意思的是,就在这场争论发生的一九四零年,纳粹德国的军队横扫欧洲大陆,英国亦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豪情万丈的奥登逃往美国寻求庇护,奥威尔却坚守在祖国担任空袭警报员。谁是真正的英雄呢?是鼓吹杀戮的人,还是尊重生命的人?
当前线正在浴血奋战的时候,“大后方”的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却急剧恶化了。而这与法西斯分子的破坏无关。负伤之后,奥威尔脱离了前线的战斗,并逐渐转而以旁观者的视角来看待这场战争。他与妻子居住在巴塞罗那的旅店里,那里的气氛几乎比前线还要紧张。在前线,你可以看到远方的敌人,你清楚地知道谁是敌人,也清楚地知道如何置身于敌人射程之外;在后方,你却分不清谁是告密者、谁是朋友,今天的朋友明天可能摇身一变成为告密者,今天的革命者明天可能被宣布为奸细——“当时或几个月后在巴塞罗那生活过的人们,谁都永远忘不了由恐惧、怀疑、仇恨、遭审查的报纸、人满为患的监狱、奇长无比的购买食物的队伍以及成群结队到处巡逻的武装士兵等等所产生的恐怖气氛。”执政的共产党竭力清除所有的对立派别,仿造苏联建立起庞大的“克格勃”机构。他们炮制出一个又一个的“阴谋”来,似乎每天都有阴谋在酝酿,并以人们想象不到的方式发生,于是镇压变得理所当然了。每一个人都成为潜在的被镇压的对象:“哪怕你几乎与这场阴谋不沾边,这种氛围也会迫使你感到自己就像是一个同谋。你仿佛整天待在咖啡馆的角落里小声说话,时刻担心邻桌的人是不是警察局密探。”没有人喜欢生活在这样的氛围下,尽管住在高级酒店里,奥威尔感到还不如回到硝烟弥漫的前线。
奥威尔的那些身经百战的战友们,一个接一个地从他身边消失了。没有人知道他们被关押在哪里,也没有人宣布他们的罪名是什么。“那梦魇般的气氛真是一言难尽——这种特殊的不安感源自谣言的变化多端、报纸的新闻检查、武装人员的频繁光顾。”奥威尔试图拯救一位名叫柯普的比利时志愿者,他甚至不惜冒着自己被捕的危险前去为柯普讨回被查扣的军官证。柯普军官证出乎意料地拿到了,但他最终仍未能让柯普重获自由。通过一次难得的探监的机会,奥威尔亲眼目睹了监狱的可怕和政治犯待遇的恶劣:“当你目睹了西班牙监狱——包括用于关押政治犯的临时场所——中的生活之后,你就能够意识到,一个生病囚犯得到适当照顾的几率是多么微不足道。这些监狱只能被称做地牢。在英国,只有退回到十八世纪,才能见到诸如此类的场景。人们被囚禁在狭小的牢房里,只能勉强容身;人们甚至被关进地窖或其它更为黑暗潮湿的地方。这并非暂时为之,而是长期如此:人们常常被关押在那种地方长达四五个月之久,从来见不到一线光明。他们全天的食物只有污秽不堪、少得可怜的汤和一两片面包。”这与法西斯的集中营是何其相似!如果革命丧失了人道主义的根基,还值得去信仰吗?如果革命必须达致革命者被其所吞噬的后果,奥威尔只能抽身而退了。
这场血雨腥风的战争,留给了奥威尔若干难以忘却的记忆。视觉的、听觉的、嗅觉的种种感受混杂在一起,“战壕里的气味、山中的曙光延伸至无限的远方、子弹无情的啸叫声、炸弹爆炸的刺眼光芒和震耳回响、巴塞罗那那清新寒冷的黎明、兵营里军靴踩踏的印迹、十二月党人们仍然信仰革命、购买食品的长队、红黑相间的旗帜,以及西班牙民兵的面容”,不一而足。有骄傲,也有忧伤;有愤怒,也有失望;有温馨,也有冷漠。这场战争改变了奥威尔的政治信念和人生价值,他也由此触及到了斯大林主义最恐怖的核心所在。如今,半个多世纪之后,昔日许多诗化和神化西班牙内战的作品早已被人们忘记,惟有这本薄薄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获得了经典的地位,这就是真相那不可摧抑的力量。坚持言说真相的人是最让人尊敬的,直面真相方能拥有预言未来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奥威尔的那部更加伟大的《一九八四》,也算是在这场战争的硝烟中诞生的宁馨儿;而这本阴郁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亦可称之为《一九八四》的“前传”吧。
——二零零六年八月五日、六日
──《观察》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