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最早知道哈维尔,是从摇滚杂志上看到的地下丝绒乐队(Velvet Underground)介绍,他当过捷克总统,是个剧作家,还是一个摇滚乐迷。这三种身份的结合,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有些疑惑。但当时这种疑惑并没有驱使我去阅读他的文字。
2011年12月18日哈维尔去世,8天以后,高华去世。那年年底,在考研复习的间隙,自己各处找两个人的文字来读,通过少量可以读到的文字,可以隐约感到那种精神的燃烧,慢慢打开了一个不同的视域。
今年八月下旬采访阿列克谢耶维奇女士,那段时间,自己隐约在找一种关于信仰的回答,那次采访的最后,阿列克谢耶维奇女士的一段话,“我更像是??艺术的信徒,信仰这个世界上花园、飞鸟、天空等等这样美好事物的创造者。所以其实更应该说我信仰善与美这一类的东西。”,坚定了我自己对于信仰的理解。
这种对于信仰的理解,在哈维尔《致奥尔嘉的信》中已经提到,“真正的信仰不是一种迷惑人心的东西所引发的迷狂状态,它是一种内在精神状态,一种深刻的存在感,一种你或者有或者干脆没有的发自内心的指导,它将把你的存在提升到一个更高水平。”
今天是哈维尔逝世五周年纪念日,搜狐文化以这篇专访作为对哈维尔的纪念:

哈维尔
嘉宾介绍:崔卫平,人文学者,写作诗歌及电影批评,社会及政治批评,并译介当代中东欧思想。她的著作有:《带伤的黎明》、《积极生活》、《正义之前》、《我们时代的叙事》、《思想与乡愁》、《迷人的谎言》等。
<img src="https://www.chinesepen.org/wp-content/uploads/2016/12/71376c8f6cfd4384bd08e0d0a401d5b3_th-300×234.jpg" alt="71376c8f6cfd4384bd08e0d0a401d5b3_th" width="300" height="234" class="alignnone size-medium wp-image-76011"
崔卫平
理解哈维尔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不断去发现的过程
搜狐文化:今年哈维尔逝世五周年,您如何看待哈维尔?
崔卫平:哈维尔去世5年,虽然他离我们越来越远了,但是他的思想却是越来越深入人心。尽管不一定提到哈维尔的名字,但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人们强调自己的公民身份,认为自己对于周围环境承担一份责任,认为需要从自己做起,这正是哈维尔被广泛接受的体现。同时理解哈维尔,对我们来说应该是一个不断去发现的过程。他是1936年出生的人,1936年是捷克第一共和国时期。他在童年经历过民主,受过完全不一样的教育,拥有不一样的起点和视野,看到过一些我们没有看到过的东西。
我正在看的这本2014年出版的哈维尔传记,作者Michael Zantovsky 是哈维尔当总统时的新闻发言人,其中详细描绘了当年哈维尔他们是如何分工的。在他们那份著名的文本中,哪些东西不是哈维尔的,哪些是他的。比如,强调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已经加入《赫尔辛基协定》(1975年),其中涉及人权保护以及东西方经济与科技方面的合作,按照刚刚加入的协议来办,这个主意不是哈维尔的,但是下面这些主意是哈维尔的,它完全超出了在阶级斗争教育下成长的人们的视野,是一个团结和责任的视野:“……是各种不同信念、宗教和职业的人士之自由……是以人们的团结和友谊为基础——他们对于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密切相关的理想的命运,承担了一些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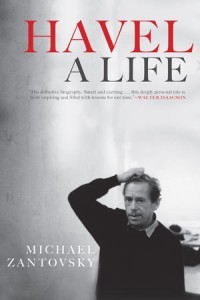
Havel:A Life by Michael Zantovsky
搜狐文化:这份责任意味着什么?
崔卫平:意味着他们为此站出来说出真话,甚至为此做出牺牲。他们当中许多人为此付出了自由、工作、青春、健康,甚至付出了生命,比如哲学家扬·帕托切克,七十多岁了在一次长长的审讯之后去世。但更多的责任并不意味着他们后来拥有更高的权力,丝毫不是说——当年的付出是往道德银行存款,需要的时候再提取出来。我见过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有教师、打字员和牧师等,还有小说家伊凡·克里玛和他从事心理辅导的太太,这批人完全没有进入权力的领域,他们还是做以前的工作,他们在自己的专业工作领域中完全独立。哈维尔本人也绝不是为了权力。在那种情况下,不能想象有所谓职业革命家或政治家。
搜狐文化:当时他们有什么具体的行动?
崔卫平:对于知识分子来说,重要的是怎样建立一个平台,尤其是言论自由的平台,大家首先都能够自由的表达,表达自己喜欢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觉得什么样的政策对自己有利或者不利。至于这个社会应该往哪里去,那是在一个自由讨论的平台上,让全国人民去选择的事情,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那应该是在一个平等自由的选择以及互相协商的结果。
哈维尔从他的角度有力地推进了行动。至于后续能够发生什么可能也不是他所能想到的,实际上可以说他们并没有想到后来发生的事情。这种做法比那些以为自己已经完全了解社会的整体,急于下一个整体判断,甚至希望整个社会都按照他的判断去做,顺着他的手指去看这个世界,是完全不一样的思路,哈维尔更谦逊。
哈维尔只是说出人人心中有,但没有表达出来的看法
搜狐文化:他做出了哪些推进的行动?
崔卫平:我能全说出来吗?(笑)。实际上他有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当中谁高谁低,有时也分不出来。任何事情不是一个人做出来的,罗马城不是一天建立的。1975年哈维尔给当时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写过的一封信,他分析了一种谎言状况对于全民族道德和精神长久的腐蚀,给每个人造成了巨大的道德损失。在一个存在巨大压力而谎言盛行的社会里,人人都会选择压力较小的方向释放自己的能量,表面上做出很顺从的样子。实际上人格是分裂的,头脑里面想的问题和现实的举动是两回事。
哈维尔只是说出了大家心里都有、但没有公开说出来的想法而已,这是哈维尔非常有力的部分。比如为恐惧所驱赶,同时又被利益所诱惑。他也没有将自己放到这个社会之外,没有觉得唯独自己已经得着了真理,而对于他人采取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他认为,实际上每个人都接受这样的生活,接受各种各样的贿赂,每个人都有一份责任,只是根据所处位置有责任大小的区别而已,拥有更大权力的人应该有更大的责任。但并不意味着较小权力甚至没有权力的人就没有责任。
当哈维尔这样表述时,他没有想到如何以言辞锋利吸引人,以肤浅的俏皮代替真正的智慧,他只是说出了暂时没有公开的秘密而已。
搜狐文化:“每个人都有责任”是一个很高的要求。
崔卫平:指的是人人都在其中这件事情,没有那么高。这个说法也不是从天而降,哈维尔深化了它。他的这个说法应该是继承了阿伦特关于“极权主义”的思考。阿伦特讲“恶的平庸性”的时候,她不是在为艾希曼开脱,而是强调人人都在这个制度里面,都有可能是艾希曼。这样一种机制能够运行,每个人都有责任,否则机制不可能运转,虽然没有在形式上取得你的同意,但是沉默是可以被视为或者歪曲为同意的表达,虽然实际上是没有办法表达同意或不同意。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沉默也是危险的和有危害的。无论如何,提出每个人的责任是非常意义的。
搜狐文化:他如何描述当时捷克的问题?
崔卫平:那时候不是“捷克”,而是“捷克斯洛伐克”。他批评当时那个社会整个被利益牵着走,一般人以消费为先。而这个消费社会,是经过权力看不见的手改动过的消费社会。人们表面上的消费,背后实际上有他们不能说的话,不能做的事情。这样一来,哈维尔就能够将所处社会的问题,与当时的国际环境结合起来,用一种国际社会能够理解的语言表述出来。他能够把在捷克发生的事情放到整个国际环境当中去,他使用的语言是国际性的语言,能够在国际社会里面,和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都能够进行新鲜的富有活力的对话。
语言怎么样才能够捕捉到不断流动变化的现实?这是一个大问题。现实始终在流动,不同力量在重组,语言也需要有更新。在某种意义上,改变语言的游戏规则也十分重要。哈维尔认为他所处的那个社会只是西方社会的一副夸张了的漫画,是一种讽刺模仿,并没有一味地强调其特殊性,像这个国家的统治者那样。他因此赢得了国际社会的了解和理解。
哈维尔拥有一种道德敏感
搜狐文化:哈维尔如此坚定的行为与他的宗教信仰有关么?
崔卫平:他不愿意强调自己这方面,我也不认为他是因为宗教才这样做的,他首先表达出来的不是一个宗教的理念或者宗教的牺牲精神,哈维尔是1936年生的人,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哈维尔是个谜。我认为我有一些看不见的东西吧。毕竟我们都是“在红旗下长大”,民主社会里面有些东西我们真的可能看不见。他具有那种道德上的敏感,这需要多少教育才能完成。
搜狐文化:“道德敏感”指什么?
崔卫平:能够在人们司空见惯、充耳不闻的现象面前,停下脚步,开始思索和表达,这就是敏感。包括从来不轻易伤害他人,不给正在遭受压力的人们以新的压力,不给正在一线工作的人们施加来自你的压力。
哈维尔的道德敏感还包括他文字上的适度和节制,他从不故作惊人之语。他说话一直很有分寸、有节制、不取严苛和急切,不耸人听闻。因此哈维尔现在已经被人视作“心灵鸡汤”了,但是在说这种话的人那里,一点也没有迹象表明,他可以拿出比哈维尔更加有力的东西,能够让我们环境中的人们以及国际社会都感到眼前一亮。
搜狐文化:道德敏感似乎可以促使道德进步。
崔卫平:表面上的道德激烈和严苛,不一定正好代表道德高度和道德进步,后者恰恰是通过宽容来体现的。尤其是针对身边的普通人,对待自己的朋友,言辞尖刻,是内心逼仄的表现。
搜狐文化:捷克当时如何处理语言上的粗暴现象?
崔卫平:人们以前被压抑久了,一旦打开就会有很多东西要表达,就会有一些不加思索的,或者不去倾听别人的表达。假如一个人长期在一种压抑的环境中长大,这种压抑也会对人造成一种扭曲,别人一直以一种代表真理的口吻跟他说话,他也可能会以另外一种代表真理的口吻跟别人说话。民主的素质也表现在知道自己的界限在哪里,而不是轻易越过这个界限。
捷克转型期间制定的《布拉格对话守则》,针对民主运动当中人们应该怎么说话,怎么讨论问题,为了争取一个更好的对话平台应该有什么样的规则,近年来也被国内的人们经常提起。
哈维尔是一个很幽默的人
搜狐文化:您还欣赏哈维尔哪些思想?
崔卫平:我还特别哈维尔当选临时总统后说的一些话。他说共产主义并没有包揽和结束所有的恶。那会儿遇到了很大的问题,社会突然打开,有的人想要寻求暴富,力气大的拼命挤,挤掉那些力气小的,也有贫富不均,同样也有冷漠,就像那部俄罗斯电影《危楼愚夫》里表达的。列克谢耶维奇的书中也多次写过,她讲了很多苏联在解体后的情况,人们的日子并没有一下子轻松起来,许多人感到很失望,但你不能把它完全归置于前面的社会制度,人们自己也要为这种状况负应有的责任。
搜狐文化:通过阅读哈维尔的作品能够感到他是个真实的人,以您的了解,他平时是个什么样的人?
崔卫平:哈维尔是一个很幽默的人,不把自己看作是真理的化身。幽默不是讽刺,讽刺仅仅针对别人,幽默是拿自己开玩笑,不把自己弄得高大上。他会说自己小时候,他是资产阶级家庭出身嘛,他叔叔开了布拉格最大的一个电影厂,然后他说他自己小时候很肥胖,胖到什么程度呢?胖到不能跨过一条小沟,而下课之后呢,同学们轮流上来拍他的胖大腿,以此来消遣解闷。如何把自己弄得可笑,这是他经常喜欢做的事情。这就提醒我们,在最为困难的情况下,最需要勇气、坚韧的时候,也不要忘记自己是一个凡身肉胎。
他退休以后有一次去美国,在一个图书馆做讲座,他说自己现在是个退休的总统,别人就不太好称呼他,称呼他为前总统还是退休的总统呢?在捷克历史上没有这样的情况,总统经常是被罢黜的。

剪刀手姿势的哈维尔
搜狐文化:他有什么缺点么?
崔卫平:他自己说犯过一个错误,他自己为这个事情懊恼得很。“七七宪章”发布以后大家都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哈维尔是第一任发言人,他在1978年初被抓。在审讯中,他说自己不想再当发言人了。他觉得这虽然是真话,但是不应该跟警察去说。
他一直为公民事业耗费了自己太多时间精力而焦虑。他知道当发言人更是如此,但还是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了这个责任。只是他很后悔为什么要把“不想做发言人”告诉警察?他说非常不应该告诉警察。当时为什么要说呢?这件事情连他自己也觉得有点奇怪。至少是缺乏经验吧,虽然也是自己的真实想法,但没有必要在那个时候说,会被官方所利用。他从狱中出来之后很沮丧,也因为这件事,后来他在运动中做了更多的事情。
特别可贵是他的朋友们后来的反应,他们肯定从广播或者官方途径听到了哈维尔的这个表达,但是他们选择相信哈维尔本人,而不是相信官方。他从狱中出来以后大家都没有疏远他,还是把他视为一样的朋友,对他特别好,与过去一样的信任。人也有软弱的地方,在压力之下说的话肯定会有违心。他的朋友们与他一样拥有更高的责任,所以就能够达成更多的谅解和团结。
搜狐文化:为什么我们同样的情况更多的是没有同情的谴责?
崔卫平:你也感到了?比如有人被迫上电视认罪,另外有人是为了显示自己的道德高度,选择与这些倒霉的人们决裂。这就缺乏团结和谅解的精神,尤其是不能帮助形成一种宽松的气氛。
搜狐文化:您在翻译《哈维尔文集》和《通往公民社会》(米奇尼克著),有没有遇到比较有意思的事情?
崔卫平:我记得“团结”(solidarity)这个词,尤其在翻译《通往公民社会》的时候经常会遇到这个词。在我们国家,“团结”这个词的能量已经被提前释放完了,一般人们包括我本人在内,不一定能够捕捉到这个词的全部含义,怎么写上“团结”觉得怎么不像,没有力量。后来在翻译中我就想方设法把“团结”译成“休戚与共”、“同甘共苦”、“风雨同舟”、“命运与共”这些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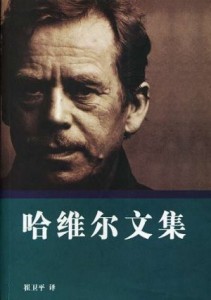
来源:搜狐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