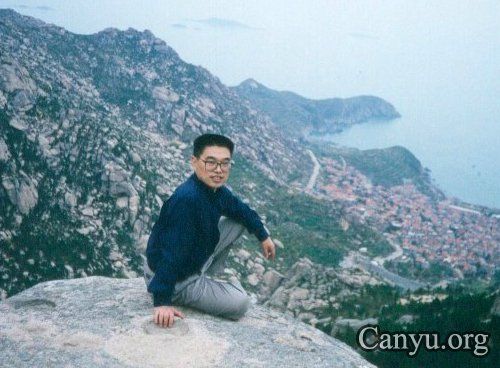12月11日,我从武汉专程乘车来到应城市,开始以旁观者的身份,了解民间的百姓与官员对导斌一案的反映。经过一天的调查访问,我喜忧参半,喜的是,少数民众能理解他,忧郁的是,大多人是冷漠和麻木的,被酱化的没有了灵性(柏杨语)。中午十二点,中巴车驶进应城市客运站空空荡荡的广场,下车后我首先向一个卖水果的中年妇女询问,是否认识杜导斌这个人,中年妇女说不认识,我又接著向几个打听,都说不认识。我很扫兴,只好信步走在街上,来来往往是忙碌的人群,多数是为生存奔波的小市民。来到一个“世纪网吧”里,我走了进去,网吧里全是十多岁的小年儿童,都在兴高采烈地玩著游戏,他们当然不会知道一个思考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中年人因言获罪被关了。我向主人模样的三十多岁的中年妇女打探杜导斌,她心不在焉地说:“听说过这个人。”我又问他是怎么回事,她不无遗憾地说:“听说是写反党的文章。”尔后叹息说:“又有工作,家里条件又好,怎么不走正道?”我一呆,这时,又凑过来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问是怎么回事,中年妇女就对说杜导斌这个人,中年人好像是中年妇女的丈夫,他心不在焉地说:“现在有个工作干干就不错了,他一个人能把天顶翻吗?真是自讨苦吃!”我淡淡一笑走了。
座的士来到位于大智路的市供销社,医疗保险办公室就设在里面。上了漆黑的走廊,二楼办公室里是导斌曾经办过公的办公室,由于已是中午下班时间,只有一个二十来岁的女孩在值班,她很不友好地对我说:这个人已很长时间没来上班了,我进一步问导斌干什么去了?她不耐烦地说:出事了,我又她问:“出什么事了?”她说:乱写文章。我听了倒吸一口凉气。
下得楼来,墙外用三张大红纸写著市人大代表选举的名单及要求,推荐的两个侯选人是张国柱和左保生,两张大红纸分别写著他们的事迹简介。在《财口战线第三选区第一选民小组选民名单》中,我没有找到导斌的名字,我当时心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有关法律,只要没有剥夺政治权利,你即使在狱中,也是有选举权的,当然,视人权为草芥的党魁们,自然不会在乎导斌的一票了。
乘摩的来到市公安局,在金碧辉煌的大厅里是出出进进的人流,身穿制服的警员们一个个目空一切,我见走进一个膀大腰圆的警察,忙很客气地向他打探杜导斌这个人,他警惕地看我一眼,冷冷地问:“你是他什么人?”我谎称是他朋友(实际上我与导斌互不相识。)那警察又问:“是社会上的朋友还是写文章的朋友?”我反问:“这有关系吗?”他瞪了我一眼说:“关系大著呢,你是写他那样的文章,下一个可能就要关你了。”我轻松地一笑说:他写的文章违法了吗?就因为因言定罪?他恶恨恨地看了我一眼,一转头走了。
我又向三四个警察打听杜导斌的情况,他们不外乎一个观点:杜导斌是写了反动文章,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攻击中国共产党,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大傻瓜。我心想:这些人是被政治谎言灌输后扭曲了的思想,是不折不扣的犬儒者,他们怎么会理解杜导斌?
我询问了数十个做生意的人,他们大多没有听说杜导斌这个人,少数知道的,也是一知半解。我又到城建局问了几个公务员模样的人,他们有的漠不关心,有的说,杜导斌是乱写文章,现在是既害了家庭,又害了个人前途。我伤心地想:毋须讳言,在这些人冷漠和无知的背后,是长期专制制度压抑下,丧失了分辨是非的能力,一切事物只能凭情绪和直觉反应,没有了是非曲直,没有了对错黑白,他们怎么会理解杜导斌呢?我能向他们解释什么呢?
又一次来到杜导斌办公的供销社院落里,迎面碰上一个三十来岁的青年,手里拿著个公文包,我忙向他打听导斌的情况,他认真地说:“杜导斌的文章我看过几篇,真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的问题,我佩服他。”我已打探了不少于三十人,没有听到一句公道的话语,听了欣喜不已,我忙问他姓什么,他说他姓王,我又问他:“导斌现在关进去了,你怎么看这件事?”他悠悠地道:“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都是勇敢的人,这社会把人都戴上了假面具,谁还敢说真话?杜导斌,了不起。”我由衷地为导斌骄傲和自豪,我又问他是做什么工作的,他笑而不答,犹豫了一会儿才说:吃官饭的。
望著他远去的背影,我高兴地想:这一趟我没有白来,终于在他家门口找到一个理解导斌的人。在狱中的导斌呵,虽然我与你素不相识,不仅我与你心灵相通,你的身边还是有人能够理解你,你应该欣慰。
二00三年十二月十四日于武汉
大纪元首发
《曾仁全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