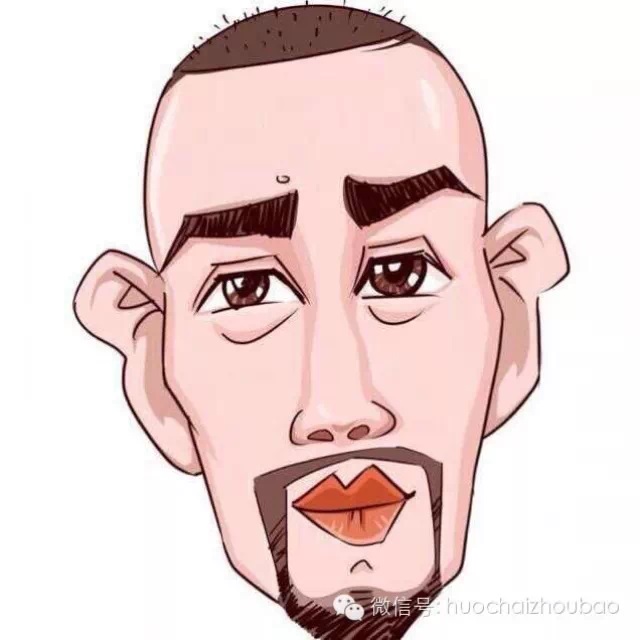尾生 火柴天糖 2014-10-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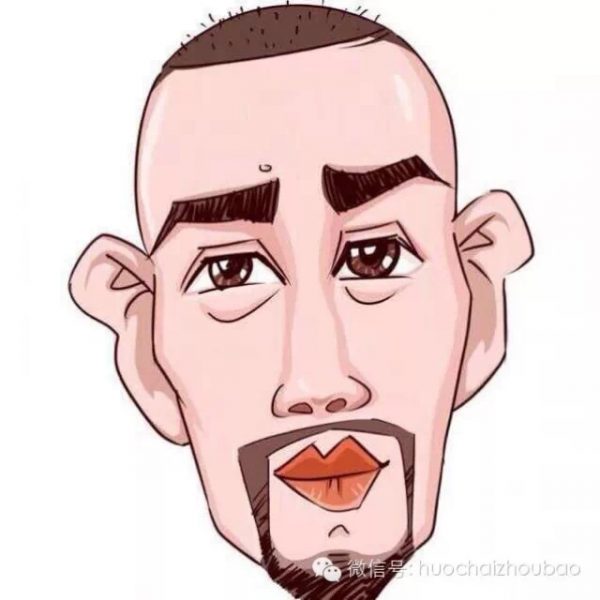
刘一木,湖南文化名人。我这样讲,或许他爱听。因为这是人性。
一木曾嘱我写一首命题诗,送给他的,就叫《一木这个人》。长时间以来,我一直未敢动笔,因为人这东西太难写了。我们都希望在别人的眼中看见自己。萨特说他人即地狱。其实,他人也可以是镜子。一木写诗。诗歌也是心灵的另一面镜子。通过诗歌也好,通过他人也罢,其实我们都是想认识那个真实的自己。虽然有时候,我们连真实是什么也不知道。

一木复杂,复杂得像春天。
有时候他会在复杂中迷失,不知道自己到底该开什么花,结什么果。
一木,虽然属于春天里的植物,却不知道自己是花是草是树抑或是整个春天。然而过于复杂的人是写不出诗歌的。诗歌属于心灵诚实的人。诗歌属于爱情和童年。从这个角度来讲,一木又是一个复杂到没有长大的孩子。他聪明,有时候又显得愚拙。他世故,有时候又单纯得近乎幼稚。
一切都不可琢磨。仿佛一木一首诗歌《秋》里说的“一晚的功夫/秋就来了/一切在迹象之外/鸣叫的鸟说/这是密谋的结果。”外在的迹象可以在一夜之间变换,而内在却是一种密谋的结果。这就像他这个复杂的人,从外看上去他瞬息万变,脸上有着春夏秋冬的季节,而内心又是算计与密谋。在一种矛盾的复杂中,在这变换无常的人世,内心又怀揣着一只不安的鸟的自由梦想。

我们就像海中孤独的航船,人性,就像大海,难以预测他的喜怒。
我很想写一首诗歌送给一木,但我实在写不出来。与其说一木难写,不如说人性实在太微妙。人性善否?人性恶否?人性非善非恶否?人性亦善亦恶否?人性无善无恶否?我不知道。
北岛说:“在一个没有英雄的时代,我甘愿作一个人。”其实在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作一个人,而不是作一个动物也是很难的。
一木兄固执地坚持着人性。可我们虽然作为人存活于这个世界,但人到底是什么?或许我们在把别人当镜子希望照出自己的面貌的时候,心灵之镜或许能更真实照出自己的本来模样。
一木在一首《心》的诗歌里的说:“欲望与存在/相互磨损/身体沉重如一块/黑色的巨石/向前眺望/就算折叠成/一只灵动的飞鸟/又如何呢/幻影无边/心有时无限/有时有限。”“欲望与存在相互磨损。”这就是事实。
我们总是被身体的情欲所捆绑,然后我们在自我的争战中磨损着心的存在抑或欲望。我们的身体就像“黑色的巨石”在心的空间里下沉。我们有时候感觉身体在心灵里得到了无限的自由,有时候又觉得心灵在身体里得到有限的束缚。一木心中始终藏着一只飞鸟,但他又时时表现出悲观的情调,在有限与无限的挣扎中徘徊。
一木曾经是基督徒。基督徒相信人还有灵性的层面,相信有神的存在。神其实是一面圆满的镜子,在神面前我们才能照见自己的残缺和污秽。一木现在固执地相信人性。
我但愿一木能从我的眼中认识他这个人,当然更要紧的,或许诗歌可以打开他的心灵之镜,照见的他才更加真实。
2014年10月27日 于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