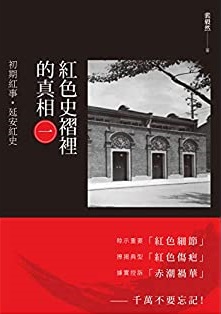 《红色史褶里的真相》第一辑: 初期红事(13)
《红色史褶里的真相》第一辑: 初期红事(13)
「二十八个半」的由来与结局
中共党史上有一赫赫有名的团体——「二十八个半」(亦戏称「二十八宿」[1]),当年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国留学生的一个松散团体。之所以声名赫赫,当然是「二十八个半」出了声名赫赫的人物,对中共党史留下重大刻痕。那么,这一团体的由来与结局呢?
一、莫斯科中大
十月革命后,为不让「帝国主义将新生的苏维埃扼杀在摇篮里」,亦为推动「世界革命」,赤俄政府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成立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大」),名誉校长斯大林,为东方各国培养革命干部。也有为培养西方国家红色干部的学校——斯维得洛夫大学,亦称西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1930年解散,改为莫斯科外语师范学院)。[2]
1921年10月21日,「东大」正式开学,最初隶属教育人民委员部,后由俄共中央(布)直接领导,共产国际派代表参加管理,学制初定七个月,后改三年。专业均为政治类:党的工作和政治教育、工会运动、行政法律、经济。1921年底学生622名,1922年学生933名,涵盖七十多个民族,除了中国学生,还有蒙古生、土耳其生、朝鲜生……[3]
1923年国共合作,赤俄政府决定再办一所专门培养中国革命干部的学校。正在筹办中,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为纪念孙中山,命名莫斯科中山大学,东方大学部分中国师生转入「中大」,1926年正式成立。进入「中大」的国民党系学生:蒋经国、郑介民、戴笠、谷正纲、谷正鼎、屈武、邓文仪、刘咏尧、张秀兰、吴家钰、何重汉、卜涛明、王崇武、邵志刚(邵力子之子)、魏淑英(李宗仁之妻)…… 是年,赴俄生费用明确由苏联政府负担。[4]据不完全统计,1921~1930年,苏联共培养1400余名中国学生,其中300余名国民党员。[5]
「四·一二」国共破裂,国民党与苏联关系随之断裂,国民党驻共产国际代表邵力子离开中大回国,从此中大理事会不再有国民党成员。[6]直至1932年「一·二八」后,日本豁露全面侵华意图,苏联为了以华制日,再次援助国府,国民党才与苏联恢复邦交。[7]
国共分裂后,不少工人干部逃俄,俄共无法安置他们,统统送入「中大」,引起「中大」学生的分裂。这批工农干部认为此前的学生是不革命或动摇小资产阶级,俄共也认为中共知识阶级成分太重,在中国没有力量而导致「大革命」失败,新来的工农学生才是真正革命分子。不久,校学生会由新来的工人学生占领席位,夺了校内学生活动的领导权,形成「学生派」与「工人派」的对垒,所谓北大派「陈独秀和谭平山的地位已经被瞿秋白掳夺」。[8]
1928年,「中大」更换校牌「中国共产主义劳动者大学」,不久改名「苏兆征大学」[9],但师生仍呼前称「中山大学」。此后,当然只收中共学生。直至1930年停办,「中大」共招收四期学生。1925年第一期340名,1926年第二期300余名,1927年第三期百余名,1928年第四期百余名。[10]
第一期七班学员:邓小平、左权、傅钟、谷正纲、谷正鼎、邓文仪、林柏生。
其它著名学员:曾中生刘少文中将。
1956年中共「八大」,95名中央委员,至少27位留苏生,主要毕业于莫斯科中山大学。
莫斯科中大为中国共运输送了最坚定的赤徒,以及一颗颗只知马克思主义的赤色大脑。张琴秋在中大,啃了两遍俄版《资本论》。[11]
二、十天大会
1929年暑假,「劳大」学生赴黑海度假,疗养所成了辩论地。争论焦点为二:
一、拥护「中大」支部局还是拥护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而支持哪一边,联系着大革命失败的责任与是非、中国革命的理论与策略。
二、学制四年还是一~两年,要不要按正规程序既学俄文又学理论?
米夫、王明的支部局认为从中国革命长期打算出发,必须培养一批有理论根柢的骨干,必须进行正规教育——先学俄语再学理论。而中国学生多为大革命后在国内无法立足的干部,许多还是文化很低的工农干部,认为学俄文学理论实无必要,国内斗争那么激烈,希望短期培训后赶快回国,一两年学制已经很长了。
亲历者刘英(后为张闻天妻,1905~2002):
像我这样的人,同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感情很深,心中燃烧着复仇的火焰,希望得到学习提高,早日回国投入斗争,很自然地并不赞成支部局的教学计划,对拥护支部局的同志那种反对中共代表团的态度也不满意。而像我这样的人,在「劳大」学生中占的比重很大。这样,在平时,争论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尤其是在板报委员会里,后来几乎天天都要争执。那时板报几乎每天一期,而板报委员会主席陈昌浩就是坚定地拥护支部局的一个。
9月,黑海度假回来,中大支部举行全体师生例行总结大会,由俄人支部书记做报告,会议发言主要围绕以上两个焦点激烈辩论,最后进行表决,史称「十天大会」。而「十天大会」之所以出名,关键是选举时出了后来名声很响的「二十八个半」(反对派起的外号)。
大会一开始,提名主席团七人名单,就起争论。名单上有余笃三、中共代表团成员张国焘、区委书记芬可夫斯基、共产国际监委主席索里茨。盛岳说王明并未出席「十天大会」,已回国,任上海《红旗报》通讯员、沪东区委宣传干事。
刘英:
激烈的争论在这次会上总爆发了。……会场上很混乱,赞同时鼓掌、欢呼,反对时起哄,因为两派观点尖锐对立,所以鼓掌、欢呼的声浪和嘘声、起哄声常常混成一片。激烈的时候甚至挥舞拳头,相互威胁。争论的问题主要是教学计划的问题、大革命失败的是非问题、中国革命的理论与策略问题。[12]
据陈修良等人回忆,「十天大会」为支部局精心布置,意在整中共代表团与反支部局的同学。此前已有「江浙同乡会」、「第二条路线」(对中大支部局有意见者)、「反中共代表团」等一系列事件,校内矛盾已相当尖锐。残酷斗争那时就开始了。如王明集团多次拉拢张仲德遭拒绝,便以「江浙同乡会」罪名逮捕张仲德,未经审讯即由格别乌(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即契卡)判五年劳改,释放后再抓回,最后死在苏联。王明曾以共产国际名义找「不同意见者」李一凡谈话,用俄语告知共产国际东方部想派他回国接办中央机关报《布尔什维克》。李一凡回答:「我不会做买卖。」王明很尴尬,满脸通红。
「十天大会」,各派上台发表意见,互相攻击,闹成一片,几乎动武,主席台无法控制。张国焘讲话时,法国来的华工上台想打,被俄国人阻止。最后,争论焦点汇聚「支部局路线是否正确」?支部局自认为执行了「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路线,众多党团员则认为支部局执行的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不仅有官僚主义,还有贪污问题。
大会发言者:秦邦宪、吴玉章、王稼祥、董必武、盛岳、余笃三、李剑如、吴福海、张仲德、张崇文、李一凡、溥庆、唐有章、郭妙根、张祖俭。张仲德、李剑如的发言与支持支部局的人针锋相对。余笃三、李剑如的发言批评了王明宗派小集团。据王观澜回忆,董必武立场坚定,反对王明集团操纵支部局搞宗派,批评搞教条与唯成分论,不同意打击人、整人,把凡是不同意见者都说成反党分子、托派,帽子满天飞。
陈修良分析:支部局的人想打倒中共代表团,特别想打倒瞿秋白、邓中夏,因为不少「劳大」学生经常去代表团处谈话。1928~1930年夏,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为瞿秋白、张国焘、邓中夏、余飞、陆定一。「中大」学生中经常有人散布流言蜚语攻击中共代表团。瞿秋白、邓中夏甚至上了板报漫画,进行人身攻击。[13]
三、「二十八个半」
意见分歧太大,只好付诸表决。大会最后一天上午,支部局向大会提交〈解散团支部局的决议案〉,许多原来追随王明集团的人均未举手,五百多名「中大」学生均投反对票,只有二十八人举手赞成,而这「二十八个」正好扎堆站在主席台左边,很容易计数。事后,被称「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嘲笑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的革命者,以示轻蔑。[14]
表决后,米夫见大势不妙,下午搬来区委书记芬可夫斯基,用区委的名义命令大会结束。
盛岳开列的「二十八个」名单:
王明、博古、张闻天、王稼祥、陈昌浩、沈泽民、凯丰、杨尚昆、盛岳、夏曦、肖特甫、李竹声、殷鉴、陈原道、何子述、孟庆树(王明妻)、张琴秋(沈泽民妻)、杜作祥(陈昌浩妻)、李元杰、王保礼、王盛荣、王云程、袁家镛、孙济民、宋泮民、汪盛荻、朱阿根、朱子纯(女)。[15]
未出席「十天大会」的王明之所以位列榜首,乃是这一派公认的头头,「中大」支部局负责人。
陈修良对名单提出质疑:孟庆树、朱子纯为团员,不可能有表决权;杜作祥、宋泮民并不活跃,进入名单有点不可靠。
至于那个「半」,即徐以新(1911~1994,后任外交部副部长)。一说年纪最小,又是团员;一说徐对支部局的态度前后不太一致,故算「半」个;也有说弃权。[16]
四、深远影响
惊心动魄的「十天大会」结束了,「斗争」根子深深埋下。刘英:
「十天会议」结束时进行表决,形式上支部局一边取得了多数,实际上许多人弃权,而弃权的人其实都不是赞成支部局的,只不过有顾虑而没有明确表态而已。……「十天会议」的混乱局面,使得学校领导以至联共、共产国际都认为「劳大」学生党员队伍严重不纯,决定进行「清党」。不久就在联共监察委员会直接领导下成立了清党委员会。[17]
1929年冬,随着苏共清党,「劳大」也停课搞运动,日日夜夜「战斗」在会场。年底,支部局忽然召开全体党员大会,组织委员王云程手拿两页信纸宣布:河南人赵言清(俄名马马也夫)自杀,留下遗书,揭发校内存在庞大托派秘密组织,操纵广大党团员「十天大会」上向支部局进攻、反对党的领导,提供了一份百十来人的托派名单。此后,校内学生陆续失踪,说是被送回国、共产国际找去谈话,实际上逮捕了,其中有唐有章、李一凡、张仲德等。
几百名学生遭受冤屈,五六十人被逮捕,李一凡后被流放西伯利亚,遭受迫害二十二年,1958年才回国。被逮捕的学生不少死在苏联,如张仲德、李国暄。一部分学生送回国,如「十天大会」主席团成员余笃三(后死于鄂豫皖苏区肃反)、李剑如。瞿秋白三弟(景白)反对支部局,清党时被格别乌逮捕,后失踪。少数人飞黄腾达。李国暄仅因同情俞秀松、周达明、董亦湘,为他们送了毛毯,就被隔离五年,1937年下半年起,再也听不到他任何消息。《江苏革命史料》1983年第八期载文,董亦湘被王明诬为托派,1938年被捕,经其俄籍妻子与弟弟董涤臣请国际红十字会帮助寻找,苏联中央军事检察院1959年通知:「他没有罪行,应恢复其名誉。」[18]
国内的党内斗争也相当激烈。博古妻阿金,江苏省委妇委书记,受不了白色恐怖的沉重压力,精神失常,送苏联治疗。[19]
「二十八个半」另一重大政治动作为斗争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瞿秋白。据杨子烈(张国焘妻)回忆录:「中大」学生不断向瞿秋白投诉,瞿秋白批评了支部局书记柏尔金(米夫部属),因此「二十八个半」在柏尔金支使下——
……箭簇就射向瞿秋白。杨之华在学校和秦邦宪(即博古)争论得面红耳赤。有一天中国大学又开会了,这是斗争瞿秋白的会,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的张闻天、秦邦宪等长篇大论地责骂秋白。[20]
陈修良忆文:「二十八个半」在板报上用漫画丑化中共代表团的瞿秋白与邓中夏,将瞿秋白画成一只拿烟斗的猴子,将邓中夏画成一个小丑。而且这时就出现「反党右派分子」。板报主编即盛岳(忠亮)。[21]
五、「二十八个半」的后来
「二十八个半」的人生道路,各各有异,既两极分化,亦有中间人物。
八名党内要角:王明(1955年赴俄不归)、博古、王稼祥(文革批斗)、张闻天(文革批斗)、沈泽民、凯丰、杨尚昆、陈昌浩(1967年自杀)。
四名烈士:陈原道、夏曦、何子述、宋泮民(冤杀于湘鄂西肃反)。
追随革命:王盛荣(后任湖北冶金厅副厅长,文革入狱)、徐以新、孟庆树(随王明赴苏,1983年病逝于俄)、张琴秋(文革跳海)[22]。
病故:殷鉴(1934年被捕,后因病保释就医,不久病故)。
不详:肖特甫、朱自舜、杜作祥。
变节者:
李竹声(中组部长、政治局委员、上海中央局书记,入「中统」,1951年被捕,1978年死于秦城)
盛岳(中委,接李竹声任上海中央局书记,被李竹声供出被捕)
孙济民(团中央组织部长)
袁家镛(江苏省委书记,后入「中统」)
朱阿根(江苏省委组织部长,一说退党)
汪盛荻(江苏省委宣传部长,1950年代初期在湖南被处决;一说退党)[23]
王云程(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1933年被捕,1934年出狱,回家务农)[24]
「疑似」叛徒
王保礼(莫斯科中大副校长,一说叛变,在上海大马路搜捕留苏同学)
李元杰(传说叛变)
1932年5月,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形势极其严峻,团中央局机关先被破坏,团中央书记王云程、组织部长孙济民被捕,旋公开叛变,致使罗登贤、廖承志等被捕。1934年6月 26 日,上海中央局(中共中央进入苏区后设立)书记李竹声、秘书长李德昭、江苏临委书记赵立人等26人被捕。李竹声叛变,供出苏区存在上海的窖藏黄金。在李竹声劝说下,赵立人亦叛变。李竹声1973年死于狱中。此后,盛岳代理上海中央局书记,袁家镛接任江苏省委书记。1934年10月,盛岳被捕叛变,出卖五名同志。袁家镛叛变后加入国民党「中统」。此前,江苏省委组织部长朱阿根亦被捕叛变,上海中央局妇女部长杜作祥亦被捕。[25]
夏衍回忆录《懒寻旧梦录》:
(1935年)2月19日的突击行动不仅逮捕对象和机关都相当准确,而且使中央局机关、组织部、宣传部、文委、左联、社联、印刷厂……等,同时受到了打击。事实很清楚,没有李竹声、盛忠亮这两个王明死党的告密,2月19日的大破坏是不会那样严重的。[26]
从此,上海党组织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直至1936年4月下旬冯雪峰从陕北来沪。
「三十五人」大案
留苏生中还有一桩「三十五人」大案。2010年,当事人苏飞(1915~ )出版的回忆录,终于浮出史尘。
苏飞,辽阳人,1933年加入中共,1935年冬被捕,日本宪兵队因无证据释放,满洲省委派他入莫斯科东大学习。1937年4月苏联内务部将东方大学分校数十人先后逮捕,打成「日本特务」、「现行反革命」,判刑五年,7月押往北极圈内劳动营,「劳改营中的外国人以中国人数量最多」。1942年4月,苏飞刑满,1943年与数百名刑满释放人员入伍,参加卫国战争。1954年,大难不死的苏飞终于眷回国,中组部副部长帅孟奇(东大生)接待,分配外文出版局任俄译,俄妻任外文局图书馆管理员。1956年,中共为这批苏联回来的幸存者平反,恢复党籍。
文革爆发,苏飞夫妇再次被打「苏修特务」,1970年5月9日,俄妻苏玛莉驱逐出境。1971年底,苏飞入狱,1976年5月7日判刑十年。1981年,刑满释放的苏飞离开京郊延庆监狱,66岁,一头霜雪,无家可归,外文出版社收容。一年多后,他才与俄妻联系上,1983年赴俄团聚。1988年携妻回国,希望洗清罪名。
不久,戈巴契夫宣布为斯大林时期所有受迫害者平反。2002年,一位苏联大肃反受害者女儿,在克格勃解密档案中找到康生起草的绝密档(1937年1月14日)——〈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曾多次提出关于立即解决有关35个人中国人的问题〉,其中12人(包括苏飞)被认为「有必要隔离」。87岁的苏飞这才明白当年被秘密逮捕的缘由。2003年6月,苏飞致函中共领导人要求平反,9月获批,法院重新立案审理。2007年2月8日,北京高院宣告苏飞无罪。此时,苏飞92岁。一生都绕进去了。[27]
同时,莫斯科中大也是中国托派运动发源地,部分师生深深卷入俄共政争。1927年10月,斯大林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开始出俄共中央委员会。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游行中,进入红场的部分苏联学生突然掏出布旗挥舞,呼喊反对斯大林、拥护托洛茨基的口号,引起拥斯派学生的反击,发生斗殴。「中大」队列经过列宁墓时,托派生也突然打开旗子,高呼「执行列宁遗嘱、罢免斯大林、拥护托洛茨基」,斯大林及共产国际领导人大失体面。一周后,11月14日联共中央及中央监察委员会召开特殊联席会议,开除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两人党籍。第三天,1923年1月代表赤俄与孙中山发表联合宣言的越飞,因同情托洛茨基开枪自杀,成为俄共反托运动倒下的第一位高干。12月联共「十五大」,批准开除托、季的决定,同时开除75名托派骨干。1928年1月托洛茨基被流放东南边疆阿拉木图,苏联全境开展大规模肃托运动。莫斯科中大的托派学生,遭到残酷打击。[28]
「江浙同乡会」案
1927年,六七名「中大」生在宿舍改善伙食,学生会主席从窗下经过,听里面笑语喧哗,传出浙江口音:「可以江浙同乡会啦?」(实为开玩笑)学生会主席汇报给米夫、王明,认定中国学生中有反动组织「江浙同学会」,先后派出三批联合调查组,牵连所有江浙籍学生,共150余人,包括蒋经国、董亦湘、陈修良、孙冶方,以及非江浙籍的左权等。经瞿秋白再三申辩,此案才告一段落,但因王明撺掇米夫作梗,一直未做结论,瞿秋白被取消中共代表团长资格,限期回国。[29]
1927年11月7日十月革命十周年盛大庆祝游行,中大队伍经过红场时突然打出横幅「拥护托洛斯基」、「反对斯大林」,结果一些中国学生被开除学籍,120余名同学流放西伯利亚,很多人没能活着回国。[30]
师哲记述:
「江浙同乡会」的事情发生在1927年下半年到1928年之间,起因于蒋经国等。蒋经国原在中山大学念书,那里的江浙同学比较多,十天半个月到中国饭馆吃顿饭。1927年10月,苏联从中山大学、东方大学抽调了一部分同志到陆军大学(在莫斯科)、军政大学(在列宁格勒城)等军事学院学习。蒋经国同萧劲光、李卓然、曾涌泉等一起到列宁格勒的军政大学学习。这时,蒋经国享受红军军官的待遇,每月领津贴费约七八十元。留在中山大学的江浙同乡们给他写信,时常开玩笑,时常开玩笑说,你的会费还没有交,意思是向他要钱,也就是要他请客。蒋经国寄钱时也戏称交会费。这些信不知落在什么人的手里,便认为他们是搞小组织,组织了「浙江同乡会」。党的六大前后,这件事在中国学生和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里就成了一个重要的问题。[31]
初稿:2014-2-28~3-2;增补:2015-6-20
[1] 张国焘:《我的回忆》,东方出版社(北京)1998年,第三册,页237。
[2] 李莎:《我的中国缘分》,李英男、姜涛编译,外国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北京)2009年,页57。
[3] 马贵凡编译:〈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介〉,《党史通讯》(北京)1986年第8期,页40。
[4] 陈碧兰:《我的回忆》,十月书屋(香港)1994年,页153。
《黄平遗稿》,《党史研究资料》第四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页75。
[5] 裴超:〈「朝圣取经」的首批留苏中共党员〉,《党史纵览》(合肥)2012年第12期。《文摘报》(北京)2012-12-1摘转。
[6]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东方出版社(北京)2004年,页48。
[7] 罗章龙:〈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风雨历程〉,《红色往事》,济南出版社2012年,第一册政治卷(上),页43~44。
[8] 质朴(「中大」国民党生):〈致陈公博函〉(1928-3-20,巴黎),《革命评论》(上海)第2期(1928-5)。万大鋐主编:《共匪祸国史料汇编》,中华民国开国文献编纂委员会、中华民国国际关系研究所1973年,页9。
[9] 苏兆征(1885~1929),海员工人出身,1925~26年省港罢工领导人,中共第五~六届政治局常委,1929年2月病逝上海。
[10] 张崇文:〈莫斯科中山大学与「十天大会」〉,《红色往事》,济南出版社2012年,第一册政治卷(上),页8。
[11] 《王若望自传》第2卷,明报出版社(香港)1992年,页81。
[12] 《刘英自述》,人民出版社(北京)2005年,页34~36。
[13] 陈修良:〈莫斯科中山大学里的斗争〉,《革命回忆录》增刊(一),人民出版社(北京)1983年,页49~67。
[14] 陈修良:〈莫斯科中山大学里的斗争〉,《革命回忆录》增刊(一),人民出版社1983年,页62~63。
[15]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东方出版社(北京)2004年,页222。
[16] 盖军、于吉楠:〈陈绍禹是怎样上台的〉,《党史研究》(北京)1981年第2期,页31。
[17] 《刘英自述》,人民出版社(北京)2005年,页35~36。
[18] 张崇文:〈莫斯科中山大学与「十天大会」〉,《红色往事》,济南出版社2012年,第一册政治卷(上),页7~13。
[19] 张金保:〈六届四中全会前后〉,《革命回忆录》增刊(一),人民出版社1983年,页79。
[20] 万亚刚:《国共斗争的见闻》,李敖出版社(台北)1995年,页22~23。
[21] 陈修良:〈莫斯科中山大学里的斗争〉,《革命回忆录》增刊(一),人民出版社1983年,页62。
陈修良撰述、唐宝林编著:《拒绝奴性》,香港中和出版公司2012年,页82。
[22] 《王若望自传》第1卷,明报出版社(香港)1991年,页394。
[23] 丁玲指汪盛荻1933年5月对其劝降。《丁玲自叙》,团结出版社(北京)1998年,页108~109。
[24] 中组部、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会大辞典(1921~2001)》,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页748。
[25] 唐玮.:〈「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人生结局〉(二),《党员干部之友》(济南)2001年第11期,页57。
[26] 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补本),三联书店(北京)2000年,页185。
[27] 《苏飞回忆录》,北京时代弄潮文化公司2010年。朱理轩、李文华:〈「三国囚徒」平反纪实〉,《中华读书报》(北京)2015-6-3。
[28] 吴晓:〈中国留苏学生反斯大林游行事件〉,《炎黄春秋》(北京)2003年第10期,页32~35。
[29] 陈修良:《孙冶方革命生涯六十年》。《王若望自传》第1卷,明报出版社(香港)1991年,页390。
[30] 《王若望自传》第1卷,明报出版社(香港)1991年,页391。
[31] 师哲:〈我所知道的周恩来同志的某些情况〉,《怀念周恩来》,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268~269。
原载:《南方都市报》(广州)2014-3-6(初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