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荣与马廷
“文革”兴起后,老百姓被撕裂为红五类与黑五类。红五类包括工农兵,再加上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其中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必须是“革命”的才够资格,工农兵则是天生的好人,不用加这个定语。黑五类也没有定语,都是坏蛋,包括地富反坏右,不知道为什么不包括剥削工人的资本家。本来红五类的人数占压倒性多数,但东搞西搞,红五类中不断有人被揪出,人数越折腾越少,阶级敌人的队伍却日益壮大,随着走资派和叛徒、特务的陆续加盟,黑五类也逐步扩展为黑七八九类。
对这些七七八八的黑几类我是再熟悉不过的。我们家就有不少,而且品种全,当时有一个时髦的词语“池浅王八多”专门用来形容这种现象。我的奶奶在土改中被荒唐地定为富农,后来又莫名其妙地升级为地主。姥爷是辛亥革命时参加过武昌首义的革命前辈,后来稀里糊涂地成了右派,母亲是出了名的顽固右派,父亲的头衔就更多了,什么黑帮、特务、走资派,几乎所有的坏人他都当了,幸亏不是蒙古族,没当成内人党。我本人有一些“反动言论”,但是侥幸漏网,和反革命分子擦身而过,不过舅舅是国民党将军,当属货真价实的反革命。虽然我们家把黑几类几乎全部包揽,却独缺一“坏”。我对这个“坏”真是陌生的很,既感到些许恐惧,又怀有强烈的好奇,他们究竟是什么样子呢?

黑五类:地富反坏右……
奶奶是富农,
妈妈是右派,
爸爸是黑帮、特务、走资派
阀门厂留用的刑满就业人员正好可以满足我的好奇心。
王荣是我见到的第一个坏分子。在一次分组学习时,他被指派来参加,领导的意图是让大家先互相熟悉一下。王荣个子很矮,一副标准的四川人身材,他像首长视察一般昂然而入,目光炯炯神态自若,完全没有想象中坏分子应有的低眉垂首和唯唯诺诺,我们几位兵团战士反而显得不知所措,十分拘谨。王荣面带微笑,用一口独具魅力的川音不卑不亢地自我介绍:“我是王勇,王,三恨一许”,他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指在空中写了一个三横一竖的“王”字,“勇,光勇的勇。”我听了以后差点笑出声来,心想你老兄一个被判过刑的人硬要和什么光荣不光荣扯在一起,实在是滑稽,不过也很欣赏他的气度。后来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我常常学着他的四川口音开玩笑:“我姓王,三恨一许,王八的王……”
王荣非常聪明,但不对别人动心眼,他性格豪爽仗义,威望很高,很少有人把他当作“二劳改”来冒犯,领导也要让他几分。2009 年,一些战友为纪念兵团成立四十周年回到包头,王荣成了最耀眼的明星,大家排着队争着与他合影,他也忙得不亦乐乎。当年和他关系最好的叶鲁玺感叹说王荣现在真是牛×,要想见一面也不容易了。
王荣的聪明不仅仅表现在工作方面。由于被判过刑,组建家庭成了难题,王荣另辟蹊径,从四川老家娶回一位眉清目秀的农村姑娘,轰动一时,引起“二劳改”们纷纷仿效。

王荣的夫人没有户口和粮本,只好买一些高价粮。有时我和叶鲁玺送去一些多余的食堂粮票,王荣则一定要在家中摆酒招待,每次都是如此。即使对方是关系密切的朋友,做了一点无足挂齿的事情,他的尊严不允许自己受人恩惠。
在兵团的十年中,除了回家探亲期间,我没有到别人家吃过饭,只有王荣是个例外。我们的关系熟得不能再熟,但是无论对他过去的经历有怎样的好奇,我却始终回避着这个话题,直觉告诉我那是他心中不能触动的隐秘。我结识的“二劳改”朋友都和我谈过自己的经历,在这一点上王荣仍是个例外。我知道只要开口询问,肯定是不会吃闭门羹的,但我更清楚,这种特殊经历会使一些人的心灵非常敏感,千万不要轻易去触动,这也是对别人应有的尊重。当然,是有点遗憾,那就遗憾吧。
有一次酒至半酣,王荣谈起童年趣事,突然红了眼圈,哽咽良久,举杯的手,竟不由颤抖起来。伤口过了这么多年,一碰仍在流血。我低着头坐在一旁,喉咙一阵发紧,默默地满斟一杯,一饮而尽。

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一定不止一次地在他的脑海里翻腾。我没有借机询问,我不愿意面对朋友的尴尬和辩解,这实在是一件太残忍的事。
我曾听见王荣和别人吵架时冒出一句“老子就是那么二百来块钱!”我也曾听说他在类似“严打”的运动中以盗窃罪被从严惩处,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究竟是怎样的窘迫居然使他这种性格的人伸出手,我无从得知,也难以想象。
后来随着阅历的逐渐增多,知道不少人入狱并非犯下什么重大的罪行,却因此耽误了一生。我们不曾受过生存的逼迫,没有切身体会,不知道在“严打”之类的运动中以法律之名埋葬了多少冤魂。当年那个在杜甫屋外偷枣的老太太,犯下的过错再大能有多大呢?窃钩者身陷囹圄,窃国者弹冠相庆,量变到质变,竟是如此。
只要说到王荣,人们往往要提起马廷。从1969 年秋我担任质量检查员起,马廷一直是我的授业恩师。马廷是杭州人,解放初期,只有十六七岁的他就在公安局当侦察员,十九岁时已经是副科长,曾因破案有功而得到朱德委员长签发的嘉奖令,可谓少年得意。马廷有了女朋友后花钱大手大脚,当时管理比较混乱,他开始挪用罚没的赃款。起初还可以用工资补上,后来窟窿愈来愈大,酿成大祸,最终以贪污罪入刑,从西子湖畔沦落塞外。每言及此,师父痛悔不已。他曾向我出示年轻时的照片,瘦瘦的脸颊透出些许稚气,头上顶着大檐帽,英姿焕发,如今却已是满脸丘壑的“二劳改”。马廷要我一定以此为鉴,而他已是一失足成千古恨。每当师父情绪低落,我便要师父讲当年破案的故事,以过五关斩六将的业绩来冲淡败走麦城的惨痛记忆。

马廷全心全意地向我传授知识和经验,没有一点保留。现在回想起来,愈发感到难能可贵。作为刑满就业的“二劳改”,地位低下,技能就是唯一可以安身立命的饭碗。为了培养我这个徒弟,他不惜掏空箱底。
马廷得知我自学机械制图后很高兴,大概觉得孺子可教。他把我带到自己的住处,从锁着的箱子里捧出一个包装考究的盒子,轻轻地抚摸着,打开后,天鹅绒的衬底上摆满了各种不锈钢的圆规、分规、鸭嘴笔等制图工具。师父要我拿去使用,我被它们的精美所震撼,明知这是师父的心爱之物,却假装客气一番后收下了。
师父的循循善诱同样令人难忘。初学制图时,我觉得三视图很繁琐,总是喜欢用两视图,自以为得意。马廷看了后予以诸多鼓励,最后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制图最重要的一点是让别人容易看清楚,容易看懂。”师父的教诲如醍醐灌顶,命中要害。做事情一定要目的明确,不能只顾炫耀自己,舍本逐末。这句话,我至今铭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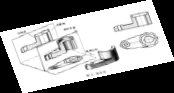
 有时我工作中出了问题,马廷主动承担责任,为我背黑锅,在生活方面也多有关照。我挨整后,他几次向领导建议,恢复了我的质量检查工作。这些事,他做了,却从未向我提起,这些事,我知道,也从未向他道谢。作为师父,马廷倾尽了全力。作为徒弟,我也合格。工作中不给师父丢脸,也总是十分敬重师父。有时领导的指示被我顶回去,领导会绕个弯子找马廷来疏通,师父的意见我总是尊重。我曾被称为“二马廷”,我为此感到荣幸。
有时我工作中出了问题,马廷主动承担责任,为我背黑锅,在生活方面也多有关照。我挨整后,他几次向领导建议,恢复了我的质量检查工作。这些事,他做了,却从未向我提起,这些事,我知道,也从未向他道谢。作为师父,马廷倾尽了全力。作为徒弟,我也合格。工作中不给师父丢脸,也总是十分敬重师父。有时领导的指示被我顶回去,领导会绕个弯子找马廷来疏通,师父的意见我总是尊重。我曾被称为“二马廷”,我为此感到荣幸。

怎么搞的!
是我的责任!
王荣和马廷的身材同样矮小,两个人的聪明程度也不相上下,至于哪个技术更高则是大家经常争论的话题。王荣的强项是实践经验丰富,技术精湛,体力充沛,但文化程度比较低,识字不多,马廷在实践和理论方面比较均衡,按照谁也不得罪的鸡贼说法就是两位各有千秋,难分高低。
他们二人之间互不服气,尤其在我们这些年轻人面前绝不向对方示弱。记得有一年秋天,王荣提醒我们注意防止呛火,马廷不以为然,“秋高气爽,空气干燥,怎么会呛火”,“秋雨连绵,空气潮湿,当然容易呛火”,两个人脸红脖子粗地争得不可开交,我们在一旁笑作一团。尽管他们互相竞争,但不互相拆台。按照当地的俗语叫做“技术拿人”,意思是凭真实本领和对手较量,而不能靠下三滥手段取胜,那样就是“屁股屙人”,为人不齿。这种君子之争在如今恐怕已经绝迹。
他们两位是车间里最重要的生产技术骨干,像车之两轮,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大家起初叫他们的姓名王荣马廷,后来称他们王朝马汉,把他们比作是包公的左膀右臂。心情不好时骂他们为王㞗马蛋。

来源:微信公号:老鼠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