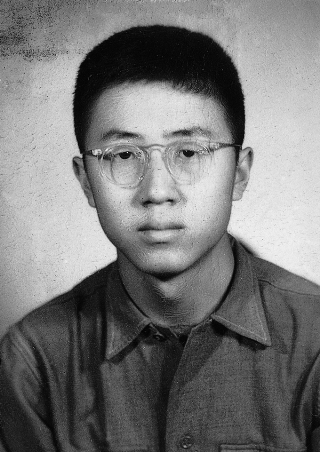嘉陵江畔的瞰江饭店
我开始有比较连贯的记忆,是四岁的时候。所以我觉得自己的一生实际上好像是从这时正式开始,而且是从一个梦境开始的:五光十色的星星点点组成立体回旋的长河,不停地来复流动。我悬浮其中,不觉自身之存在,惬意、瑰丽。后来回想好像是梦到了原始的混沌,梦境中只有这些,再没有现实尘世中那些更具体的物事。这是我记得的第一个梦,怎么来的这个梦?可能那是我刚从昆明到重庆头两天的梦。为什么呢?虽然我记不得那第一次坐飞机的情形,但是记得后来两次在同一条航线上来回飞的感受。昆明至重庆之间,高山起伏,上空气流很强,那时在这条航线上飞的有中央航空公司的、中国航空公司的和德国欧亚航空公司的飞机。和现在的客机比起来太小了,所以颠簸得非常厉害。和现在一样,每个乘客座位前面的靠背上都插有纸袋,是供呕吐用的。我每一次几乎都要吐半袋子。由此可见第一次下飞机之后会长时间保持飘浮晃荡的感觉,直到头两个晚上还做起飘浮回旋的梦。
我穿着一件白色的小睡袍,睡在靠窗子的一张草绿帆布行军床上。不止一个晚上,响起了什么声音。爸爸就扒在我床边的窗口,把头,甚至半个上身都伸到窗外,反复大声喊着:“关灯!关灯!……”。我渐渐懂得,那是来空袭警报了。爸爸是政府机关公务员,大概在这个时候负有提醒周围公众的责任。
这是嘉陵江畔岸坡上的一家小旅馆。初到重庆,在我童稚的心理上觉得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都住在这里。只有一个小房间,我的小床对面(进门那一面)靠墙是爸爸妈妈的双人床。床前侧墙下是一张方桌,三四把方凳。另一堵墙那里有一个放脸盆的木架子,大概还堆着一些杂物,其中有一个圆筒状的绿色大帆布行李袋,可以用一个“D”字形可开闭的铜环穿过圆筒袋子上边镶有铜圈的一串孔束紧袋口。进门左手,爸爸妈妈床脚附近摞着大大小小几口皮箱。——我大概基本上没有遗忘什么了。房间外面的情形则记得模糊。似乎上了木楼梯没有几个房间,楼下仿佛有个小柜台,下了木楼梯背面有扇后门。总之是个小小的旅馆,严格说来只能叫“客栈”,但是我后面要说到,它倒是有一块响亮的招牌。
白天爸爸去部里办公了,留下我和妈妈守在这小房间里。妈妈开始教我识方块字。人、手、刀、狗、猫、我、你、他、爸爸、妈妈……,背后都有图画。抗战初期的这些东西,包括后来看到的许多图书,纸张和印刷都是很精美的(也说不定是从南京、上海带过来的)。抗战晚期就一落千丈了。妈妈把教过的字一张一张翻出来叫我认,还把字这样排起来读,再那样排起来读。我学得很快,入学前就认识了不少字。
妈妈还教我唱歌。最初教的是“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妈妈告诉我“鬼子”就是派飞机来炸我们的坏蛋日本人;有个“大刀队”是专门杀日本鬼子的。但是我那时说话还不能准确发音(妈妈常常笑我是“大舌头”、“方舌头”,就像我后来知道的京戏大师马连良一样,但是我长大以后舌头就不大了),我把“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唱成了“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叹气”。这又成了妈妈津津乐道的一则笑话。还有《义勇军进行曲》里的一句:“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这个“炮火”我还不知道是什么。那时爸爸的一个朋友姓“贺”,曾经带他的太太和男孩来我们住处玩过。我叫那个男孩“贺哥哥”。南方话“贺”与“火”这两个字唱歌的时候听不出差别。贺哥哥比我大几岁,有点顽皮。总在屋里不停的跑来跑去。因此我一唱到“炮火”两字时,脑子里就浮起那个“贺”哥哥穿着背带裤在“跑”的样子。“炮火”在我脑子里变成“跑贺”了。
后来妈妈才教了我一些儿童歌,其中有一首:“Blue bird,blue bird,(这里空下一个当时没有听清楚的字)I see you,oh no!I see you”。后来去北碚以后又教了我许多别的歌。
此外妈妈还教我折纸。一张方纸可以折成小船(有蓬的和没有蓬的)、飞机、手枪、青蛙、猪头、衣服、裤子、猴子、灯笼、八角盒。还有一种鸟,就是现在情思细腻或者追求时尚、附庸风雅的少女折来表示寄托某个心愿的所谓“千纸鹤”。我能够静得下心来,折得非常整齐,一丝不苟,常常得到妈妈的夸奖。
因为住在旅馆里,饭是到外面去吃的,或者有时候饭菜都由旅馆茶房从外面叫来,装在一个竹子编的提盒里拎来,所以家务事并不多,妈妈有足够的时间给我启蒙教育,和我一同消遣光阴。但妈妈总还有一些别的事情要做。她在做事的时候,我常常是在桌边跪在方凳上一个人玩积木。我有一大盒、一小盒,两套积木。我照着图上的样子搭,自己也想出新花样来搭。因玩得专心,所以至今我记得那些长长短短的、形状各异的积木块各是什么颜色,还记得那彩绘的门拱、窗拱,还有一个大笨钟……总之,都是古典欧式建筑的构件。
天天或者隔天就有的事情是空袭警报。突然间就从不远的地方传来凄厉的“呜————”高一阵低一阵的长鸣。于是妈妈就急忙把方桌上的东西挪开,把几床被褥都盖在桌子上,拉着我一同钻到桌子底下蹲着,直到听见解除警报的汽笛声。不知为什么我们那时没有去防空洞而是采用了这个简易的方法躲轰炸。棉被和方桌当然挡不住炸弹。但是我想也许那时日本人的轰炸机小,往往是低飞投弹,而且低飞扫射。可能因为那时机关枪子弹的穿透力不强,几床棉被和桌板大概是挡得住的。还可以抵挡别处被炸时飞来的弹片。
午饭好像多数是去饭馆吃的,一家三人在一起(大概预先和爸爸约好会合的)。重庆是山城,房屋由江边向内层层升高,街上有坡道,有石阶。我印象比较深的一家馆子,朝嘉陵江的一面没有墙只有栏杆,在那里越过前面低处的房顶可以看见嘉陵江。吃过些什么菜我不记得,倒是牢记着一样东西,那是蒸出来很白、很松软的竖圆墩状的馒头(后来我听上海人叫“高脚馒头”),带着刚出笼的清香,还有点甜味。
有一天,我们正在馆子里吃午饭,空袭警报来了。而且听到我们那个旅馆的方向传来“轰”的一声,人们在唧唧喳喳议论。爸爸妈妈有些紧张起来,连忙牵着我往住处赶。到那里一看,不好了!恰恰就是我们住的那家旅馆中了弹,听他们说不是普通的炸弹,而是一颗“燃烧弹”。
我和妈妈站在街道的另一边望着;爸爸和一个茶房冒着烟火冲进正在燃烧着的旅馆,一趟又一趟的把行李物品抢出来,放在我和妈妈身边,然后又进去抢救。进出几趟以后说不行了,楼梯已经烧断了,上不去了,于是就到此为止。好在据说大多数重要的东西都抢救出来了。后来听妈妈说她的一把小提琴没有抢出来,烧在里面了。我以前不知道有这个东西,因为在那里没有见她拉过。肯定是在南京的时候就有的,去重庆后在旅馆里也不便用,就堆在别的行李中间,我没有看见。倒是可以肯定,我喜欢的两副积木也被烧了,因为印象中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玩过积木。
我们从此告别了这家旅馆。住在四川的那些日子里,一家人都跟着妈妈说昆明话,爸爸也带着上海口音学昆明话,于是从他们口中听到那家旅馆的名字,我一直以为是叫“康家饭店”,后来也是这么记着的。直到1983年,我出差成都路过重庆时,专门去凭吊旧地,曾在嘉陵江边一带踯躅良久,并没有看见什么“康家饭店”,却终于找到一家“瞰江饭店”。我想是了,这个字号对于处于江边旅馆来说既贴切又雅致。昆明话里面没有ng结尾的音,所以“瞰江”和“康家”很容易相混,哪来的什么“康家饭店”?那一年爸爸还在世,但我后来还是忘了与他核实这个悬念。直到他去世后,含泪翻阅他那些写得工工整整的,政治运动中的“交代材料”,才证实了我的推断。在交待抗战初期那一段中,赫然写着“瞰江饭店”。当然,我1983年见到的瞰江饭店已经不是记忆中的那个简陋的小旅馆了。
北碚磴子坎农家
后来怎么离开重庆市区去到北碚乡下,我毫无印象。也许大乱多时后疲劳的旅途中我睡着了。起先,我们搬到一个叫“磴子坎儿”的村子里,住在一户农家。有围墙,进门有个小院坝,一横一竖两侧各有一所平瓦房,都盖在一尺多高的台阶上。我们就在对着院门的那一所屋里占了一间,长方形的。宽的一边有窗子朝着院坝,窄的一边还有个小窗子朝着屋外。我特别记得我们住进去以后在这小窗子上钉上了新的绿色铁纱来挡蚊子,所以这时候应该是夏天。还有一个证据是有一天晚上爸爸有个同事送来一个椭圆形的大西瓜,这是我所记得的第一次吃西瓜。这也说明爸爸机关里当时因空袭日紧,疏散到这边乡下的不止我们一家,所以有同事住在附近。爸爸还是天天去办公,这说明办公的地方也已不在重庆城内,而是同样疏散到北碚乡下来了。
院子和房子里面都很干净,好像从上述那两所房子的间隙中向后去还有房子。那家有一个不到十岁的女孩,剪成像男孩子那样的短发,皮肤洁白,她身上穿的土布的半长不短的侧襟上衣和土布裤子都已经洗白了。他们叫她“有蓉”(至少按南方话是这样发音的),她有时带我出去玩,但次数不多。平时还是我和妈妈在一起,她继续教我识字,而且开始用铅笔写字。这事都在上午。她给我规定了每天要认会多少(仿佛是五个字)、写多少。然后妈妈就说她要去“变把戏”,“变”饼干给我吃。那饼干做成各种动物和别的东西的形状,又好玩又好吃,或者是因为好玩就觉得好吃。但是每次妈妈去“变”饼干的时候都不许我跟着她去,而且还要我转过身去不许看。说要是我看了,饼干就“变”不出来了。大概是得这样,因为要是让我看见了,我馋起来的时候就用不着麻烦她,我自己会去“变”了。也可见大概那时候在那里买到点东西已经不大容易,所以妈妈要对我“定量供应”了。
在那里妈妈又教我唱了些歌。
一首是“小羊儿乖乖,把门儿开开,快点儿开开,我要进来”。“不开不开不能开,妈妈不回来,谁也不能开”。小兔子也没有开,小青蛙也没有开,……只有小螃蟹不听妈妈的话,被狼吃掉了。
还有一整套的组歌,是一出小孩的歌舞剧,是妈妈小时候在学校里表演过的。讲的是一只老麻雀领着它的小麻雀学习怎么样飞。然后老麻雀出去找食了,留下小麻雀“一个人”在窝里,时间长了肚子很饿。这时来了一个小男孩,和小麻雀做了朋友。还带她到自己家里去玩,请她吃东西,玩得很快乐。可是后来老麻雀回来找不到自己的女儿了,非常着急悲伤。幸好后来找到了。小男孩很后悔自己做的事,并想到如果自己走失了,妈妈会怎么样。他诚恳地向老麻雀道歉。小麻雀也告诉妈妈“这位小先生(所以我知道那小孩是男孩,不是女孩)”待她很好,于是大家都欢欢喜喜。小歌剧的各段采用了不同的好听的曲子。开始学飞的那一段很欢快,后来转入悲伤用的是《苏武牧羊》的调子。爸爸也会从头唱到尾(大概是跟妈妈学的)。他有时回家早,搬个小矮凳坐在小院子里,我坐在他膝盖上,他就有声有色地唱起那歌剧来。唱到“哎呀不好了,女儿不见了!”就故意唱得哭声哭调的,并做出一副苦脸。这时我就忍不住“唉、唉、唉……”地哭起来,爸爸只好赶快收起哭脸,说:“不要紧,不要紧,你再听下去后面就好了”。
住在那里,周围无人,倒是个不用担心打扰别人的好地方。可惜妈妈的小提琴没有了,不知怎么又变出了另一样东西。是一根有一排圆孔的长竹管叫做“箫”。妈妈有时静静的一个人坐在那里吹。箫吹出来的声音总是有些凄楚悲凉,如泣如诉。妈妈从小没有了母亲(听说我的嫡亲外婆很贤惠,秀丽端庄而且精于琴棋书画。可惜在妈妈三岁时她便弃世而去。),虽然身在富贵之家,但幼女失去亲娘的抑郁心境久久挥之不去,性格中难免不时流露出多愁善感的一面。
有一段时间,村子里的人都紧张起来,嚷着:“豹子来了!”说是有一头豹子,这几天几乎每天下午都来村里兜来兜去。豹子会吃村里牲畜也会吃人。果然我那时可以听到院墙外面有凄厉的“呜——呜——”的声音,大家听到这声音就像在城里听到空袭警报一样害怕,躲在家里不敢动。当然我从来没有看见它,不知道它是什么样子。但是有一个晚上我在梦中看见“豹子”了,那是一个脸上画得很可怕,并且戴着一顶后来我在京戏里看到的官帽子(乌纱帽)的人。后来想想这虽然荒唐,但是事出有因。仿佛还记得那时“有蓉”曾经带我出去看过露天土台子上演的什么戏。上面就出现过那么一个难看可怕的人。直到那时我还没有见过别的可怖的东西,所以做梦看到的“豹子”也就成了那个样子了。第二年我们又搬家后,爸爸妈妈带我到北碚公园去玩,才在动物园里看到了真的豹子。
流亡中的异姓大家庭
在磴子坎儿大概只住了一个夏天,然后我们有了一个比较固定的住所。那个地方叫“小磨滩”,也叫“小湾”。也许这两个地名定义的范围不同,一个是村名,一个是乡名。一条水流清澈的河,两边坡上都聚集着一些房子,特别是临河的房子,都是在向着河的那一边用粗竹子撑起的吊脚楼。有一座平直的石板桥把两岸的屋群连成一个村落,其中好像也杂有店铺。那里没有陡峻的地势,但在桥附近总可听到哗哗的水声。那座石桥为什么是平的而不是拱的呢?很可能它既是过河桥也是拦水闸,所以有水声。而且在桥的下游不远处左岸就有一架高大的、竹木构成的水轮车,被水冲着不停地转,推动水轮边小屋里的石磨。这个村子之所以叫小磨滩大概就是得名于此。听说还有一个地方叫“大磨滩”,但我没有去过。
我们不住在河畔村子里,而是住在左岸离村子大约半里多远的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的公务员临时宿舍里。那是一所简单的平房。中间是一个堂屋(也可以叫客厅、饭厅),两边靠后各有一个大房间,前面又各有一小房间。我们一家三口住在右边大间里。对面大间是一家姓牟的,有四口人。牟伯伯年岁最大,总有四十开外了。在这里他的地位也最高(是个什么“长”),他整个样子酷似从照片和画像上看到的蒋委员长:剃了蒋的“新生活”头;留着黑黑的小胡子;平时多半穿讲究的长衫;春秋出门戴毡帽,冬天戴的毛皮暖帽,套上呢大衣甚至黑大氅,提一根粗手杖——活活一个“蒋委员长”。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本来长得有点像,愈发故意模仿。总之那时就有个传说:有一次他是下飞机还是走到一个什么重要地方,两旁站着的士兵马上叫“立正!”,站得笔挺地对他行举手礼,真的把他当成蒋委员长了。
他的太太牟伯母和妈妈差不多年龄。当时懵懂,几年之后在重庆妈妈收到她寄来的信和小照,才觉得这个牟伯母很俊,颇有风韵。他们有两个女儿,大的叫曼梅,比我小一岁,剪的“童话”头。她妹妹叫小玉,刚会走路。后来我们常常一起玩“扮家家”,我做爸爸,曼梅做妈妈,小玉做女儿。记得有一次我们学大人一样商量着请谁和谁来做客(这时周围邻居有几个小朋友)。可是小玉老是不安分,一点不听指挥,还要哭。我们终于烦死了,叫来她“外婆”(牟伯母)把她抱开去,再也不理她了。
我家前面那个小间住着一个中年人,他叫周曾祚。听大家说他是个“工程师”,就是说人家照着他画的图来造房子。司法行政部为甚么也有“工程师”?(那时说的“工程师”是狭义的,专门指设计造房子的工程师)到我长大后听爸爸说起那时他是设计建造牢房的。他是个有学问的人,年龄比我爸爸大一些,也是上海人,和爸爸很要好。细眼长脸稍微有点黑,上牙有点曝。整个看着却给人以和善憨厚的感觉。他通常穿一件朴素的长衫,偶尔也穿西装。听说她的太太和孩子仍住在上海或南京,没有到重庆来,所以他独自在那里住一个小间,里面有一个单人床和一个书桌。渐渐地我和他成了好朋友,他的小房间也成了我经常去串门的地方。一是因为他脾气好,我很喜欢。再就是他会画画,画一些漂亮的涂了颜色的房子,说是打仗胜利以后回南京我们大家就住这些房子。他激起了我最早的一个志愿,就是长大了也要当工程师,而且我开始喜欢画画。
但是我喜欢他,最主要的是他能满足我“打破沙锅问到底”的癖好。他懂得不少科学知识,可以回答我当时能够提出的种种问题。例如他告诉我不是太阳绕地球转而是地球绕太阳转。他拿一顶帽子和一个皮球比划着对我解释月亮怎么反射太阳的光,并且为什么我们看到的月亮会变圆、变半圆、变月牙。还说到行星和太阳系,太阳比月亮远,有几个行星比太阳更远。我问他:“再远一些呢?”他说还有,我们看见的满天星星都是很远很远的像地球或太阳那样的东西。“又远一些呢?”,“还有,但是眼睛看不见了”。于是有一天晚上醒来以后,我想到这个问题睡不着了。那么在我们外面到底有多大呢?不管远到哪里,总是还有“外面”。外面就算没有东西也还有空着的地方,那么就是说在我们外面不管多远也不会有“边”?!想到这里有点害怕起来,因为这和我平时看习惯了的一切太不一样。还有,以前、以前、以前,有没有开头呢?开头以前又是什么?以后、以后、以后,有没有完结呢?完结了以后又是什么?我第一次对这些万世难解的根本问题产生了恐怖感。可我再没有和大人去讨论过。只是有一天早晨醒来,我急着把爸爸妈妈蹬醒(记得那时我已经没有自己单独的行军床,房里只支了一张大床,我睡在爸爸妈妈脚跟头)问出一个比较实在一点的问题:“地球一直在空中飞着,会不会有一天它碎了、散开了?”。这又成了一个笑话,妈妈还因此给我讲了一个“杞人忧天”成语故事。
牟家前面的那一小间好像没有固定的人住。曾经短时间住在那里的有时是“七姑姑”有时是“八姑姑”。大概是早在我们搬到这里来以前,爸爸他们机关里的一些同事结成了兄弟姐妹(也许只是好玩,不过在战乱逃亡时期可能也有互相照应患难与共的意思)。牟伯伯就是老大;周伯伯是老五。七姑姑就是老七,她姓梁,是北京人,说话声音很好听。脸是“田”字形的,有一对酒窝,总是带着娴雅的微笑。后来回想有点像电影明星胡蝶那个样子。八姑姑姓孙,是福建人,说话快、朗爽,有一双漂亮的眼睛。其它的老二、老三、老四、老六、老九都不住在这个屋里。他们可能也来过,但因为见得少,我对他们没有留下什么印象。
有时这屋里很是热闹。晚上请了一些住在别处的同事来,吃饭、包饺子、谈天。除牟伯伯周伯伯大一些外,其它都是三十上下的年轻人。有时还拼起一张长桌子,大家围着坐,开游艺晚会,玩各种游戏,夹杂着个人表演。唱歌的、清唱京戏的、奏乐器的、讲笑话的等等。记不清是谁站起来唱了一首“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唱得悲嘁动情,有人掏手帕擦眼泪了。后来在不只一部电影里看到这样的情景,我小时候见过,所以看到电影里这情景觉得格外真切。这里面没有一个是四川本地人,都是逃难来这里的,这时都不知道“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大人们这些年月里的复杂情思我当然是无从知觉,在我那里一切都是新奇快乐的。
中秋节那个晚上也有一次聚会。牟伯母和妈妈做了几个很大的蒸鸡蛋糕,大家还用各种颜色的纸剪成不同形状的“盘子”,特别是圆的象征中秋月亮。这些“盘子”都用来放鸡蛋糕(大概那里买不到后来我才知道的月饼)。上桌子之前大家还要抽签定身份排座次。我记得爸爸抽到“马夫”,所以不许他上桌子,叫他拿了坐到一边去吃。那次当然也有游艺节目。
从堂屋前门出去,是用竹篱笆围起来的一个小院子,右边高些,左边低些。院子里栽了几棵树,还种了点花,但是都是新栽的,还没有长好。堂屋后边靠右侧也有个小门,出去也有个窄一些的院子。后面有两间小草屋,一间堆柴草,另一间是厨房。那房子的顶是茅草盖的,有一次妈妈和牟伯母在厨房里面炒菜,大概灶底下的火烧得太大,锅里的菜油被烧着了。两个女人慌了手脚,牟伯母的胆子比妈妈大,她赶紧把筲箕里的菜倒进锅去,想把火压住。不料那火反而一下窜得更高,把草屋顶烧着了。后来还是附近一个农夫挑一担水来,才把火扑灭了。
我和曼梅不是在屋里就是在这前后小院里玩。我们这个房子的右边隔几丈远还有一所房子,里面有一个比我大一些的男孩,有时候也和我一起玩。他也是一个“贺哥哥”,也姓贺。我们攀谈起来,他问:“你几岁了?”,“我五岁,你几岁?”,“我六岁,比你大”。后来过了不记得多少时候,站在他家门口(我记得他家房子建在一个土台子上,所以门口有几级石阶)又谈起这个话。我还是五岁,可是他说:“我现在七岁了”。我回去问妈妈,为什么贺哥哥六岁变成七岁了,我还是五岁。她说:“你再过半年也要六岁了”。这是我们快要离开那里的时候的事,但我感觉我们在那里呆的时间很长。
更远处似乎零零落落还有别的房子。有时不知哪儿来的几个男孩、女孩聚到我们前院、后院篱笆门口来和我们一起玩。记得有一次,一个比我大些的女孩子搂着我的肩膀,摆着“脑壳”很得意地对大家宣布:“二天(四川话”以后“的意思)长大了我要和他结婚的!”显然对此我还不知道怎么发表意见。除了这句话,这个宣布和我“订婚”的女孩是个什么样子,姓什么叫什么我全不记得了,很可能那时就没有知道过她叫什么。
大人们隔些日子就要到远些的地方去买吃的用的东西,叫做“赶场”。常常听他们说起的一个地方叫“歇马场”,还有一个叫“兴隆场”。“歇马场”好像更有名气。“场”就是乡镇上定期的集贸市场,我都只听过,没有去过。
(待续)
来源:《青春·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