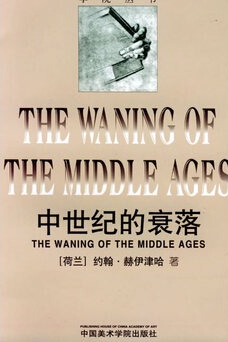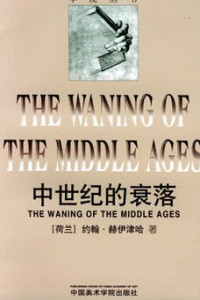最近读到《中世纪的衰落》的汉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10月版),其作者为20世纪荷兰人约翰·赫伊津哈,他被誉为欧洲文化史大师。
约翰·赫伊津哈认为,中世纪末期(14、15世纪),法兰西和尼德兰人的宗教生活受两个因素的支配,即“极端饱和的宗教气氛”和显著的“以形象表达思想的倾向”。具体表现为:“无论多么微不足道的一件事或一个举动,都常常与基督教和‘拯救’有瓜葛”;“每一种思想都寻求以形象来表达自身”。
“极端饱和”意味着宗教生活不能再沿着原来的方向发展了;追求以可见的形式表达思想终究免不了走向形式主义。于是,社会中出现了“狂热的虔敬与冷漠的嘲讽”之间“强烈地对峙”。这种对峙局面和紧接着的文艺复兴、宗教革命、理性启蒙有着时空上的关联。从这层意义上来看,欧洲人由中世纪走进近代社会,就是从冷嘲热讽上帝及其代理人开始的,或者说,民智的开启正是始于渎神。
先看看那些虔敬的举动。亨利·苏索是一位高尚的神学家,他出于对圣母玛丽亚的崇敬而随时随地向妇女致意,有一次,他为了给女乞丐让路而掉进水坑;在餐桌上,吃一个苹果的时候也要本着三位一体的名义,先吃掉四分之三,剩下的四分之一则再以“圣母给他羸弱的儿子耶稣一个苹果吃时的那种慈爱”,才将它连着皮一起吃了,因为孩子们吃苹果是不削皮的;圣诞节过后的一段时间,他不再以苹果佐餐,因为耶稣刚诞生不久,还不能吃苹果;他喝汤时也要分成五口,因为基督身上有五处伤口;而最后一口还得分两次入口,因为血与水是从基督身体的一侧流出的。
有一位王侯在朝圣之旅上赤足在大雪中行走,拥戴他的人们听闻此事,即以稻草、毛毡铺路,但他刻意绕道而行,以致伤脚,数周不能行走。
卢森堡的彼得,体弱多病,自幼就完全献身苦修,当他兄弟笑时,他会严厉申斥,因为福音书告诉我们,主曾哭泣却未曾笑过。
还有更夸张的举动,圣吉勒祈求上帝不要让他的箭伤痊愈,以考验他的承受能力;圣徒们总是要在日常的食物中拌入灰烬,故意睡在妇人身边以考验自身的坚贞。
这些例子,或许对于实践者个人来说是神圣的,“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则蕴含着严重的危险”。因为宗教对生活中所有关系的渗透,意味着生活的自然平静将受到扰攘。例如,有许多信徒因狂热盲信圣母“童真受孕”的教条,培养出一种对性欲厌恶的情感。这些人不仅反感那些曾经结过婚的圣徒、否定有私通关系的教士施行圣礼的效用,而且企图以童真作为原则要求教会和社会生活,这就触犯到俗世的利益。
“十四世纪末,大量的渎神现象在世人中间流布”。一位荷兰民间布道者,以拟人的形式,把基督比作酒徒;作家们将基督比作“无餍的贪食者”;将圣餐比作烤羊肉:“在火上烤,好好烘培,别烤焦或烤着了。就好比东方的羊羔在两堆炭火之间烘烤一样,高贵的耶稣也是这样在受难日被置于受难十字架上,被缚于两堆火之间,慷慨死去,带着他对我们心灵和救赎的热心仁爱——他确实是被慢慢烘烤着来救助我们的”。一个心智平庸的人也有这样的思考:耶稣希望玛丽亚应该与那个正直的老头(约瑟)结婚,因为耶稣希望自己是婚生的而非私生子,这样便可以符合法律,且免去了不少闲言碎语;年青人甚至公开说出,他们之所以经常去教堂,是因为能在那里看一眼那“鲜艳如初绽的玫瑰”的美丽人儿;中年男女经常离家去朝圣,“乃出于娱乐”,或可暂离配偶捕获艳遇。而当这些行为被劝诫时,他们就举出那些有同样行为并视之泰然的贵族和教士来替自己辩解。的确,“渎神一直是贵族的一种大胆消遣”。
一位垂危的船长对他的同伴坦承他深深地触怒了上帝:“我不能够相信三位一体的任何文字,或者诸如上帝的儿子竟然屈尊进入到一个凡间女人的肉体中这类说法。我要说,我也相信我们死后没有灵魂……从有自我意识起,我就固持这种见解,我也将固执到底”;巴黎市长也不相信祭坛的神圣并对之加以嘲笑,他从不过复活节,也不做忏悔;有一位修道院的院长,在他被选举就任院长的当天,还得知其姘妇生了一个儿子,便忘乎所以地说:“上帝保佑我,今天,我当了两次父亲。
文艺复兴时期的领军人物如伊拉斯谟、拉伯雷都加入到嘲讽圣徒的行列,而圣徒正是宗教“以形象表达思想”的生动例证。“在大众的眼中,圣徒是活着的,像诸神一样”;“大量有生命力的信仰被具体化到圣徒崇拜中”。圣徒成为当时宗教的极其真切和亲近的人物,他们身着时尚的服饰(文艺复兴以后,他们才保持统一的古典着装),以“救世主”的身份,频繁穿梭在“瘟疫缠身、半死不活的病人和香客中间”;“圣徒亲切的身影能令人产生一种类似于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看到指路警察一样的慰藉”。这是出于虔敬的一面,而嘲讽的一面则把他们视为带来恐怖的恶魔。有一则乞丐玩笑是这样写的:“一个乞丐跌倒在地,嘴里满是散发恶臭的唾沫,抱怨着造成他潦倒如此的圣约翰。另外几个则浑身溃烂,那是因为隐士圣弗亚克勤的错。噢,你,达米安不让他们喝水,圣安东尼烧了他们的关节,而圣皮佑斯又使他们跛足、瘫痪”。在这两极的对峙中,人们自然会想到,圣徒们既然有能力消除恶魔,那么他们为什么不会是恶魔的制造者呢?
对教士的公开轻视,“是贯穿中世纪的一股潜流”,原因非常简单,“高级教士的世俗化和低层教士的腐败”,尤其是行乞教士阶层首当其冲地受到蔑视。人们憎恨那些挥霍无度、大吃大喝的僧侣教士;人们乐于听到对于教士恶行的控告。以致于“一个痛斥牧师状况的布道者肯定会博得喝彩”。在冗长乏味的布道现场,每当会众们昏昏欲睡时,布道者就会以抨击教士的腐败来打起他们的精神,“每个人立刻变得专注而且可爱起来”。
老实说,《圣经》的教条中也存在招惹想象的隐患,比如童真受孕、基督复活、人在听弥撒的那天是不会眼瞎或突然中风的等等,一旦人们与上帝的精神联系失败了,它就成为亵渎话题。而引致人们与上帝精神失联的正是上帝的代理人,他们或因为太过“亲近”而缺失了神秘性,或行为的不检点而授人以柄。当过多年忏悔牧师的热尔松对渎神的心理学本质了如指掌,他认为那些渎神的人是真诚的,即使他们此前曾立誓信奉上帝,但决不是立伪誓的人,“因为他们无意于立誓”,是被逼出来的;而且他还发现,“那些本性纯洁、简单的年轻人总是不可抑制地试图亵渎或摒弃上帝”,因为他们还不具备足够的信仰的经验。
中世纪末期,个人主义已经萌芽。人们之所以嘲弄别人的虔诚,在于显示自己是一个思想自由的人。人们普遍认为圣者都是伪君子,只因厌倦了过分负荷的宗教文化(思想的形象化),腻烦了那些絮絮叨叨对于信仰的急切呼吁。而当时的有识之士,他们只是觉得民众的虔信过于旺盛会伤及教会,热尔松认为:“再没有比无知虔信更危险的事了”。而渎神的言行恰恰可以矫正这种风气,只要它不导致道德和教义上某种革命性变化,教会就是可以容忍的。或许正是此一时期的“渎神”之举,成为其后的200年里“侮辱作为哲学辩论中的一种修辞方式是可以接受的(雅克·巴尔赞语)”欧洲文化风气之滥觞。
吴长青2015-5-19
来源: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