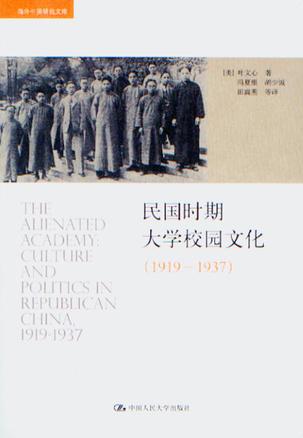一个所谓好的体制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允许人的自由。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而个人的独创能力实际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如果大家都只会念经、背经,开口都说一样的话,那是不可能出任何成果的。
“我以为,一个所谓好的体制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允许人的自由。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而个人的独创能力实际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如果大家都只会念经、背经,开口都说一样的话,那是不可能出任何成果的。”
这是著名学者何兆武在口述史《上学记》谈到民国时期西南联大为何能在战争年代,创造出人文和科学的奇迹时语重心长地概括的一句话。近些年来,民国范儿、民国热成为一种风靡出版界和读书界的热潮,世人对现实文化状况的忧虑和不满,都被寄托在对于民国文化浓墨重彩的怀旧之中。而1949年前,国立、省立等公立大学,教会大学和私立大学三足鼎立的高等教育体制,形成的多元学术文化和卓越的学术成就,更是成为今人念兹在兹的话题。最近,研究民国文化和教育史的权威学者叶文心访问上海,而其1990年由哈佛大学亚洲中心出版的以民国时期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圣约翰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大学等高校与政治、社会、文化之关系为研究课题的博士论文The Alienated Academy: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Republican China,1919-1937(《疏离的学院:中华民国的文化与政治1919-1937》),去年翻译成中文出版(题名为《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我趁机就民国时期的大学、文化与青年学生心态等话题专访了她。
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叶文心,是伯克利加州大学东亚研究院首位亚裔院长,也是创院30多年来的首位女性院长。其自身家族史也颇不平凡:外曾祖父是近代思想家严复,父亲是“中央社”首任台湾特派员叶明勋,母亲是小说家华严(严停云)。三十多年前,叶文心选择以民国大学史为题做博士论文研究,也是因为父母的缘故,“我对民国时期校园文化和政治的模糊意念,在某些方面来自童年时期母亲教我唱的歌。我父母都成长于民国时期的教会大学,父亲是福建协和大学的,母亲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我对他们这一代人从哪儿来这个问题很好奇,总想搞明白是怎么回事。”可以说,叶文心的民国大学史研究,除了学术的公义之外,也是传承家族记忆的一种独特方式。
正如有评论者指出的那样,这虽然是一本“老书”,但在此时此刻的大陆出版中译本,却正逢其时,可以为当下的民国文化热和民国大学热增添来自历史学的厚实分量。在专访结束时,叶文心优雅而专注地谈及其下一步的研究计划,是研究晚清以后这一百年来的中国教育史,在政治文化与经济社会的脉络里来呈现中国新式教育的百年历程。
对民国的怀旧是一种反思的态度
田波澜:近些年,在中国大陆知识界出版了一批有关民国时期大学的回忆录、口述史和小说,比如何兆武《上学记》、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鹿桥《未央歌》等都广受读者欢迎,关于西南联大的系列纪录片也受到年轻一代大学生的好评,作为一位研究民国大学史和文化史的权威,你如何评价这种对民国大学的怀旧热潮?
叶文心:这里头有几个反应,第一个是好奇,为什么1949以前的大学和1949以后的大学有相当的不同?大家喜欢看这样的书,是因为想要知道曾经在这个土地发生的事。第二个是寻找解释,想要知道今天的中国跟那个时代的中国,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并探寻过去一些有趣的事情或者情怀为何在今天的生活里面消失了,这是一种反思的态度。
第三,从历史学者的视角来看,民国时期,未必是大家日子都过得很好的时期。现在这种怀旧浪潮只是把焦点放在当年历史现象的某些层面,可是关注一些层面,并不表示能完全捕捉到那个时代的困难与困惑。
总的说来,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挑战和困惑,需要做出不同的选择。我们现在看前人曾经走过的路,之所以能把它当作怀旧的题材来看,部分原因也就是那个时代曾是问题的问题,今天已经解决了,不觉得它们是问题。而今天也许发生了其他的问题,所以大家忽然对前朝往事产生了兴趣。
田波澜:在中国大陆比较有影响力的几部研究民国大学史的著作都是美国学者所撰写,除了你的《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1919-1937)》外,还有魏定熙教授所写的《北京大学与中国政治文化》,以及易社强教授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相对于这些学术分量很高的著作,大陆很多名校也不乏校史著作,但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力,你觉得是哪些因素影响了大陆学者对民国大学史的书写水准?
叶文心:我想关键在于,这是一种文本性质的区别。每一个学校都书写它本身的校史,美国学校也不例外。可是校史不等于涵盖高等教育史的近现代史,或者说透过高等教育以及大学的经历让大家来阐释近现代中国历史的脉络。这两种文本在基本性质和书写的指向目标性上,有着基本的差别。你所提的这几本书,虽说魏定熙着重北京大学的经验,易社强着重西南联大,可是他们的目的是透过书写北京大学、西南联大(和我所关注的圣约翰大学)等民国大学史的一个面向来展示更宽广的一些问题,比如知识人的风貌。这些美国学者的作品主要的意涵,是透过一群大学里的知识人的历史经验来呈现中国近现代史的某些侧面。
其实中国近百年来的教育史,本身是包含在学术史、知识史、思想史、文化史等脉络里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这样的历史著作是很不容易写的,现在有些人往这方面努力,可是什么时候写得出来还不一定,因为这个工程比较大。老实说我正收集材料想写这样一本书,在我的第一本书的基础上把它扩大出来,让它照应的面更广一点,关注的时段更长一点。大致的意思是透过百年中国教育制度的变化或者说是高等教育的变化来看中国的近现代史,同时也可以反过来,从中国近现代史的变化来看百年高等教育的内涵以及变化等等,这两者是相互依存的关系。
党化教育:从正面转向负面
田波澜:你这册关于民国大学的研究,其实不仅仅是一种文化史的研究,也注意到了大学与政治力量的关系,有一些篇幅讨论国民政府试图控制大学的党化教育。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对大学推行党化教育的根源和表现形式是什么?成效如何?
叶文心:党化教育这个口号,是国民政府在广州的时候提出来的。在那之前的国民党是一盘散沙的国民党,直到1923到1924年之间,孙中山在广州演讲三民主义,国民党才有所谓的成文的主义。党化教育的意义一方面是要把三民主义作为全党一致并为大家熟知的党的宗旨和理论,另外更关键的是要把党作为一个组织建立起来。
在黄埔建军之后,即在军队里建立政治指导员制度,要把党的思想灌注到军队里面。国民党也希望把党化思想推行到大学校园里,所以创办了当时的广州大学(以后成为中山大学),希望广州大学跟上海的资产阶级大学不一样,大学生都抱持三民主义的理想,是为国为民有纪律的大学生,而不是像上海圣约翰大学那般,学生只顾自己社会地位的上升或者生活上的享乐,把学位当做社会地位的装饰品。所以它的党化在三个领域同时进行,先把国民党党内党化,然后把军队党化,再把大学党化。这是1927年国民党执政以前的情况。
北伐革命之后,国民党进入到江浙地区,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势力随之延伸到北方主要的大学校园之内。国民政府进行党化教育,就遭遇到原有校园文化的抗拒并引发冲突。透过教育部的行政手段跟资源的控制,国民政府半强制性地推行了党化教育,这些措施大约从1928年开始引起知识阶层的反弹。当时就有人提出人权问题,说“连上帝说的话都可以怀疑,难道孙中山或者三民主义是不可以怀疑的吗?”或者“对党义和国民党国策的辩论,在大学校园里如果不去进行的话,那岂不是一党专政了吗?”
所以在北伐之前和北伐之后,党化及其作用,在校园里的意义截然不同。国民党在广州时期如果不推行党化的话,北伐时期它的军队跟学生,在思想上就不能统一,在组织和动员上也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可是它进入江浙以及北方——1927年以前的文化重镇之后,它以一党专政或者一党独大的精神来压制多元化的思想潮流时,就立刻引起抗争。所以自1928年起,教育部开始以政府的力量强制要求校园进行党化教育,就立刻使党化教育在知识界成为带有负面意义的一个名词,甚至成为抗争的对象。在还没有当权之前,党化可以统一思想、加强组织纪律、提升战斗力,是有助于革命的。可是一旦从一个革命党变成执政党,仍然继续推行党化教育,党化就变成了钳制自由思想、限制舆论空间的一个统治工具。所以,在位与不在位,是革命时期还是当政时期,这个区别其实对于“党化”的实际意义是很大的。
“二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化里,上海大学的作用非常大”
田波澜:你在书中专门有一章讨论民国时期上海最著名的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认为它是资产阶级阶层再生产的最重要的管道,而且依托于上海这个最具有国际性和现代感的大都会,这些大学成功地实现了儒家中国的知识范式的现代转型,通过科学知识、职业技能、良好语言等来获取财富,开始成为一种新的社会职业伦理。这所大学对民国上海上流社会文化的形成产生了哪些影响?而像圣约翰大学这样的教会大学最后的命运如何?
叶文心:圣约翰大学在上海地区大概是当时西化的资产阶层最主要的一个培育中心,也是他们建构社会网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制。它不只是一所大学,它和教会有关系,同时它的学生除了上学之外,也进行社会活动。透过校园里的学生生活以及联谊生活,学生跟学生之间也有社交生活,所以总体说来,它除了一种知识上的传承或者说是专业知识的训练之外,同时还建构了社会性的人脉跟网络,帮助开发了一些社会意识或者是社会服务。
这些教会大学的命运,大概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抗日战争发生后,沿海都被日军占领,很多沿海的资产阶层迁入内陆,很多学校都搬进租界,像福建或浙江的教会大学,不能搬到租界,有的就搬到山里去。对于教会学校来说,或因有英美背景而被日本人当作敌对势力看待,或因华裔的资产向内地或海外迁移,在资金来源上大大减缩,因此受到很大的打击。1945年以后,国民政府虽然回来了,但是经济没有恢复,对教会大学来说仍然是不能恢复战前的盛况。第三个时期是1949年以后,很多教会大学的资产跟其他学校合并,很多学校停办或者资产被冻结、或者是被拆散,在院系调整的时候被其他学校吸收掉。圣约翰大学在1949到1952年被拆散并且并入上海多所高校,按照并入院系数量排序,依次是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上海第二医学院,其校址为华东政法大学所用。
田波澜:非常有趣的是,你既讨论了培养资产阶级的上海圣约翰大学等教会和私立大学,也专门讨论了培养和吸纳革命者(如恽代英、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张太雷、彭述之、李季、李达等)的上海大学。对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革命文化甚至20世纪中国革命来说,上海大学主要扮演了什么角色?
叶文心:上海大学非常有趣,值得进一步研究。将上海大学和圣约翰大学做一个对比的话,我们可以看出这两种大学的不同。圣约翰大学是先办的大学,先盖了房子、有了教授、设置了课程,然后才招生,再在这个基础上逐渐扩充,所以是学校培养学生、学校建制学程,学生是交了学费来上课的,这基本上是圣约翰大学的办学模式。
上海大学正好相反,它是先有一批愿意做教授以及愿意做学生的人集结在一块,由他们主导建立的一个校园,所以房子是他们找的,经费是他们筹措的,课程是他们根据自己的学识、认为什么样的课程最有助于解决当时民族国家和社会政治的问题而创设的。所以上海大学从一开始名声最响亮的是社会学系,其包含的内涵五花八门,不过最基本的意图就是要跟社会发生关系,那个社会就是当时的工厂、工人、工厂里的种种社会现象、外地人进入上海遭遇的种种困难等。他们是先有问题,以此为核心来推动学校的成立。他们创立的学校,房子不怎么样,住得也不怎么样,得到学位以后能否找到一份工作也说不定,来上学的人都是仰慕这几位思想家或者是文学家的大名而来,从这个意义来看,上海大学的创校和圣约翰大学创校的动力是完全相反的。
很有趣的是,通常从有关上海大学的回忆录,我们看到的都是社会系的活动。其实上海大学还有一个英文系,以及搞会计统计之类的系,这要看国民政府教育部的档案才能看得出来。为什么英文系、会计统计之类的系也可以成立,而且招的学生也不少,但在上海大学的校史里头却默默无闻?原因很简单,通过这些学科他们也招收一些希望学得实用知识以后以此谋求职业而不是寄情革命的人,这些系收取不菲的学费,间接支持了社会系的革命活动。因为上海大学认识到,它是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一个组织,除了提倡社会革命之外,它不能不做别的事,所以开设了一些有实用价值的学科,招收了不少学生并收取了不少的学费,用以支持革命活动。
在二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化里,上海大学的作用非常大。最主要是因为它在传媒里头有极高的可见度。它和圣约翰大学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类型的传媒上出现。圣约翰大学在当时的报章以及期刊上经常出现,且多是慈善、义卖、跳舞等资产阶级上层社会的活动。上海大学也在当时的报章和期刊上经常出现,可是它出现的渠道不一样,它出现在自己办的革命刊物里,这些刊物本身是它的活动的宣传品。如果它进入到譬如上海工部局的档案里的话,就往往跟罢工、罢市或者警察想干预的活动有关,这就是当时上海大学直接或间接让公众知道它的名声的一种机会。尤其是它的社会系,瞿秋白等人所组织的一些罢工、罢市或者在工厂里面进行的工人识字班、夜校等活动,在群众中间有高度的影响力。
田波澜:很多读者对于你在书中描述的学生群体因各种思潮、学费高昂、生活贫苦而形成的迷惘和苦闷情绪特别感兴趣,这种叙述其实也在某种程度上平衡了对民国大学生活过于浪漫主义的历史再现。在你看来,这种后五四时期的充满“异乡感”(也即是没有归属感)的校园思潮,对于当时知识青年的拥抱革命产生了何种影响?
叶文心:国民政府当政以后,从1932年到1937年这5年之内,在经济上受到全球经济不景气影响,最严重的是1933和1934年,1935、1936年,中国跟日本在华北的关系进一步恶化,1937年就开始全面打仗了。所以在1932到1937年之间,这些上海地区的教会大学,虽然培养出一批资产阶级的子女,拿着大学的文凭,可是他们找不到白领的工作。尤其毕业生中大多是非理工科的学生,他们所修习的科目多是商科跟经济,却正好遇上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更是找不到新式企业中的白领工作。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教训这些学生说,你们之所以找不到工作,是因为你们在大学里习惯了西方式资产阶级的生活,如果你们愿意放下穿长衫的身段,加入短衫人实际动手的行列,或者愿意到内地去,一定可以找得到工作。
教育部经常以这样的口气来教训1930年代上海城市里的大学生。大学生群体中也许有的人的生活是浮华的,可是在内地经济萧条、失业剧增和农村凋零的背景之下,能够上大学的人,总算是交得起学费的人,所以一定会被说成是生活奢靡的。国民政府对教会学校“奢靡”的这种批评,跟国民政府当时在经济上所遭遇到的不景气大有关系。他们想解决的问题之一,是有一大帮手里拿到大学文凭却不能够就业的青年人,这些人都是精英出身,这些人都曾积极投入国民政府的中国现代化图景,而这群人面临失业,对整个国民政府体系有着强烈的不满。
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固然是拥抱革命,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在1930年代尤其是在大学所处的城市之中是处于低潮时期。中共已经从江西苏维埃撤出,红军开始长征,辗转向陕甘宁地区行进。上海和北京城里的知识青年如果想要寻找由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话,这个力量在1930年代的都市里头还处于低潮期。他们直接投奔延安或者革命根据地,是必须要到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才能够发生的。当时国民政府在城市里的统治力量是很强大的,那个时候的知识青年,即便有倾向社会主义的愿望,可实践起来也很困难。但虽然这样,1930年代还是有不少人组织读书会,自己摸索社会主义的道路,不过这一帮人跟中国共产党的党组织没有关系,他们要到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才逐渐找到组织。
“消费主义文化,对当时上海大学生的影响应该是不小”
田波澜:你在书中也写到上海一些私立大学的学生,在教育部的报告里呈现出的完全是消费主义者的形象:“这些大学生们从不关心任何严肃的事情。他们过着娱乐休闲的生活。他们的衣着昂贵,饮食考究。他们消费进口商品。他们经常出入影院和舞厅。他们出门坐着雪佛兰汽车。他们既不关心国家大事,也不关心他们的学业。”你如何看待消费主义文化对大学精英文化的影响?
叶文心:民国时期的大学精英,并不是都集中在上海,南京和北京等其他一些城市也有大学生。在1919年到1937年之间,全国将近四分之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是在这三个城市接受教育的。但是总的说来,北京、上海、南京是三座不同的城市,有三种不同的消费形态。国民政府教育部最不满意的是上海。它对在它政府大门口边上的南京中央大学的学生群体的消费形态,批评意见还不算是很大。北京大学生是另外一种消费文化形态,也不是国民政府批评的重点。它批评的重点是海派的消费文化,这里面大约也包含了一些意识形态的因素,比如对于所谓海派、买办文化和帝国主义的不满。
上海在民国时期除了是一个教育中心之外,中国的出版事业、电影事业、百货店、广告业等以市场取向为主导、以商业性诉求为主的文化产业也基本上集中在上海。国民政府最不满意的是这些以西化为取向、以牟利为目的的文化出版业。跟这些相对应甚至对抗的则是由国民政府主导的、受宣传部门指挥的非赢利性的文化事业。
这种消费主义文化,对当时上海大学生的影响应该是不小。多半大学生爱看西洋电影,当然国产片在上海也有相当市场,不过像圣约翰的大学生多半看进口的西洋电影。多半的资产阶层在四大百货公司进行消费,但是这未必表示说每一个大学生都在四大百货公司进行消费,只是说在这些公司消费是经济地位的一种象征或符号。多半的大学生,包括圣约翰大学的大学生是不会去四大百货公司的,比如邹韬奋也是圣约翰大学的学生,他没有相应的消费能力,不到四大百货公司去进行消费,可是在一般人的眼里,他也难免被目为带有一些西化的生活习惯。所以并不是说每一个圣约翰大学的学生都一定到四大百货公司进行消费,只是当时社会、官方和媒体形成一种刻板印象:若有大学生在四大百货公司消费,那准是圣约翰大学的学生,或者说准是教会大学的学生。我母亲也是圣约翰大学毕业的,我就问过她,当年去先施、永安买东西是怎么样的?她说她在圣约翰四年从来没有进过先施、永安,先施和永安是太太、少奶奶去的,不是大学女生去的。
田波澜:今天中国的北大、清华、复旦等名校都在各种压力下宣称正向着世界一流大学迈进,但学术界的丑闻不断,学术生产流于形式主义,学术人才流失严重,无论是学者群体自身,还是社会各界,对大学(包括学者专家群体)的评价似乎越来越负面化。回首半个多世纪以前的民国大学史,你觉得今天的高等教育管理部门和大学应从中吸取怎样的传统与遗产?
叶文心:民国时期的大学可以发展出多元化的门类,给学生们提供了更多选择空间。比如北京大学跟圣约翰大学是性质完全不同的学校,圣约翰大学跟中央大学的性质又完全不同。同时从区域性上来说,每一个省省会的大学都各自发挥出他们在专业上的特色,譬如当年的武汉大学跟广州的中山大学很不一样。所以对学生来说,没有法子拿一个同样的尺度一路比划下来,说北大清华一定排在前头,它不是有一个顶尖的金字塔,而是在多元多样的办学宗旨下,有更多学校可以结合本身优势跟地方特色,让学生在当时的情况之下得到素质最强的教育。所以从整个体制来看,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体制比较活络一些。
民国时期进大学也没有统一的高考,因此大学的入学标准或者大学的课程,对中学教育或者小学教育,就不至于造成从上而下一刀切的纪律或者规范,不至于说有些小孩还没有进幼儿园就已经开始考虑需要进哪个幼儿园才能进得了北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民国时期高等教育其全部的图景,对我们今天来说可以汲取的是,它提供了一个比较多元化的模式,同样都是优质教育甚至顶尖教育,但是这个顶尖的内涵可以多元多样。同时,这个顶尖的教育更可以让学生们结合个人的长处和优势,或者是他所来自的地方的需要或长处,来发挥或是接受那样的优质教育。对优质教育内涵的理解是比较有弹性的,面相是比较宽广的。
更主要的一点是,大学本科的教育内容里,职业训练的成分比较低,而人文通识的成分比较强,民国时期的教育所希望培养的是能够具有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的人,而不是一个进入到一定的岗位之后就能够很快上手、具有专业科技知识的人。就是说专业科技知识并不是不重要,可是它让大学不只是一个高层技术人员的训练班,而更是针对每一个人全面发挥的需要而提供一种更为全面的教育,公民教育、社会关怀、人文素养、社会文明都包含在内,不只是把教育或知识工具化。民国时期的大学虽然五花八门,这些学校也未必做得非常完善,可是在办校理念上,多半是朝这个方向走的,这可能是它的一个长处。
而民国时期的大学之所以能够这样,一方面它所承继的是传统中国对教育的理解,另一方面它透过教会大学也受到西方通识教育的影响。可是中国的教育从晚清以来之所以需要改革,就是因为从晚清以来大家都认识到中国的知识人必须大大地强化对自然科学和科技知识的理解,否则他们只能空谈而不能真正对国家有贡献。所以总的说来,这三块都很重要,不可偏废。
叶文心,早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后赴美深造,1984年获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1994—2000年任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现任该校历史系讲座教授暨东亚研究院院长。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文化史、社会史、上海都市文化史等方面的研究。主要著作有:The Alienated Academy: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Republican China,1919-1937 (《疏离的学院:中华民国的文化与政治,1919-1937》)、 Provincial Passages: Culture, Space,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 (《乡下人的旅行:文化、空间和中国共产主义的起源》)、 Shanghai Splendor: Economic Sentiments in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上海繁华:都会经济伦理与近代中国》)等。
来源:腾讯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