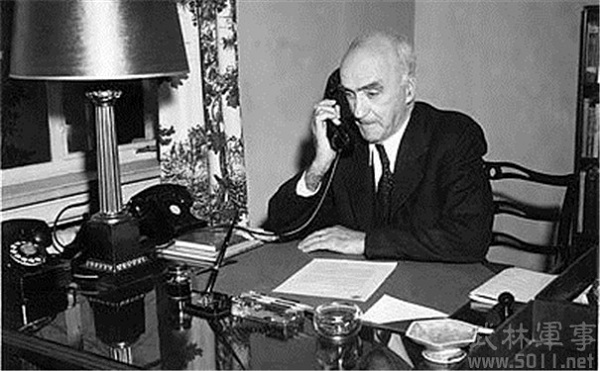(1)
司徒雷登在中国可以说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尤其是五六十岁以上的人,大约没有人不知道这个美国人的。之所以这位传教士出身的现代著名教育家的名字为全体中国人所熟悉,是因为毛泽东那篇著名的文章《别了,司徒雷登》。至于他为中国现代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则是因为司徒雷登身上的政治符号而受到屏蔽。
毛泽东这篇发表在1949年8月18日的政论文,在中共建政以后,收入了中学语文课本,跟他的《桃子该由谁摘》一样,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思想。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毛泽东的这篇文章,甚至影响了几代中国人对于美国这个国家的认识和情感。直至今天,在1949年之后出生的中国人中间所弥漫的反美情绪,也是从这篇文章开始。更甚而至于的又叫人感到可悲的,毛泽东的这篇文章,竟然影响到了司徒雷登这位深爱着中国的美国人的归葬遗愿。
一个中共领导人的文章具有那么巨大的作用,这是令人深思的。在西方,具有法律效力的契约是必须遵守的。但是毛泽东作为一个政党的领袖,他的话居然具有了比法律文本更大的约束力,影响力,而且还影响了几代人。这种口含天宪的现象,只能说明中国还是一个人治的社会,或者可以反过来说,中国人的思想依然停留在皇权社会,对于皇权依然是顶礼膜拜。
司徒雷登1876年在杭州出生,到1962年去世,八十六岁的生命涵盖了差不多一个世纪的中美关系。司徒雷登出生在一个美国传教士的家庭,他的父亲约翰?林顿?斯图尔特在1869年从普林斯顿神学院毕业后,只身来到杭州传教。为了融入下层人民的生活,学好中国语言,他租下了一家鸦片馆楼上的一间房间。三年后,具有苦行僧精神的老约翰因为过度劳累和营养不良,只能回美国短暂休养。身体复原后,不仅约翰自己回到了杭州,还带回来一个叫做玛丽?霍腾的美国姑娘,这是他的新婚妻子。
约翰在西湖边上的贫民区建造了砖木结构的两层小楼,把家安在了杭州。他在此地参与建立了教堂与学校,司徒雷登以及他的三个弟弟也是出生在这个叫做耶稣堂弄的小弄堂。在这儿,司徒雷登度过了他终生难以忘怀的童年。1887年,11岁的司徒雷登和他的弟弟被父母送回美国,为的是让兄弟们接受更好的教育。
回到美国,他与大弟戴维寄养在阿拉巴马州的的姨父母家里,进入当地的莫比尔学校学习。从中国来的司徒雷登兄弟在同学们看来是两个怪物,他们用筷子吃饭,用中文唱赞美诗,有时候还穿着中国的服装。他们对美国的语言和文化显得很无知,他们走到哪里,都会被人围观,遭到揶揄和嘲弄。这些都深深刺伤了司徒雷登兄弟的自尊。
(2)
到了十六岁,司徒雷登进入弗吉尼亚大学的潘托普斯附属中学,该校是前总统杰佛逊的旧邸,风景优美,专为世家优秀子弟所设,同学来自好几省,交往中没有阿拉巴马州穷乡僻壤的陋习之气。这儿没有人知道他的中国经历,他也绝口不再提起中国。司徒雷登慢慢的恢复了自尊,成为一个真正的美国男孩。
司徒雷登回到美国求学的十多年时间里,学习成绩十分优异。受到家庭的影响,司徒雷登在1899年23岁的时候决定进入南长老会设立在佛吉尼亚首府里斯曼的协和神学院深造。司徒雷登对于自己的人生规划,在选择作为一名教师作育英才还是听从神的召唤毕生奉献上帝,感到十分踌躇。作为一名神父就要赴召去中国,而小时候在中国受苦的记忆难以磨灭。他回忆起儿时随父母在中国布道,有时候露宿街头,发劝世文;有时候到穷乡僻壤,和愚民为伴,到处受到讥讽,甚至被侮辱。但是虔诚的宗教信仰战胜了自私之心,司徒雷登选择了做一名上帝的使者,把福音带给人类。
1901年,正是中国义和团扶清灭洋的暴乱刚刚平息,24岁的司徒雷登加入了义勇外邦布道团,这就注定了他必然会远赴这个东方之国,在这儿度过他的一生,为这个遥远的故乡奉献自己的一切。
司徒雷登所要终生为之服务的中国,正在处于迈入现代化的剧烈动荡之中。他个人的命运也一定会随着这个国家的社会演变而谱写自己的生命之曲。对于把基督教的文明输入这个有着悠久历史,却没有宗教精神的华夏民族,其中的困难司徒雷登应该是有着思想准备的。这些困难对于服膺于上帝的传教士不算什么,他们的宗教情怀所释放出来的精神力量,一定是令人惊叹的。中英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多少传教士络绎不绝,前来东土,克服千难万险,把上帝的福音带给顽冥的子民,这不是用一句文化侵略所能概括的。毋庸讳言,传教士把博爱带到了中国,其中不乏可歌可泣的事件。当然,在这片精神贫瘠的土壤上面,基督的精神能否深入其中,改变华夏民族的精神面貌,可能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这里面受着历史文化以及社会政治的影响。但是,如何来评价一百多年历史的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当然是有待讨论的,有待历史学家,思想史的专家给出令人信服的结论,而不是受到政治的影响,轻率的给以否定。
我以为,司徒雷登把在中国传播福音作为终生的职责,出发点应该是对他的出生地的国家的人民一片爱心,而不是为了用基督教来奴役中国人民。当然,文化优越的心理一定是有的,在他看来中国社会的落后,贫困,闭塞,就是没有基督的博爱精神。有了对基督的信仰,这一切都可以改变。
(3)
1904年,司徒雷登与艾玲结婚,同年12月,携艾玲返回中国。16年来,司徒雷登第一次与父母团聚。从此,司徒雷登开始了他与中国近半个世纪的不解情缘。这个美国人,从一个传教士,后来成了一个教育家,对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后来,在中国最重要的社会大变局的1946—1949的那几年中,司徒雷登做了美国驻中国的大使,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执掌中国权力的见证人。司徒雷登在出使中国这几年,奠定了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关系的格局。
如果司徒雷登仅仅是作为一个在中国传教的牧师,那么他的一生很可能就跟他的父亲一样,终老中国,或者随着共产党的执政而离开中国。这个真正热爱中国的年轻人,在传播基督精神的时候,把中国的儒家思想的“仁”,融汇在基督教的“爱”之中,提出中国基督教的本土化。他基于基督教的博爱精神,以《论语》的话“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为圭臬,以孟子的民本思想为指导,一心一意要培养中国自己的基督教领袖。
在浙江传教的时候,司徒雷登搞来一条船,称为“船房”。这个操着一口杭州土话的外国传教士,开着他的这条船,漂遍浙江的江河湖泊,城镇乡村,向广大乡民传播福音。1913年司徒雷登的父亲去世了,安葬在杭州九里山的基督教传教士的墓地。在他四十岁的时候,司徒雷登受聘于南京金陵神学院的教职。于是,他带着母亲和妻子,来到南京,开始涉足中国的教育界。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当年在义和团运动中被烧毁的北方四所教会大学的创办者决议合并为一所大学,并组成委员会,筹组新学校以及委任新学校的校长。由于司徒雷登在中国宗教界和教育界的声誉,委员会决定延聘司徒雷登为新大学的校长。美国“海外传教运动”的领袖罗伯特斯皮尔的推荐书这样说,“司徒雷登深切了解中国,在华传教人士中对中国青年最具影响力,而且才华与学养出众,思想开朗,中外人士都心仪其人”。基督教青年会国际协会副总干事布鲁克曼这样推荐司徒雷登,“司徒雷登的才具足以出掌任何教会机构。他出生在中国,此为其他同行所望尘莫及。他中文和英文都运用自如,而且深谙中国文学,可称一时无二。他的心灵也属难得的品质。我相信他举世无仇敌。在未来的大学里能调和中外,折中新旧思想的,我不作第二人想”。当时许多朋友都知道这是一个难以收拾的烂摊子,各方矛盾重重,经费十分困难,劝他别接受校长一职。开始司徒雷登也颇费踌躇,答应先北上实地了解情况再做决定。
(4)
1919年1月31日司徒雷登抵达北京。此时正值寒冬腊月,朔风刺骨。当时的校址,蜗居在北京内城东南盔甲厂一带,四周污秽不堪,难以扩展。协和大学与协和神学院的校友和同仁,就校名、校址、预科等问题激烈地争执不休。司徒雷登表示,在校名、校址、预科等问题未能解决之前,不敢接受任命。司徒雷登回到南京等候。这时有一个叫做诚敬一博士的朋友提出新大学易名为燕京大学,电告北京委员会得到认同。委员会屡屡发电催促司徒雷登北上就任,司徒雷登在提出易校址和另聘人为学校募款两项条件得到明确答复后,于是携夫人来到北京上任。
为了筹建燕京大学,司徒雷登费尽了全部的心血。那时候,可以看到一幅颇为奇怪滑稽场景,一个洋人骑着一匹毛驴,在北京四处转悠,这是司徒雷登在为学校选址;为了得到美国富豪和中国富绅的赞助,他四处奔波化缘。为了筹措办学经费,他数次往返美国,甚至一连几天陪着一个半聋的老太太聊天玩游戏,为的是她的财产遗嘱里别忘了燕京大学。他曾叹息,“每次见到乞丐,我都感到自己是属于他们一类!”凭着司徒雷登的良好的声誉和广泛的人际关系,他从美国带回了250万美元的办学资助。这对于当时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
燕京大学新校园终于建成了。这是一座近代中国规模最大,环境最优美的校园。这座中西合璧的现代化大学,倾注了司徒雷登的心血。为了把燕京大学办成中国一流的大学,他努力把名不见经传的燕大跟哈佛、牛津、普林斯顿这样的世界一流大学合作,并且延聘国内一流学者任教,并与外籍教师同等待遇。一时燕大名师云集,很快就名声大噪,跻身于国内名牌大学之列。
司徒雷登作为燕大之父,他对中国教育最重要的贡献是把燕大这样一所教会大学办成了一所世俗的普通大学,为燕大注入了民主之魂。他大胆提出要“使燕大彻底中国化”。他说,“燕大必须是一所经得起任何考验的、真正意义上的大学,至于信仰什么,这完全是个人的私事。”他宣布,不必像以前那样,把宗教作为必修课,甚至也不必一定要做礼拜。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作为校长,十分支持和理解学生运动。他说,中国的学生运动是全世界民主运动的一环,学生是中国的希望。“他到校就任第一天,学校空无一人,学生都去参加示威游行反对巴黎和会。燕大学生是五四运动主要参与者,被捕学生数人,司徒雷登出面请北洋总统徐世昌予以释放,并接见释放的学生,与学生友好交谈。在一二九运动中,司徒雷登带领学生走上街头,走在队伍最前面,高喊反日口号。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司徒雷登被日军拘捕关押,直至日本宣布投降后才获得释放。
(5)
司徒雷登为中国的近代教育做出了巨大的开创性贡献。对于他的贡献,多数的中国人并不了解。这是因为中国的官方把事实屏蔽了,官方对事实进行了扭曲。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只会去宣传对中共给以帮助的外国人,比如白求恩。毛泽东的一篇《纪念白求恩》,让全中国的中国人只知白求恩,而不知陈纳德等等为中国抗战牺牲的美国飞虎队飞行员。实际上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里,在中国的民族解放的战争里,许多西方人士给与了巨大的帮助,他们的高尚无私的博爱情怀,应该为我们所了解和铭记。
假如司徒雷登只是作为一个教育家而终其一生的话,他也不会在身后得到恶谥。司徒雷登生命的转折是在1946年他70高龄之际,出任了美国驻中国大使。这项任命注定了司徒雷登最终的悲剧下场。
任命司徒雷登作为美国大使,是马歇尔和艾奇逊等美国政府自由派的决定。在他们看来,思想自由的司徒雷登,有着深厚的中国文化背景,一定能不辱使命,敉平国共两党的战端。这绝对不是一项知人善任的任命。司徒雷登出生在中国,在中国度过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他是一个出色的传教士,更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但是绝对不是一位优秀的外交家,更不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作为一位驻华大使的使命,已经完全超出了司徒雷登的能力了。
司徒雷登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有着坚定的宗教信仰,有着一颗慈祥善良的心。他对中国文化十分熟谙,他热爱中国,爱好和平。他的政治理念是自由主义。他一厢情愿的希望国共两党化干戈为玉帛,,可是他压根儿的不明白国共之争就是国家政权的争夺,就是在中国上演了多次的改朝换代,这是不能谈判的。作为美国政府,深切痛恨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在抗战胜利之后的迅速腐败,杜鲁门政府面对蒋政权的腐败甚至做出了经济制裁的严厉措施。司徒雷登恰好作为美国政策的代言人,扮演了反蒋的角色。可以想见,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对司徒雷登一定是极为不满。另一方面,杜鲁门政府里面的马歇尔艾奇逊之流,对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存在好感。因为,在四十年代中期,毛泽东通过他的宣传喉舌,明白无误的传达出中共的政治理想是建立一个类似于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毛泽东还屡屡伸出橄榄枝,发表社论,赞美美国,甚至赞美华盛顿、杰佛逊、林肯等美国民主之父。毛泽东的这番表演,不仅迷惑了美国政府,同样也迷惑了司徒雷登这位政治斗争的外行,更迷惑了中国大多数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当然,美国政府竭力拉拢毛泽东,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不希望毛泽东倒向斯大林的苏联。
(6)
所以在国共内战时的军调会,时常会出现美国代表庇护叶剑英压制张治中这样奇怪的场面。不得不承认,正在处于政治上升时期的中共的宣传做得真好。毛泽东不仅在军事上逐步转为主动,更是在外交上压过了国民政府,使得美国这个世界民主领袖放弃了在中国的民主化代表国民政府。这应该是美国历史性的错误。司徒雷登的悲剧就在于在这个历史转变时刻,他扮演了一个不很光彩的角色。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攻占了南京。国民政府仓皇南迁广州。耐人寻味的是,随着国民政府搬到广州的外国使馆,只有苏联的大使。留在南京的外国使馆甚至还包括梵蒂冈。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先生留在使馆一百天,直到当年的8月8日取道上海回国。在这段时间里,司徒雷登几次接触中共南京当局,纡尊降贵的跟自己的学生黄华见面,提出要北上拜见周恩来。当周恩来表示司徒雷登可以到北京参加燕大的校庆,他竟然欣喜地说,这将是美国迈向承认中共政权的第二步。他认为自己在南京静候一百天是第一步。
此时的毛泽东已经志得意满的入主北京,早已不是当初那个声称要建立民主中国的中共领袖了。坐上了龙庭的毛泽东决意要报复一下支持国民政府的美国。这位新独裁者正在酝酿他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正在制定他的一面倒向苏联的外交政策,正在计划坐上东方共产阵营第二把交椅。可是司徒雷登还在一厢情愿的充当美国的外交使童。《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宏文发表于是年的6月30日。一切都尘埃落定了,毛泽东明白无误的竖起了反民主,反美的旗帜。司徒雷登只能收拾行装,打道回府了。这时候,国民政府向司徒雷登提出,取道广州返美,对国民政府做出一个象征性的支持,也被司徒雷登绝拒绝了。这时候的司徒雷登一定是感到万分沮丧,他把国民政府彻底得罪了。
就在司徒雷登在回国的途中,毛泽东在8月18日发表了那篇著名的《别了,司徒雷登》。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毛泽东性格的一个展现。在这篇文章里面,毛泽东逞口舌之快,对司徒雷登竭尽揶揄嘲笑,对美国这个在百年中对中国援助最多的国家一概抹杀。百年美中外交史成了美国对中国的侵略史。毛泽东历数了美国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意气风发的毛泽东豪迈的以全体中国人的代表自居,历数美国这个国家的罪恶,完全忘记了还在几年前自己对美国的向往和尊敬。毛泽东作为胜利者,觉得自己可以任意的歪曲事实,羞辱一个伟大的国家。这篇文章,可以说是一篇反美檄文。从此,美国作为一个邪恶的国家留在了许多中国人的心里。
(7)
毛泽东借司徒雷登发泄了他对美国的仇恨。可怜的司徒雷登成为了美国外交政策失败的替罪羊。作为一个失败的外交家,美国政府也把责任推给了司徒雷登。回到美国后,美国政府对司徒雷登下达了禁言令:不准接受记者采访;不准发表演讲;不准谈论美中关系。
客观地说,司徒雷登作为一个外交家是不成功的。在中国改朝换代的那三年里,可能任何人来担任驻华大使,都很难改变中国的政权易手。在美国方面,杜鲁门政府对中国共产党这个崛起的政治势力完全不了解,而站在西方的价值观念上,对于国民政府的腐败和蒋介石个人的独裁,美国人不能容忍,恰好这个时期主导美国政府外交的是马歇尔、艾奇逊等自由主义者,这就决定了美国的对华政策摇摆不定。在国民政府方面,抗战耗尽了这个国家的元气,国民党绝对没有能力连续进行两次战争(抗日卫国战争和国共内战),加上国民党政府官员的大面积的腐败,使得对于抗战胜利有较高期望的全体中国人深感失望,国民政府很快的失去了民心。在共产党那里,它是抗日战争唯一的胜利者。抗战后,中共被洗白了,实力增强了,加上苏联的支持,足以叫板国民政府。中共的政治宣传,使民心迅速倒向了中共。蒋介石作为国民政府的首脑,缺乏战略远见,没有看到这一点。因此,司徒雷登只能是悲剧收场,他得罪了自己的政府,也得罪了国民政府,共产党也把他作为反美的靶子。
司徒雷登回到美国,很快就中风失语。1952年,燕京大学被撤销,所属的院系被分配到八个院校,北京大学搬进了燕园。作为司徒雷登事业的象征,燕京大学的裁撤,对于这个风烛残年的老人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是年,万念俱灰的司徒雷登写信给杜鲁门,请求辞去驻华大使的职务,杜鲁门接受了他的辞职请求。司徒雷登开始撰写回忆录《在华五十年》。在轮椅上度过了十多年后,1962年,司徒雷登在寂寞中去世了。他留下遗嘱,由他的学生傅泾波作为遗嘱的执行人。他在遗嘱中规定,死后火化,骨灰与安葬在未名湖畔他的夫人艾玲合葬。但是,司徒雷登夫人的墓早在文革初期就被推平,墓碑已无处可寻。
由于中美两国的外交现实,司徒雷登的遗愿迟迟未能实现。他的学生兼秘书傅泾波为老师魂归燕园而奔波。1986年8月,经中共中央书记处圈阅同意,司徒雷登作为原燕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安葬临湖轩。正当大家忙于墓碑的设计,为来年的安葬仪式准备的时候,不料风云突变,北大的一群马列主义老太太,坚决反对司徒雷登归葬未名湖,理由是司徒雷登是毛泽东定性了的帝国主义分子,不能改变。中国驻美大使馆通知美方暂缓办理。1988年,傅泾波怀着未竟的心愿去世了。
(8)
傅泾波的儿子傅履仁是美国第一个华人陆军将领,他继承父亲遗愿,继续为司徒雷登的安葬奔走。到了1998年,趁着克林顿总统访华的机会,时任北京麦道公司总裁的傅履仁向驻华大使尚慕杰提出,由麦克海公使与中国外交部磋商,原则上获得北京大学的同意,低调安葬司徒雷登。可是,天有不测风云,1999年贝尔格莱德的中国大使馆被炸,司徒雷登的归葬泡汤了。
时间来到了2006年,时任浙江省省委书记的习近平率浙江省政府代表团访美,傅履仁在会谈中谈到了司徒雷登的归葬问题。不久傅履仁回访中国,浙江省外事办主动对傅履仁提及此事,很快向傅履仁确认司徒雷登可以归葬他的出生地杭州。
燕京大学的校友会内部意见分歧,有人坚持老校长一定要归葬燕园。可是经历了种种波折的傅履仁主意已定:避免节外生枝!最后达成共识,葬于杭州是目前的最佳选择。2008年11月17日,司徒雷登在去世46年后,终于以燕京大学创始人的身份在杭州安葬。
司徒雷登最终没能完成他的意愿,这不仅是他本人的遗憾,也使所有发自内心尊敬这位为中国的教育作出杰出贡献的美国朋友的中国人感到愧疚。出生于中国,热爱中国,毕生为中国人民服务的司徒雷登,难道他的归葬竟是那么可怕的事情吗?就会触犯了领袖的禁忌吗?在对待司徒雷登的问题上,可以看出我们这个国家的胸襟和气度,可以看出我们这民族是否懂得感恩。曾是燕京大学的学生冰心说,“我就不爱听什么‘别了,司徒雷登’,人家司徒雷登帮助过很多进步学生,好几个人都是坐着他的车才去了解放区。应该感谢每一个帮助过自己的人,忘恩负义不好。”
且别说毛泽东的那篇雄文,栽给司徒雷登的罪名本身就经不得推敲。即使他为执行美国的外交政策而令毛泽东不满,也不能把司徒雷登当作政治靶子。难道毛泽东忘记了曾经对司徒雷登那么的尊敬吗?1940年司徒雷登在重庆坠马受伤,毛泽东马上发出慰问电,由周恩来转交面呈。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时候,宴请过司徒雷登。那时候的毛泽东对司徒雷登是恭敬如仪。毛泽东在跟美国撕破脸的时候,把一个对中国人民有恩的人进行妖魔化,这种前恭后倨的态度并不是政治家应有的风度。
如今司徒雷登已经长眠在杭州郊外的安贤园公墓了。一代教育家终于回到了他的出生地,与杭州这片山水相伴。都说历史是一种慰藉。可是,当我们叙说司徒雷登个人的历史的时候,折射的美中外交的历史,却丝毫没有令人感到慰藉和温暖。我仿佛看到翻不过去的这一页是多么沉重,司徒雷登的中国情缘,令我感到我们民族的冷酷和寡情。
文章来源: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