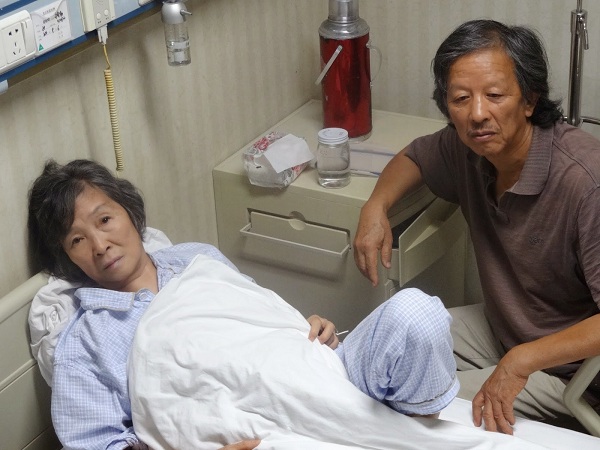《敢问路在何方?》
我一直认为台州是红色台风的“风眼”,风眼应该是安全的。但这一次回到浙江台州,打开手机,跃入眼中的短信竟是:“围剿官恶、官黑,小心横着回家!”
可见有人给我发来《死亡通谍》,2001年夏天,我《起诉政府卖淫》,在中山小学前的“椒江娱乐总汇”被迫拆除后,我夜晚回家时,曾遭两蒙面人的伏击。现在我有帐蓬、睡袋和画毡,又有跟踪的护驾和长夜值守,我就露宿在白云山麓。18、19日天气睛朗;20日天下小雨,我躲进了凉亭,监视的在轿车上避雨达旦。21日天睛,我背起帐篷上山露营,22至24日因天雨躲进寺庙,台州访民朋友给我送来两袋的上访材料,一些本想响应绝食访民在24日给我送来了《丁子霖致高智晟公开信》和刘路的《把绵羊和山羊分开》等网络下载的文章。
我震惊了,身体颤抖着像风中的纸片。刘路的倒戈,丁子霖的糊涂,高智晟发起维权绝食成了搞“政治”,有人以愚昧或清高向中共表示奴性。如果一个民族丧失了是非,整个社会就会盲目地跪倒在权力脚下。我无言以对,帐蓬外淅淅沥沥的大雨有如我心灵的泪,正洗刷着我们的良知。一夜无眠,为了寻找灵魂的净土,我决定从这个拥挤的城市遁逃。
25日晨,天下大雨。雨停后,在仍是黑云压顶绝望的日子里,我坐车去仙居,从下阁经上王四村,向括苍山攀登。面对雨后空蒙,括苍山重峦叠翠。极目而望,眼前是一道平卧的山岗,据说它是一千年前,聚义造反的方腊被南宋王朝招安的宋江围歼,曾落荒经过的地方,一代英豪,同室操戈,气短如此!
一路踢着土坷垃、石块,沿着土路漫无目的地向前走,内省加上闷热,汗水很快就给我冲了个澡。路上行人极少,且个个都再普通不过。为了打发无聊,我唱起了电视剧《西游记》里的主题曲《敢问路在何方?》。我喜欢这歌名和旋律,于是改换了开头两句,哑着音,昂首高歌:
背着背包,被人跟踪
送走晚霞,迎来日出
一路放歌,和鬼嚎
斗罢艰险,又出发,又出发
啦啦…啦………
几番番春秋 冬夏,
你尝尝酸甜 苦辣;
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
一夜沉睡,连梦也不来打扰,山上的日子,过得真象是一个童话。
晨曦揭开了长夜的黑暗,一觉醒来,只觉得我的头有些沉重。钻出帐蓬,我站在山巅上俯望,阳光下的村落掩映着嫩绿色的丛林,几柱白色的炊烟,袅袅而上,这是一个看似不错的新开始。
极目远方,我愣愣地想:受尽磨难的父亲和疼爱我的母亲去世了,都长眠东边的山野;连贯此山脉的北方,有我为我岳父母购置安葬的公墓,竟被台州恶官丁林超刨掘,成了游魂野鬼;遇害暴死街头的儿子严溯宇躺倒在椒江南山公墓的丛林之下。每一次的生离死别都铭刻在心,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突然我很清晰地记起了逝者的音容笑貌,仰望碧空,他们正逶逶向我飘来……
默默流淌的泪水在我的眼眶中噙含,山风吹过,落下的一阵晨露,和着我的眼泪谪下,如果他们还都活着多好……如果灵魂不死,以另一种方式存在于这个世界,我就不会如此地孤独。如果如果不再是如果。为什么世界展现给我的,总是那么多的无望呢?我咬住唇,可是眼泪仍模糊了视线。
嚼着方便面,和着山泉吞咽,我突然发现两棵松树下都有成堆的烟蒂,我的转移害苦了跟踪我的“随从”,我决定给公安打个电话,表示我目前不可能再回北京……但打不通,原来,手机和小灵通均无信号。
翻看刘路《把绵羊和山羊分开》的文章。中华民族是属 “羊”的?中国人有太多的“沉默的羔羊”和“待宰的绵羊”被喝狼奶的左右着。1994年,我在被关押在北大荒双河监狱强劳时,画过《晷系列—1989.64!!!?》(250×250公分) 的水墨,画面中,墨色铁幕下,血痕纵横的天安门前懔栗的是三只绵羊。2001年在通州《宋庄画家村》,我在圆明园画家(新疆)魏林的画室前,看到魏林创作的一个装置艺术《待宰的绵羊》,就是一个挖在院里的中国地图形的羊圈,圈中关押、拥挤着成堆的绵羊。在腥风吹红了的中国,面对暴政的血雨,难道只能万马齐喑的噤若寒蝉,千夫诺诺的奴相!何必为暴政歌功颂德或用似是而非的论道为独裁制涂脂抹粉。
宁鸣而死 不默而生。中国人什么时侯才能走出恐惧和谎言的阴影……
乱世浮生, 一种沉重的悲壮充塞在我的内心,可惜并没有人见证我的新生,很多事情都将成为过眼云烟,随风而逝。我仍引用林昭长诗《普洛米修士受难的一日》中的一段:
还能忍受吗?这些黑暗的
可耻的年代,结束它们,
不惧怕阿西娜的战甲
不迷信阿波罗的威灵,
更不听宙斯的教训或恫吓……
他们一个个都不复留存。
在括苍山上,手机不再有信号,在监控与强行孤立下,和外界失去任何联系。至3月6日,突然发现监视人员撤了,就整理帐蓬、睡袋、画毡塞进登山包,赶紧下了山。给朋友挂了电话,才知当天是全球万人绝食的声援,我特别感动地也绝食了一天。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