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维诺的绝笔之作《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共收录了五篇他未来得及付诸讲演的文学演讲稿。第一篇题为《轻逸》(《Lightness》),主要谈论了文学价值观里轻与重之间的对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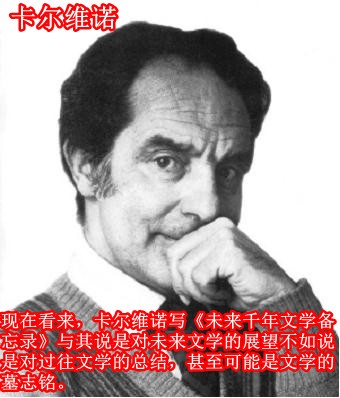 自从现代主义文学产生并逐渐足以与古典主义文学相鼎力后,这两个带有物理性质的、意义相反的字所共同表达的含义,便在文学领域有了探讨的价值。现代主义致力于减少作品的沉重感(无论人物、故事、结构还是语言),古典主义则与之相反,严肃性(或者说一本正经)是他们永恒的追求。作为现代主义的代表作家,卡尔维诺在这篇演讲稿中更侧重于对“轻”的价值判断。
自从现代主义文学产生并逐渐足以与古典主义文学相鼎力后,这两个带有物理性质的、意义相反的字所共同表达的含义,便在文学领域有了探讨的价值。现代主义致力于减少作品的沉重感(无论人物、故事、结构还是语言),古典主义则与之相反,严肃性(或者说一本正经)是他们永恒的追求。作为现代主义的代表作家,卡尔维诺在这篇演讲稿中更侧重于对“轻”的价值判断。
关于轻与重的对立关系,卡尔维诺天文地理地扯了许多,然后总结出“轻”的三个特点:极度轻微;不断运动;是一个信息的矢量——“重”的特点除了也是矢量外,其他当然皆与“轻”相反。在卡尔维诺所举的例子中,卡瓦尔康蒂和但丁的那两句基本相同的诗的对比,直接而明确地展现了这种相反性:
还有徐徐落下的白雪,寂静无风——卡瓦尔康蒂
有如大雪在无风的山中飘落——但丁
仔细品位并对比这两句诗。无风的日子中的雪表现出一种轻飘的、寂静中的运动,这是两句诗唯一的相同点。在但丁的诗中,地点“山中”占重要地位,限定着“大雪”的运动。而在卡瓦尔康蒂的诗中,“白”和“落下”则把风景融入了一种茫然的期待中。但两句诗的本质区别在于第一个词。卡瓦尔康蒂使用连接词“还有”,将雪景与前后的其他景观置于同一平面上,使其成为目录一样的一系列形象的展现——舒展并且呈现。但丁使用连接词“有如”则囊括了比喻范围中的所有景象,并且包含着一种具体的现实——限定并且实在。
卡尔维诺说:“在卡瓦尔康蒂那里,一切都在极快地运动着,我们体现不到其恒定性,只能见出其效果。而在但丁那里一切都具有恒定性与稳定性,事物的沉重感已恰如其分地确定。”由此,轻与重的对比与对立关系便比较明晰了。卡尔维诺以此总结出几个世纪以来两种相互竞争的文学倾向:一种倾向致力于把语言变为云朵一样、尘埃一样、磁场中磁力线盘旋于物外一样的某种毫无重量的因素。另一种倾向则致力于给予语言以沉重感,事物、躯体和感受的具体性。我认为大而言之,这便是现代主义与古典主义的分野了。
“轻”涉及的是高级抽象活动,并且具有象征价值。卡尔维诺同时特别指出它应该是精确的、确定的,而非模糊的、偶然性的——“应该像一只鸟儿那样轻,而不是像一根羽毛”。
当然,讨论轻与重的话题,不能不提到极具代表性的米兰·昆德拉的小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小说反复将轻与重、灵与肉各自进行对比,并相互对应。我很赞同卡尔维诺在演讲稿中对此的评述:“《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实际上是对生活中无法躲避的沉重表现出来的一种苦涩的认可,这不仅仅及于他的祖国所遭受的那种极度的、无所不及的受压迫的处境之中,也存在于我们大家所处的人类命运之中。对于昆德拉来说,生活的沉重主要存在于威迫,把我们的公共和私人事物裹挟得越来越紧的威迫。我们在生活中因其轻快而选取而珍重的一切,于须臾间都要显示出其无法令人忍受的沉重的本来面目……”我们追求轻快的感觉,却发现这竟是我们所无法企及的,这便是“不能承受之轻”,从相对的一面而言也就是“不能忍受之重”。
 卡尔维诺在演讲稿中将“轻”分为“深思熟虑的轻”和“轻举妄动的轻”,并且说“经过严密思考的轻会使轻举妄动变得愚笨而沉重”——严密思考和轻举妄动之间的界限是什么?卡尔维诺并没有说,这也的确很难做出界定。我想至少在昆德拉那里,他一直不认同的革命活动家哈维尔的种种行径,肯定算是“轻举妄动”了,但若没有后者的努力,捷克恐怕还会长久地笼罩在捷共强权之下。由此而论,在某些特殊的生存环境中,文学价值观里的轻与重又具有了非同一般的意义,成为了生存理念与斗争方式。
卡尔维诺在演讲稿中将“轻”分为“深思熟虑的轻”和“轻举妄动的轻”,并且说“经过严密思考的轻会使轻举妄动变得愚笨而沉重”——严密思考和轻举妄动之间的界限是什么?卡尔维诺并没有说,这也的确很难做出界定。我想至少在昆德拉那里,他一直不认同的革命活动家哈维尔的种种行径,肯定算是“轻举妄动”了,但若没有后者的努力,捷克恐怕还会长久地笼罩在捷共强权之下。由此而论,在某些特殊的生存环境中,文学价值观里的轻与重又具有了非同一般的意义,成为了生存理念与斗争方式。
至此,还可以引伸出另一个很有现实价值的问题:轻与重,是手段还是目的?
在我看来,真正的轻与重都是手段,追求个性与自我、实现自由与福祉的手段。昆德拉的小说的成功之处就在于认清了这一点,王小波的小说也是如此,还比如诗仙李白的清新飘逸与诗圣杜甫的沉郁悲怆,无论轻与重都是对现实的认知和对理想的求索,都是一种生存理念与斗争方式。一旦忽视了这一点,“轻”者会陷入无尽的虚无,“重”者会陷入无尽的灰暗,最终导致文学上的虚无主义,这在中国当代的主流文学群体中可以举出许多例子来。
卡尔维诺以卡夫卡的小说《木桶骑士》结束了这篇演讲:在一个缺媒的冬夜,主人公提着个空木桶去找煤,空木桶却载着主人公飞了起来。木桶骑士骑着空木桶,飞翔在寒夜中,飞向那能将空木桶装满煤的地方。
我们的空木桶何时才能装满我们所求索的东西呢?
2007年9月27日
《吾诗已成》
